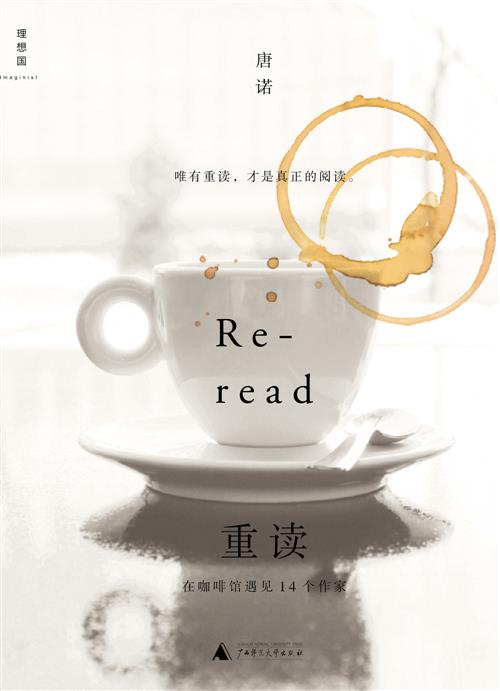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15-01-01
定 价:56.00
作 者:唐诺 著
责 编:简心怡 杨静武
图书分类: 文学评论与鉴赏
读者对象: 大众读者
上架建议: 文学︱散文
开本: 16
字数: 320 (千字)
页数: 4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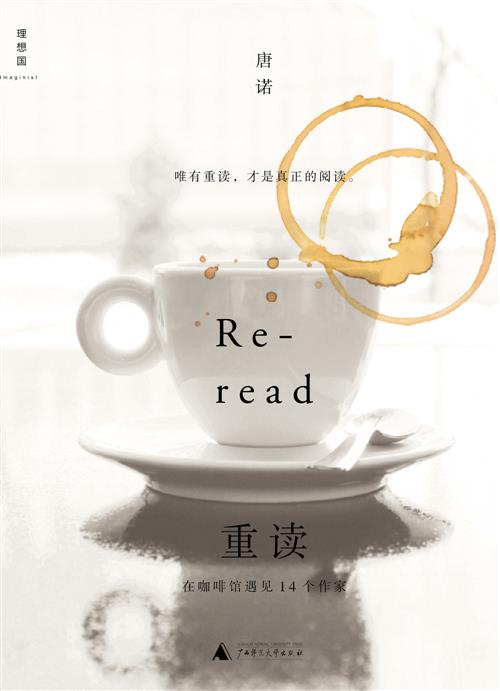
每一次我们重读一本书,这本书就与从前稍有不同,而我们自己也与从前稍有不同。——博尔赫斯
海明威,《渡河入林》——太长的好运气有其难以逃遁的代价,它最终会变成你损失不起的东西。
库斯勒,《正午的黑暗》——一个忠贞的信徒,勇敢到可以抛开所有赴死;但作为一个人,他却怯懦到不敢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康拉德,《如镜的大海》——在寻求梦想、信念和价值的历史路途上,人把“伟大”一事自恋地揽为己有遂变得虚伪,而忘掉了他本来只是想企及一个比自己巨大高远的东西。
纳博科夫,《普宁》——人有迁徙的自由,也等于说人有不迁徙的自由;前者我们当它是个庄严的誓言,而后者则是一个亘古的文学主题。
果戈理,《狄康卡近乡夜话》——所以不可以笑,笑会让你肌肉松弛表情和善,甚至认为日子还过得下去。你改变了自己,就不会去改变世界。
以赛亚•柏林,《现实感》——你四下环视,身旁同行的俱是想当掌权者策士、满心向往呼风唤雨大游戏的人,杂在这堆糟糕透了的旅伴之中,你要如何令人相信,你们走同一条路,要去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本书收录的十六篇文章,一句一字,都是作者数年来定时定点、在台北某家咖啡馆里写下的。无有节制的所思所想,关于那些应该一读再读的了不起著作,关于当今正在失落的幸福题材、价值理念,更关乎我们自身。面对书籍与人生的无限清单,重读,毋宁是一次中途的驻足和折返,想清楚自己究竟要接近什么、看到什么,以及为什么出发。因此,所谓的遇见,其实是一种保证的相遇:现实世界里好东西来得快消散得也快,你得上下求索,自备而来。
一个优秀读者,一个成熟的读者,一个思路活泼、追求新意的读者,只能是一个“重读者”。——纳博科夫
唐诺
本名谢材俊,一九五八年生于台湾宜兰,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
曾与朱天文等共组著名文学团体“三三集刊”,后任职出版公司数年。
近十余年专事写作,曾获多种文学奖项,朱天文誉之为“一个谦逊的博学者、聆听者和发想者”。
2013年出版散文力作《尽头》,探索极限和人的现实处境,获评《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与台湾金鼎奖。
简体版说明
前言
渡过这条河,到树林子里死去
神说,只有我能令日头停止
大海•作为一个史诗舞台
一本没读过的契诃夫小说和小说的无限之梦
大麻•鸦片•人造天堂
普宁•以及纳博科夫
《八月之光》,以及约克纳帕塔法小说
被思想扭曲的小说灵魂
有关认识博尔赫斯的几点补充
《一个烧毁的麻风病例》以及格林自己
我想,也可以这样读《波多里诺》
关于《巫言》
走过神迹之门
集体性暴力迫害的秘密及其终结
附录一 自由的核心
附录二 在天命使者和君王策士之间
本书各篇文章出处
简体版说明
来到大陆,这本书变得稍稍不同,却是多出来的——一是它多了个书名,叫《重读》;二是多找出来两篇文字,咖啡馆里又遇见了两个作家、两位自由主义大师,小密尔以及以赛亚•柏林。只是,得委屈他们躲附录里,其实大家的存在位置当然是完全平等的。
校对这两篇文字,把我自己带回到稍早几年的台湾,2004年前后,那是台湾民主的反挫时日,或者说,暴现台湾民主根基严重不足、民主原来这么脆弱,民主一再轻易滑向民粹、眼前所有人忽然翻脸变得无知无识也似还极残酷的时刻。作为一个选书编辑和半个书写者(当时),我能做的,无非是希望人们好好多读几本书,重新学习民主政治的ABC,重读小密尔、柏林等人老早已仔细讲清楚并殷殷叮嘱的著作(《论自由》、《现实感》等),希冀以知识的光来对抗无知无识的黝黯,并假设这个世界仍是讲理的。其实,原已收录的讨论《基甸的号角》(宪法和大法官制度)和《替罪羊》(民粹的集体附魔现象及其神话,及其制造操作)这两篇,都是一样的思维和企图,写于同一段时日,也都伴随着原书的出版作业(当时定名为“台湾民主丛书”,但果不其然销路不佳)。这几篇文字或称之为书的引论,也就是竭尽我所能地把大家引到、骗去原来那部应该一读再读的了不起著作去。
想起来,《基甸的号角》和《论自由》二书更早都已在台湾出版过,我自己第一次阅读分别是小学六年级和高一。这算重新出版,重读之前的必要重新出版,这也呼应了小密尔这番我牢记的、并希冀它确实如此的断言——真理并不一定获胜,事实上,更多时候真理一直吃败仗,甚至会被彻底歼灭。但真理有个很动人的特质,那就是它不会就此销声匿迹,它仍会被再说出来,也许隔一段时日,在不同地方,由不同的人,这会一直发生,直到它终于获胜,或至少站稳脚跟取得承认为止。
我不知道别的人怎么想,对我自己是,这非常重要,这么多年来,我知道怎么和失败每天相处,不至于丧失勇气。
重新出版联结着重读。重读,这个多出来的书名,作为一个再次的相互提醒,是理想国这群每天和书相处的编辑朋友讨论出来的(一再以各种方式重读同一本书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我欣然接受,因为这本来就一直是我的想法、我对阅读一事最根本的主张,这也合于这本书的全部事实。
以下简单的话是作为一个读者、而不是作为一个书写者说的。我自己偶尔也参与书写这一侧,不过是让我经验地、实地地证实而已——重读,有一部分是意识到时间这最根本的东西,包括时间总量的截然差异,还包括时间位置的微妙但也许更重要差异。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书写者耗用于这一本书、这一题目和思维的时间总量,总是远大于阅读者,比方两年的书写/三天的阅读,粗糙的估算是243比1;如果我们再合理地假设,书写者极可能是比我们要聪明而且专注的人(书写过程正是一段最专注的思考过程),也必定是之前就比我们准备更多更好的人,这个时间比例的实质差异势必拉得更开,所以,书怎么能够不重读呢?此外,也就是这里我真正想讲的,时间的拉长,意味着一个书写者跨越了星辰日月不同季候,曾站在不同光影、温度、氛围、不可见空气中分子的种类和浓度,不同情感和眼前之人的不同触发可能的各种时间位置,重读,尤其是相隔一段时日的重读于是非常非常必要,丰硕的事物一次只露出一面、一部分,三天内,你大致只在同一个时间位置、同一心绪和视角里,来不及让这本书、这个观看思索对象转过来。
一个只见一次的人,我们称之为认得、知道,也许可能就这样失去理智爱上他,但我们不会也不敢说了解他;一本才读过一次的书,我们则称之为开始,这才开始。
这样。
比无限清单更好的阅读,那就是重读
14个作家、14本书,还有两位自由主义大师——所谓的遇见,其实是一种保证的相遇
伟大的作品,值得一读再读。唯有在不同生命阶段的一次次重读中,它们的伟大才会一点一点显现,一次又一次给予我们启示与勇气,面对生活的琐细与生命的虚无。唯有重读,这些伟大的心灵才得以唤醒、重放光芒,不再只是一个沉睡的名字。
海明威/库斯勒/纳博科夫/果戈理/博尔赫斯/契诃夫/波德莱尔/福克纳/格林/艾柯/刘易斯/小密尔/柏林……
美丽的东西没理由死在我们这一代人,这是犯罪行为。——唐诺
渡过这条河 到树林子里死去
《渡河入林》,让我们渡过这条河,到那边的树林子里坐下休息,这是欧内斯特•海明威一九五○年的作品。从当时到现在,绝大部分的文学评论者认定,这本书正是海明威一生最糟糕的东西,烂品味、烂风格,而且更要命的,滥情。如此说来,我们今天干嘛还读它呢?
但我们静下心来听加西亚•马尔克斯怎么说—“然而,尽管像是对他的命运的一种嘲弄,但是我仍然认为《渡河入林》这部最不成功的小说是他最美丽的作品。就像他自己披露的那样,这部作品最初是作为短篇小说来写的,后来误入长篇小说的丛林中。在一位如此博学的技师笔下,会存在那么多结构上的裂缝和那么多文化构造上的差错,是难以理解的。他是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善写对话的能工巧匠之一,在他的作品中同时存在若干那么矫揉造作甚至虚伪的对话,也是不可理解的……这不仅是他优秀的长篇小说,而且也是最富有他个人特色的长篇小说,因为这部作品是在一个捉摸不定的秋天黎明写的,当时他怀着对过去岁月的无法弥补思念之情和对他所剩不多的难忘生命岁月的预感。在他的任何一部作品中也没有留下那么多有关他个人的东西,也不曾那么优美、那么亲切地表现对他的作为和他的生活的基本感受:成功毫无价值。他的主人翁的死亡看上去那么平静、那么自然,却神秘地预示了他本人的自杀。”
如果可以,我实在很想让这篇文字在此就画上句号。这部最不成功的小说是他最美丽的作品,是在一个捉摸不定的秋天黎明写的,这应该什么都够了不是吗?
事实上,这是我个人第二次一笔一字手抄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段话,上一回是我写《阅读的故事》一书时,处理的问题也是为什么明明知道却还要阅读一个作家失败的作品,有些基本的话在哪里已经讲过了,重复是最尴尬的(不只小说创作如此,生活本身也是如此,因此自我抄袭并非仅仅是文学创作者的独特禁令而已,还是某种做人的基本礼仪),除非是够好的话,是只听一遍不容易尽意的话,所以,让我们再一次仔细聆听加西亚•马尔克斯,然后从这里再试着往前走下去。
这样子可以吗?
最初的死亡之地
《渡河入林》,越过了小说自身的内容由作者额外地命名,使用了一个掌故,一个历史性的死亡意象—这是美国南北内战时,托马斯•杰克逊将军临死之前的一句话,就如同我们晓得大象会生命本能地知道死亡已经找上来,会孤独但平静地走向它。海明威以这样的命名,毫不隐瞒地告诉我们,《渡河入林》正是一个杰克逊一样的老兵,知道了并静静迎向死亡的故事。
美国籍的老兵,但死亡却发生在遥远的威尼斯。熟知海明威生平的人自会晓得,这是有意思的,因为这里正是一辈子猎犬般嗅闻、追逐战争的海明威,生平第一个抵达的真正战场。那是一九一八年一次大战差不多胜负已分的落幕时刻,他是以红十字救护人员而不是他想要的杀人士兵的身份赶上,然而“幸运”的是,他倒真的在火线战壕中挨了奥地利军的机枪,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腿。这日后证明是一次一本万利的受伤,供他吹嘘一辈子,不管是酒酣耳热的言谈中抑或文字里;而更加划算的可能是他被送到米兰红十字医院的那段养伤经历,在这里他热烈追求一位名为库洛斯基的漂亮护士未果,但现实的失败转换成十年后小说的胜利,那就是一般公认他最好的小说《永别了,武器》,里头的凯瑟琳•巴克莱根据的原型就是库洛斯基。不同的只是,可由海明威意志操控的凯瑟琳回应了他的追求,而且上床、怀孕,最终死于难产,春梦一场。
海明威小说中的想象成分一向不多,或者应该讲他的想像力总先执行在现实生活中,先把生活弄得戏剧性不堪,留给小说所剩不多的想像力,不如说是某种不甘心的意志、某种报复,用来改变他力有未逮的现实结果,泄愤或过过瘾用的。
然而,《渡河入林》这次他却选了一言不发的威尼斯,或者不该讲是选择,而是想起来了。他一辈子和死亡开各式各样浮夸的、感伤的、“老子不怕你”粗鲁的玩笑,但威尼斯在这一切之前,那时候的海明威才十九岁,无人认识,恶习亦方兴未艾,威尼斯是他最初的死亡之地,在这里,他首次和死神擦身而过,也许还瞥见过死神的容颜一角,他小说里头的死亡从没这么质地真实过,是最开始也是最后的。
《渡河入林》书末的死亡写得极简极短,打完野鸭子之后,心脏病暴烈袭来就这么完结,留给他的时间只够写张纸条,交代他无福也无力保有的那方昂贵翡翠和那幅女孩的画像,连感想都没有,遑论教训和智慧,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的“那么平静、那么自然”。
之前的海明威可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才不过十年前的畅销书《战地钟声》(“丧钟为谁而鸣”,另一个直接标示死亡的书名,但不是个人的,是四海一家的),前去帮忙作战炸桥的西班牙文教授“英国佬”罗勃•乔丹,书末腿部中弹(还是腿部)单独留下来死,从赶走不舍扔下他的游击队同志,和美丽的女主角玛利亚依依话别,到孑然一人等待死亡或敌军到来(看哪个先到),海明威足足写了上万字—赶走游击队同志是带种的汉子,话别玛利亚是深情且无私的情人(“只要我们俩有一个活着,就等于两个人都活着。你明白吗?”),然后便是无惧无悔的、窥破生死的哲学家,我们试看这喋喋不休的独白的其中一小段:“他又俯视山坡,心里想着:我讨厌离开这个世界,如此而已。我真讨厌离开它,但愿我在世间曾做过好事。我已经付出生前的一切才华,努力以赴了。你是指现有的才华吧。好,现有就现有吧。如今我已为自己的信念战斗了一年。如果我们在此地打赢,我们到处都可以打赢。世界是一个好地方,值得为它一战,我真讨厌离开人间。他告诉自己:你运气不错,才能度过这么美好的一生。你的一生和祖父一样精彩,只是不像他那么长命罢了。就凭最后这几天,你的一生就可以比美任何人。你曾经那么幸运,你不想抱怨什么。只是我真希望有办法将我学到的一切传诸后人。基督啊,最后几天我学得真快……”
删节号以下的更尴尬,尤其是乔丹开始陷入半昏迷状态却仍呓语不休时。海明威一直喜欢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公爵受重创仰躺在战场山坡看着无垠天空、看着法军前来、最终看见拿破仑一眼那个经典片段,可想而知,托尔斯泰可一点也不会喜欢海明威这段滑稽的摹本。
人生命里总有一些不可以狎腻、不容许乱来的东西,死亡是其一,我们不是不可以跟它和解,不是不可以含笑待它,但我们得晓得它是庄重的大事。
那一个秋天黎明
《渡河入林》在一片文字的伤亡狼藉中,写得最好的有形片段是威尼斯本身,干净、冷冽、线条清明、海明威自己不加入静静一旁看着的威尼斯,这本来就是海明威小说书写的绝学所在,也是他“真希望传诸后人”的最重要部分,后来一堆远比他好的小说家都感激他这方面的示范和启蒙,加西亚•马尔克斯便说过是海明威教会了他怎么写一只猫横过马路。
但海明威自己一摩拳擦掌进来、赋予哲学和感情往往就惨了,《渡河入林》尤其“亲切”地表现他这个大麻烦无遗。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指出“矫揉造作甚至虚伪的对话”,其极限演出就是书中上校和他十九岁“女儿”伯爵小姐的不好卒读情话(难怪卡尔维诺这么温暖有教养的人,会用到“厌恶和恶心”这么狠的两个词),如何忍耐并挨过这几长段夜半私语的折磨,遂构成了我们可否顺利读完这部小说最严厉的考验。
这里我们得停下来稍稍解释一下。我们其实很难讲这些绵绵情话不写实,是dirty old man的纯幻想,而应该说是海明威式的“奇特写实”—海明威有过四次婚姻不说,中年之后,他以畅销大作家的身姿徘徊好莱坞不去,视之为他另一个战场和猎场。他自称“海爸爸”,收了一堆年轻貌美的“女儿”,包括演他《乞力马扎罗的雪》的爱娃•嘉德纳和演他《战地钟声》的英格丽•褒曼云云,但书中的这个“女儿”伯爵小姐有更简单更写实的出处,那就是阿德里安娜•伊凡西奇,他另一名当时就是十九岁的女儿。这事告诉我们自然主义显然是有问题的,只因为事实本身既不平坦也不等值,事实还可以弄得远比想象更虚假,因此,选择本来就是书写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成分,我们并不需要作家事事据实以告,有些事敬谢不敏他留给自己就行了。
当然,败笔不只充斥在书中的甜蜜部分,也恣意泼洒在书中的咬牙切齿部分。
在小说中公报私仇暗算别人是海明威的一贯书写恶习,此番《渡河入林》他流弹四射依然,名单非常长,位阶高如艾森豪和巴顿将军,莫名其妙如小说同行也是领先他拿到诺贝尔奖的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私密如他那位巾帼气的才离婚第三任老婆玛莎•盖尔霍恩等等。这倒不是说小说家不可以生气不可以骂人,读书学剑意不平,愤怒不满从来就是小说书写最大的驱力,但其中仍有层次的问题、格调的问题,在暗街背后开枪的小流氓行径和严肃郑重的愤怒批判仍大有分别。
一样写战争,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也一样竭尽修理法俄两大名将拿破仑和库图佐夫之能事,不仅在小说情节中耐心且细腻地揭露,还在穿插的作者雄辩部分指证历历地质疑,深澈而且手段磊落;更重要的,我们晓得托尔斯泰是从头到尾反对战争的,他真正的标的直接就是战争本身,他撕毁法国和俄国这两纸战神画像,把两人降等(或还原)为如阿诺德《多佛海滩》(Matthew Arnold,Dover Beach)诗中那样在暗夜之中盲目杀人的无知士兵,可以完全不必涉及个人私怨,这使得《战争与和平》这部大小说既承接下失传已久的壮阔战争史诗,又同时瓦解了整个战争神话。海明威不同,他是神话战争的人,又要抄战争捷径直接扮演英雄,没空从基层干起、从正规战慢慢打上来。人类历史上其实一直存在一批这种人,通常的结果是成为佣兵,游击战是他们所能有的战斗形态,而“上校”则是他们最喜欢自封也最具象征性的美丽头衔,因为上校意味着仍直接杵在火线开枪作战,是战士的顶点和佼佼者,符合着此种战争民粹论(《渡河入林》书中海明威投射的主人翁可不就正是上校吗?)。海明威比他这些同类幸运或说了不起的只是,从西班牙内战到二次世界大战,他拥有着一个世界级大作家的人人得买账身份,分不清算劳军算报道或观光,既有机会直接闯到战争的指挥核心,又可以随时脱离避开一切危险,人类战争历史上拥有这样如电动玩具暂停键、取消键的人并不多。如此,我们就清楚了,海明威修理艾森豪和巴顿,大体上只是某种战争英雄位置的争逐,以及战争解释权的争逐,由妒恨之心所推动,以诉求下层战士的民粹语言讲出来,如此而已。
这些遍在的失败累累告诉我们,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言“最富他个人的特色”“留下那么多有关他个人的东西”这一点,自然也包括了他过去的种种恶习,甚至包括了他惯性的不诚实在内。《渡河入林》不是一部忽然大彻大悟、重新做人的忏悔录,通常那只是一种更高明的表演,一种更大的虚伪而已,只因为人心改变的方式及其轨迹不会是这样子的,我们晓得,诚实,尤其是诚实地对待自己,也得是一种习惯才行,它可以开始但不能只停留于某种灵光一闪的善念。当下再真诚的善念,也许够你瞬间去做某一件很疯狂的好事情,比方说捐出自己全部财产给东非小孩或牺牲自己生命救人云云,但不可能立即拉动盘根错节几十年之久、已有可惧沉沉重量的生命整体;也许还够你写一篇恳切反省的短文或在当天的日记信誓旦旦,但绝不足以支撑一部耗时而且得回转光天化日生活细节本身的长篇小说。
我们实际些来看,《渡河入林》书写的那一个“捉摸不定的秋天黎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现实日子?那是一九五○年,彼时他已年过五十,早已越过了人生的折返点,二次世界大战亦整整结束五年了,昔日的光荣战场如今成为残败的废墟,人们看的想的不再是杀人的英雄,而是数千万的尸体;而海明威自己,整整十年没交出任何像回事的东西,上一本的《战地钟声》尽管空前畅销,但在严肃性的文学评论界当时就不断响起质疑的杂音,问题是,战后的反省空气,让他的书写处境雪上加霜,西班牙内战可供他写《战地钟声》,而关于二次大战他能写些什么?《西线无战事》、《生死存亡的年代》、《第五号屠宰场》这样控诉战争的作品是吗?
一切都约好了似的往下坡走,好运气已完全预支光了,其中最真实最无法遁逃的,我猜是他整整糟蹋了五十年的身体(不是作战负伤的,除了十九岁那回,他一辈子从未真的打过仗,那是长时期放荡酗酒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这么讲,海明威是个努力调慢生命时钟的人,从身体及于心智和人格,努力让自己停留于某个年轻时光,躲避苍老,也躲避跟着年岁而来的必要自律、道德心和责任感云云这些沉重东西,好保有唯我的、自恋的完整行动自由。然而时间会拆穿这些诡计的,衰老可以展延一段时日,但终究会债主般找到你,要求连本带利地整付。之前,他喜欢而且一再触碰死亡这个题目,一部一部小说和死神挤眼睛扮鬼脸,好证明自己是不怕死的硬汉子一条,但叶公好龙,死亡并不总是如想象中、如你召唤它的那般璀璨如花,绝大多数时候它就只是瓦解和腐朽,并不需要伤口,也找不到伤口。
《渡河入林》中,海明威拼了命要我们看到老上校战士勋章般的一身旧伤,尤其是和声般绕梁不去、已达重度恶心层次的那只残破变形的右手(以至于把一个十九岁的伯爵小姐写得像恋尸癖的色情狂一般),但真正冒出腐败气味的不在这里,死亡静静地躺在我们的眼角余光之处;书里头自知将死的老上校是不怕死,但这掩盖不住写他的海明威自己的深沉畏惧,以及他的不知从何说起。
这也许正是《渡河入林》这部小说最暧昧也最复杂的原因,它是病征,相当彻底地暴现了海明威的各种致命弱点(包括书写技艺以及他的行为、心智和人格),但也有某种恍惚的感觉和发见掺入其中,偏偏这些之于他很陌生的真东西,是海明威既没习惯也无力捕捉和表达的,这些异质东西他没办法在书写中妥善地消化融解,遂造成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令人难以理解的“那么多结构上的裂缝和那么多文化构造上的差错”。然而,正因为海明威书写上的力有未逮以及小说结构的崩解,却也使他无暇遮掩,从失败的谎言之中透露出实话来;或夸张点来说明,《渡河入林》失败到一种地步,宛如一具小说的尸体,唯尸体会说话,尸体的主人生前也许是个说谎成习的人,但尸体只会讲真话,包括讲出他的主人的说谎恶习。
我以为,海明威自己也察觉出《渡河入林》之于他的异样意义,他对评论者的一面倒恶评反应十分激烈,其中极可能包含了某种委屈,是放羊的孩子好不容易讲了真话却不被了解、不被嘉许的那种委屈。凭借着这股咽不下去的愤愤不平之气,他宛如神助地在极短时间内写出了《老人与海》一书,冲破了自己江郎才尽的书写暮年,书中那条长达十八英尺却遭评论者鲨鱼群痛咬成一架光秃秃骨头的大鱼,正就是这部《渡河入林》。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