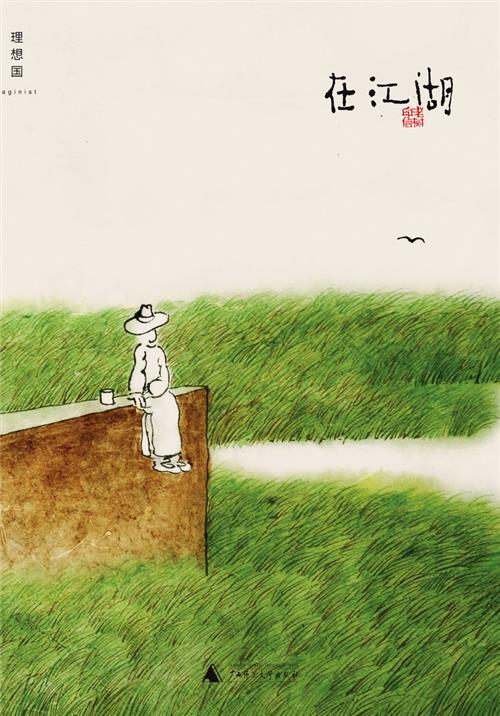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15-07-01
定 价:69.00
作 者:老树 绘著
责 编:王家胜
图书分类: 中国现当代随笔
读者对象: 大众读者
上架建议: 文学 艺术
开本: 32
字数: 108 (千字)
页数: 3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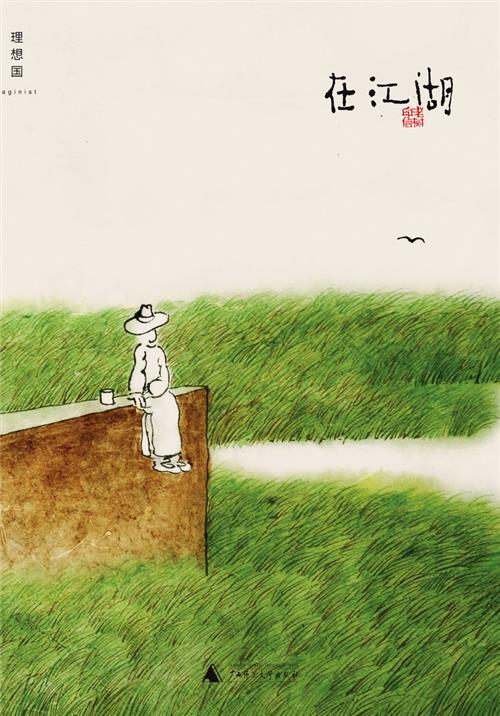
这是红遍微博的“老树画画”的一份回忆录,一份对画画、对审美、对这个世界的内心告白;也是一本极具标志性的老树式长衫人物画集。一图,一文,即可窥见老树完整的画中世界和画外行藏。
画分七组,“日常”、“闲情”、“花犯”、“心事”、“时节”、“江湖”、“桃源”,最具标志性的老树式民国长衫人物画,加上最有味道的老树式“歪诗”,连接起来就是这个独特的长衫人物的世界,就是老树自身的世界。
文有七题,以“答客问”的形式,讲述老树从画的经历、师承,谈自己的画,说自己的“诗”,字字都是“自家的思,自家的爱,自家的园子,自家的菜”。
老树(新浪微博“老树画画”),本名刘树勇,1962年生于山东临朐,198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艺术系主任。
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自习绘画,问学于梁崎、王学仲、霍春阳诸师。后开始致力于视觉语言与叙事方式的比较研究,广泛涉及文学、绘画、电影、书法等领域。90年代中期以后,转而关注当代中国摄影发展及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有大量批评文章行世,著作数十种,并策划诸多影像展览。目前,主要从事影像的媒介传播研究和具体实践。2007年始,重操画业。
序]老树无瘿 / 钟鸣
日常(画集一)
[答客问] 业余的状态也许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闲情(画集二)
[答客问] 在民国的一座废园子里闲逛
花犯(画集三)
[答客问] 逃避现实是我唯一的内心现实
心事(画集四)
[答客问] 画画儿只是一件个人的私事儿
时节(画集五)
[答客问] 绘画与摄影:哪个更真实?
江湖(画集六)
[答客问] 文字与绘画的关系
桃源(画集七)
[答客问] 风格的统一其实是创造力匮乏的表现
[跋] 多说几句话 / 老树
[跋] 多说几句话 / 老树
二〇〇七年,重新对画画有了兴趣。手艺捡起来,竟然就画到现在。这期间有朋友喜欢,也是好奇,问这问那。于是约着吃酒,闲扯。扯着扯着,认真了,竟然有了问题。问题后面又有问题,问题里面还有些细碎的问题,于是,闲扯变成了随后几次有预谋的访谈。这本书中的文字,就是数回谈话的整理集成。
按理说,一个画画的,不应该说那么多话。尤其是跟画相关的话,说得越少越好,最好是不说,让那些叫作批评家的人专门去说,或者让别人只是看着那些画在那里琢磨,否则就有“画不够,文来凑”的嫌疑。
好在我没有这样的焦虑,因为本身不是专职画画的。不是专职画家,至少就有三个好处:一个是不用靠这门手艺吃饭,不用混到那个叫什么界的圈子里去。另一个是,因为不靠这个吃饭,所以不用把画画当个了不起的事儿来看待,可以乱画乱说一气,图个高兴自在,不用在意专业人员的看法和脸色。第三个是,我是学语言文学专业出身,又混在大学里教书多年,本职工作,就是说话。不说话时,还要做研究码字儿,于是总在胡思乱想,有了想法还要写出来,都成习惯了。很多想法单靠画张画说不大清楚,于是,还是得在画画之外来说一说。
作为一个业余绘画爱好者,持续的绘画过程给我带来的影响谈不上有多大,但却很具体。其中一个具体的影响是,它改变了我个人跟外部世界各种事物的关系。比如,在没有画画之前,每天出得门去,眼睛投向一个混乱嘈杂的远方,内心充满抱怨和没来由的愤怒,与无数活泼泼的生命擦肩而过,从无数奇妙的事物旁边匆匆走过。自以为对身边的一切熟稔于心,其实却是一无所知。正是因为画画,开始注意到四季的移易、风物的变换,开始仔细地观察不同花儿的样子、颜色变化,叶子是对生还是互生的,从某个角度看过去物体的阴阳向背,物体表面的不同肌理,马路上的一条裂痕,横亘眼前的一根树枝,等等。这个变化似乎微不足道,但对于我来说就很重要。能够觉察到自己的这个一无所知,心中开始有了谦卑,老实多了。在这个惶惶不安的时代里,在我这个年龄上,能谦卑一点地活着,复归于对周边事物的好奇与专注,并因了这种好奇与专注,渐渐有了一种持续的喜悦和平静。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另一个具体的影响在于,因为动手去画画,让我找到了一个契机和线索,把过去做过的不同事情,分别开来去理解却总也捉襟见肘的事理,渐渐打通了。过去所学的东西,继而挂在嘴边儿谈论的东西,总要落在某个专业的领域,所谓术业有专攻。这种分别起初有不得已的缘由在,时间长了,专业跟专业之间便有了越来越清晰的区隔,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个的利益团伙儿,一干人马混迹其间,所谓专业的说辞听上去更像是一些狡猾的阴谋。而我们总是被这样的说辞所诱惑、引导、暗示,渐渐误入一条狭窄的通道,而且确信这就是世界本身的样子。问题在于,一条活生生的性命在这个世界上周游一遭,他的无限丰富性、暧昧性、随机性,他所感受到的这个世界的整体性和没有边界性,怎么会因为某一专业的说辞和暗示所限定?在我个人的切身经验来说,这种专业的分别,因为动手绘画的缘故,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因了画画,找到了一条小小的缝隙,切入进去,左拐右行,渐渐打通此前涉足各界而生出的种种疑惑,道路在心中渐渐宽阔起来,眼前慢慢有了光亮。很多以前混乱的思绪慢慢有了条理,以前不明白的事情开始变得清楚起来。
所以,与绘画本身比起来,我更享受这个渐渐明白一些事理的过程。打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人得提前有个明确且伟大的目标,将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样子想得挺好,甚至很具体,等到这个将来时变成了现在时,发现事先想好的那个样子搁不进现实这个时空里去,于是方寸大乱,百般纠结,一路焦虑,搞得自己都不想好好活下去了。
我个人的经历一再地告诉我,人其实是可以做一切的事,有机有遇,种种的幸运,种种的不得已,在我看来都没有那么重要。谁说我一定是个画画的?谁说我一定是个做摄影研究的?没有那么重要,不过是机缘巧合,正好走到了这里而已。此时此刻,待在这里,一意简净,认真地做着手里的事,得一份平静,就可以了。至于明年、后年做什么,谁知道呢?
苏东坡先生当年说如何做文章的话,同样可以拿来说人当如何行走于世间:“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对于容易着急的人来说,这话听上去飘飘忽的,有点儿不大靠谱。其实说得挺实在,翻译过来就是,顺其自然。
所以,还是顺着这个自然走吧,不必刻意把自己设计成个什么样子。别提前说那个将来。到了将来,再说。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雨打一池新叶,风过十步短亭。坐看翠色与眉平。人界总无趣,花间却有情。
此身此生此世,且度且思且行。什么得失输和赢?要紧是快活,何必求浮名?
——老树
我第一次看他的文人画,一看便喜上眉梢……幅幅闲得不同,愁得也不同。
树勇本就精于中外摄影、图像史,反省力极强,故构形取之有道,绘之有神,非一般学院派的死板,或那么“启蒙”,那么“文艺”,而是活脱脱的日常生活,自家忖思,自家怜,自家园子,自家菜,恐怕连友人亡故、引车卖浆、内心的逃逸,都可成画,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也就是一个“小人物”的烦恼,而这烦恼,却又寻了绚丽的色彩,养了自己的宁静,给了别人视觉与解脱。虽不见佛,却恍若有佛,即便一只抽屉,也恍然大有文章可做,超然如此,已或然是另一种“丈山、尺树、寸马、豆人”了……
——钟鸣
1,这是一份“老树画画”对这个世界的内心告白,一本极具标志性的老树式长衫人物绘画集。乱世绘本,绝妙好词!好玩,通透;厌的是假模假式、假情假意,喜的是真人真趣,对自己内心基本的真诚。“要紧是快活,何必求浮名?”网友妙评:“画这画的人,心在天上游荡呢!”
2,精挑细选,全彩印刷。从3000多幅画中精选近200幅画作,辑成“日常”“闲情”“花犯”“心事”“时节”“江湖”“桃源”七组,勾画出老树笔下“长衫男子”的日常琐细和内心世界。下笔是民国形象,画的却是当下都市流浪人的内心。洒脱,真率,呆萌,可爱,有的是闲情逸兴,却又身在江湖,逃不开尘世俗务、孤独缠身。每幅画就是清茶一盏,能提神解乏,能咂摸出隽永滋味,慰藉人心。
3,老树自己最在意的书。以绚丽的色彩,养自己的宁静。“我只是写心中一点小小的趣味儿,一点儿小意思小空间,好玩儿。”关于画画,关于自己,老树想说的,都在这本书里了。
4,陈丹青、蔡康永、涂子沛、洁尘、于谦、杨浪、杨林、袁冬平、杨葵、钟鸣等等各界名人共赏,无数网友争相留言唱和。
[答客问] 业余的状态也许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节选)
西门烟树:你一直是在做摄影方面的研究工作,教学也是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怎么忽然就画起画来了?是不是小时候就学过?
老树:其实我到上大学之前,一直就是生活在农村,又处在一个知识信息极度匮乏的时代,对绘画真是一无了解。我的老家山东潍坊的临朐县现在是个书画之乡,喜欢字画的人非常多,还是个北方最大的奇石集散地,有点头面的人物过年送礼都要送轴字画或者是一块奇石。又都喜欢盆栽盆景,哪怕是在农村,你也会看到家家都会摆几盆花,弄块怪石、挖株老根养个盆景什么的,而且多喜欢养迎春花,当地人却一定要把它叫作梅花。当地会画画的人也非常多,很多人都喜欢画两笔竹子,而且都画得不错。民间也有很多郑板桥画竹的收藏,因为郑板桥曾经在潍县做过几年县令,当地人很以这点为自豪。尽管大多是伪作,但可以看出当地人好文尚古的趣味来。临朐县七贤乡有个叫李达元的老先生,专擅画竹,我上大学时放暑假回家,曾经去拜访过他。他还给我父亲画过一张中堂,现在还挂在家里。两边是另一位老先生焦鼎芳写的对联,字也写得好,学何绍基和舒同体,但比舒同要写得老辣厚道。当地过去还出一种宣纸,跟南方出的纸完全不同。纸厂的一位推销员是我家的一位亲戚,过去推销纸就专门往全国各地的画家书法家家里跑,说是去送试用纸。因为这个缘故,他家里就有不少武中奇、肖娴、魏启后、于希宁、李苦禅等等书画家的字画。那时的画家不大把画当个事儿,有送纸的人来,都要画张画写幅字送给他们。我记得他家里武中奇的字比较多,因为武老先生的岳丈家就在我们那个小镇的边上。近一二十年来,这个地方考取全国各地美术院校的学生也非常多。山东艺考生是全国最多的,而山东最多的是在潍坊。这些艺考生中多数都是要去学画的。从这些事中,你可以看出当地人的这种喜好和趣味来。
潍坊的木版年画很有名,套色印刷,大红大绿的,铺张而有世俗的元气,很棒。但是,在我小时候却看不到,因为民间年画的内容在当时来说基本上就是牛鬼蛇神、忠孝节义,当时是当作“四旧”被扫除掉了。过年时贴个灶王爷还得偷偷地买来贴在灶间。那个时候看到的最多的画本,主要还是每年买来挂在家里墙上的那些政治宣传画。其次是小人书,也就是连环画,《鸡毛信》、《东郭先生和狼》、《三打白骨精》,多了。那时看连环画约等于今天的看电视,而且互相传借着看,直到把一本连环画翻得稀烂为止。看完了,就记得那些故事了,画家倒没怎么在意。
展览倒是看得多,那是一个接一个的忆苦思甜展览和大批判的展览。你别小瞧了这些画,我以为抛开那种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动机不管,单纯就想象力而言,那些展览和画充满了那个时代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真是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小的时候我很迷恋这些画,也很崇敬画这些忆苦思甜展览和大批判展览画的人。记得是一位本村姓孙的画匠主理此事,长得高大,样子憨厚质朴,手却巧得很。画要摊在大队部的一个会议室的大案子上画,用瓶装的那种很粗糙的水粉颜料画出来,然后贴到一大面墙上去供人参观。我经常去看他画画。记得有一次去看,他正在画一个大地主,肚子很大地挺着,穿一黄马褂儿,一手拿算盘,另一只手上戴一只大金戒指。旁边则是一个瘦瘦的戴眼镜的账房先生正在收租子。能看出来,他一个人猫在这间大屋子里画得很享受,而且也不用到地里去干农活儿,这在当时的农村来说就是一件很让人羡慕的事情了。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画的那些旧社会出门逃荒要饭的人,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扶老携幼,背着破铺盖卷儿、拄根棍子走在荒野之中,天空是一缕缕灰暗的云彩,地上的树木都没有叶子,寒风凛冽,吹着路边枯黄稀疏的野草。画得那个凄凉啊!真像个旧社会。搞得我多少年过去之后,偶然看到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科柯施卡的画,觉得简直就是忆苦思甜展览的奥地利版本!还有就是大批判展览中画的刘少奇,一嘴大牙,一个大鼻子,鼻头儿上一定是红红的,还有几颗麻子。很多被打倒的老干部的面部特征都被放大夸张到了一看便知道他是谁的地步,而且脸谱化了,很好学。看得多了,这些显著特征我们都熟悉了,就常常用来画某某同学,相互取笑攻击。
这大概就是我最早看到过的展览,而且数量、规模都很大,隔三岔五地就展一个。后来到了北京,或者出国旅行,在美术馆里看到老师带着一群小学生溜溜达达地在那里看那些世界著名艺术家的作品,边看老师边给讲解,我都会站在一边呆看上半天。我就想,当初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些什么东西啊!当年待在农村,外面的事什么都不知道,油画国画版画什么的就更不清楚了。说起画家来,就知道有个齐白石,因为小时候我家的暖水瓶上印着齐白石的一幅画,画的是红叶秋蝉,还是我父亲告诉我的,说这是个大画家,了不起。另外还知道一个徐渭,因为在我父亲存下来的一叠五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杂志的封底上印着一张徐渭的画,一个骑驴的古代男人,印象深刻的是那驴的腿和蹄子一笔画下来,像是写草书的样子,所谓的逸笔草草。我就知道这么两个画家,还只看到过他们各自的一张画。那个年代在农村你看不到画册,更看不到像今天这样多的作品展览。我的关于画家的记忆就是那两张印刷品和画面上他们的名字,其他的就一概不知道了。
西门烟树: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的呢?
老树:开始学画是在大学一年级,一九七九年的秋天,很晚了。刚入学,班里要搞点学生活动。我们的班长王竞上大学之前就在天津艺术博物馆工作,说那里正好有个黄宾虹、齐白石、徐悲鸿三人的画展,我们就组织去看。一看我就傻了。你想,那是一九七九年啊!那时候我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这么了不起的人。过去看的只是非常有限的几张印刷品,头一回看到真迹,从那些笔触当中,你仿佛都能看到当时画家画那张画时的样子和想法、心情,真是太动人了!我几乎顿时就想画画了,尽管根本不会画,但忽然就有了一种非常非常大的想学画的冲动。
我甚至因为这个冲动都想转学了,有一阵子我特别想从南开转到天津美术学院去上学,弄得有一段时间焦躁不安连饭都吃不下了。我打听了一圈儿,明白的人对我说,美术学院是艺术专业学校,当初考试录取都不一样,你个学中文的没法转到那里去。但又说学美术史还是可以的。我说只要能进美术学院,能就近跟着那些老师学画画,学什么专业也无所谓。系里的老师又跟我说,教育部规定可以转学,但理论上可以,操作起来非常麻烦。后来几经努力,还是没有转成这个学。于是只好自己业余来学画画了。当然,后来,过了很多年,我很庆幸当初没有转成这个学,庆幸在南开中文系打下的这个底子,但那是后话了。
……
西门烟树:那时北京跟外地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资讯比外地城市发达得多,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上海都要发达。国外来个展览,顶多了到上海展一展就走了。所以,一有这样的展览,很多外地的画家都往北京跑。你到了北京,看画、学画就算是如愿以偿了。
老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比如八三年春天的卢浮宫藏品展,稍后一点儿的蒙克的画展,等等,在当时看了真是很震撼。但是真正来了北京,待下来了,感觉反倒不是那么回事儿了。画当然还是天天画,但不知道怎么画了。那些大家的画都摹仿了一个遍,画得挺像是那么回事儿,画谁像谁,可就是不像是自己的画儿,感觉哪儿哪儿都不对劲了。再去看那些越来越多的画展,就更觉得泄气,觉得自己根本不是这个材料,又不是科班出身,怎么也弄不成个事儿。特别是过了几年,结婚了,有孩子了,生活一下子变得非常具体起来了,你还在那里充满理想地画画儿,感觉简直就是在找死!很快,对画画这事儿就有点儿心灰意冷了。除了上课,在外面上各种能挣点儿外快养家糊口的破课之外,唯一跟画画沾点儿边的事,就是给各种文学杂志画插图。从八六年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我给很多杂志画了不少的插图,一直到九二年开始做书才停下来。可以说,从八六年到二〇〇七年,有二十年没有再正经地画过国画了。
这段时间我做过很多事,偶尔会去注意看看别人画的画儿,但自己好像已经没有这个想再去画画的冲动了。唯一有画画的冲动,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冬天,学校放寒假时,一下子刻了一百多张黑白木刻,印出来贴在墙上,激动了一阵子。因为当时很压抑,看不到什么出路,不知道做什么才好,就将这种心情通过这些木刻给宣泄出来了。但这事做完了,也就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再也没有画画的冲动了。心里就想,画这些东西能怎样?日子还是这样过着,还得为衣食奔命,还是看不到有什么好一点儿的前途,很悲观。
一九九三年春天,我在驻北京的一家香港文化公司兼职,接了一个活儿,为香港的《号外》杂志做一期有关当时中国前卫艺术家的报道专号。除了要采访那些做地下音乐、纪录片、前卫设计的艺术家之外,重点就是要采访那些主流美术圈儿之外的那些画家们。有一段时间,我就在当时圆明园一带的画家村拍照片,跟那些艺术家们天天泡在一起。那些后来名声大噪的艺术家如方力钧、岳敏君、祁志龙等等,就在一起闲聊、吃面条、喝酒。一开始也挺激动,大概人都会这样,喜欢没有管束的自由,喜欢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过去看过的那些艺术史,那些艺术家的传记当中描述的艺术家们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方式在这里一下子给找到了。但没几天我就不那么喜欢了。我跟个旁观者一样看着他们披头散发啸聚城郊荒村,画画、酗酒、打架、搞女人,到处借钱缴房租,跟村民和警察斗智斗勇。要是放到过去,那正是我渴望过的一种放浪形骸的艺术家的自由生活。但我却感觉很失望,一点儿想入伙的冲动都没有了。我远远地看着他们,远远地看着我曾经渴望经验的生活方式,拍完照片,然后走开。
我想在画画这件事上我是彻底地废掉了。有时闲下来想想,我都不明白当初我自己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兴趣要去画画,有时不吃不喝不睡,除了生活必需,几乎所有的零用钱都扔进了画画当中,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画了画儿。除了读书和画画,别的什么都没干过,也不想干。可突然一下子,不画了,再也不想画了。
西门烟树:是什么原因,让你又重新开始画画了呢?
老树:二〇〇七年,我的父亲被诊断出来是胃癌,住进了医院。过去你觉得他们总是健康的,会一直好好的,很少意识到他们也会老去,会生病,会死去。知道这件事后,心里特别乱,什么也做不下去,睡不着觉,就找出过去用过的笔墨旧纸来画几张画,权当是解闷消遣。也不知道画些什么,就试着用国画的笔墨去画自己过去画的那些单线的小说插图,结果一画又找回当年那种着迷的感觉了,一发不可收拾,天天晚上就是画,一画就画到天亮。过去画画的那种局促也没有了,关于怎样画画的那些繁杂的规矩也都一时记不起来了,就索性什么都不去管了,爱谁谁了。什么用笔用墨,什么造型要如何如何,都不再去细想了,就是想怎样画就怎样画了。这样画画让我感受到过去画画时没有过的那种放松自如。这让我重新享受到画画的快乐,让我从一种焦虑当中出来了。尽管我知道这些画毛病很多,但我管不了这么多了,我只是想借着画画让自己放松下来快活起来。这可以说是我重新画画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庆幸的是,这个目的我达到了。至于画得如何,那是以后的事,或者那根本就不是个事儿。反正在画画这件事上,过了整整二十年,我不再像过去那样着急和焦虑了。我想这跟年龄和阅历有关。二十年里做这做那,似乎跟绘画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后来发现,绘画本身没有什么,也不那么重要。绘画最终要表现的是绘画者人生经验的丰富性,是他对于自己这些经验在理解上的深度和高度,说白了是他作为一个人的整体境界。陆游谈作诗的理法时说过一句话: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其实画也一样。诗也好,画也罢,它只是一个显现与表达的介质,它本身是没有多少内涵和深度的。是一个人的眼界、阅历、人生境界赋予它真正的内涵。至少在我个人的经验和理解当中是这样认为的。
你看,我一直就是在一个业余的状态里画画儿,一会儿画,一会儿又不画了,过一阵子可能又想画了。过去一度特别想专业地来做这个事儿,想过那样一种职业艺术家的生活,但我现在不再这样想了。现在我喜欢这个业余的状态。我不想强制自己去做些什么,尤其是不想扎到人堆里去跟着大家起哄。我还是喜欢一个人猫在一个清静的地方,不被外人和破事儿打扰,做着自己特别想做的一点小小的事情。喜欢时可以画上一阵子,或者几年,都可以。忽然不喜欢了,放下不做就是了,就可以去做点儿别的什么你又开始喜欢做的事儿。随心所欲,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心境上处于一种无可无不可的状态。这是让我觉得挺高兴的一个状态。
……
西门烟树:这种生活在今天很多人看来很丰富很浪漫啊!你的画中就有这种浪漫的气息。
老树:我画这些花花草草时,基本不用想象,重回记忆就可以。有些朋友也在微博上问我说:你平时过的生活很浪漫吗?为什么这些画儿看上去会感觉很浪漫?说实话,经验那些事物之时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浪漫不浪漫的。你想想,几个孩子跑到山里去挖草药,那是很辛苦的活儿。当时想的,就是今天出去,能找到、挖到更多一些草药,然后卖掉,能够挣多一点儿钱,补贴家用。也就是说,你身处其中时,是没有这些所谓浪漫的想象的,你只是处在那样一种非常具体的日常化的经验当中。后来你离开了那个地方那种现实生活,你跟那个地方和生活现实有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了,已经没有那种真实的身体的辛苦体验了,已经成为一种记忆了,再加之后来城市生活的经验和比较,你会怀念彼时的生活,生出种种美好的精神层面的想象,这个时候,才会有你所说的这种浪漫美好的感觉。
比如有一年夏天,我突然喜欢吹口琴。二叔送了我一只。白天要上学,要下地干活儿,不能吹。傍晚了,干完活儿回家,将猪喂上,把鸡拦到鸡窝里去,饭做好了,院子扫净,暮色时分,弟弟妹妹趴桌子上做作业,父亲在外地,母亲也还没有回家,自己一个人站鸡窝上去,从墙头上往西看。我的家在村子最北面的村头上,家后面就是无边无际的旷野,要不就是麦田,要不就是青纱帐,尽头是一抹青山。我就在暮色苍茫时分,坐墙头上面对着暮色中无边无际的玉米地吹口琴。
再比如,小学二三年级时,教室是一所大庙的正堂,很高,里面黑乎乎的。春暖花开季节,同学们都会到处去掐各种各样的花来,插到各种瓶子里面,摆在教室很宽的窗台上去。同学们在上课,偶尔会抬头看看那些五颜六色的花儿,笑笑。年纪已经很大的老先生倒背着手来来回回闻那些花儿。他说哪瓶花开得好看,那个掐花来的同学就会高兴上好几天。其他同学心里就很着急,纷纷到山里去折回更多的花来,于是两个窗台上的花总是满满地五颜六色地开着,一直开到春天过去了,大家的兴致才算过去。
风雅吗?今天说起来、听起来真是风雅!多美呀!那么安静的一个时代,那么风雅的人生经验,今天的人说起来听起来就跟假的一样。可那是真的,是我真切的一段生活阅历。你说奇怪不奇怪?放在今天,你会觉得那很超现实,是想象当中拟造的一个场景。但对于我个人来说,这只是写实,对记忆的重现,不用什么想象。
我们今天会很喜欢古人画的山水花卉翎毛草虫,那些诗文题识也好,却很少想到,他画的东西其实就是自己彼时彼地切身的日常生活经验。我们有时会感慨今天的人没有古人那么丰富的想象力了,其实是古代的那种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已经没有了。古时的诗人写诗并不都是在靠想象瞎编乱造,在我看来,更多的时候就是直接地状写眼前所见所感,是设身处地的真切经历。八四年我去黄山,晚上,一大帮人住在西海一间很大的板房里准备第二天清晨看日出,人多太乱,无法睡觉,我就一个人裹件军大衣往北海那边溜达,路过一片很大的松林,我就在一块大石板上坐下来听松涛的声音。四周极安静,月光从松针的缝隙里漏下来,斑斑驳驳地照在松软的地上、山石上。忽然感觉屁股下面湿了,起身发现,原来是山控流出的泉水湿了屁股。一下子就想起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诗句来。这靠什么想象啊?这就是切身经验的写实啊!你写不出这样的诗句来,不是想象力不成了,是这种经验没有了。再想想古书中记载的当年那些隐士们,多数都是些乡绅,生活在乡村当中,有个大院子,虽然不经常要躬耕垄亩,但他所看到的山川河流、田野物产、春华秋实,那都是实实在在的。他不是今天那些有了钱有了闲跑到乡村去吃吃农家乐、看看风景的城里人和权贵们。这种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说哪种人会将这些东西画得更打动人一些?
[答客问] 逃避现实是我唯一的内心现实
西门烟树:我觉得你的画更接近新文人画的范畴,更多的是在表达自己一种想象中的风景,或者说是一种想象中的趣味,而没有当下性,因为你有点儿逃避现实,躲进古人的世界当中去了。
老树: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被一个什么概念所界定,我也一直在变,不是为了变而变,而是画着画着自然而然地就走到另一个方向上去了,而且走出很远,视觉样式跟原来的画完全不一样了。比如我去年一年一直在画的一个系列和今年的一个新系列,画得更放松自如了,什么都可以画,跟过去画的完全是两个方向,但你还可以看出来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比如都远离现实,都有一种调侃谐谑的意味,等等。
人都活在当下,活得都很具体很琐碎,没有人会逃得出当下的这种又具体又琐碎又无可奈何的现实境遇世界去。但是,这样来说“现实”,还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现实”是什么?“现实”里还有哪些东西?很显然,现实有许多层次的内容。我们经验中的人事,六根感受到的物体是我们最容易明白,也是我们最常说及的现实,也就是物质现实世界当中的一切存在。写实性绘画或者是纪实性摄影表达的就是这个层面上的东西,所谓“直面现实”。但现实还有很多的层面,有些是我们看不到的,比如极其微小的微观世界中的存在,比如中国人治病。当初人们生病以为是鬼魅作祟,就请巫师来作法驱鬼;后来国人认为是阴阳失衡,通过药物来平衡阴阳治病;再后来西医通过显微仪器发现是病菌捣乱,再后来又在仪器里看到了更小的病毒。病菌、病毒是什么?也是一些生命啊!他们也要交配、繁殖、找吃的,顽强地活下去。但在这些仪器发明以前,我们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这么小的生命群体。
这些且不去细说,单就跟人的生命活动直接有关的现实当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层面,那就是人的内心现实,也就是每个人在客观现实事物面前作出的内心反应。比如他沮丧、喜悦、忧愁、暴怒,等等。比如他嘲讽排斥他人,他躲开这个现实红尘世界,就愿意回到一个当下现实根本不存在的境界当中去。比如他在想象当中回到了古代,假托成一个古人,穿着古人的衣服,悠游于林泉之下,活得跟古代文献或者是诗画中所描述的古人那样。这种对想象当中的古代文人生活世界的认同,同时也就是对当下现实的拒绝和排斥。这种姿态让他看上去像个不合时宜的人,一个不是向前活,而是活着活着,活回古代世界里去的现代人。你看看周围许多人,你仔细地想想你自己,这其实是很多人当下真实的内心状态。
我觉得,这种状态是当下现实世界当中的一个最大的也是最为重要的现实。它涉及了现实世界当中最为真实和本质的一个层面。那就是活在当下现实世界中的现代人,却在厌倦现实,甚至痛恨现实。他们觉得自己活错了时代,活错了地方。至于古代世界是否真有他们想象得那样美好,那样让人自由自在,其实也未必。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古代世界是他们梦中的一个理想的所在,一个完美之所。他们也不可能真的能回到古代世界当中去,他们这种向往不过是表达出对现实存在的不满和厌憎之情,这才是他们的目的所在。
你说这种内心现实不是当下最最重要的一种现实吗?你看,又出贪官大鳄了;滥使滥用的农药、化肥、食物添加剂搞得我们什么都不敢吃了;房价越来越贵搞得我们都快睡马路上去了;好不容易攒钱买了辆汽车,可出行阻在路上一动不动都快要崩溃了;恶性杀人案连续发生搞得我们都不知道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了;孩子在学校里你都不知道那些教师会干出什么龌龊勾当来了,等等,等等。可作为一个平头百姓你能怎么着?你再小心再躲着,不知道哪一天这种倒霉的事儿就会砸到你的头上!这就是我们舍身其中的现实世界。你无力改变这个世界,那你还不活了?你内心又愤怒又悲哀又绝望,你总不能也去杀人吧?你只能在网络上在手机短信上发泄发泄,编个段子调侃一番,出出气。就像八十年代末期的一个诗歌流派“撒娇派”的宣言里说的那样:“与天斗斗不过,与地斗斗不过,与人斗更斗不过,于是,我们就撒娇。”你想一想,这种情绪,这种内心巨大的动荡与纠结,难道不是当下现实世界当中更为重要的一层现实?
我觉得,很多画画的人还是把现实理解得太过简单了。新中国初期,老画家们要改造思想,要积极表现自己的政治立场,就去画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新面貌,画佛子岭水库、十三陵水库,画鞍钢、水电站、红旗招展的农田基本建设,农村大食堂、拖拉机、抽水机什么的这些新生事物都进到画面里去了。其实他们画得很艰难,心里挺不情愿的。你看看当时他们写的那些思想改造的文章就知道,他们当时真是不知道如何是好,也无从下手。“文革”之后,他们都不好意思提这个时期的事,再画,又画回古代山水的趣味里去了。
这就是说,这些画只是他们在某一个时期迫于外在的需要和生存的压力作出的妥协,跟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从骨子里其实并不认同。如果说画儿在内容上有个标准的话,我想最简单也最直接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些画都要表现画家的内在经验,起码的,他要对自己画的那些东西那种趣味儿有个诚实的认同感。你看,当代新文人画那些画家什么都画,但画的趣味儿、笔墨的趣味儿却都是古代的。他们就认同那种趣味儿,拒绝当下现实的这种粗暴无道。他们就是要做有关古代的白日梦,甚至他们的日常生活都在模拟古人的样子,唱唱昆曲、打打太极,以逃避这个他们身处其中却又特别不喜欢的时代。你能说他们就不当代了?
因此,画的当代性不能从画的题材上来判断。有些题材选择特别具有现实感的画也未必就是要表现当代的情境,可能他还有别的什么用意。比如你看刘小东近年来画的油画,表面上看过去是在画民工,画时尚青年,但我觉得他关注的其实主要不是在表现这些东西,而是在迷恋绘画本身。你看他画画的过程,他特别迷恋这个画的过程,画得很享受,色彩、肌理、关系,大笔用色刷过来又抹过去,很享受。不是画的内容,而是绘画本身让他很享受。从这个角度看过去,他画什么其实是无所谓的。
你再看我们的电视,每天有多少的古装历史电视连续剧在播放?有那么多的国人在看、谈论。国学大讲堂天天在那里扯淡,说起那些事儿来跟他亲身经历过似的,那些帝王将相都跟他亲戚似的。历史类图书也在大量出版。人们置现实话题于不顾,成天迷恋于说那些前朝破事儿,为什么?你说这些现象有没有当代性?这本身是不是个特别重要的值得关注的当下现实?
回过头来说,没有人会将那些有关唐朝内容的历史电视连续剧当成是唐朝本身。同样,也不会有人把我这些表达民国趣味儿的画当成是民国的样子。这些画中的情境只是我个人想象中的一个民国,与民国没有本质上的关联。再说了,民国本身是个什么样子也不重要。画古代人也好,画民国也好,说到底,都是当代人站在当下的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经验,只不过这个经验不是眼前的视觉经验,而是在内心当中发生和存在的一种内在化的经验罢了。
西门烟树:可是,艺术总是来源于生活嘛!你怎么理解你的绘画经验与现实经验的关系?
老树:如果只是笼统地来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句话没有多大的毛病,但也等于是句废话。你说什么不在“生活”当中?这句话等于是在说艺术与生活不在一个地儿。其实我们通常所说的“生活”,指的就是眼前的“现实”的意思。过去我们常说“艺术来源于现实生活,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两句话,颠来倒去地说了很多年,以至于我们从不怀疑它的“正确性”。我们的头脑当中总是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固执的“是”和“非”的分别,而很少有一个“有”和“无”的观念。“是”就是好的,就是正确的;其他的就是坏的,反动的,就是个贬义词。这种简单二元的不由分说的是非观就像一种病毒程序一样输入了我们的头脑,进而成为我们判断一切的基本指令。当这种论调上升为“真理”之后,它就再也不能被怀疑了,你只有信服它,按照这套说辞去行事。问题是,世界上的事能有非此即彼这么简单吗?要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倒不如说“生活来源于艺术”更准确一些。当然,这是个更复杂的话题,不说也罢。
我不相信这些屁话。我画画为了什么?现实够麻烦的了,在现实当中你再烦也得硬着头皮去做事,因为你躲不开啊!但你可以在梦里,在写作的时候、画画的时候躲进一个自己的世界里去歇一歇喘口气。所以我画画的动机就是要逃避。我为什么不能逃避?我连这点儿自己选择的权利都没有吗?我怎么总是要对现实,对我的工作,对我的家庭,对我过去承担的乱七八糟的事情负责任?我为什么就不能为我自己痛痛快快地活上几天?为什么我自己的内心生活就是不重要的?当我面对社会、国家、民族、现实政治需要时,当我面对那些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艺术观念时,我就一定得放弃我自己的内心生活吗?
逃避现实是我唯一的内心现实。逃避现实生活当中的那些公共标准、公共要求指标,逃避那些令我尴尬难堪、令我不那么舒服的困境,这就是我真正的也是最最重要的内心现实生活。逃避开现实那些功名利禄的诱惑,逃避单位里那些嫉妒的眼神、那些毫无意义的表格规章制度,逃避那些婚姻家庭的负累,逃避女人带给我的指责、要求甚至因爱恋而生成的托付终身的恐惧,逃避我内心当中因长期的教育带给我的那种身为一介匹夫却要担当国家民族大任的可笑而虚幻的道德责任感,逃避因为没有钱换一间大房子而在心里感受的那种对家庭的歉疚感以及在他人那里的自卑感,逃避评职称、涨工资屡屡不果的尴尬处境。在现实生活当中我真的是早就烦了,厌倦了,没有兴趣了。现实社会与理想中的生活是如此的不一致。我的一切的向往、一切的愿望都在现实当中看不到实现的可能。我确实变得很消极,我就是想要消极地活着。我愿意这样。我看不到有什么值得我去积极地活下去的理由,我也只能这样。现实有什么好?现实让我失望让我愤怒让我尴尬让我无所适从让我就想逃开。我不想按着别人教导我的那种方式活在现实世界当中了。我只想做一些我自己一直特别想做的事情,活在属于我自己的世界当中了。我就是想回到一个与现实无关的狭窄的甚至是阴暗的个人内心世界当中去了。这跟别人有什么关系?碍着别人什么事儿?有人说我的画太消极了,没有为别人提供“正能量”!什么“正能量”?不就是那些虚假的伪善的具有煽动性和欺骗性的一套套谎言吗?“文革”开始时,历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中,我们每一个人浑身上下充满的全是所谓的“正能量”,多么积极灿烂的人生啊!多么豪迈崇高的人生啊!我们从未怀疑过别人和自己,就是靠着这些无限正确、积极向上的使不完的“正能量”,我们革了地主老财和资产阶级的命,革了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命,革了我们自己的命。终于,我们成了今天的样子。
我们上的当还少吗?所以,别对我谈什么责任呀义务呀这些狗屁大词儿。我已经做得够多了。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让他人来绑架勒索的。我又不碰你们的法律,我又不害人。伤害他人也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我对此了无兴趣。我不想干那些在别人看来、在我过去看来多么有意义的事情了。什么叫“有意义”?都是胡扯!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人活着只不过是你生下来了,你不得不活着,除非你自杀掉拉倒。你说有什么意义可言?一切“意义”化的说辞都是某种利益集团为了达成一个特别的目的而故意制造出来的一套谎言。我就想胡乱地走动,胡乱地想事儿,胡乱地画画儿、拍照片儿。我就想自己在一个无人知道的世界当中梦游,自言自语。这不好吗?这干别人什么事儿?我不参加你的展览,不参加你们的评奖,我不信什么标准,我心里的愿望就是自己的标准,这不行吗?
西门烟树:所以你逃入了画中,在画里逃避开现实。你认为绘画就是要超越现实的吗?
老树:逃避其实是人的一种动物性的本能啊!不是什么社会行为、文化行为。车过来了,你下意识地就会躲开。你不躲开试试!一只蜗牛在地上爬,有什么东西过来了,赶紧把躯体缩到硬壳儿里去。就这么简单直接的一件事儿。德国现代美学家沃林格一个多世纪之前就对这一本能作出了独特的阐述,只不过他是从人类的艺术表现角度来说的。他认为,正是现实世界的变动不居,导致人类的持续焦虑与恐惧。他称现实世界是一个充满了特殊与随机变化的世界,人类要想摆脱这种恐惧,最重要的办法即是由这个特殊的变动不居的世界当中找到一个本质的一般性的绝对的世界。他没有将这个世界引入个人的内在世界当中,而是将抽象的世界看作最为本质的和人类赖以逃避现实的世界。他还考察了德国一个少数民族原始艺术的这种抽象化倾向,并由此认为这是人类从艺术的角度摆脱现实的偶然性和现实焦虑与恐惧的最重要的途径,同时也是人类的一个重要本能。沃林格这部著作叫《抽象与移情》,辽宁人民出版社出过译本,你可以找来翻翻。这本书与康定斯基的《论艺术里的精神》一书,分别从艺术考古学、艺术人类学和艺术实践与研究的不同角度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从而成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时期抽象艺术实验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与我谈到的这种个体在内心当中对现实世界实施的逃避策略不同的是,他将人类的逃避欲望引向了一个绝对的超验的境界。但无论以何种方式最终达成这种逃避,都说明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人类逃避现实的苦难是一种必然的努力倾向和本能。正视现实,并积极地介入参与到现实生活世界当中去当然是重要的,但并不能看成人类唯一的和必须作出的选择。就我个人生存的经验和能力来说,面对现实更多的是一种恐惧,改了半辈子了也没有多大起色。这样一个人还要逼着自己一定要积极地投身到现实社会当中去,跟很多打了鸡血一样成天慷慨激昂的人混在一起,干那些自己根本就不喜欢也不擅长的事情,这不等于是去找死吗?在我看来,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高下是非的分别,而只是取向不同而已。
另一个是,人类逃避现实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而且都有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人之一生其实就是一个逃避现实苦难的艰难行程。他认为人类逃避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宗教、幻想(文学及艺术即属此列)、超越(哲学)、麻醉(毒品)以及自杀。他谈到的以艺术的或者文学的、幻想的方式来逃避现实,可能是一种比较可取的方式吧?我们不好这样断定。但人类总体的价值观比较认同这种逃避的方式。其实不独幻想,那些被看得很高的理性探讨,也成为艺术家借助艺术这个媒介逃避现实的重要一途。比如现代主义实验当中非常重要的所谓纯粹绘画语言的探索,从人的切身经验的角度来说,也算是一种合法化的逃避途径。用那个走在这条道上的最具代表性的画家塞尚的话来说就是,绘画并不表现现实世界,而是与现实平行存在。我喜欢这个“平行”的说法,我觉得这更接近艺术的本质和现实功能。一平行,你就有个安居之所了,你就可以从现实的经验状态当中脱离出来了,你就可以合法化地沉潜在另一个层面的世界当中去了。我想这跟吸毒后那种将幻觉当作另一个真实世界的状态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总之,你算是逃出来了,不落在那个让你焦虑万分找不着北的现实世界当中了。我们的艺术理论当中总要说到艺术有它的自律性,有它的语言本体,或者说艺术自成语法,等等,无非是在努力地肯定这个跟现实世界平行存在的、可以让人逃避进去的艺术现实世界的合法性和真实性罢了!
你刚才说的那句“艺术来源于生活”后面,还有一句叫作“高于生活”。如果这句话像塞尚那样是从艺术具有超越或者平行于现实之外的意思来说的话,它就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艺术比生活本身更高超更重要更有意义更牛逼这个层面来理解它,那就近于荒谬了。绘画怎么会比生活高呢?想什么呢?有什么东西比生活本身更复杂、更具有感染力、更浑莽无形?而且这话在逻辑上也不对。艺术本身就在生活当中啊,以艺术为理由的逃避现实之举本身也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啊,它怎么会高于生活?我还是喜欢将艺术看作是在生活本身当中的一种特殊的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处所。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个可逃避的去处。也正是因为有了“艺术”这个说辞,我们才有一个可以合法逃避现实世界的理由和借口。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