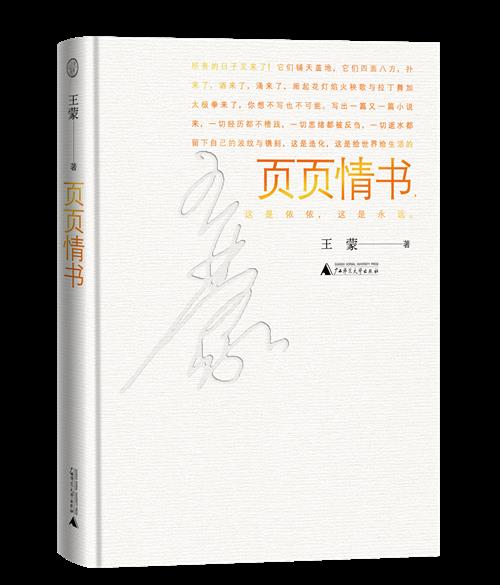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0-02-01
定 价:49.80
作 者:王蒙 著
责 编:徐碧姗
图书分类: 名家作品
读者对象: 文学爱好者
上架建议: 小说
开本: 32
字数: 250 (千字)
页数: 4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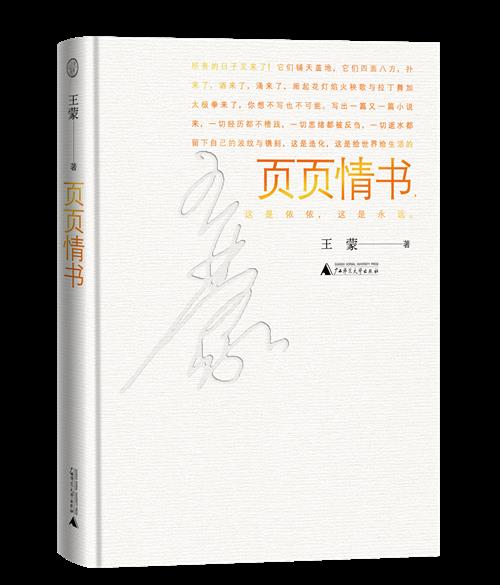
本书收录了进入21世纪以来王蒙创作的12篇中短篇小说。既有反映北京郊区农民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迈入新世纪后生活与情感天翻地覆的变化,如《山中有历日》《小胡子爱情变奏曲》等,又有描摹北京高档别墅区富人生活状况的千姿百态,如《悬疑的荒芜》《岑寂的花园》等,还有表现城市丧偶老人晚年相亲的幽默遭遇,如《奇葩奇葩处处哀》等。郊区农民新生活的千变万化,别墅区富人新世纪的奢华情趣,城市丧偶老人新情感的艰难曲折,处处反映21世纪后中国城乡出现的人们衣食住行及意识、观念上的变化,每一篇小说都堪称情趣与哲理并存,体现了作者丰厚的人生阅历和情感,不愧为“人民艺术家”。
王蒙,男,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中国当代作家、学者,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生死恋》等近百部小说,共1600万字。他不仅创作小说,还撰写解读传统文化的作品,比如孔孟老庄系列。2019年9月,王蒙被评为“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序
秋之雾
太 原
岑寂的花园
悬疑的荒芜
山中有历日
小胡子爱情变奏曲
明年我将衰老
杏 语
奇葩奇葩处处哀
仉 仉
我愿意乘风登上蓝色的月亮
女 神
附录一 我要告诉你奇葩们的故事
附录二 怀念与夙愿
上世纪的最后五年,我开始了自传三部曲的写作,《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九命七羊》,写得酣畅淋漓,顺风顺水,后出版于二○○五—二○○七年。其时我曾经表示过,写完了这几部书,到二○○四年,我七十岁了,估计该告老辍笔,游山玩水,花鸟虫鱼,颐养天年了。
这时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出版人刘景琳先生动员俺写一部关于老子的《道德经》的书,我畏难,谈到了自己古代哲学史、古代汉语方面没有受过科班教育的短板,刘兄强调的则是我经验、经历、思考、分析、灵性方面的所谓长处。终于他说动了我。于是我开始了对于孔、孟、老、庄的进军,然后发展到列子与荀子的解析与感悟。我读得、活得、写得、想得、讲得越来越充实,打开了众妙之门,其乐无穷。
有点“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意思了。这个期间的小说创作,主要是系列微型或片段接连的小故事与寓言,一开始叫《笑而不答》,后来叫《尴尬风流》,以启示理性思维为主。也还有点动静。
光阴似箭,生活仍然是浪花起伏,感慨良多,小说情的激发仍然时时冲击着我。二○○五年,一次大雾中从天津回北京,乘车走了一夜,一夜听着梅花大鼓,拨动小说之弦,而后我写作了中篇小说《秋之雾》,有怀恋也有叹息,有刻画也有情思。二○○八年,太原之行让我回想起当年瑞芳在这里读工学院(太原理工大学)的情景, 百感交集,发表了短篇小说《太原》,与早几年写的《济南》堪称短篇姊妹。二○○九 年,发表了《岑寂的花园》,回忆中涌现了许多新鲜与发展的元素与兴头,有欢呼也有无奈与哭笑不得,端的一面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面是“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是繁花迷眼、热热闹闹的风景。然后在二○一二 年,经历了芳去世的生离死别、痛苦与珍惜、往事与现实、画面与声响之后,我的文学情感的流淌又激荡起来,迅猛起来。二○一三年,出版了获得新生的尘封旧作《这边风景》。同年冬在澳门大学,我写了散文诗式的短篇《明年我将衰老》,发表于二○一四年一月号的《花城》,获得了当年《小说选刊》的奖项。一身二任,后来收入了同年舞蹈型新作长篇小说《闷与狂》成为其中一章。一位尊敬的副总理读了此篇专门为此在大年初二给我打了电话。
而与《人民文学》编辑部同志特别是马小淘小朋友的打交道,蓦然助力于再次打开了中短篇小说的创作闸门。我写大城市郊区的农民,我写几十年的沧桑,我写心情里贮存了多半辈子挥也挥不去的记忆与幻想,我写仍然的爱恋、趣味、好奇、记忆、重温与条分缕析,析不明白,就干脆大大方方地留点小说的神秘。二○一二年是《悬疑的荒芜》《山中有历日》与《小胡子爱情变奏曲》,二○一四年是《杏语》,二○一五 年四月号,《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上海文学》同期发表了我的新作《仉仉》《我愿意乘风登上蓝色的月亮》与《奇葩奇葩处处哀》。然后二○一六年是非虚构中篇小说《女神》。而二○一九年,一月是中篇《生死恋》,短篇《地中海幻想曲》与《美丽的帽子》,三月是非虚构中篇《邮事》,十二月则是接近长篇小说的《笑的风》……对不起,俺不仅是耄耋肌肉男,更是耄耋小说狂。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生命的甘苦与丰盈的牵挂,用四季的花饰与飘飘摇摇的花瓣落叶编织你们;所有的日子都去吧,我琢磨你们,写下了你们,涨起了不比四十年前乏弱的晚潮。
我终于明白,立正!我向一切显示出安宁与尊严的老作家致敬与祝福!至于自身,管他古稀耄耋,管他生离死别,管他往事如烟非烟,管他老生马谭杨奚式的慢抬快落四方步,管他搁笔者的不平心理,写啊,写!写小说是多么快乐,人生经验了那么多,快乐幸福了那么多,悲伤哭泣了那么多,微笑了也晾凉了那么多……所有的日子又来了!它们铺天盖地,它们四面八方,扑来了,洒来了,涌来了,闹起花灯焰火秧歌与拉丁舞加太极拳来了,你想不写也不可能。写出一篇又一篇小说来,一切经历都不糟践,一切思绪都被反刍,一切逝水都留下自己的波纹与镌刻,这是造化,这是给世界给生活的页页情书,这是依依,这是永远。
本书是王蒙完成自传三部曲歇笔数年后重返创作以来主要中短篇小说的结集,是作者丰富人生阅历和依然蓬勃的创造力、深厚老道的笔力的集中体现。收入其中的12篇小说,展现了小说创作的无限空间和无穷魅力。如作者所言,“《秋之雾》是低沉的大管协奏;《太原》是小提琴的回旋曲;《岑寂的花园》是戏剧或歌剧的序曲,浪漫中不无谐谑;《悬疑的荒芜》是新新闻体。《山中有历日》与《小胡子爱情变奏曲》是朴素的现实主义,而《明年我将衰老》是感觉派与印象派”……小说中的人物,有风趣幽默、吃苦耐劳的新时代农民兄弟,也有奢靡张扬、情感阴郁的新型文化富豪;有深陷往事追忆青春的孤独老人,也有寻求晚年幸福的黄昏恋相亲者。农民、富豪、知识分子、上流人物、青春少年、夕阳老者,人物性格突出,形象鲜明,成为一组流光溢彩的人生百态图,耐人寻味。作者笔触遒劲而深情,语言丰沛、气势磅礴,每一篇小说都堪称情趣与哲理并存,体现了作者丰厚的人生阅历和情感,不愧为“人民艺术家”。本书并配以作家何立伟专门为此书创作的插图,相得益彰,增加了阅读趣味。
《秋之雾》
重复是伟大的力量,重复有一种威严,重复是不可抗拒的,重复使他快乐之中又有些胆战心惊。看来也是天意,是命。他本来就应该好好听一下久违了的桃花调。桃花调的味道好极了。像是桂花糯米藕,像是即墨老酒,像是陕北石榴,像是西湖莼菜,像是致幻的神秘果。由于年轻,由于天翻地覆,由于外力和自身的幼稚天真,他与桃花调一告别就是——别梦依稀咒逝川,古音六十九年前!
一声桃花曲,双泪落君前!他终于得到一个机会在去国以前听一听,听完,就告别啦。外国什么都好,假使都好吧,就是没有故乡小调。中国什么都好,故乡小调也式微了。不微也没有多少缘分了,听东西只能在孩子时候,大了,一边听着梅兰芳哪怕是帕瓦罗蒂,也同时会分心想到下一次会诊的方案或者下一年度的预算。像一部旧电脑,他的数据库装的东西太多,岌岌乎自爆。他也只有在雾里,在无法快速行驶并且完全无事可做的这几个小时,做到了专心聆听。听了还要再听,听了还要再听,既疲劳又甜蜜,既伤心又满足,伤心也令人得到满足的快感。好比是还债,还债的时候你感到解脱,也感到惭愧和痛惜,不是痛惜钱财,那钱财本来就不是你的,痛惜的是你为还债用了那么长时间,还清欠债,您也老啦。
他要在一个晚上,在公路上,在大雾里还上他儿时欠下的、青年时期欠下的一种说不上是什么感情的感情债、曲艺债、艺术债、少年与青春债、家乡债。还有所有的男人欠下杜丽娘们崔莺莺们的债。古往今来,男人们欠下的风月债还少吗?
多少个夜晚,他是握着手术刀而不是握着女人的手度过的。
那么雾呢?雾的形成是最简单的物理学。没有风,没有蒸发,空中的气温没有能够比地面的凉,形不成对流……那么雾的消除呢?它需要日晒,它需要风,它需要气温的急剧改变,或者,很简单,却是很难操作,只要好好加一下温。
那么乌克兰呢?乌克兰、俄罗斯,也有许多大雾。乌克兰在大雾里,有许多苏联的歌词为证。库奇玛、亚努科维奇、尤先科、基辅与顿涅茨的选民,他们将怎样破雾起航,决定自己的命运?大雾总会散去,那么黑海舰队的出海口呢?疯了,真是疯了,他并不是基里尔呀,他叶夏莽管那么多干吗?
这就是桃花调。他大概已经听到了第十几次了。一晚上听了十几次桃花调,他也算对得起桃花调了吧。这就是桃花镇的即将绝种的演唱,像娇莺之语,像春情春水春意的有节制的泛滥。地球上每一天都有物种消失:语种消失、民族历史消失、文物被破坏、民间文化样式消失、曲种消失。随着人的告别,他们会带走许多过往、许多珍贵、许多挂记。
……也许能吹起一阵清风,也许至少明天早晨会出现一个鲜红的太阳,也许浓雾会完全散去,也许他重新考虑远行多伦多的决定,也许虽然八十了也仍然可以去去再来,也许他还会回来听桃花镇的桃花调和再考虑一下颅外科手术的刀剪用具的改进。
也许他还能再来一次黄昏恋。十年来,不是没有人要做他这个老家伙的媒。有一个女诗人,他很有些喜欢。后来他读了女诗人的作品,她的特立独行、她的狂叫激愤与蛮不讲理令他战栗惊服,他终于望而却步、临阵脱逃。有一个女经理,他思而生怵。有一个女领导,他自惭形秽。但是他在碧云死后没有少与一个个的并非没有吸引中国工程科学院院士的魅力的女子一起喝咖啡喝可乐。说一些人家与自己有时候有兴趣,有时候找不出词来的话。
他甚至偷偷想过:最好与一个农村来的保姆结婚,他喜欢这些质朴和勤劳的女人,她们当中有许多人读过高中,她们现在也都挺胸、健康、爱打扮,有一个邻居家的家庭服务员眼睛像影片中的“小花”,陈冲饰演,他想入非非了一两分钟。她们和医生都是天生的务实派而不是某某精神派。把文学说成人学好生奇怪,他觉得医生、体育运动员与保姆才是,至少同时也是人学家。“爱情”这个词,是“五四”以后,才传进来的。爱情像鲜花开放,像电光火石,像小提琴华彩乐段,像大雨后现出的彩虹,像解冻时分的桃花汛。没有经历过爱情的人很不幸。整天唱抒情曲小夜曲盼望花开电闪彩虹横天冰雪融化汹涌澎湃的人则是上了“爱情”两个字儿的当,也许是俄罗斯乌克兰文学的当……自找苦吃,还要旁人的命。
当然,娶一个三八服务公司介绍的家庭服务员——他羞于启齿。
就这样思忖着,一年过去了,又一年过去了,花儿开了又谢了。没有开的也谢了、枯了。还有什么可说?
是他而不是别人,落伍了。时代不同,人人都可以像诺贝尔奖得主科学家一样地挑战极限,为了爱情,为了青春,为了上天的恩典:还活着。
《太原》
我想拉一下你的手。
然后是我们夜走北京城,我们在参加完保卫和平的集会之后去吃了夜宵馄饨和烧饼。是那一次集会使我第一次听到了巴拉圭和乌拉圭的国名。此前我们熟悉的和平人士多是法国人,约里奥·居里、法齐、阿拉贡、毕加索。北京集会上有一位巴拉圭诗人在和平集会上朗读了他的诗。我想以后也许我会被邀请作类似的朗诵。
巴拉圭至今没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然后我们走路,一路我都在唱歌,你的倾听,你的眼皮与人中的轻微抖动与对于歌词的轻声默诵,比我的歌声更迷人。那时候我“认识”许多爱笑的女孩子,然而她们的笑太肤浅。你的笑是不一样的,你的笑承担了太多的分量。我们互相讲述着不幸的童年,父母、家世。你甚至于告诉我,你的皮肤的特点是冬暖夏凉。这使我觉得亲得要死。我们走过了地安门和后海,我们感觉到了微风与水香和柳树新枝的芬芳。我们走过了银锭桥,走过了北海后门与养蜂夹道,甚为窄细的养蜂夹道也让人感到那么安全,那个时候中国的词典上“犯罪”两个字消失了。西单、天安门与前门……那时的路灯稀疏而又飘摇,昏黄而又沉静。可能是我们走路走得饿了,走过饭馆的时候我们闻到了菜肴的香味。你说你最喜欢吃烧饼,包括芝麻烧饼与马蹄烧饼。一旦餐饮,香甜永远。一过八点,所有的饭馆与商店都打烊。开始入睡的伟大城市含情脉脉,略带神秘,无限流连,休养生息,准备明天,流行的口号是要与时间赛跑。偶尔有几辆汽车驶过。我们觉得坐汽车的人都是伟人与准伟人,都是钢铁一样的英明领导与救世英豪。而大街上的行人似乎只剩下了咱们俩,咱们俩代表着青春、新一代,亲爱与抚摸咱们的城市。甚至于“城市”两个字也是解放以后流行起来的,带几分苏俄味儿。解放前我们知道市、城、闹市、街市、古城、城郭,却很少讲“城市”。解放了的人们都重视唱歌与听报告,从歌曲与报告中我们学会了“城市”一词。而如果唱了歌、听了报告还一起走了路,一起欣赏了喜爱了自己的城市……那就是,那当然是爱情。
我问你,你喜不喜欢“城市”这个词?你的回答是愈来愈喜欢。
这些单纯与阳光,是从什么时候改变的呢?为什么会改变呢?这是郎若漾至今闹不清楚的。
然而确实是改变了、消失了,对于这样的改变郎若漾是迟钝的,他以为光明压根是永远的。终于他无情地、冷淡地、傻子一样地接受了改变的无所不在。
改变了的所有的人的命运。人无百日好,花无十日红,社会没有千日的太平。
《岑寂的花园》
我在追捕我的影子。
我的心里有一块石头,我的身上有一条绳索,我的喉咙里有一团毒火。而我的右手上是一道血腥的疤痕。每天都有白色的轰炸机向我丢炸弹。我的影子狡猾灵活,它拉着我跑得无影无踪。它的聪明,它的快乐,它的永占上风,它的无往而不胜,使我也不能不佩服和惊叹。
而我的右手永远流淌出黑色的血。
这一天我抓住了影子,我扼住了它的咽喉,这是唯一的一个日子,它不敢奔跑,它的遁身术无法发挥效力,它的隐身法也不工作。甚至于,它一见到我就低下了头。
这是八月十九日,胡老师的祭日。
它说:“我们的一生中会有许多难过的事。世界没有承诺过使你永远开心的义务。一阵大风吹过,许多花朵凋零,如果是龙卷风则会造成船车倾覆房毁人亡。然而大风是无法避免的,没有风就没有雨雪,没有降水,没有气候与季节。历史也有时候刮风。天地无情,以万物为刍狗。历史无情,尤其以青年人为刍狗。你算老几,你能做什么,你能改变什么,你能负什么责任?人只不过是狂风吹过来再吹过去的沙砾。”
它又说:“你为什么对我赶尽杀绝?也许我做得并不比别人好,我不是英雄,不企图用自己的脖颈去阻挡挫钝历史的利刃。我不是智者,不可能在人海如沸的时候保持孤独和冷静——我要说,这样的智慧其实是冷血的谨慎与自私。我究竟做了什么?有哪一句话哪一个举动是我自己独断专行的?哪一件哪一句没有听命于……我的绝对权威的主人!那么对不起,不是我而是我们,我们与十几亿同胞有多大的不同?如果说不是优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话,至少不会低于劣于百分之九十八的人!”
它又说:“你怎么可能,尤其是我怎么可能,当时就知道十余年后这些都变成了四个坏人之罪?我们相信历史有历史的逻辑,导师有导师的神机,蓝图有蓝图的宏伟,代价有代价的无可避免。我们相信了,我相信了,你能让我怎么样呢?有的人到现今也宁愿相信这一切的伟大辉煌,相信自身的峥嵘岁月与那鲜红的标帜!”
它还说:“哦,有多少推诿过失的无赖左右逢源,有多少妒贤嫉能的废料高举虎旗,有多少不学无术的混蛋接受桂冠,有多少以蹬踩为看家本领的小人一路青云,有多少落井下石的流氓转眼变成趋炎附势的宠儿,有多少血迹斑斑的右手在那里书写慈悲与博爱,你不懂吗?健忘才能健康……而你,你究竟怎么了?你有什么可亏心的?”
我嗫嗫嚅嚅地回答:“我接受你的雄辩的无懈可击……我并不想起诉你。我其实无言以对,我不能控告,不能倾诉,不能——甚至不能忏悔,不能当原告,却又不能当被告,不能投案自首。只是你杀死了我的善良,或者任何力量通过你的手杀了我,你杀死了我的相信与开心,你杀死了我的青春、爱情、歌声。你杀死了一只洁白的湖鸥。在一个从来没有罪责与忏悔意识,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怜悯与宽恕的空间,告诉我,你还能洋洋得意?你还能无往而不利?你还能保持着你的成功者的身段吗?”
《悬疑的荒芜》
老王夏季与几个老伙计一起吃饭,一位领导的孙女,据说是重点学校的高才生,还是班干部,前来给老人们敬饮料。女孩子说的是:
“我敬祝各位爷爷奶奶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发挥余热、培养后辈、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老王还没听完就傻了。
老王也在视听媒介中欣赏过一次据说是最成功的讲演:
“朋友们、同志们,春风送暖,阳光明媚,风景这边独好,江河日夜奔流,灿烂的前景在向我们招手,英勇的前人在向我们注视,危机也是机遇,难点更是热点,困难的后面是奋起腾飞,坎坷的后面是阳关大道,我感谢你们的包容也感谢你们的厚爱,我赞扬你们的辛劳也赞扬你们的奉献,没有付出就没有美好,没有辛劳就没有丰硕,没有曲折就没有成功,没有理解也就没有拥抱……”
老王几乎晕了过去。
老王梦见一位男青年向女孩求爱,读道:
“啊,我爱你,我想念你,我思考你,你不仅有美丽的容貌,你更有美好的心灵,容貌会衰老和变异,心灵却永驻青春。我们的结合会带来圆满,我们的温存会滋润生命,我们的和谐会经营宁馨,我们的热烈会燃烧激情,我们的相爱是我们生命中的火把,我们的火焰是暗夜中的光耀。你是我的奇葩,我是你的雄鹿;你是我的小雨,我是你的晨风;你是我的追求,我是你的给力;你是我的黄羊,我是你的马驹;你是我的朝霞,我是你的雷电……”
这位青年很可能获得了演讲比赛的冠军,很可能被邀参加电视节目。电视节目正在涵盖人生的诸方面:择偶、治病、烹调、司法、升学、就业、婆媳与妯娌关系,都已经成为收视率高、广告收入好的良性节目了。在电视节目生活化的同时,反过来整个人生也学到了节目化、作秀化的路子了。
……总会有一天,哪一天?人们会自自然然地说话。你是谁就是谁。你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你本来啥模样就是啥模样。困难在于,倒胃口处在于,你本来是方块3,却一定要以红桃A的样子与词汇、逻辑与口气发声;你本来是黑桃Q,却硬要以梅花老K的谱儿来发言。你越来越不像你自己而像别人,甚至不是像别“人”而是像一架别的录放机与扬声器了。
这其实是让老王捡了便宜。他有什么卓见真知?未必。他不过是没有完全忘记怎样拉拉家常,怎样不必戴上面具,怎样亲切自然、本来面目。他确实缺少做一个非老王而是老李或老陶的勇气与脸皮。他有时甚至佩服那些明明是老侯老朱,却以老马老吕的角色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哥们儿姐们儿。
老王在“锵锵”节目中也还是有所把握的。但他听到人们信口说话,随机搭茬,就像听到了民歌小夜曲或情人枕边的喃喃低语一样由衷喜悦。他无法想象谈情说爱的人们会准备发言稿。真情无稿。然而真情是不完美的,真情一定不会完满无缺。当他自己能够随意地本色地说话的时候,他感觉到的是他的任意说话,竟然被抬举为帕格尼尼范儿的小提琴演奏。
“锵锵”的貌似随意任性的机灵至极的主持人,其实也不是不注意应该注意的颜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一位年轻的地市级领导,提出某个会议上说话可以“肆无忌惮”,后来很快受到了白发高龄、德高望重的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领导人的公开批评。
谈了两个小时,相当于四套节目。老王在领取了少量劳务费用并与有关合作人士愉快告辞以后,助手对他说:“您的别墅那边出事了,进去了贼,可能偷走了东西……”
《山中有历日》
老王到这个村来居住已经满十五年了。这次走过吕二凤开的杂货店,与二凤闲聊了几句。在二凤的热情邀请下,他走进他们的店铺看了看。有一套体量不小的风铃引起了他的兴趣。风铃其实不完全是铃,应该叫风铃兼风管或风笛才对。大小不同的五个金属管子,稍稍有风,管壁发出的是叮叮咚咚的清脆撞击与呜呜嗡嗡的悠长之声的和鸣,管内的空气发出的是CDEGA五个闷音,或者也可以说是多瑞米骚拉。五个音无序地或因无序而似乎有序地参参差差地响了起来,忽然一声像《紫竹调》,忽然一声像《梅花三弄》,忽然一声像京剧过门中的《夜深沉》,忽然一声像《小放牛》。忽然随着风力的加大风笛激越起来,它挑动得你泪眼迷离,世界如何会这样眼花缭乱,悲喜莫名。一会儿又因为风力的减小而淡漠了下去,它抚摸得你万念俱空,山沟里竟如此淡淡浓浓,终于失落。来无影,去无踪,似有意,更无情,没有所谓,却是心惊。而金属管壁的碰撞,清清脆脆、零零碎碎,如水,如波涛,如滚动铁环,如春汛破冰……
山野的人也是这样,碰碰撞撞、起起停停。风起了,声起了,动人得心醉心软,撩拨得你无比动情。原来会有这样散漫与游移的旋律,诉说着捏不成个儿、画不成形状的喜怒哀乐,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诉说什么。风要停了吗?在你刚刚摸着了一点脉络,体会了一点天籁的时候,慢慢地,声音渐趋收起,共鸣余震仍然长远,再长远它也渐渐卷起来了,一直是若有若无,若无若有。你感到的是留恋与失落,既空虚又充实。你忽然想为山风与风铃、风管与风笛浅哭一场。
终于,你笑了。
笙管本无律,清风顾盼闲。哀哀稚子意,眷眷亲人怜。岁月悲华发,流光爱少年。山中有历日,年尽不言寒。
(唐诗有云:“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
幼小便失亲,山深自本真。几行逝水泪,一片朝霞洇。或有野村梦,岂无花蕾心?春夏秋冬后,情仇过眼云。
“山吧”样样宝,处处闻啼鸟。游客沟沟至,大巴路路跑。现钞结现场,新妇抱新小。惜取花开日,曲吟“金缕”好。
曲唱金衣缕,歌吹杨柳枝。情人应有泪,父老岂无持?鸟散伤秋晚,虫集苦夏迟。山光日日好,愁心淡如丝。
《明年我将衰老》
然而我失去了你,永远健康与矜持的最和善的你,比我心理素质稳定得多也强大得多的你。你的武器你的盔甲就是平常。你追求平常心早在平常心成为口头禅之前许久。对于你,一切剥夺至多不过是复原,用文物保护的语言就叫作修旧如旧,或者如故如往如昔。一切诡计都是游戏与疏通,都是庸人自扰与歪打正着,都是过家家很好玩。我乐得地回到我自己那里,回到原点。它不可伤害我而且扰乱我。我用俄语唱遥远,用英语唱情怀,用维吾尔语唱眼睛,用不言不语唱景仰墓园。一切恶意都是求之不得,都是解脱,免得被认为是自行推脱。是解脱而不是推脱,是被推脱所以是天赐的解脱。一切诽谤都可以顺坡下驴,放下就是天堂。一切事变与遭遇都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叫作正中下怀,好了拜拜。那哥们儿永远够不着。因为,压根儿我就没有跟那哥们儿玩儿。
我的一生就是靠对你的诉说而生活。我永远喜欢冬妮亚与奥丽亚,你误会了,不是她。有两个小时没有你的电话我就觉察出了艰难。你永远和我在一起。那些以为靠吓人可以讨生活的嘴脸,引起的只是莞尔。世上竟有这样的自我欣赏嘴脸的人,所向无敌。那好人的真诚与善意使你不住地点头与叹息。那可笑至极的小鱼小虾米的表演也会使你忍俊不禁。
我们常常晚饭以后在一起唱歌,不管它唱的是兰花花、森吉德马、抗日、伟人、夜来香、天涯歌女,也有满江红与舒伯特的故乡有老橡树。反正它们是我们的青年时期,后来我们大了,后来我们老了,后来你走了。我不希望今天再划分与涂染歌曲的颜色,除非有人想搞左的或者右的颜色革命。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从来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你午夜来了电话,操持说锅里焖的米饭已经够了火候,你说“熟了,熟了”,你的声音坚实而且清晰,和昨天一样,和许多年前一样。你说你很好,我知道。你说已经不可能了,我不相信。我坚信可能,还有可能。初恋时我的电话是41414,有一次我等了你七个小时。而我忘记了你的宿舍电话号码。我顽强地一次、两次、一百次给你拨电话。你说,让过去的就永远过去吧,而我过不去,从十八岁到八十岁。我睁开眼睛,周围是电饭锅里的米饭气息,是你的仍然的声音,使我平和,使我踏实。
生活就是这样,买米,淘米,洗菜,切菜,然后是各种无事生非与大言欺世。然后是永远的盎然与多情的人生,是对于愚蠢与装腔作势的忘记,是人的艰难一把把。然后是你最喜欢的我行我素与心头自有。然后是躺在病房里,ICU——重症监护室,不是ECU,不是洗车行驶定位器,也不是CEO——总经理或者行政总裁。美国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就被认定为CEO。你走得尊严而且平安。有各种管与线,机器,设备,然后拆除了这一切……我一次又一次地抚摸着的是铺天盖地的鲜花与舒曼的《童年》——梦幻曲。我亲了你的温柔与细软。那样的鲜花与那样的乐曲使我觉得人生就像一次抛砖引玉。是排练与演出,无须谢幕也不要鼓掌。
我凝视着多年前的开幕式上各界送来的大大小小许多个花篮的痕迹。这里没有火起来,这里仍然有美好的记忆,即使网球场上养起了山羊,滑雪场上种植了桃林,近百岁的老媪唱着喝着,一个开发不成的故事,一个仍然交还给山野的故事。
在山野,我们安歇。空山不空,夜鸟匆匆。你带给我们的人生的是永远的温存与丰满。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