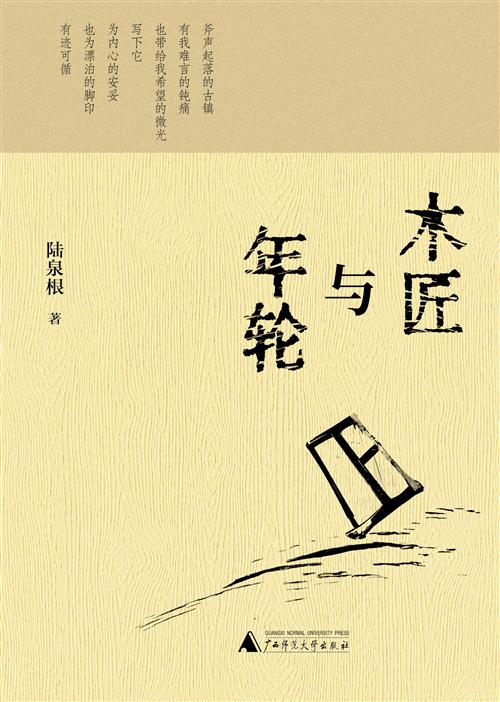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5-12-01
定 价:56.00
作 者:陆泉根 著
责 编:薛梅
图书分类: 中国现当代随笔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文学/中国现当代随笔
开本: 32
字数: 200 (千字)
页数: 2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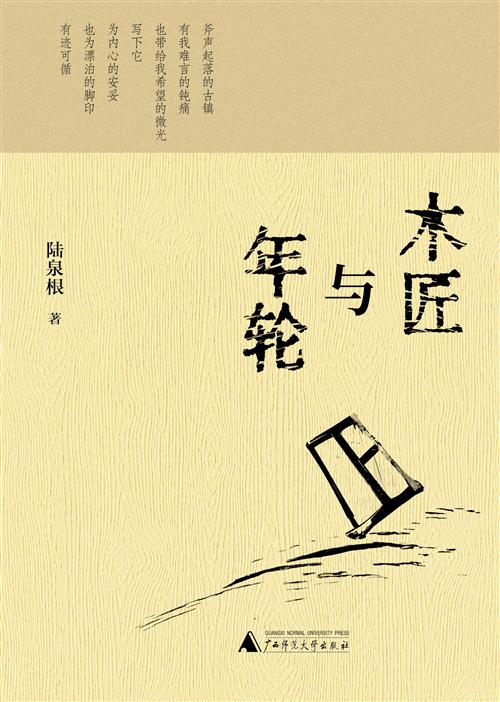
本书是作者在近几年创作的关于父亲和亲情的系列散文,共计74篇。
作者以江苏里下河古镇作为主要文学背景,以木匠父亲的人生轨迹为主线,其他人等为副线,每一篇独立成章,但相互之间又能彼此照应。父亲是一位普通的木匠,也是天下所有平凡父亲的典型代表,他不辞辛劳,默默耕耘一生,凭自己的手艺,撑起了整个家庭。作者以质朴、简洁的笔触,呈现事物最本真的模样,字里行间流露出悲悯情怀,还有历经沧桑后的练达与通透。他的文字,就如同他的父亲一般,有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构思巧妙,却不见丝毫刻意雕琢的匠气。
陆泉根,1965年出生,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散文作家,江苏省作协会员,泰州市海陵作协副主席。中国校园文学杂志首届签约作家。有散文多篇在《四川文学》《教师博览》发表或转载。曾获“东丽杯”孙犁散文奖、江苏省报纸副刊好作品评选多次获一等奖。出版过散文集《会唱歌的槐树》等。
第一辑:匠骨·年轮
1. 斧头
2. 五把修脚刀
3. 木匠老邹
4. 铁匠姓江
5. 半爿磨石
6. 碑
7. 老麻雀
8. 永不坍塌的草垛
9. 相木的父亲
10. 那辆老“永久”
11. 父亲的第三个徒弟
第二辑:炊烟·节气
12. 母亲这盏灯
13. 水缸
14、我们家的年
15. 槐香里的立夏
16. 金黄的端午
17、大暑记
18. 等一场好雨
19. 冬天是母亲的大考
20. 温暖的布鞋
21. 关于炊烟的修辞
22. 小雪无雪好腌菜
23. 冬至大如年
第三辑:巷陌·胎记
24. 西沟河,我曾经的游乐场
25. 老屋
26. 空巷
27. 运河那头是乡愁
28. 金码头
29. 串门
30. 屋檐下的年味
31. 古镇来了骗子
32. 三十一天的劳动课
33. 晚熟的苦楝树
34. 捉迷藏
35. 虹桥西巷的春天
第四辑:虫洞·光阴
36. 驼背女人
37. 摇摇晃晃的墙
38. 父亲有泪
39. 下扬州
40. 祥奶奶
41. 石头巷邹先生
42. 吴二剃头店
43. 忙先生
44. 老肖
45. 张三丰
46. 长得好好的树
47. 养鸭的二舅
48. 春天的等待
是父亲的斧头劈开了我们的永恸之诗
庞余亮
父亲生下了我们,也养活了我们。小时候,我们仰望父亲的背影,也崇拜父亲手中的工 具。握拿工具劳动的父亲是儿子心中的英雄。比如爱尔兰诗 人希尼笔下的父亲,手中永远有一把长柄铁锹——挖土豆的 父亲。
“……窗下,响起清脆刺耳的声音 / 铁锹正深深切入多 石的土地 / 我的父亲在挖掘,我往窗下看去 // 直到他紧绷的 臀部在苗圃间 / 低低弯下,又直起,二十年以来 / 这起伏的 节奏穿过马铃薯垄 / 他曾在那儿挖掘 // 粗糙的长筒靴稳踏在 铁锹上,长柄 / 紧贴着膝盖内侧结实地撬动 / 他根除高高的株干,雪亮的锹边深深插入土中 / 我们捡拾他撒出的新薯 / 爱它们在手中又凉又硬……”
同样的北半球,地球向东,一个湿漉漉的平原中央,也有一个养活一家七口的木匠父亲,握着工具整天埋头劳作。这就是作家陆泉根的父亲。他父亲手中的不是铁锹,而是一把充满温情的斧头。
“这把属于父亲的斧头比一般的斧头要重一些、大一些,单刃,斧刃锃亮,寒光逼人。斧柄是榉木的,木质坚硬,纹理细腻。除了父亲,任何人都不能碰这把斧头。”
“父”“斧”同根。自古以来,“斧”代表的就是父亲,他得持斧前行。父亲的这把斧头肯定和炉火通红的铁匠铺有关,父亲找到了最好的铁匠铺,叮嘱了这名好的铁匠师傅,不然怎么可能比其他的斧头重一些、大一些?还有斧柄,通晓树木质地的父亲肯定摸遍了平原的树林,这才选定了榉木。父亲知道生活的不容易,唯有好斧头的加持,才能去工厂、去扬州、去盐都,去任何艰苦的地方,蹚开老牛一般的生活之路。
“父亲用‘斫’‘刨’‘凿’‘锯’四个动词概括木匠最重 要的活计。一边说,一边演示。‘木匠斧头瓦匠刀’,所有的工具里,父亲最看重的自然是斧头,他最亲密的伙伴,几十年了,手柄非常的滑润养手。”
斧头是属于父亲的,也是属于儿子的。“斫”是木匠的基本动作,为了让木头成型,必须砍,必须削,用锋利的斧头去掉不必要的部分,留下可以成型的材料。父亲砍削木头,同时是在“砍削”儿子。比如儿子落榜,想做木匠,父亲让儿子来干木匠活计,直接用行动证明儿子不是做木匠的材。这样的教育简单但有效。“斫”是疼痛的,“被斫”也是疼痛的。但一个儿子的成熟必须被“斫”,“斫”去多余的部分,“斫”去柔弱的部分,从一个怯弱的落榜生到大学生,再到好教师、好作家,父亲的“斫”功不可没。
“父亲的工具箱是放不下所有好工具的,单刨子就有十几种,比如长刨、短光刨、斜沿刨、落底刨、外圆刨、内圆刨、槽刨、弯刨等。” 这是父亲的另一种工具——刨子。如果说斧头是凭硬功 夫的话,那么刨子需要的是巧功夫。“刨”是好木匠的另一个基本功,工具不再是斧头,而是木刨。《天工开物·锤锻》说“刨”是“磨砺嵌钢寸铁,露刃杪忽,斜出木口之面,所以平木”。在父亲使用刨子之后,那些被父亲用斧头处理过的粗糙木料变得驯服而光滑。因为木匠父亲的言传身教,陆泉根的文字里总是有结实的木纹和年轮,总是像刨花一般从刨眼里源源不断地吐出来,从来不浮躁,也从来不会让读者失望。
与行云流水的“刨”相比,“凿”的动作就需要专心致志,需要控制力度。“凿眼耗时多,技术性最强。父亲左手凿子,右手斧头,坐在要凿的木料上,一边凿一边掏,还不时用嘴吹出掏不出的小木屑,不停地比画着榫眼的大小。‘长木匠,短铁匠’,父亲说,榫眼不能凿大,木工活要的是留有余地,不能‘过’,过了,就无法补救。”这是父亲的“凿”。儿子的“凿”则体现在他的文字中。他的《老麻雀》《下扬州》里全是“凿”的典范,尤其是在《碑》中,父亲手中的凿子变成了更小的铁錾,而铁錾的上方依旧是父亲的斧头,但下面的材料变成了石头。
“第二天,父亲和第一缕阳光同时来到寺庙。父亲小心翼翼地把石板平放在一张旧桌上,下面用旧衣服垫实。父亲蹲下身子,按照石板上的字迹,左手握錾,右手持斧,轻轻地敲打,每錾一下,錾尖头就会腾起一股小的灰尘,父亲持錾的手也会自然地往后滑一下。錾好一个字,父亲会用嘴吹一下,用手摸一摸字痕,试着深浅。一会儿,父亲就感觉虎口有些麻酥酥的,眼睛也被腾起的烟雾弄得睁不开,他不得不停下来用手去揉。等錾好了一个人名,父亲便停下来,抽上口烟。母亲去看过一次,远远望着父亲的背影,大气也不敢喘。母亲告诉我,那段时间,父亲睡觉很不踏实,一天夜里居然叫了起来,把她吓了一跳。父亲做了个噩梦,梦到他 刻字时把石板錾崩了。”
这段文字实在太了不起了。父亲和儿子,木匠与斧头, 铁錾与石碑,全部融合在一起了,或者这样说,父亲的年轮和儿子的年轮就在这段文字中重叠成坚不可摧的宿命。我说过好多次,很多作家到了中年就向后退了,而陆泉根不一样,他一直在像苦行僧一样体悟,其根源就在老木匠的斧头里。一下又一下,他在承受,他在煎熬,他把自己的生活当成了木料,斫,刨,凿,锯,是的,还有锯,最为暴力的是锯。不管同不同意,命运总是在锯断我们的梦想、锯断我们的日子,所有的呐喊都会化为沉默的锯屑,但我们还是需要像苦楝树一样坚持,像陆泉根那样“纠缠住”自己的文学梦,不放弃,也不能放弃,即使再弯曲再粗鄙的生活,也能用“斫,刨,凿,锯”打造出我们的木器。
谁能想到父亲会生病呢?
谁能想到父亲会丢下他的斧头呢?
谁能想到父亲会用死亡劈开我们呢?
是的,父亲的动作中好像没有“劈”,但苦命的父亲还是劈下了。锯是暴力的,而父亲的斧头是沿着我们的缝隙劈下的。父亲真的不忍心,只是顺着我们悲伤的缝隙劈下,稍一用力,我们的悲伤就一分为二,一半是疼痛,一半是悔恨。于是,就有了陆泉根的《木匠与年轮》这本永恸之诗。
永恸之诗从来不会停止,唯有继续书写,才能找到那把时光深处的斧头,而木匠父亲,会在儿子的文字里重新诞生。
2025年 4月 3日,江苏泰州
(庞余亮,江苏兴化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鲁迅文学奖散文奖、柔刚诗歌奖、汉语双年诗歌奖、紫金山文学奖、孙犁散文双年奖、扬子江诗学奖、首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等。)
谁能想到父亲会生病呢?
谁能想到父亲会丢下他的斧头呢?
谁能想到父亲用死亡劈开我们呢?
永恸之诗从来不会停止,唯有继续书写,才能找到那把时光深处的斧头,而木匠父亲,会在儿子的文字里重新诞生。
——庞余亮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泰州市文联主席
一、一座文学的古镇,一位父亲的缩影
作者以江苏里下河古镇为纸,以木匠父亲的一生为墨,通过一个普通木匠的家庭史,映射中国社会数十年的变迁。这不仅是个人记忆的书写,更是一代人的集体生命印记——透过父亲的生计、家庭的日常、手艺的坚守与消逝,看见时代变迁中普通人的尊严与沉浮,兼具个人史与集体记忆的价值。
二、父爱如山,却静默如木
书中塑造了一位“不希望儿子成为自己”的中国式父亲形象。他的爱藏在刨花的弧度里,在深夜的灯影中,在那句始终未说出口的期许里。文中每一篇文字都质朴如木,情感却厚重如山。没有煽情,却处处是情;没有说理,却处处是人生。这种含蓄而深沉的亲情表达,直击现代人情感共鸣的深处——我们都在读懂父亲的路上,走了很远。
三、散文如年轮,独立而完整
四十八篇散文,篇篇独立成章,可随手翻阅;合则环环相扣,构成一部完整的生命史。作者巧妙运用悬念与细节,让日常琐事充满叙事魅力,在质朴文字中暗藏情感伏笔,使散文兼具故事性和可读性,突破传统散文平淡的刻板印象,读一篇是一幕人生剪影,读全集便见岁月长河。
四、工匠之笔写工匠之心
作者继承了父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却无刻意雕琢的匠气。他以质朴、简洁的笔触,呈现事物最本真的模样,字里行间流露出悲悯情怀,还有历经沧桑后的练达与通透。这不仅是对父亲的致敬,更是文学创作理念的践行——用最本真的方式,呈现最深刻的情感。
斧 头
斧头是木匠的门面。它的色泽、包浆和磨损痕迹能把主人的信息全部泄露出去:气力、手艺、勤劳程度。一个好木匠,少不了一把养手而又漂亮的斧头,就像父亲手上握着的这把。
这把属于父亲的斧头比一般的斧头要重一些、大一些,单刃,斧刃锃亮,寒光逼人。斧柄是榉木的,质地坚硬、纹理细腻。除了父亲,任何人都不能碰这把斧头。否则,不等父亲来收拾你,母亲会先把你骂得半死,磕坏可不是小事,一家七口,都指望这把斧头养活呢。 偶尔, 邻居借斧头劈柴, 母亲会断然拒绝——“木匠斧头瓦匠刀, 光棍的包裹姑娘的腰”, 父亲的斧头就是姑娘的腰,能随随便便让人摸吗?但熟人熟面,总有抹不开面子的时候——别慌,家里还有一把,看上去差不多,只是斧柄稍微短点,桑木的。这把斧头,功能比父亲那把差了一截:钝,吃力, 还容易卷口。我曾用桑树枝丫做过一个漂亮的弹弓,剁树枝时, 嫌斧头钝,拿来了父亲的那把——当然是偷偷地。母亲发现后惊慌失措,就像谁偷了她的钱似的。
父亲的斧头偶尔也会客串一下。每年腊月,家里总喜欢腌一个猪头,留着过年。煨之前,看着硕大的猪头,再瞅瞅那口小得可怜的铁锅,母亲常常无从下手,没了主意。这个时候, 就得请父亲。父亲会放下手里的活,扮演起一个行侠仗义的勇士,抡起斧头,“嘭”的一声,将猪头一分为二。
这把斧头之所以所向披靡,全在于淬火。这道比锻打还重 要的工艺,父亲的同事——古镇农具厂的徐铁匠做得最好,堪 称完美。徐铁匠淬火全凭经验和感觉,父亲这把斧头是他遗作中的上乘之品。父亲说,好马要配好鞍,木工手艺再好,没有一把顺手得力的斧头也不行。我经常看到,再顽固的木头疙瘩,只要下面放好垫板,父亲就能用他那把斧头把它分成想要的几个等分,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父亲的手掌厚大,手腕有力,好像就是为这把斧头而生。
斧头再好,也要保养。夏天,父亲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磨斧头:拿出中间明显凹下去的磨刀石,洒上点水,坐下来, 一手握着斧柄,一手压着斧身,来回磨着,动作轻盈娴熟。不时,父亲会腾出一只手来,给斧刃洒点水。差不多了,父亲用拇指轻轻试试斧刃,小心翼翼,然后迎着光亮,吹口气,左看右瞅,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最后用干抹布擦拭掉斧头上的水渍,把斧身插到稻草堆里——这样不容易生锈。
那个时候最让我高兴的莫过于有人家上梁。 对农村人来说,砌房子是和娶媳妇一样重要的事,立柱上梁,必须热闹一番,烧炷香磕个头,图个平安吉利。上梁是砌房漫长工期中的点睛之笔,只有威望高、手艺好的木匠才有资格被主家请去。父亲被人请去上梁时会带着那把斧头。他和另外一个木匠面对 面骑坐在房屋的脊梁上。两个“梁上君子”先是把房主装满馒头的小笆斗吊到屋梁上,稳好后,房主焚香点烛,两个木匠用斧头在梁上敲打起来,伴着节奏,一唱一和。
“良辰吉日把梁上。”
“荣华富贵万年长。”
“斧头朝上,敬祝主家万寿无疆。”
“斧头朝下,福气、财气一齐进家。”
鞭炮声响后,高潮到了,这是所有人喜欢的环节——抢馒头。其实抢的不只是馒头,还有米糕、糖果,讲究的人家甚至还有一分、二分的硬币。这时候的父亲,能随意调度下面望眼 欲穿的孩子。扔馒头需要掌握节奏,有时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有时则是铺天盖地、天女散花。偶尔,失了准星,馒头掉到烂泥地上,脏了,没有关系,会有人捡起来的,剥去外面一层, 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那种场面绝对热闹:争着、抢着、叫着、闹着,滚到一起,乱成一团;高兴、失望、狂喜、沮丧,什么表情都有。那时候我人小个矮,不太擅长抢馒头,常常空手而归。晚上,父亲回家,总会带给我们一些惊喜:几个馒头或者几颗糖。
进了腊月,父亲厂里的生意逐渐清淡,他转而忙着做寿材。寿材也称喜材,是给活人做的棺材。古镇很多健在的老人,喜欢未雨绸缪,早早把自己另一个世界的“房子”准备好,不给 子女增添麻烦。老人们是挑剔的——这辈子吃了苦,下辈子该享享清福,“住”的地方得讲究些。首先是木料。最好的自然是上等的杉木,树龄起码三十年,材质坚韧,不易腐烂。如果嫌杉木贵,就只能选择一些杂材。材料有了,剩下的就是备好酒菜,请一个手艺好且人品好的木匠。做一副寿材得花两三天的时间,慢工出细活。白身子做好后,棺材板之间的缝隙,要用生石灰、石膏、猪血等做成腻子,用刮刀披好,贴上麻布,再披一层腻子,最后刷上生漆,颜色是朱红或者墨黑。前前后后刷上七遍漆,棺材才明艳亮堂。
父亲一辈子做了多少口棺材,他没有说过,母亲也只知道个大概,八九十口的样子。这里面大部分是急就的——人去世 时或者快去世时现场制作,容不得木匠磨蹭。顺料、剖木、刨 削,大小、宽窄……必须一气呵成,最后还要在棺材的一头刻 上个大大的“福”字。好棺材有硬标准:大小合适,造型好看,木板光滑平整,板与板严丝合缝。
棺材做好,把死者放进去,棺材就成了灵柩,等待着的便是最后一个重要环节——封棺。 用粗大的铁钉把棺材盖钉牢。这个环节,是整个工程的结尾和高潮。封棺时会拿到额外的红 包。我目睹过父亲封棺的过程。封棺时,父亲拿着缠有红布条的斧头,“啪啪”狠狠地将大头铁钉钉进棺板里。
每次做完棺材,特别是寿材,回到家的父亲心情总有一些不难察觉的愉悦,当然不仅是因为有了收入。在古镇,一个木匠的最高荣誉,是有人请他做棺材,这代表认可和尊重。更何况,做的是棺材,“棺材棺材,升官发财”,多好的隐喻、多好的祝愿!父亲的情绪是会传染的,先是母亲,接着便是全家。那几天,家里总是充满笑声,其乐融融。
高中毕业,我准备死心塌地跟着父亲学这门手艺。我好奇地看着父亲的一套行头:斧头、刨子、凿子、墨斗……最让我 感兴趣的自然还是斧头,握在手中,虎虎生威,平添几分阳刚之气,难怪古镇人说:木匠是一世斧头三年刨。父亲笑笑,说:“别忙别忙,你先推推刨子吧。”父亲的工具箱里有不少刨子。 有一点必须交代一下,父亲的工具箱是放不下所有好工具的,但刨子就有十几种,比如长刨、短光刨、斜沿刨、落底刨、外圆刨、内圆刨、槽刨、弯刨等。父亲选了一个长刨,随后,他做了个示范:站好弓箭步,双手紧握木工刨的耳柄,呼呼地刨了起来,父亲的动作平稳协调,雄赳赳气昂昂的,似乎并不吃力。只一会儿,父亲的四周便落满了刨花。我如法炮制,怎奈刨子不太听话,艰涩,推不动,像一头不听话的牛。不一会儿,我便腰酸背痛,气喘吁吁。也许是用力不均,木板上坑坑洼洼,凹凸不平。望着我,父亲语重心长地说:“这需要用眼睛观察调整的,凡事都有方法、窍门,要琢磨、思考,怎么样,这还比学习辛苦吗?”我满面羞愧,无言以对。没过几天,我重返校园,开始了复读生涯,第二年如愿进了大学。
我结婚的时候,父亲将近六十,身体大不如前。他毅然决 定,利用业余时间给我打一套家具。节省开支不说,亲手做的 家具还结实、牢靠。父亲准备用杉木做料子,打一套组合式的。 戴起老花镜,父亲一手拿着木工笔,一手拿着《最新组合家具式样》,勾勾画画,研究得很是仔细,还不停征询我的意见。一个多月的起早贪黑,父亲完成了他的大作。考虑到我的宿舍狭小,父亲创造性地打了一个“截角橱”。这套家具,货真价实,外表是三合板,内膛全是实打实的杉木板。结婚后,我搬过三次家,这套家具完好无损。
退休后,为了生计,父亲又去扬州、盐都打工,带着那把斧头。那时是我们家最为困难的时期,我们的工资低,父亲的退休工资更低,只有几十元,三弟正在外面读书。后来,三弟考上研究生,做了大学教师,结婚生子,父亲才算真正喘了一口气,彻底退休。斧头也跟着他退居二线:劈木柴了。只是,用过以后,父亲依旧小心磨好,按时保养。每年春节,我们兄妹几个都到父母这里团聚一下。除了准备好吃的,父亲会劈很多木柴,以备煤炉引火之用。
偶尔一次身体检查,父亲被查出胃癌,我们兄妹几个慌成一团。确诊后,我们决定动手术——自然瞒着父亲。进入手术室前,护士要测量身体指标,想不到,身高超过一米七的父亲, 体重只有八十多斤。换病号服时,我看到了一个瘦骨嶙峋的父亲,我的眼泪簌簌不止。出院后,父亲更消瘦了,颧骨突出,身子佝偻,动作迟缓,看我的时候,就像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中的父亲:眼窝凹陷,目光深邃忧郁……
父亲的双手没有了缚鸡之力,走路要拄着拐棍,慢慢悠悠——毕竟也是七十好几的人了。那把斧头早已无人过问,被丢弃在厨房一角。因为缺乏保养,已锈迹斑斑,失却了往日的风采——谁都可以乱碰乱摸,母亲也不再说什么了。斧刃卷了,还豁了几个小口,青面獠牙一般,特别是边上裂了个口子。这个致命伤,明显是使用不当所致……
拖着病残之躯的父亲抓起斧头,细细端详,就像看着一件珍藏多年的古董,脸上露出遗憾的神色,喃喃自语:“可惜了,我这把斧头。”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