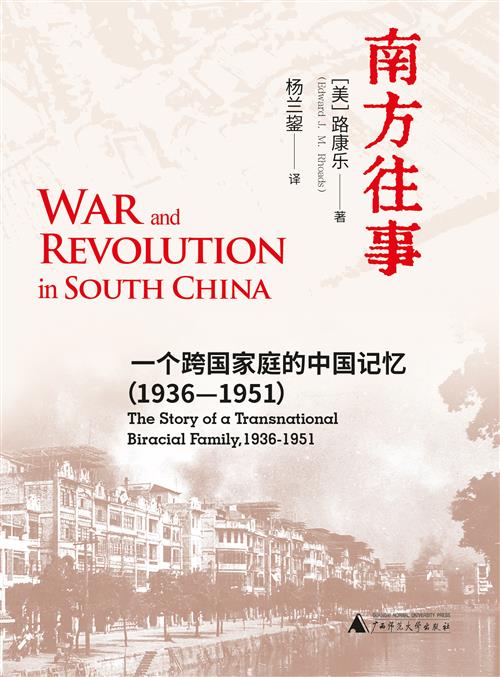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5-11-01
定 价:88.00
作 者:(美)路康乐 著;杨兰鋆 译
责 编:唐俊轩,唐娟
图书分类: 中国史
读者对象: 历史爱好者
上架建议: 历史/历史地理
开本: 32
字数: 250 (千字)
页数: 3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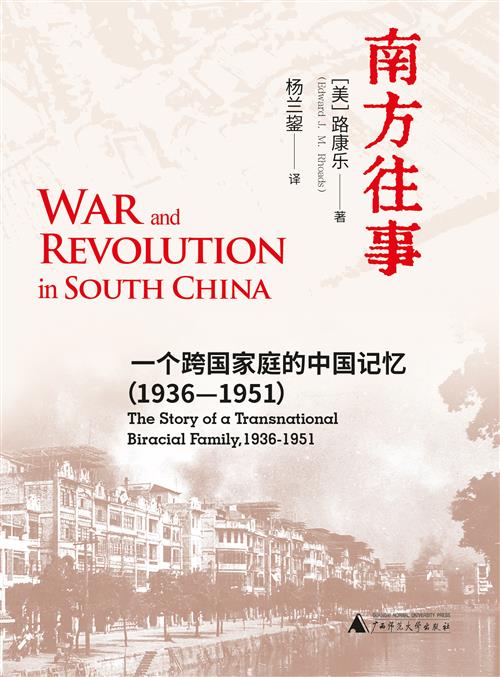
这是一部以微观视角叙述华南地区战争与革命历史的著作。美国学者路康乐以自身家族为蓝本,讲述了 1936年至1951年间,他的美国教授父亲与中国新女性母亲组成的跨国家庭,在华南大地历经战乱与变革的颠沛与坚守。
从广州岭南大学的初遇与结合,到香港沦陷后的骨肉分离,从粤北逃难的绝境求生,到重庆战时的短暂安定,再到战后重返广州等,这个家庭辗转多地,见证了广州轰炸、香港保卫战、岭南大学流亡办学等被忽略的华南战事。
书中既有个人命运的悲欢:母亲挣脱传统束缚的新女性姿态、父母跨国婚姻的坚守、与保姆阿何的相濡以沫;也有宏大历史的缩影:战争对普通人生活的撕裂、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等。个人记忆与文献史料交织,让冰冷的历史有了温度,展现了大时代下个体生命的坚韧与光芒。
路康乐(Edward J. M. Rhoads),1938年生于中国广州,中美混血。197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在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族群关系等方面著述颇丰,其著作《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获2002年列文森中国研究著作奖。
引 言 / 001
一、我的母亲 / 009
二、我的父亲 / 048
三、华南地区遭逢战事(1936—1941)/ 064
四、香港沦陷(1941—1943)/ 103
五、一家人的团聚(1943—1944)/ 146
六、在重庆任职于美国政府机构(1944—1945)/ 179
七、重返广州(1945—1948)/ 203
八、赴美休假(1948—1949)/ 234
九、共产党执政(1949—1951)/ 249
结 语/ 284
致 谢/ 296
引 言
1937 年 7 月, 全面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在华北地区爆发, 然后迅速向南蔓延至法属印度支那边境。 但除了个别著作——主要是麦克里(Macri)和朱平超(Zhu Pingch o)的作品,近十多年来多部抗战题材的英文出版物都将关注点放在了华北和华中战场, 基本忽略了华南地区的种种遭遇。 这些作品记录了华北平原和上海的战事、黄河堤坝溃决、河南大饥荒(1942—1943)、大批难民涌入武汉和重庆、 上海沦为“孤岛”、 重庆大轰炸、 华北地区的“焦土政策”,以及浙江的难民潮。华南地区的情况怎么样?本书中的“华南”指的是“岭南”,即分隔西江(珠江的干流)和长江的“南岭山脉以南”的地区。香港保卫战、广东大饥荒(1943—1944)、曲江成为广东省的战时省会、 香港亦沦为一座“孤岛”、 广州大轰炸, 以及华南地区的“焦土政策”和难民潮……上述作品对这些事件着墨不多, 或者说只字未提。
不仅如此,上述作品基本都属于宏观历史著作,它们通过鸟瞰的视角看待抗日战争,并对其进行粗略描述。除了拉里(Lary)、穆盛博(Muscolino)和萧邦齐(Schoppa)的作品,其他著作对战争给个人造成的影响都是轻描淡写的。正如柯博文(Coble)所观察到的,“虽然抗日战争中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但显然没有一部作品从叙事主体的视角来讲述这段过往。 在战争期间, 各式各样颠沛流离的故事就是战时中国复杂境况的写照”。相对于宏观史学,微观史学可能更有助于我们把握“战时中国的复杂境况”。
因此, 如果从华南地区和当地某个家庭的视角来审视抗日战争,我们将获益良多。 本书将回答如下两个问题, 以弥补当前学术研究的不足: 这场战争对华南地区有何影响?更具体地说, 它对华南当地的某个特定家庭造成了哪些影响?
我要讲述的是我全家人的经历。1938 年,我在广州出生,在华南地区度过了前13年的光阴(在此期间我分别在重庆和美国生活了一年)。我母亲是中国人,出身富贵之家,接受过中学教育,是一名训练有素的速记员和打字员;我父亲是美国人,职业是大学教授。我们一家三口——再加上保姆阿何——在 1936 年至 1951 年之间的经历就是柯博文所说的“战时中国的复杂境况”的缩影。 这是一段以自下而上的视角讲述的历史。 虽然它只是一部微观历史(具体到了当地的街道地址),但它依然处于宏观历史的框架之内。 我们全家人在战争期间的经历未必是典型经历,但也具有一定代表性。
我的出生和成长都带有偶然性, 这是我想去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因。 我对华南地区尤为感兴趣, 所以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关于辛亥革命的个案研究。 虽然我一直对我早年的华人身份很好奇, 但和很多孩子一样, 我的好奇心还没有重到去追问我父母的地步, 而且他们两个也很少谈论自己的过去。 比如说, 从来没有人对我和妹妹提起我母亲在嫁给父亲之前曾经离过婚。 最近有位研究家族史的历史学家写道:“也许所有的父亲(母亲也是如此)都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大概所有的家庭都藏着秘密。 幸运的话, 我们还能在为时未晚的时候对自己的家庭一探究竟。回忆在堆积,而生命在流逝。当我们提出问题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可以回答了。”大约在 15 年前,那时我父母已经去世多年,而我也已经从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退休,我开始有条不紊地梳理他们(同时还有我自己)在中国的经历。 当时的我只了解基本情况,对细节并不清楚。我父亲来自美国费城(Philadelphia),1936 年远赴中国, 在广州的岭南大学任教。 他在那里结识了我母亲——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两人结了婚,然后在1938年生下了我。(虽然我父亲任职的学校是中国十余所“基督教”大学之一,但他本人从未当过传教士, 所以严格来说, 我从来都不是“传教士的孩子”。)在我出生后不久, 广州遭到日军侵占, 我们全家和岭南大学一起迁到了香港。然而三年后,香港也被日军占领了,身为敌国侨民的父亲被关进了当地的俘虏收容所,而母亲带着我前往粤北地区(广东省北部)避难。后来,我父亲被遣返回了美国,但他又找准时机来到了粤北与我和母亲团聚。不久之后,我们再次踏上了逃亡之路,这次的目的地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重庆, 父亲在当地的美国战争情报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美国的宣传机构——找到了一份工作。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我们回到了广州和岭南大学。1948年至1949年,也就是我父亲休假(即学术休假 )的这一年, 我们全家一直都待在费城。此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接续上演,而共产党已经胜利在望。 在其他外国人纷纷逃离中国的时候, 我们却回来了。 然而在一年多之后的 1951 年 2 月, 我们再一次被迫离开, 而这一别便是永远。我们全家不止一次两次地被迫转移,而是多达四次,分别在 1938 年、1942 年、1944 年和 1951 年。
成文史依靠的是史料来源。 哪些资料可以更加全面地讲述我们一家在中国的经历?很可惜, 这样的资料不多。 我父母可能写过一些东西,记录他们的战时经历,比如家书,但是保留下来的寥寥无几。既没有书面或其他形式的回忆录, 也没有家族档案。 勉强算作路家家族档案的东西包括父亲的美国护照、 母亲的中国护照、 父亲的保险单、母亲和前夫的离婚协议书、父母的结婚证、我和妹妹的出生证明、我的受洗证明、 母亲的美国签证申请表、 我在中国学校的几份成绩单、几张家庭照片,还有费城一座墓地的契约(我父母安葬于此)。
虽然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期, 我曾和父母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 但我自己没办法提供丰富的信息。1951 年我们全家离开中国的时候,我才13岁。可能有人觉得,那个年纪的我应该能记得不少事情,尤其是我们在中国度过的最后一段时光。但或许是因为我们在那 13 年里被迫四处搬家,我的记忆就是一团乱麻。一方面,我无法确定某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了。比方说,1943 年,我父亲在离家一年半后出现在了粤北, 我觉得我当时是躲在床下的。 可这是真的吗?答案无从知晓。另一方面,我现在知道了一些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但我完全想不起来。 比如我第一次踏进校门的情景, 这通常是人生中难以忘却的回忆。 那是在 1944 年的秋天, 我们全家刚到重庆不久,6 岁的我进入只招收男生的启明小学就读。 我之所以知道这件事, 仅仅是因为我在为数不多的家族档案中发现了我在这所学校的成绩单。 但即便如此,我对这件事还是没什么印象。总之,这本书绝对不是一部回忆录,而是一部基于文献资料的史书,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既然我本人记得的事情不多,家族档案也寥寥无几,那我怎么可能将我全家在战时中国的经历撰写成书?一般来说, 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 一个人能对过去了解多少?对于这种情况, 其实有不少解决办法。 就像从事任何历史研究一样, 我去查阅了其他文献。 对我而言,首要和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就是岭南大学校董会的档案。 正是这家机构——总部位于纽约——聘请我父亲前往岭南大学任教, 而且一直是他在华期间的雇主(唯独有一年例外)。这些档案的纸质原件都保存在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收藏了一套缩微胶卷副本)。 另一个重要来源是位于马里兰州学院公园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分馆, 美国战争情报局的档案就保存在这里。 在抗战结束前后,我父亲曾在该情报局的驻华机构工作了两年。 此外, 我还在各大学图书馆里找到了父亲生前同事的资料, 其中既包括他在岭南大学共事的嘉惠霖(William W. Cadbury)、包令留(Henry Brownell)和白约翰(Gilbert Baker)等知名人士,也包括他在战争情报局的同事克里斯托弗·兰德(Christopher Rand)、威廉·L. 霍兰(William L. Holland)和埃弗里特·霍金斯(Everett Hawkins)。其他机构也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档案资料, 比如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该馆保存有近代中国的海关档案)、英国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费城的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和长老会历史学会, 以及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 关于我母亲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我询问了我的舅舅们、几位表兄妹和一位外甥,还查阅了美国移民局西雅图和纽约分局的档案,从中了解到不少信息。
在完成档案研究之后, 我对全家人在战时中国的经历有了更多了解, 远远不是刚启动这项研究时的略有所知。 这是不是说我对想了解的情况已经成竹在胸?不完全是。 我还不清楚为什么我父亲一开始就选择去中国。对于我母亲的第一任丈夫,我也是仅知其名而已。1942年初, 我母亲带着年仅 4 岁的我和保姆阿何从日本占领下的香港回到粤北, 我不知道母亲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我粗略勾画了三条其他难民选择的逃亡路线, 但我不知道我们家选择的是哪条路线。 在抵达粤北后, 母亲很快就在曲江县海关找到了一份工作, 但我不知道在父母分隔两地的那一年半里,我和母亲到底住在什么地方。遗憾的是,我对家里的“阿妈”(即保姆)阿何了解不多,尽管她在 1939 年(也可能是1942 年)来到香港和我们一起生活后就成了我们家的一分子。 由于缺少家族档案, 我对父母在经历过这么多磨难后的心路历程几乎一无所知。我有信心重构他们的生活,却没办法再现他们的所思所想。
最后要说的是,我从这项研究中收获了两大感悟。其一,在抗战期间, 华南地区动荡不安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华北和华中地区。 其二,我对母亲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在这部以战争为背景的家族史中, 我的母亲——作为中国新女性中的一员——书写了重要篇章。 下面讲述的既是她的故事,也是我父亲的故事。
作者路康乐以自身家族为切口,将华南地区的抗战与动荡,浓缩进一个中美跨国家庭的辗转历程中,每一段经历都扎根于真实史料与个人记忆,让宏大历史有了具象的温度。
书中既有对广州轰炸、香港沦陷、岭南大学流亡办学等被忽略史实的还原,也有对母亲作为“新女性”的坚韧、跨国婚姻的坚守、与保姆阿何相濡以沫的细腻描摹。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交织,文献档案与家族故事互证,既避开了宏观史学的空泛,又挣脱了私人回忆录的局限,为读者打开了理解战时华南的全新窗口,是一部兼具历史深度与情感厚度的作品。
华南地区遭逢战事(节选)
我的降生让父母更加操劳。1938 年 1 月 7 日, 正好是卢沟桥事变和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六个月后,我在岭南大学的附属医院出生。为我接生的是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岭南大学附属医院担任主治医生的陈元觉(Chan Yuen Kok,1903—1942)。我的中文名字“路康乐”意为“健康快乐”, 而且和岭南大学所在的康乐村同名。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英文名字是“Edward John Michael”(爱德华·约翰·迈克尔)。九个月后的 1938 年 10 月 9 日,白约翰为我施洗。这位圣公会传教士比我父亲早几个月来到岭南大学, 后来在 1966 年至 1980 年期间被选为香港和澳门的主教。 白约翰是我的教父(sponsor), 我们在模范村的邻居贺辅民教授和他的太太威妮弗雷德(Winifred,1898—1986)是我的教父母。
在我受洗后的第三天,日军加大对广州的空袭,并在华南加大侵略力度。10 月 12 日,日军第二十一军在香港东北部的湃亚士湾(Bias Bay, 即今天的大亚湾)登陆, 不到十天就冲进了广州城内。 10 月21 日这一天, 广州军民几乎“在 24 小时内全部撤离”。(广州的情况和武汉大不相同。 华中地区的武汉市由三个城区组成, 日军在历经四个月的激战后才将三个城区同时占领。)国民党广东军政首领余汉谋——接替陈济棠统揽广东党政军大权——不战而撤,这或许是蒋介石用空间换时间的大战略的一部分。余汉谋将军和吴铁城省长遭到了广泛批评。 由于二人的名字都语带双关, 于是余汉谋被人们嘲讽为“无谋”,而吴铁城则是“失城”。国民党军队沿着北江撤退到了广东北部。
“广州城在一场捍卫荣誉的大火中毁于一旦,”英美烟草集团(British American Tobacco)的 代 理 商 理 查 德·P. 多 布 森(Richard P.Dobson)这样描述道,“在沙基涌堤岸, 正对着沙面岛的一排店铺遭到蓄意纵火……事件的高潮是黄沙站的一座弹药库发生爆炸,震碎了沙面岛上的大部分窗户, 将多座房屋从地基上连根拔起。”据 1939 年春在广州采访的记者哈利特·阿本德(Hallett Abend)说,“……日军摧毁了广州这座伟大而繁荣的城市……” 在这场浩劫中,珠江大桥依然屹立不倒,基本完好无损。
此时岭南大学的新学年已进入第三周, 李应林也已经就任新一届校长。在得知日军占领广州之后,岭南大学立即宣布停课,通知学生们回家。与此同时,在美国领事馆的紧急建议下,香雅各顾问把西方教职工的妻儿——包括我母亲和她十个月大的婴儿——在珠江航运关停前送到了香港。 这是我们全家第一次背井离乡。 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 我们又举家逃亡了三次。 在 10 月 13 日抵港之后, 母亲带着我——同行者中至少有一位岭南大学的工作人员,她就是美国人艾丽斯·乔伊·(麦克唐纳)坎贝尔(Alice Joy [MacDonald] Campbell)——前往香港岛湾仔区的六国酒店(Luk Kwok Hotel)临时避难。和沙面岛一样, 英属香港当时还不是日本侵略的目标。 岭南大学的大部分中国教师也都逃到了香港, 在那里躲避战乱的 50 万中国难民中就有他们的身影。 我母亲的父亲颜向初和他的两房妻室,她的姐姐志坚及其家人,也都身处其中。
在听取当地华人校董会的建议后, 纽约校董会马上收回了岭南校区的所有权, 防止它被侵略者占领, 因为当时美国也尚未与日本开战。 香雅各顾问在汇报中表示, 他正安排人员在校内升起 12 面美国国旗。 这样一来, 就算日军火速占领了广州其他地区, 他们也不敢进入岭南大学(沙面岛就是例证)。 其实岭南大学可以像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一样在中国的被占领区继续运转 ,但它没有这么做, 而是将教学活动转移到了英属香港, 尽管它在广州的实体校区依然存在。
香雅各顾问、 大部分西方教师, 连同几名中国员工, 都选择留下来守护康乐校区, 防止它遭到破坏。 科比特(Corbett)在岭南大学的官方史中写道:“历史学家包令留负责照看奶牛、 猪、 水牛和山羊。 数学家麦丹路(Wilfred E. MacDonald,1881—1943)经营着一家园艺店,销售水果、蔬菜、牛奶和黄油。物理学家聂雅德(Arthur R.Knipp,1887—1974)和化学家富伦(Henry Frank,1902—1990)一起管理发电厂, 保证校区的照明和供水。”岭南大学教职工还在校内搭建了一个难民营——广州的五大救助中心之一。 香雅各在 1938 年 11月中旬的汇报中说,“我们校内有 6500 名常驻难民”,还有“300 人在北门外苦苦哀求我们收留”。 尽管困难重重, 西方教师和他们的配偶还是想方设法让难民营维持了一年多,直到 1940 年 1 月底才关闭。
留守在广州的西方教师中并没有我父亲,因为香雅各顾问认定他“在香港(比在广州)更有价值”。就这样,在和我们母子分别了近十天之后,我父亲来到香港的六国酒店和我们团聚。 和他一起赴港的还有西方语言文学系的三位同事。他们将和中国教师共同努力,重启岭南大学的教学活动。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广东省政府批准,李应林校长与香港大学展开磋商, 希望借用港大的部分教学设施。11 月 14日,在广州校区停课约一个月后,岭南大学在香港恢复办学,此时共有482 名学生, 只比以前减少了 20%, 因为大多数岭南大学学子在香港都有亲戚。 起初,被派往香港的西方教师几乎全部来自西方语言文学系。在接下来的 1939—1940 学年,应李校长加强师资力量的请求,更多留在广州的西方教授——包括包令留(历史)、富伦(化学)和聂雅德(物理)——都被调往香港,而香雅各顾问仍然留在广州。
香港沦陷(节选)
我母亲和我,还有保姆阿何,也在这支返乡大军之中。我们离开了香港,可我父亲还在赤柱拘留营里备受煎熬。香雅各顾问——他本人被关押在广州的拘留营里——在 1942 年 3 月 29 日的一封信中写道:“路太太要带着幼子返回内地……有人在一周前就告诉我了。” 如前所述,多亏了温策尔·布朗的那名学生帮我母亲带话,我父亲才知道我们已经不在香港了。 我们可能是与我外祖父和姨妈志坚同期离港的,说不定是大家一起结伴而行。
但和他们不同的是,我们在内地的最终目的地不是已经沦陷的广州,而是广东省北部,即粤北。虽然日军已经占领了广州和香港,但由于兵力短缺,他们无法将控制范围扩大到这两座城市和珠江三角洲以外的地方。因此,撤退的中国军队得以在粤北地区重新集结、巩固实力。 粤北中部的曲江县(现在是韶关市的一个区)被定为广东省战时省会和第七战区总部,余汉谋出任第七战区司令——尽管余汉谋因为将广州拱手让给日军而备受批评,但他身为蒋介石的心腹,并没有受到惩罚。包括岭南大学在内的多所学校也陆续搬到了曲江。粤北是非沦陷区的一部分,也是广东抗战的“大后方”。因此,一些离开香港的中国人并没有回老家,而是来到了曲江。尤其是莘莘学子,国民政府不但资助他们的路费和学费,还免除了他们的兵役。
根据岭南大学和港大多名学生的回忆,从香港到曲江主要有三条逃难路线。第一条是先乘船到广州湾(湛江市的旧称),然后经陆路先后到达广西桂林和湖南衡阳。例如,陈香梅(Anna Chan,1925—2018),也就是后来的陈纳德太太(Mrs. Claire Chennault),就选择了这条迂回曲折的路线。 当时陈香梅还是香港岭南大学二年级的学生。1942 年5月, 在拿到出境许可证之后, 她和几位姐妹首先乘坐渡轮前往澳门(作为中立国葡萄牙的统治区域,澳门从未被日本占领),然后换乘另一艘船去了广州湾——位于法属印度支那的西南海岸。广州湾是法国的“租借地”, 它在名义上听命于维希法国当局, 所以在 1943 年 2 月之前并没有被日本占领。广州湾的外围地区就是非占领区。陈香梅和她的姐妹们分乘几顶轿子被抬到了广西玉林——其他难民都是步行,接下来可能和其他人一样搭乘卡车或轮船去了柳州,在那里坐上了湘桂线(衡阳—桂林)列车,从桂林出发奔赴衡阳。最后,她们在衡阳转乘粤汉线列车,向南开往曲江。在抗战期间,曲江是粤汉线南段的终点站。
第二条是途经广东惠州的陆上逃难路线。1942 年夏, 香港大学大四学生黄丽松(Rayson Huang)和弟弟黄励文(Raymond Huang)选的就是这条路线。两人先是乘坐大巴车前往香港新界东北部边界的沙头角,然后乘船穿过大鹏湾到达对岸的一个村子。他们在这里碰到了一名付费导游, 跟着他徒步穿过一片盗匪出没的“无人区”, 来到了惠阳的淡水镇,即现在的淡水街道,当地驻扎着一支国民党军队。一到淡水,就表示他们踏上了非占领区的土地。他们从那里搭乘一艘小型内河船来到惠州——粤港澳地区的枢纽城市,然后换乘另一艘内河船沿东江到达老隆镇。最后,两人上了一辆烧木炭驱动的卡车,在老隆镇内的公路上行驶了四五天后终于抵达了曲江——香港政府救济处的所在地。 从老隆到曲江的这条公路很可能是在军阀陈济棠主政时期修建的。
按照缪丽尔·洛克伍德(Muriel Lockwood,1899—1991)——基督教青年会秘书骆爱华的妻子——的说法,除了广州湾和东江这两条路线, 其实还有从香港到曲江的第三条逃难路线, 即“广州路线”。曲江处在广州以北约 145 英里的位置, 而日军的控制范围还不到这个距离的一半。虽然从广州到曲江的铁路已经被撤退的国民党军队破坏了, 但水路(北江)和公路这两种路线依然可行, 都可以到达广东战时省会曲江。
我不知道母亲带着我和阿何是如何从香港来到曲江的。 香雅各本人给出了两个不同的中转点。 他在 1942 年 4 月 5 日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路太太带着幼子途经广州湾进入了内地”, 然而他在一个星期前写的却是我们“会从江门中转,前往内地”。 江门市位于珠江三角洲,与惠州和东江都相距遥远。这说明我们很可能走的是“广州路线”。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许我们是和我外祖父、姨妈志坚以及他们的家人结伴而行的,大家一起从香港来到广州,然后他们直接留在了广州,只有我们三人继续北上,前往曲江。一年后,也就是 1943 年,时年 13 岁的表哥罗文被亲戚(或朋友)从广州带到了曲江,在非沦陷区的一所中学读高中。 他父母本打算去曲江和他团聚, 但不久之后,“广州到粤北的道路被封”, 夫妻二人只好带着另外两个孩子去了澳门。十几岁的罗文只能孤身一人在粤北度过余下的战争岁月。
根据历史学家管沛德(Peter Cunich)的讲述,逃离香港的人们“要在路上奔波几个星期,还得面对各种危险。难民们只能把财物装进手提箱或背包里带走”。 有些人“不得不长途跋涉, 即便能找到旅馆过夜,也得忍受房间里的蚊子、臭虫等害虫”。 这一路上的大事小情基本都是我母亲一个人在张罗,身边还有一个年幼的孩子要操心,好在阿何帮了不少忙。 她历尽磨难才带着我们来到了曲江。4 月 3 日,身在曲江的骆爱华在汇报中提到, 在“抵达这里”的岭南大学教职工中,有“一位英语教授的妻子康特里·斯特里特女士(Mrs. Country Street)”,并补充说,“我可能把她的名字拼错了。但我说的这位女士还带着她 4 岁的儿子”。 骆爱华确实把我父亲的名字弄错了——把路考活(Rhoads)说成了斯特里特(Street), 但他显然就是在说我们母子俩。 如果说我们是在 3 月中下旬从香港出发的,就像香雅各早前提到的,我们要花两三个星期才能到达曲江,那么时间刚好相符。我们起初是从广州逃到香港避难, 可如今我们再一次沦为了难民; 当然,我父亲被遣返回美国时,和我们的情况也差不多。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