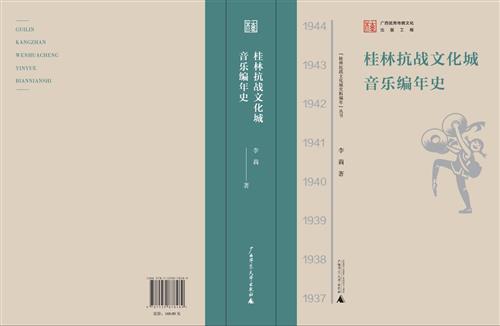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5-08-01
定 价:168.00
作 者:李莉 著
责 编:魏东,伍忠莲,程卫平
图书分类: 专业史
读者对象: 文化研究者
上架建议: 历史/专业史
开本: 16开
字数: 550 (千字)
页数: 6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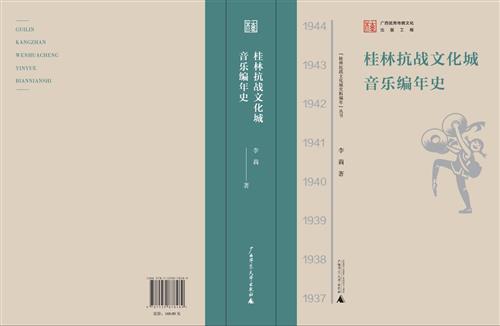
作者爬梳剔抉桂林抗战音乐史料,运用音乐史学的实证和思辨性方法论,结合社会学、政治学等研究视域,以大历史、音乐史发展状况为背景,以桂林抗战音乐史事件为核心论点,以及相关的背景材料,进行编年史排序。
书稿以编年史书写体例,以事件为标题,以重要文献为导入,对该事件进行描述和历史解读,结语部分对桂林抗战音乐史的发展做整体分期总结,并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桂林抗战音乐发展的重要意义,体现出抗日统一战线在桂林音乐界的形成与贯彻,是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和策略在桂林抗战音乐运动中的成功实施。而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和策略在桂林文艺界的实施,对桂林抗战音乐运动的蓬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李莉,女,博士,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泰国宣素那他皇家大学博士导师。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和艺术史论。代表著作有《区域音乐史的历史回首》《广西民国音乐史研究》《广西音乐文化的历史研究》等。代表论文有《“国共合作”中的武汉抗战音乐》《1938:音乐家在武汉的分歧与对峙——兼及刘雪庵的活动》《从罗泊湾汉墓音乐文物看南越国礼乐》《清代湖北府县释奠礼用乐的历史变迁》等。
目录
绪论 4
一、选题缘起 4
二、研究现状 5
三、文献、思路与方法 8
第一章 抗战音乐在广西萌生和左翼余波 1931 年—1937 年
第二章 桂林抗战音乐兴起和歌曲《故乡》诞生 1937 年7 月—1938 年
第三章 轰炸中的桂林音乐生活和“三厅”文艺兵 1939 年
第四章 抗战音乐蓬勃发展和《黄河大合唱》唱响桂林 1940 年
第五章 皖南事变后桂林音乐转变和马思聪演奏会 1941 年
第六章 桂林音乐多元走向和歌曲《你这个坏东西》 1942 年
第七章 桂林音乐会西风盛行和新歌剧讨论 1943 年
第八章 桂林文化城演出落幕和伟大的西南剧展 1944 年—1945 年
结语 430
一、抗战音乐文化的萌生和早期发展(1931-1938) 430
二、“国共合作”中抗战音乐的多元繁荣发展(1939-1940) 433
三、“国共合作”破裂音乐生活的艺术化倾向(1941-1942) 436
四、抗战音乐的由盛而衰(1943-1944) 439
五、中国共产党对桂林抗战音乐的领导和推动 441
参考文献 458
绪论
一、选题缘起
抗战音乐文化研究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20世纪红色音乐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当代学者李诗原教授对抗战音乐有这样的一个总结:“第一,抗战音乐的主体是中共抗日武装及其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而非前期国统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的音乐。第二,抗战音乐主要是在中共组织领导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主流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而非那种表达民族精神、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形成的抗战音乐,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体性、连贯性。”[ ]这是我们研究中国抗战音乐文化应当有的正确认识态度。由于近现代中国政体的复杂性,在对于抗战音乐文化的研究中往往按照区域又分为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等不同政治背景下的区域空间。这些区域空间中体现了不同性质的音乐文化特征。
在抗战音乐文化的整体表现形态上,抗战歌咏活动是具有共性特征的基本主流的文化现象。歌曲和歌唱是艺术的表层表现形式,而从歌咏事件的产生和歌咏活动形成规模时,则不可缺乏社会各方组织的力量,这些组织都在活动运动中产生着不同的作用和价值。以群众为核心的歌咏活动,人民是最基础的力量,而以专业音乐人发起的音乐活动,其目的还是唤醒人民,参与者还是以普罗大众为主。因此,人民在抗战歌咏活动中是核心,只有真正唤起民众的积极参与,歌咏才能从星星之火发展至磅礴的运动。围绕着抗战为主题的音乐事件,除了人民参与的群众歌咏、专业歌咏和各种音乐会活动,还包括为了音乐蓬勃发展而进行的音乐创作和推广工作,这样必然涉及到音乐家的活动。音乐家的活动除了涉及创作、推广音乐作品、参与音乐活动,还包括艺术家们拿起笔进行涉及抗战音乐活动的报道、评价和思想阐述,由此就上升到思想的层面和思潮的兴起。正确的思想舆论对于抗战音乐的发展方向有着积极的影响,有时一个刊物而树立的话语权,不比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歌咏活动影响力小。这个力量可从《新音乐月刊》为代表的抗战音乐刊物的出版发行量和影响力方面得到充分的证明。此外,抗战时期的音乐教育事业,无论是解放区,还是国统区,都不可能离开以抗战音乐文化实践为主的教育工作和学生活动。而一切围绕人的运转事件,青年往往是核心,他们形成的各种团体为抗战做贡献;思想的力量也在其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并指导着他们的行为和方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统区产生深远影响,并且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实施各种举措对国统区的抗战音乐文化进行推动影响,乃至公开和秘密的领导工作。因此,国统区、沦陷区也存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艺工作,以人或事件引导着国统区抗战文艺的发展。综上所述,抗战音乐研究是内涵丰富的,对它的考察必须以音乐史学为基础,结合社会学、美学、政治学等多维视域,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大课题。
近现代,尤其在抗战时期广西在中国有着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以新桂系为代表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崛起,一方面广西省政府于30年代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的改良,使得原本落后的广西逐渐走向强大。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先后沦陷,国统区尤其以西南重庆、桂林、昆明等城市成为了文化发展的重心地区。由于广西新桂系奉行相对开明的政治政策,桂林逐渐成为了一个文化发展的中心,一时有“北有延安,南有桂林”的抗战文化城之说。近年来笔者也尝试对于桂林的抗战音乐活动、文化城的音乐家、音乐刊物和音乐书籍、报刊中的抗战音乐史料等进行微观的研究。在前辈学者厚重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虽有所进展,但是一直未能有真正实质意义的突破。期间,加之课题史料因为桂林图书馆搬迁、以及民国文献的密封保存等诸多因素,而造成部分史料已经无法翻阅,以至于对于桂林抗战音乐史研究进展缓慢。然而,科研工作必须有一定时期有相关阶段的呈现,因此,虽未能完满解决各种困难,还是在现有基础上对桂林抗战音乐史按照既定计划进行编年史的一个呈现。
二、研究现状
桂林抗战音乐研究在学界有着丰富的成果,其中主要体现在广西地区理论家的执着耕耘,代表研究者主要有李建平、冯明洋、王小昆、陆铿荣、陆璎、笔者等,以及音乐史学家戴鹏海。1988年,研究桂林抗战文艺的代表学者李建平研究员首先发表了《抗战时期桂林进步音乐活动述评》一文[ ],开启了广西地方学界对于桂林抗战音乐专题研究的序幕,文中内容也成为其后续完成的著作《桂林抗战文艺史》中的一节。文艺理论界对于桂林抗战文化的关注,促进了音乐理论界对于桂林抗战音乐专题研究的关注。对于抗战音乐研究的热忱,或也被另一个音乐学者的学术活动进一步所引发——20世纪90年代初,音乐史学家戴鹏海先生为撰写《陆华柏音乐年谱》频繁赴南宁。音乐史学严谨学风和方法论——“用史料说话”,对后来以半生生命热情从事“桂林抗战音乐研究”的王小昆,有着深远启迪。[ ]
20世纪90年代末,广西艺术学院王小昆[ ]为负责人、桂林艺术学校陆铿荣为核心成员的课题组,开始了对桂林抗战音乐的深入研究。后陆老师不幸去世,工作由王小昆继续。他一方面爬梳历史文献中的音乐史料,一方面抢救式挖掘口述史料,赴各地采访历史当事人,如薛良、林路、马卫之、廖行健、陆华柏、甘宗容、甄伯蔚、罗惠南等,并陆续在国内重要音乐刊物上发表了系列论文。[ ]2005年王小昆教授出版了著作《桂林抗战音乐文化研究》、2008年编著桂林文史资料第五十三辑《抗战时期桂林音乐文化活动》[ ],也恰是那年冬季,我与王小昆老师初次见面,而不久后,王老师因病,永远停住了研究的脚步。此外,王小昆相关成果多也分别录入文艺理论界编辑的《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8卷。[ ]
冯明洋教授是另一位对桂林抗战音乐文化研究有着重要贡献的专家学者。冯教授是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学者、中国音乐史学家,也是倡导音乐文化学的代表人。[ ]在桂林抗战音乐领域,他也是最早研究的专家。原广西艺术学院讲授音乐史课的冯明洋老师,从1960年任课时就重视乡土教材建设,曾组织师生采访本院老音乐家中桂林抗战音乐运动的亲历者满谦子、陆华柏、李志曙、甄伯蔚等,并为他们立传。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中国音乐史学会先后成立,冯明洋当选为两会理事,这些珍贵史料才有机会油印集册,在全国音乐专业会议上散发。1984年,中国剧协、音协及其广西、广东分会在桂林举办“西南剧展40周年纪念”活动前夕,广西人民出版社文艺部总编刘铭涛特邀广艺丘振声老师,率先编辑出版了《西南剧展》一书到会赠发。同时邀冯一同前往采访与会老艺术家,计划编辑出版一套“桂林文化城丛书”,其中的《音乐卷》委托冯明洋负责。从大会获取大量信息和历史线索后,冯老师及时组织了由他任主编的编委会,成员有广西音协的李佳向、崔宪,桂林图书馆唐国英,冯老师的史论专业学生陈洛和孙巍。他们充分利用教学实践和寒暑假时间,遍访桂林、武汉、重庆、上海、南京、北京、广州、香港等地健在的老艺术家和当地图书、档案、文史馆站,广泛收集文图音像书谱资料,奋战至20世纪90年代初,以八年抗战精神整理出书稿百万余字,写成《桂林抗战音乐运动述论》初稿八万余字。但因出版社刘铭涛的病逝,丛书计划无以为继。试投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虽接受但要求大删大改近半。删改后却又因经费问题多年无着。无奈拖至21世纪初,论文初稿得以在《中国音乐学》2002年发表。2015年删改近半的书稿《浩歌》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历经三十年磨难终成正果,学术研究确实贵在坚持。[ ]
时至今日,两位先生对于桂林抗战音乐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至今无人超越。王小昆教授几乎是将全面学术生命热情倾注于桂林抗战音乐史研究,代表著作论文集《桂林抗战音乐文化研究》。冯明洋老师涉及多学科重要学术研究,《浩歌》以“浩歌声里请长缨——桂林抗战音乐运动”长文为核心,以收录历史文献为特色,并兼有唐国英先生编纂的“大事记与社团简介”。二位学者对这一课题所做的筚路蓝缕的功勋,是我们后辈学子学习的榜样,他们的成果也一直指引着后续的研究者。遗憾的是,二位先生尚未完成桂林抗战音乐史完整“史书”的书写工作。
陆璎编辑,是21世纪初叶执着关注“桂林抗战音乐”的代表青年学者。他陆续发表了系列论文,涉及抗战音乐活动、音乐团体、音乐刊物和音乐家张曙、林路、刘式昕、吴伯朝、陆华柏、马思聪、满谦子等,以及西方音乐在桂林文化城的传播等研究内容,参与出版《桂林抗战艺术史》《广西民国音乐史》等著作。[ ]从成果来看,陆璎进行的研究更加内容丰富一些,但是,从对音乐历史评价认识的深度上却是不如前辈学者。此外,真正成为史书的专题研究著作尚未有人完成。笔者早期对于桂林抗战音乐文化的研究亦存在这样的问题。[ ]因而,如何将桂林抗战音乐的研究更加深化,是我在整理桂林史料过程中思考的问题。因此,本著力求以编年史书写,努力为桂林抗战音乐史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三、文献、思路与方法
音乐史研究,首先还是以文献研究为核心,对于历史文献的考证、分析和解读是根本的方法论,本书侧重方法为编年史写作。编年史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是按照时间顺序记载历史的编撰方式,注重史料的全面性,历史事件的真实叙述,以历时年月日的方式,勾勒历史的发生、发展,探讨历史本质的研究方法。抗战时期,北有延安,南有桂林,并称抗战时期的文化城。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至1944年9月桂林防守司令部先后下达第二号疏散令和第三号强迫疏散令,桂林民众大撤退止。期间七年,桂林抗战文艺蓬勃发展,抗战音乐活动从未间断,促进其发展蓬勃的内因,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倡导,艺术家与民众爱国主义精神的发扬,也有政府“有保留性”的组织与推动,中国共产党公开与隐蔽的文艺政策和策略的推动,以及国内外战局的影响。诸多因素,使得这一隅之地的抗战音乐历史,既有中国抗战音乐文化的一般规律性,也有着特殊的研究价值。而这一切,使得以编年体方式撰写桂林抗战音乐史书成为一种可操作的研究模式和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首先,爬梳剔抉桂林抗战音乐史料。前述有王小昆编著桂林文史资料第五十三辑《抗战时期桂林音乐文化活动》、冯明洋《浩歌》上下册,两书皆是以呈现史料为特征的史料汇编类文集,对本书史料查找工作有重要的引领意义。此外,史料集著作亦有着为后人研究作嫁衣的重要奉献意义,对于学术研究发展有着基石意义。本书的前期工作也包括了史料收集工作,对各种史料,竭尽可能地援引第一手资料,二手资料则作为一种参照。前辈著作所呈现史料主要是抗战时期桂林地区报刊上所发表的部分音乐论文,以及音乐刊物等史料的基本信息,而涉及具体音乐事件的“边角史料”并不在其中,这些则是建构编年史重要的考证证据,是对历史事件追溯源流辨析真实的关键性材料,也是本文对史料发掘的新贡献。本书史料主要包括民国报纸中涉及音乐的各类报道、音乐评论、音乐文章等,具体有《救亡日报》《桂林日报》《广西日报》《扫荡报》《力报》《大公报》《曙光报》(桂林版),以及《南宁民国日报》《柳州日报》等;民国桂林以及其他地区出版连续刊物、音乐刊物等,如《教育旬刊》《创进》《抗战文艺》《战时艺术》《十日文萃》《广西教育通讯》《音乐与美术》《新道理》《国民教育指导月刊》《每日新歌选》《新音乐月刊》《音乐知识》《艺丛》等;桂林出版音乐歌集、音乐著作和民国档案公文文献等。
其次,钩沉史料、以个案方式对重要事件做针对性研究,以微观与宏观角度把握桂林抗战音乐史的发展。现有研究成果也多有关于桂林抗战音乐的大事记写作,最早见上于世纪80年代的《桂林文化大事记》[ ],后《浩歌》《抗战时期桂林音乐文化活动》两则文献亦有大事记部分。然则,大事记与编年史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重于述而不著的事件记录,以事无巨细、详尽为上;音乐编年史则注重对于音乐事件的史学解读,尤其注重把握关键性事件,以个案方式深入阐释,解读音乐事件和现象的发生、发展和影响,力求探寻音乐史的本质和规律。
总体,运用音乐史学的实证和思辨性方法论,结合社会学、政治学等研究视域,以大历史、音乐史发展状况为背景,以桂林抗战音乐史事件为核心论点,以及相关的背景材料,进行编年史排序,以音乐史视域阐述浩瀚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壮丽图景。本文框架分为绪论、编年史和结语。编年史书写体例以事件为标题,以重要文献为导入,也作为时间的标记,按文对该事件进行描述和历史解读,结语部分对桂林抗战音乐史的发展做整体分期总结,并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桂林抗战音乐发展的重要意义。
本书在史料收录的视角上打破了“桂林抗战音乐完全由外省文化人输入”的常规认知,这一视角的转换,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桂林文化城形成过程的理解,更彰显了地域文化内在的生命力。在此基础上,通过大量史料进一步展现了桂林抗战音乐从单一走向多元的繁荣历程,不仅记录了《黄河大合唱》等巨作在桂林的上演盛况,也收入了反映当时文艺思潮的活跃与争鸣的大料史料,如“音乐的民族形式讨论”等,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思想碰撞、艺术争辉的生动历史现场。
此外,在整体框架的设计上,作者并未局限于音乐本身,而是运用音乐史学的实证和思辨性方法论,结合社会学、政治学等研究视域,将桂林抗战音乐置于“大历史”的宏大背景中进行考察。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路径,使得音乐事件不再是孤立的艺术现象,而是与政治风云、社会变迁、民众心理紧密相连的时代注脚。在这一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可以清晰地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桂林音乐界的形成与贯彻,从而揭示了政治力量与文化发展之间复杂而深刻的互动关系。
1932
◇满谦子谈音乐教育的窘况
新音乐何时入广西?按照音乐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应不晚于20世纪初学堂乐歌的传入。广西的新式学堂可追溯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时任广西巡抚黄槐森创办的“体用学堂”,聘请唐景崧主持教务;至宣统元年1909年,广西有政法学堂1所,中学堂14所,小学堂1078所,优级、初级、简易师范学堂10所,高等学堂1所(1902年“体用学堂”由巡抚丁振铎改为“广西大学堂”),女子学堂20所,实业学堂7所,主要集中于省府桂林地区。[ ]但是,广西地区的新学教育发展是在1933年起雷沛鸿主持“国民基础教育运动”之后,而广西学校的新音乐教育也至此,渐渐有所成绩。
作为第一位广西籍专业音乐人——满谦子先生[ ],曾经对广西1932年“国民基础教育运动”未开展前,他所见广西音乐教育情况做如下表述:
“(一)环境方面 广西向为闭塞之区,文化之落伍,自不待言,尤以艺术一门,知好者竟若凤毛麟角。所以对于音乐方面,除却一般城市中民众的戏曲和学校中的毛毛雨等之外,便别无所闻了。那末,整个的环境既是这样陋俗,和一切旧习的印象,既是这样深刻,要想在这种情形之下,去输进一种特异的音彩来刷新一般的耳目。真是不容易的事。所以在一个学校里面,简直是没有办法去着手。何况更加之省教厅的学制,在每一个五六十人男女大小长幼不齐的班中,每周只有一小时音乐课。讲乐理呢?还是教唱歌呢?真不知怎样去分配才好。复次,学校的成见,向来是不注重音乐的,所以一班学生,每逢上这种课的时候,除却当是一种瞎喊的玩意外,再没有别地念头。
(二)教授方面 有以上这样大的一个难题,教授方面,自是无法可想。单以唱歌来说,对于音调一项,他们只能唱五音阶的歌。如加上了fa或ti等的音在内,便好像一架坏了音的风琴一般,死也弄不准确。至于有变音或变调的歌,就更不用说了。对于歌词也是如此;稍为有文艺价值的歌词,便感觉毫无兴味。若是像《妹妹我爱你》俗不可耐的东西,便马上可以背得出。……讲到练习发音,那简直是个大笑话。……说到乐理一层,那更使我失望了。……五线谱竟说比三角几何还难,……这样一来,简直不能使他们有看谱的技能了,何况每周只有一小时音乐课,怎办?所以,为着要使他们多发生些唱歌兴趣起见,我只得把简谱一齐应用。……
(三)教材方面 说到教材方面,真是个最难解决的问题,同时又是我一个最大的缺憾。因为要从一个幼稚和有恶习的过程中,跳到一个有规则和有艺术的环境里,同时又没有经过相当的阶级和步骤的训练,这比上天还难,绝对办不到的。就以歌曲来说吧,中国现在所有的歌曲,虽名为中学的教材,其实是中学最不适用的教材。有的稍为浅易的,曲调却沉闷呆板不堪。有的曲调稍为好听的,却又难唱。因此在一班只能唱五音阶的学生中,授之以沉闷呆板之歌,便不能提起兴趣。授之以优美悦耳之曲,便感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这样一来,要预算一学期的材料,买许多的歌书才选得出。但我国现在所谓有些艺术价值的歌书,又能找到几多?又能有几多可选得出来适用于这种环境?所以在一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情形之下,不得不追憾到我学识不足了。假使我能够自度曲的话,那末,这种毛病,这种缺点,我虽不敢自负完全能补救,但我相信总不至于会反将毛病弄坏些。
(四)待遇方面 ……”[ ]
满谦子,原名满福民,是广西第一位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音乐人才,1929年秋入校,学制五年师范本科,主修声乐。1932年因“一二八”淞沪战役,满谦子休学回家乡,在柳州广西省立四中和龙州省立七中任教各半年。从满谦子1932年所见,20世纪30年代初期音乐课虽然在广西学校教育中普及,但也存在着各种困境。学制混乱,学生基础薄弱;学校中唱歌竟以黎锦晖[ ]《毛毛雨》之类的流行歌曲为主;教师薪资菲薄,师资极度匮乏。另外,虽然舆论上广西仍然处于如火如荼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中,但从学校师生的音乐活动来看,抗日歌咏发展是毫无起色。首先,是可唱歌曲的不足,学生音乐教材的匮乏;其次,是学生歌咏能力欠缺。1931年广西省宣传部提出的“编辑抗战歌曲”的工作,实际也未能真正有效开展,原因必然少不了缺乏“音乐人才”一条。此时的广西是新音乐的蛮荒之地。
从满谦子的言谈中可知他所理想的音乐教育是学生能够掌握五线谱、简单的西洋发声法,能歌唱具有一定艺术性的歌曲,显然是与现实多有差距。而此时广西上层知识分子对于音乐的看法,也多脱离于现实的世界,且有倾慕西方艺术音乐的风气。另外,满谦子面对广西音乐教育的窘境,感怀自己不能作曲的遗憾,在他回到上海音专后,开始了学习和弥补。他作为师范本科,主修声乐师从周淑安、苏石林、应尚能等名师,辅修作曲师从黄自,辅修钢琴等。音专的学习为他未来的音乐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抗战初期满谦子成为广西抗战音乐活动的领导者。从他的一生来看,他是广西新音乐史和音乐教育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
◇从西洋音乐,谈“音乐与人生”
1932年5月《南宁民国日报》副刊《浪花》发表了长篇音乐文章《音乐与人生》,作者石玉昆,当是与雷沛鸿一起参与广西教育工作的教育家。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论及音乐美学的观点中“艺术与人生”是一个惯有的话题。
“……谈到人生,我又感觉——不如说自慰——不要因为不得志便抑郁,悲哀;要在艺术姊妹行中求得些新的快慰。……
……现代的尘寰,是一个充满腥秽的尘寰;现代的尘寰,是一个苦闷烦恼的尘寰。在这尘寰的各部,虽然有披雅娜,怀娥铃,钢琴,管弦乐……然而,然而也不过是木偶式演奏而已。奏演的人,是否了解音乐的底蕴?是否了解音乐的含蓄?
……‘乐圣斐德芬Beethoven底音乐,是法兰西革命的反映,是音乐中的自由平等四海同胞的呼号声;修芒Schumann底作品是十九世纪中叶徘徊于欧洲全土的新精神——浪漫主义——底音乐的反响;华葛耐尔Wagner底乐剧Music drama,是现代精神的表象,是现代的民众声Vox Populi’。在在的可以体验得出现代的音乐,‘能广大地自由发展人类底智情意的活动,精密地发表人类尘内生活Inner life’。……
吾们知道现代的音乐,根本上完全建筑在和声Harmony上面——即音之谐和——音乐本身的音节既在谐和,□于人们当也感化成一个谐和的精神了。那,才不至于残忍,才有和平可言。所以,要免除人类上残酷无人道的战争,惟有提倡美化的音乐,惟有谐和的音乐才可以感化人们残酷野蛮的兽心!”[ ]
《音乐与人生》表达了作者认为音乐是艺术中最能与人的精神生活密切接触,因而,也是最能改善人格修养的艺术。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分子,精神层面往往有对现实不满的种种苦闷,他们崇拜西方科学和艺术,希望能够用西方的艺术来感化人类,甚至认为只有谐和的音乐才可以感化人心免除战争。因此,这不是一种理性的思考,而是借用了对西方音乐情感论的一些认知,而希望通过音乐寻求心灵的安慰。
又如同年树焜发表于《浪花》的《我们的慰安者》[ ]一文,文中表达:音乐是生活中的安慰,它是普遍的,没有阶级性也没有限制的,只要你接受它或者欣赏它,你就会从它这里得到安慰。文章遍引哲学家、音乐家,乃至理论家田边尚雄等的语录,揭示音乐的伟大。然而,这仍然是一个没有真正接触“地气”,空泛的理想,没有真正面对音乐与中国时代现实问题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世界,犹如处于庙堂的诗人笔下的田园歌。
石玉昆和树焜是中国转型时期新文人的代表,他们的言论有着时代背景印记,是此时中国所存在的一种音乐思想的范式,也是时代的诸种思潮中的一种。我们可以从西方的音乐思潮中管窥到中国知识分子模仿的痕迹,也能从中国传统文人的思想中找到文化的基因传承。而随着地方抗战风气的衰退,广西抗战的乐歌悄无声息,《毛毛雨》等歌曲充斥学堂,地方音乐美育亟待发展。
1933
◇音乐研究会/社的萌生和发展
1933年夏,《南宁民国日报》“社会版”报道了上海工部局乐队和大同乐会联袂的一场音乐会,盛赞“中西音乐第一次会奏——世界大同之朕兆!”[ ]中西音乐文化的融合并存,是20世纪东方音乐文化现象中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中国的国乐和戏曲,一方面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艺术,处于让人喜爱,但又让传统思想者蔑视的地位;一方面作为艺术的修养,知识分子和学生们也乐于习之。这种美育的风气,在广西的进展也是相对缓慢。1933年南宁省立女子三中和某女高,分别成立了音乐研究会,成为了《南宁民国日报》11月稿的新闻素材。省立女子三中学生自治会组织音乐研究会,有军乐队和口琴队,四五十人参加;另有一高中女生组织音乐研究会,分为口琴、箫、扬琴、二弦(二胡)等四组;以“娱乐”“陶养性情”为目的。[ ]
从另一则时讯可以看出此时广西地区的学校和坊间的音乐美育和国乐传承也有一定的普及,且多以“研究会/社”等为名目,并与抗战时局之宣传工作相互联系。如,北流县社会贤达赵希天[ ]等,“以暴日侵凌、列强窥伺、国势日蹙、民气不张,拟组织一粤剧团作化装宣传,一以唤起民众抗日救国,一以灌输文化辅助教育”,但考虑人才缺乏,“故先组织音乐社”成立“国乐研究社”。[ ]后续类似社团又有南宁市民罗星南等组建的“国乐研究社”,扶南县机关公务员等组建的“音乐研究社”等。[ ]地方民教馆亦从民族教育的角度纷纷开设“音乐研究会”等组织。[ ]广播电台为“罗致本市音乐专家协助播音”,于1934年6月17日成立音乐研究社。[ ]
从1933至1935年,广西各种音乐研究会纷纷涌起。1935年5月26日广西省党部南宁同乐会也成立了一个“音乐研究会”。[ ]同乐会为同年4月27日成立,“以陶冶德行、增进艺术技能、养成互助精神、联络感情及宣传三民主义与本省建设为宗旨”。[ ]该会建立音乐研究会曾设立中乐组(杜式洲为组长)、西乐组(刘鹤云为组长)和歌唱组(雷廷俊为组长),并延聘多位指导员指导会员。[ ]成员涉及机关、学校等党部同乐会会员,从后续偶尔报道来看,音乐会主要也就是参与同乐会聚会,表演“同乐大会”中的游艺活动,并无更多影响力。如,同年9月举行的第三次同乐大会游艺节目包括:军乐、话剧、粤剧、歌唱、口琴、桂剧、粤曲、音乐合奏、国技(武术)和歌舞诸类。[ ]直至1935年,满谦子归邕,创建广西音乐会,时为广西省最具有专业性和影响力的音乐社团。
20世纪30年代初期广西各地和各阶层崛起音乐研究会社体现了广西地方政府对音乐美育的重视。音乐会社之“音乐”,学生主要以国乐器乐、西洋器乐和歌咏为主;市民则以国乐、戏曲、曲艺等为重。同时,各会社也把音乐与抗战精神联系在一起,对未来的抗战宣传具有积极的意义。
1934
◇广西第一场室内音乐会和音乐论战的“第一枪”
从南宁、桂林等地陆续发生的音乐会社来看,新音乐文化在广西起步是较晚的,而广西省第一场室内音乐会则在1934年夏。同年7月,满谦子先生与应尚能[ ]老师、丁善德[ ]、戴粹伦[ ]同学赴香港、广州、南宁等地举行旅行音乐会。受到广西省邀请于广西南宁省府礼堂演出,音乐会以演唱和小提琴、钢琴演奏为主。署名拾鳞的聆听者在《浪花》发表如下评论:
“第一位音乐家唱的,当以《同志们快勇敢的武装起来》一曲为最出色,听到最末一段,那种英武蓬勃的声调,真如长江大河,一泻而出,大有沛然莫能制之的气概。可惜全篇都是英文的歌词,使得听众对于内容不免隔膜了一些。
第二位音乐家唱的,当以《茶花女中的饮酒》和《教我如何不想他》,二曲为最动听。那种快曲,和委婉连贯,高啸入云的词句,他竟毫不费力的唱出。还有他那□音的准确,愉快,转跌自然,用嗓能发出共鸣的谐声,这确实非受过四五年以上的训练是办不到的。
小提琴家的奏演,要以《小步舞曲》为最动听了。那种幽柔的音调,和清脆的琴声,若断若续,好像雪花般的在云中飞舞,引起了人们无限的情绪和快乐。他那弓弦的轻快,又好像飞虫般的在琴上跳躍着,令人目光应接不暇。这种娴熟的技艺,非有音乐天才,和六七年的训练也是办不到的。
钢琴……我很赞成这位音乐家用琵琶所奏的《阳春古曲》。……这种乐器,平时多拿来配唱的,用来独奏的很少。然而他竟能独奏得淋漓尽致,一丝不乱,正所谓‘大珠小珠落玉盘’,听他每换一个曲调好像又是一个天地。无怪博得听众的欢声了。”[ ]
20世纪30年代初期,广西首府南宁是没有音乐会活动的,更没有展示西方音乐文化的音乐会。因此,拾鳞称这场音乐会为广西历史上的“破天荒”。应尚能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留美回国后随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担任声乐教授;满谦子1929年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五年本科师范声乐专业,随周淑安、苏石林、应尚能学习,确已经“受了四五年以上的训练”;而戴粹伦是极有天赋的一位小提琴家,廖辅叔先生盛誉他为上海音专培养的“中国人之习小提琴者”“最成功的一个”[ ];丁善德为中国第一位举办独奏音乐会的钢琴家,在音专期间,琵琶、钢琴、作曲各科优秀,也常常担任老师和同学们的钢琴伴奏工作。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新音乐发展初期,专业音乐会还是以西方音乐作品为主,中国作品为辅。这场音乐会歌唱以西方艺术歌曲、歌剧选曲和中国早期艺术歌曲为主,有小提琴、钢琴和琵琶演奏。从艺术和技术的角度来看,是具有国内高水平的,也是广西历史上第一场室内乐音乐会。
然而,不想这场音乐会却引来了署名阿牛的一位乐评者的长文——《音乐家与大众》的批判。可惜,因文献缺失而无法看到原文,只能根据答文管窥。满谦子的答文和拾鳞的乐评,发表于《南宁民国日报》副刊《浪花》,都针对于《音乐家与大众》一文进行或直接、或婉转的批评。从中可见阿牛的批判观点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认为不应在广西地区介绍这样的音乐进来,如批评钢琴曲《邀舞》:“广西现在不是提倡跳舞的时代,不应介绍这种音乐进来”;将涉及情爱的艺术歌曲“与《毛毛雨》《桃花江》相提并论”;认为“广西需要军歌”,“是要能够表现拖枪开步走的音乐”。二,阿牛本人“喜欢古乐”。[ ]从中可见广西也是存在着反对音乐的西化和提倡“古乐”的国粹主义的知识分子,这和时代的背景是契合的。
音乐的国粹主义思想早已在广西有见:1933年一篇探讨“中国音乐的来源”的文章开篇如此论述:“素称‘礼乐之邦’的中国,经过了几千公转之后,——至现在——关于音方面,非但没有半点进展,而反沦亡到几乎淘汰,甚至不识什么是音乐,虽然现在的学校亦设有音乐一科,无如大家都是敷衍了事,并且它的性质多是採自欧西,没有容留国乐的余地,但是听惯单音乐曲的中国人的耳必不能领略复音和声的乐曲,反至‘画虎类犬’。所以在我个人的偏见,与其向外搜求,不如提倡,和改良国乐比较来得容易,须知中国音乐的历史已有数千年,而定律的精细,和完善冠于世界各国,渐渐因为一班文人视为:‘茶余酒后的娱乐品’,所以没有深刻的研究,和改良,以至今日之地步!”[ ]
评乐者阿牛“喜欢古乐”,他的思想显然也有着一部分的国粹主义观念。但他的落脚点实则放置在“大众”和“大众化”。“大众化”在音乐思潮中首先集中反映在新音乐的理论和美学原则,但是亦有广义的“大众化”内涵。正如“新音乐”的广义与狭义之分,“大众化”也是20世纪20至30年代普遍的一种认识。如知识的大众化教育,这就涉及到艺术领域的平民化问题。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正是步入民众教育“大众化”的时代洪流,“大众化”成为一谈文艺,则无不涉及的一个普遍观点。仅以1934年前后广西地区部分文艺文章为例,涉及:“艺术大众化”“话剧大众化”“文艺大众化”“戏剧大众化”“文学大众化”“民族文学大众化”“体育大众化”“民歌与文学大众化”“大众教育”“大众文化”“大众艺术”“大众诗人”“大众音乐”等诸多文化大众化论题的讨论。[ ]而在广西谈及“大众”“大众化”则会和行政、军学的“三位一体”制的政体制度,与广西的实际情况,以及国际(中日)情况结合起来,因此,“尚武”精神也是广西知识分子言及文艺大众化思想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特质。
阿牛对满谦子的答文和拾鳞的乐评给予及时的回应,而《音乐论战的第一枪》的标题也非常具有时代性气息。犀文言到:“古代的中国士大夫把词曲填入羌胡曲调里,是这样造成了老中国封建的歌曲;现代中国音乐家用西洋音乐谱词曲,一个圈子兜转来,将‘发扬国性’作复古的假面具。我所要攻击的便是这老中国封建艺术借尸还魂的怪现象。”阿牛显然是反对杂糅异族的歌曲和音乐的,从反对宋代词调音乐中的羌胡曲调,到反对以西欧音乐视为可以塑造中国“国性”(民族性)的中国新音乐的发展道路。或也从古代两宋局面,想到中国社会正面临的列强窥探的危机局面。他批判国内的音乐人没有创作出自己的“马赛曲”,而是用了西方儿歌填写成了《打倒列强》,认为这是中国革命的耻辱。
“中国的音乐家当以民族革命为立场,民族革命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便也是中国艺术家唯一的出路,这不能说是‘投机’,因为你是中国人便应当走这样的路的,而且也只看你走不走,如果你大骂‘投机’,却将自己投到复古的沟渠中去,或将自己投到世界主义的浑水中去,不管别人有没有‘眼光’,被批评,终是不能免的了。”[ ]阿牛以犀利的语言结束了这篇具有浓郁批判性的论战之文。
阿牛是代表了在中国面临科学、艺术的整体西化发展历程中,认定中国的道路必须经历民族革命,但是,却否定了文化西化发展的道路,具有革命精神和国粹主义观念的知识分子。后续,满谦子不再有答文,论战也就此在第一枪止住。但是,这场经历必然也会对侧重从艺术本体的艺术性来考虑艺术价值的学院派音乐家满谦子有着一定的触动,而未来,他将承担着广西音乐教育大众化的责任。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