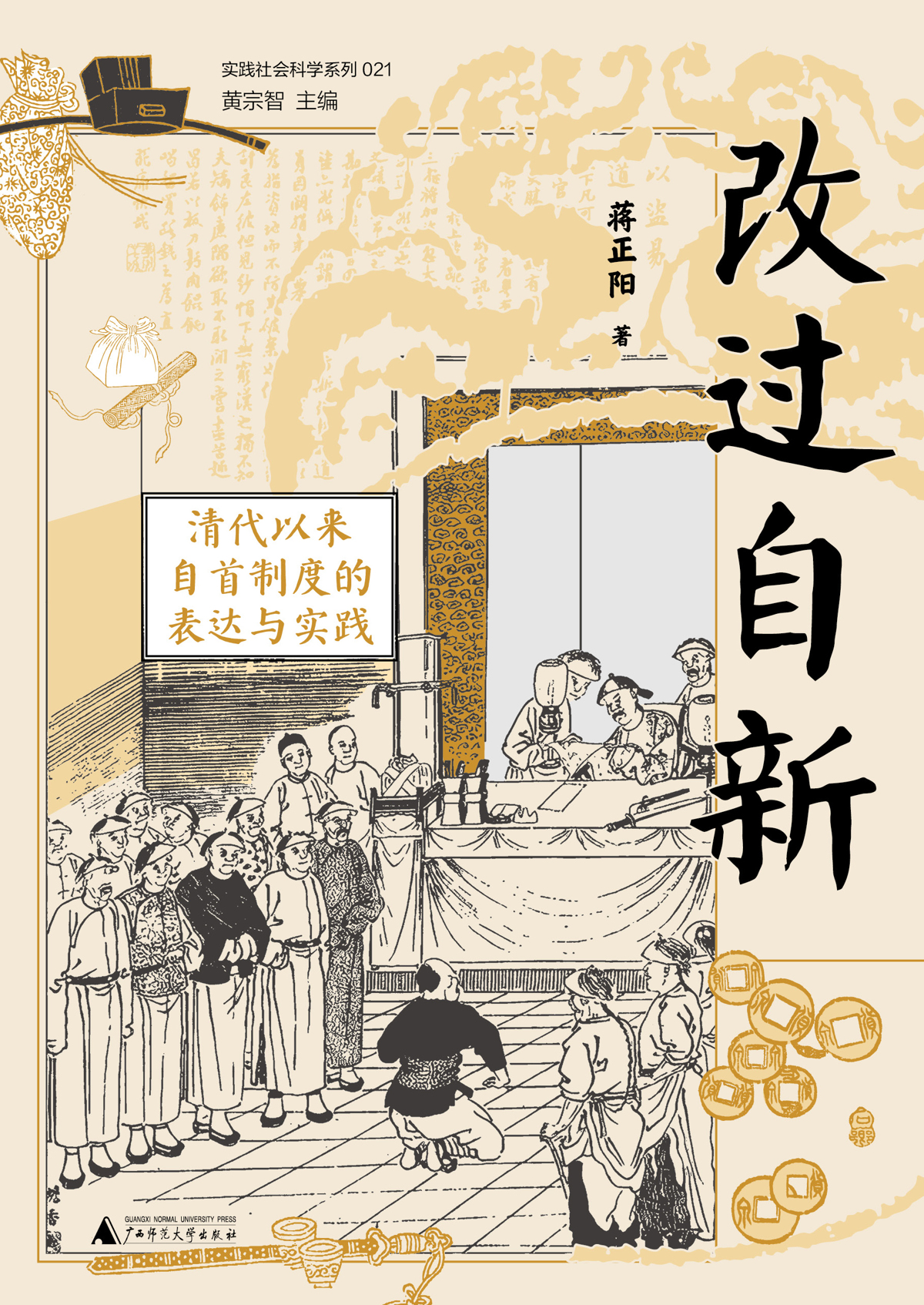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5-10-01
定 价:68.00
作 者:蒋正阳 著
责 编:王佳睿,陈焯玥
图书分类: 法律史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法律/法律史
开本: 32
字数: 164 (千字)
页数: 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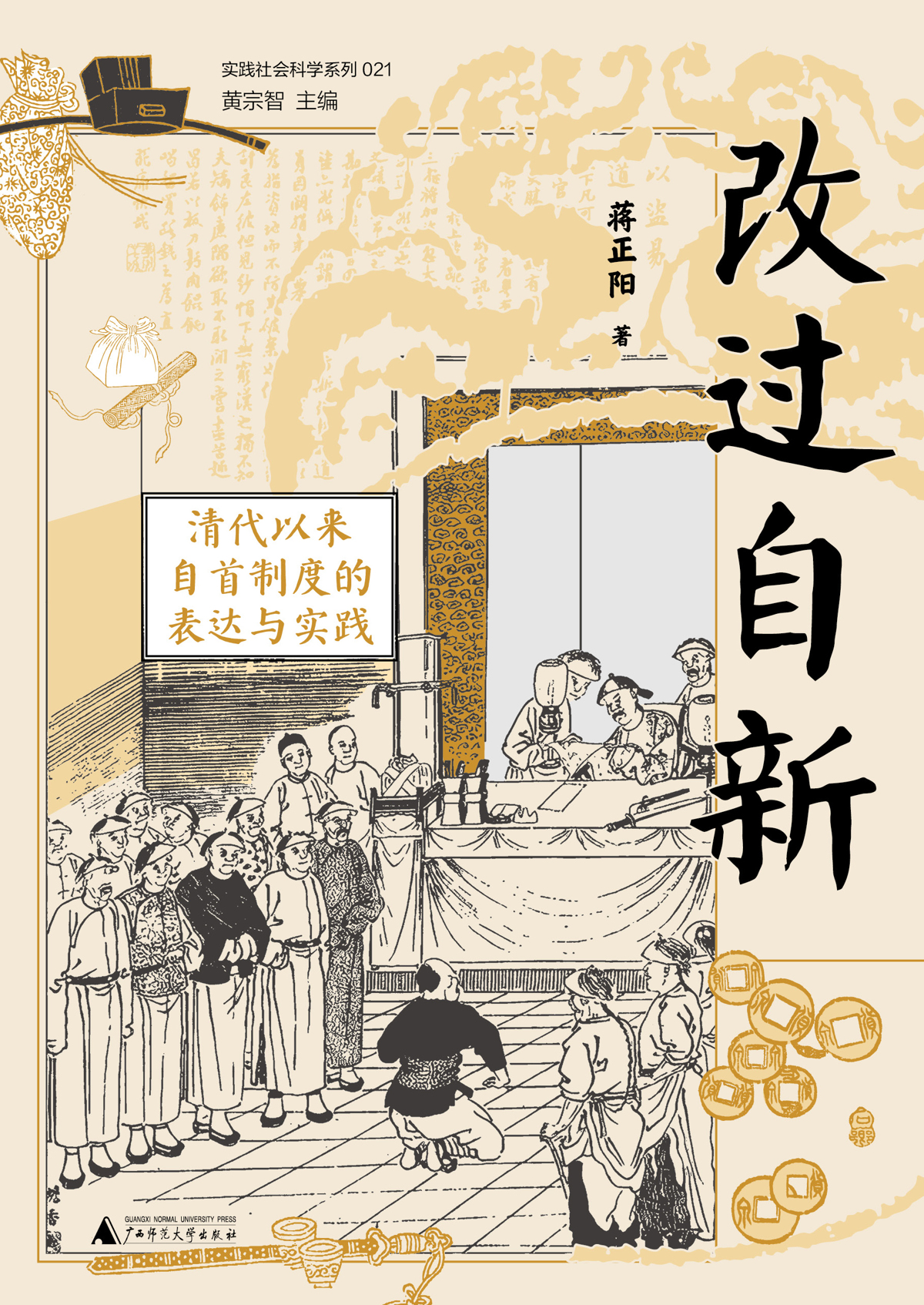
本书是一部以自首制度为讨论核心的法律社会史专著,追溯清代至今自首制度的演变轨迹。作者以丰富的史料和案例生动论述了自首制度的内涵与发展,深入剖析法律条文与制度实际运行,将中华文明独特的家国一体观念纳入法律史研究。本书打破了传统与现代自首制度割裂研究的局限,聚焦近代变局与“西法东渐”背景下,自首制度如何在变与不变中延续生命力,探讨当代自首制度对现代司法思想的吸收和对社会变迁的适应,并通过与韦伯的形式理性法等进行理论对话,揭示制度从传统“实用道德主义”向现代的演化,为理解中国法律现代化提供了深刻的理论与实证参照。
蒋正阳,河南修武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哈佛大学联合培养博士,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出站博士后,现为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律史、法律社会学等。
导论
问题的提出
理论框架
材料来源
文献回顾
各章内容
第一章 清代自首制度的实用道德主义特征
改过自新:清代自首制度的道德基础
家国同构:清代自首制度的实质理性
以例破律:清代自首实践的实用主义
第二章 清末民初大变局中的自首制度
清末民国自首文本与法理的激进变革
家族主义与自首制度的分离
西方刑事社会学派对自首法理的影响
民国自首实践的延续与保守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自首制度:以陕甘宁边区为例
边区自首从宽的原理变革
通过自首政策怀柔敌人
通过自首运动惩治犯罪
边区自首制度的实用道德主义特征
第四章 现代自首制度的工具主义转向
交易论:自首制度与司法经济的结合
扩大化:自首制度作为一种治理政策
灵活性:从必减主义到得减主义
第五章 置换与默许:现代自首制度中的个人与家庭
现代刑法中的“家”价值思考
刑事立法与实践中“家”的考量
亲属陪首、送首的解释置换与司法实践
传统与现代斗争中的家庭
第六章 韦伯理论与中国自首法律
通往现代国家的形式理性法
具体正义:个人主义与家庭一体
双刃剑:治理模式与工具主义
结论
参考文献
附表后记
序:“家”与中国法律
“家”的经验
我成长于一个传统的中原家庭,幼年得祖父启蒙,诵读四书、临摹书法。祖父厚德尚古、好读诗书,教导子孙“为众而立”,传授我们如何将儒家精神贯彻于修身齐家的实践之中。得益于此,二十余口的大家庭亲爱和睦、精诚上进。祖父一生赤心报国,早年筹办火电、钢铁、磷肥、造纸等地方工业。待功成身退,他又建立医院,兴办医科学校等公益事业。以他为榜样,我们兄弟姊妹立志诚意正心、为家国效力。因此,我们尽管专业有所不同,但研究的主题都集中于农民工、老龄人口、失范人群等现实议题。
通过生活经验,我理解了家的概念、关系中的个体,以及利他的精神。自己尽管不过是众生之一,在家里却永远是珍贵、重要的人,每一阶段的成长和进步都能得到家人真诚的关心和祝贺。伯父乐于结合自己的经历提出对我们的研究的看法,与我们交流他读经史的体会;叔父常常分享为人处世的体验,并全力支持我们的学业和发展。父母更是以身作则教育我们,父亲经营印刷,慷慨捐书,母亲从事中医,仁爱悲悯。妹妹高考那年家庭发生变故,从未出过海的父亲为供我们姊妹读书冒险登上远洋渔船,母亲重病失血,妹妹献血救母,因担心我在西安考研分心,直到过年回家才让我知道这一切。我想,这种利他精神即便不是普适的,在无数其他家庭中也一定是广泛存在的。孤岛般的个人、自私的人性,这些理论假设与我的经验似乎并不能相互印证,于是我把眼光投向历史。自首制度的沿革与实践,显示出“家”作为中华法系和中国文化的核心所表现出的强韧生命力。
为什么写“自首”?
自首制度因其历史延续性和儒家色彩,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一方面,自首制度作为“西法东渐之后的硕果仅存”(林廷柯语),有可能为思考中华法制的古今断裂问题提供思路;另一方面,自首制度本身蕴含儒家教化原理和对悔过迁善的重视,且其运行机制深嵌于“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之中,这样的整体性视野,有助于理解具体制度与政治理念、社会结构的联动。
在自首制度的延续性方面,林廷柯和葛扬焕提出自首制度为中华法系所特有,并与近世刑事政策殊途同归;徐道邻曾系统梳理了自首制度在唐、明、清律中的演变;李克(W. Allyn Rickett)认为自首作为古代中国的法律制度,至少在名义上保留至民国和共和国时代,因此,研究自首制度可以查明其如何受到20世纪的法律西方化和共产革命的影响。
普勒姆说,古老的过去从未完全失落,它就在人类生活的至深之处存续着。清末以来西法东渐的持续进程,导致中国传统法律与现行法治体系的断裂。当前法律的理论和制度规范通过“现代性”与西方法律相连,以致中国法律史成为隔绝于现实的学问。值得注意的是,在固有法律传统断绝的大背景下,自首制度在法律文本和司法实践中体现出罕见的延续性。因此,自首制度因袭损益的过程,为传统制度古为今用和传统法律现代化提供了具象视角。
在自首制度的儒家化方面,刘俊文认为自首是法律道德化的一个表现;陈顾远提出,“自首减轻,为中国法系特有之例,盖许人以改过自新,儒家诛心为教之当然结果也”;黄秉心认为自新和宥恕是自首的宗旨,并将自首制与亲属容隐、保辜制等总结为中国法律之特色;瞿同祖详细阐释了自首制度与亲亲相隐原则的配合在司法实践中产生的特殊效果;马若斐(Geoffrey MacCormack)推崇自首、相隐与相告言的立法技术,认为这种结合不仅实现了“立法经济”,还兼顾了悔过迁善和家族互助两种道德价值。
“悔过自新”:对主观的重视
自首的独特性在于,失范行为发生后,制度与人形成良性互动,含有一种教人自发回归秩序的机制。它不仅有对犯罪人内心的说服和改造作用,而且有预防犯罪和教化人心的功能。这种对个体主观情况变化的重视,是制度精细化的表现。
自首体现了“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的儒家观点,与教化思想相一致。古代理想政治反对不教而诛,主张以德化民。儒家认为教化有优于法律之社会功效,孝廉的品性来自教化而非强制:“曾、闵之孝,夷、齐之廉,此宁畏法教而为之者哉?……化使其然也。”教化可以正人心性,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因此,德礼与刑罚的关系是,刑罚服务于道德教化,只有在教化不起作用的特别情形中才用刑罚处置。
现代制度的规定局限于人与物之间的客观关系,但却忽略了人的主观认识对于客观关系的影响,即通过教化的德性指引实现关系的主客观双重调节。传统法律为突破这种主客观二元对立的思维限制提供了思路。先秦诸子解决分配问题时,不仅要划分今天法律所聚焦的所有权,还要疏导人对于财富的欲望。财富分配不仅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权界确定,也要考虑到人的主观欲望与财富的客观数量之间的互动。毕竟,建立在纯粹的利己假设基础上的制度体系,运行起来可能会被其假设的人性规避和滥用。任何逻辑精密的制度都依赖人来参与,如果缺乏对人与制度互动的认识、轻视对人本身的教育,制度异化、锱铢必较、以人为壑的极端情形就难以避免。
“家”:传统价值的载体
儒家理想中的社会格局,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延伸为国,血缘成为纽带,宗法形成秩序,从而将国家的合法性建立于自然的血缘关系之上。君之于国相当于父之于家,每一个体则要对父母尽孝,对君国尽忠。因此,以家庭为中介建立起来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并非古典自由主义所描述的对立紧张状态,而是君父臣子隐喻下的和谐共存。
同时,人不是一个个孤岛般的个体,而是定义于人际关系之中的。关系的作用不仅在于团结互助,也有互相牵制之意。在天地君亲师的序列中,天地是至高的,但人也有顶天立地的尊严;同时,人性又是受约束的,不可有无法无天的狂妄。对人的体系性认识,为个体划定了行为的范围,即上要合于天理,外要合于人情,内有道德律令的自我检视。这种整体文化和社会氛围产生的约束,严厉程度并不逊色于外部监督。由这样的个体推及而成的社会,才可能解决制度的机械性和有限性。
瞿同祖认为中国法律的主要特征是家族主义和阶级,二者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社会基础,也是法律所维护的对象。在自首制度中,对家族价值的维护表现为“亲亲得相首匿”和亲属“相告言”的并存。“亲亲得相首匿”维护的是家族利益,法律保护家庭成员超乎其他社会关系的亲密性。即使是威胁到国家和社会利益的犯罪行为,法律也允许家庭成员互相保护。家庭成员如果违反受匿条,则由法律按照“干名犯义”之罪处理。“相告言”(“若于法得相容隐者为首及相告言者,各听如罪人身自首法”)则假设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一致,即便家人出于不利目的告发犯罪者,法律也按照犯罪者主动投案予以减免,使家人的告发行为反而产生有利的审判结果。
在规范层面,两者为同一主体提供了两种相互矛盾的行为指引:虽然揭露家人的犯罪事实,符合自首之条,能使亲人免刑,揭露者自身却犯了“干名犯义”之罪;不告发家人,虽符合亲亲相隐,却可能导致案发后亲人不能减免刑罚。出人意料的是,在司法实践中,两条矛盾的规范结合却实现了最佳的社会效果:犯罪者亲属以身犯法来践行孝道,自己犯“干名犯义”条的同时,使犯罪者本人受益于其告发行为而被免罪。最终,亲属虽犯科条却尽到孝道,犯罪者虽然被告发却能免罪。家族关系因此无虞,国家亦在此过程中解决了犯罪问题。单独的每条法律都意在彰显家族价值,而条文之间相互配合又保证了对国家利益的维护,由此可见古代法律设计之精妙,体系之严整。
回顾历史,尽管清末民国之际在法律文本和理论层面已经开始摒弃家族主义,但在司法案件中,办案人员仍采取过去利用犯罪者的家庭成员侦破案件的方法,案件的发现和解决仍依赖于家庭结构的整体性。民初警察局在抓捕犯人的过程中,比较广泛地采用审问和抓捕犯罪者亲属以逼迫犯罪者自首的做法。在行为性质认定时,即使犯罪者出于担心家庭成员的主观目的被迫自首,警察局仍将之认定为自首。
放眼当前,尽管在整个法律现代化的大趋势之下,法律文本的表达越来越符合现代话语体系中的个人主义思想,但法律实践仍十分依赖于家庭连带关系。在大量亲属陪同自首、劝说自首,甚至捆绑送亲人自首的情形中,犯罪者的亲属成为国家权力与犯罪者之间的中介,甚至是案件走出死循环的关键环节。其作用如此明显,以至于在司法强制作用有限的跨国犯罪惩治中,通过接触逃犯的亲属来规劝逃犯自首成为占比最高的破案方式。
可见,家庭这一传统文化和生活因素从未淡去,而是强韧地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亲属之间关系天然密切,制度设计顺应这种天性才可能在实践中有效运行。比起试图建立一种主观意识上理想的法律模型,切合于实践问题和现实关怀的生成机制才是更可取的。推及自首制度中如何对待家庭关系,则需要反思是否必定要取消家庭一环去形成一种现代国家。
重思家庭革命
吉登斯说,家庭是传统和现代性之间斗争的场所。家族结构被认为是现代性建立的重要障碍,成为现代中国的对立面。在维新志士们看来,家族宗法结构是对个人权利的束缚。谭嗣同认为,五伦貌合神离,遏制了个人权利。康有为按照“天赋人权”的理论,在《大同书》中提出人人直接隶属于天,无需其他中介,梁启超总结该书时认为“最关键在毁灭家族”。
但是,对于个人、家庭与国家的关系的反思,需要回到近代以来的思想脉络中。清末以降破除家族这个整体的努力,并不只是为了将个人从家族中解放出来以实现个人主义,而是为了进一步实现国家主义这一终极目标。因此,家庭关系和“家”价值淡出法律视野很大程度上是主观选择和人为干预的结果,尽管确实存在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国家治理能力提高这样的客观因素。
当前法律所主张的个人主义较多基于西方的问题意识,而缺乏对社会结构中家庭现实作用的关注,以及对历史情境中“个人—家族—国家”关系的认识。故而,一方面,需要避免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单线进化史观,将家庭或家族置于自由、平等对立面的绝对化和政治化判断,考虑到在近代互动中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特殊结合;另一方面,需要认识到家庭整体在抚育后代、赡养老人等现实问题中的客观作用。
具体正义:关系之中的个体
制度设计以实现正义为目的,而对传统正义的理解不仅包括兼顾主客观的调和正义,还包括结合具体情境的关系正义。就自首制度而言,其不仅突出自首者的主观悔过意志,而且注重家庭成员之间异于陌生主体间的刑罚分配。基于客观上家庭的社会作用和主观上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结,传统法律赋予亲属之间以特别权利,并基于此设置特别的刑罚分配规则。相比之下,“理性人”的制度前提因忽视客观社会联结而单薄,因避开主观情感影响而片面。
传统中国注重群体人格的培养,人的自我确立本身是建立在与他人的联系之中的。因此,这种价值观是家庭、家族、整体或社群主义的。中国古代的法律与道德、伦理、教育形成了有机互动的体系,无视要素在体系中的功能而将其单独拿出来与西方作横向比较,结果是无法正视历史,也无法正确对待西方。在差序格局之中,每个群体与自己的关系不同,适用的规则就不同。脱离上述关系谈规则,就无法真正认识规则的作用机制。传统法律逻辑或正义观念,尊崇家族价值体系,重视推己及人的关系网络。
传统社会和法律重视家族主义,有农耕文明的时空性和家庭作为基本单位的经济基础,而现代以来商业化和流动性加强,个人所属的团体层次更加丰富。但传统家庭观念的延续和代际抚养与赡养关系的现实,使得基于个人主义的立法和法理缺乏现实解释力和实际调整作用。司法案例中当事人与近亲属的紧密联系以及司法机关对于这种互动的法律评价,也印证了家庭成员在法律上的特殊联结。有鉴于此,立法和学理也需回应“家”概念及其内部的特殊连带关系。本土法律现代化要跳出单线现代性和进化史观的认识框架,不限于特定现代法律类型的模仿和想象,而是结合历史与现实提出植根历史资源、反映本土特色、观照实践需要的现代法律,基于历史和现实提炼出更接近真实的概念工具,增强现有体系的现实性和有效性。
——选自蒋正阳《改过自新:清代以来自首制度的表达与实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0月
我们都知道,自首制度在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刑事司法实践中都占据重要地位,既往与之相关的研究通常都将传统的自首制度与现代的自首制度割裂看待,关注的要么是从传统制度中汲取本土资源,要么是从现代视角看待甚至批判传统,强调现代自首制度的效用。蒋正阳的新著试图结合这两种趋向,结合长时段、历时性的前现代与现代的比较视角,更关注从传统法到现代法的过渡中自首制度的表达与实践经历了怎样的变与不变。其论析的重点不仅在个人的意志,也在家庭、家族的影响。
在扎实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蒋正阳的新著也在理论概括层面有所推进,指出了自首制度中所蕴含的中华文明独特的家国一体观念,以及这一制度内涵在清末、民国及革命根据地时期,乃至当下的顽强延续与演化,并剖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具体而言,清代自首制度体现出与家庭关系密切相关的实用道德主义倾向,而随着法律现代化的进程,自首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变迁体现的是道德主义淡出法律的过程。但反观司法实践可以发现,不论是民国时期、革命根据地时期还是当下,对亲属陪同自首、亲属送去自首、亲属捆绑自首等行为的认定,体现出法律文本趋向个人主义与法律实践仍依赖家庭关系之间的矛盾共存。而且,作者也借由这一经验概括,主动与韦伯的形式理性法等理论对话,展现出其理论功底与现实观照。
——第三届“实践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最佳专著奖”颁奖词
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展开与韦伯的理论对话,提出关于现代性与现代法律的理解。本书也加深了学界对清代法律及其实践的认识和理解。因此,无论对法学理论研究、法律史学研究还是部门法学研究,本书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赖骏楠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经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重大课题的当下,自首制度如何在发挥现有功效的同时防止异化,是蒋正阳这本书给我们的最大警示。
——田宏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中华法律文明的长河中,自首制度始终是连接“惩戒”与“教化”的关键纽带。本书以“表达与实践”为核心视角,在清代至近现代的历史跨度里,勾勒出自首制度从纸面规则到生活实践的生动图景。
本书深入州县官判牍、刑部档案、民国司法文书等一手史料,还原了制度在基层的真实运行情况,比如清代盗案中“投首免罪”的实际适用情形,民国时期“自首从宽”与西方法理的融合冲突,乃至根据地时期“坦白从宽”政策对传统的继承与改造。这种法律条文与司法实践的对照分析,既揭穿了“制度文本即实际治理”的认知误区,也让读者看到传统法律中人情与法理的微妙平衡。
更难得的是,作者立足中国传统社会,深入探讨了自首制度中蕴含的中华文明独特的家国一体观念。在传统的自首制度下,告发家人(尤其是尊长)总是面临两难的选择:法律一方面规定“亲亲得相首匿”,也即我们常说的“亲亲相隐”,要求家庭成员互相包庇,否则即犯有“干名犯义”之罪;另一方面以被亲人告发可按自首减罪乃至免罪的诱惑,鼓励亲属“相告言”。这似乎对告发者不太公平:自己既为社会安定做出了贡献,又帮助家人减免了罪责,为何却有可能成为唯一获罪(“干名犯义”)受罚的人?然而,在作者看来,这种做法既维护了以骨肉亲情为基础的家族利益,又维护了惩治犯罪的国家利益,恰恰彰显出传统国家维护家国一体伦理秩序的治理智慧,是实用道德主义的体现。事实上,在现代法律中,尽管“干名犯义”早已被废弃,亲属“相告言”适用自首减刑的原则却一直延续至今,“送亲归案”始终作为自首制度的一部分受到鼓励。
在梳理自首制度演变的过程中,本书始终锚定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传统法律中的教化理念,对今天的立法、司法有何启示?传统家庭观念的延续,对现代法律有何影响?这些对话与思考,重新弥合长期被割裂的传统、现代自首制度研究,让本书成为理解中国法治本土基因的重要窗口。
以清代为代表的传统社会,既倡导亲属“相告言”,又要求“亲亲得相首匿”,否则即触“干名犯义”之罪。这种自相矛盾的立法,让告发家人者陷入两难境地,却让国家达成了双重目的:既维护了家国一体的伦理秩序,又能够顺利获得犯罪信息。
——编者按
家国同构:清代自首制度的实质理性
以清代为代表的帝制中国治理结构可用“家国同构”“家国一体”概括,相应的官方话语为“以孝治天下”。在法律体系中,家族和国家作为并行的价值,体现于具体规范之中。关于自首的规定,则集中表现为“亲亲得相首匿”和亲属“相告言”的并存。在价值层面,“亲亲得相首匿”维护的是家族利益,法律保护家庭成员超乎其他社会关系的亲密性。即使是威胁到国家和社会利益的犯罪行为,法律仍要求家庭成员互相包庇;如果有人违反,则按照“干名犯义”之罪处理。“相告言”(“若于法得相容隐者为首及相告言者,各听如罪人身自首法”)维护的是国家利益。在犯罪信息不为国家所知的情况下,犯罪者的亲属可以为了使犯罪者获得减免而告发其罪。在规范层面,这两者为同一主体提供了两种相互矛盾的行为指引:揭露犯罪事实,虽符合自首之条,却违反了“干名犯义”。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两条矛盾的规范结合却实现了最佳的社会效果:犯罪者亲属以身犯法来践行孝道,自己犯“干名犯义”条的同时,使犯罪者本人受益于其告发行为而被免罪。最终,亲属虽然坐刑却践行了孝道,犯罪者虽然被告发却能免罪。家族关系因此无虞,国家亦在此过程中获得了犯罪信息。两种同等尊崇的价值导致逻辑规范的冲突,相互矛盾的规范之实现,又使得两种价值同时得到维护。加之法律已经将危害国家的犯罪排除出容隐范围,其对家族关系的保护并不会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
对于国家来说,单独的每条法律都意在彰显家族价值,而条文之间相互配合又保证了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其中的立法目的和内容合于天理,法律运用和实现顺于人情,司法判决和结果惠于实效。“中国法律中的道德主义一直是与实际效用考虑结合的”,自首的制度体系无疑也印证了这一判断。自首在法律表达上体现了对儒家“亲亲”之义的维持,在实践效果上又确保了国家发现和惩治犯罪这一权力的实现,既有内在的道德精神,又有外在的治理功效。以自首制度为例,见微知著,可以推知古代法律设计之精妙,体系之严整。
自首制度的原理,深嵌于“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之中。费正清认为中国的整个道德体系是以家庭为中心的,而不是上帝或政权。儒家理想中的社会格局,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由其延伸为国,以血缘作为纽带,通过宗法形成秩序,从而将国家的合法性建立于自然的血缘关系之上。君之于国相当于父之于家,每一个体则要对父母尽孝,对君国尽忠。君主“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对国家法律而言,对家庭、家族的维护就是对国家秩序的维护,因而政治上宣扬“以孝治天下”,法律上遵循“尊卑、长幼、亲疏有别”。因此,以家庭为中介而建立起来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并非古典自由主义所描述的对立紧张状态,而是君父臣子隐喻下的和谐共存。
维护家族秩序是清代法律的重要价值,但在威胁统治权等国家利益的情形中,亲属之间的互相隐匿则不被允许。因此,法律仅在一般犯罪场合中为行为人的自主选择留下了空间。然而,亲属相告的行为有违家族价值,一直为法律所禁止。衡山王刘赐谋反,其太子上书告发,使衡山王因事败自杀。太子的结局是“太子爽告父,不孝,弃市”。在自首制度中,亲属相告通过代首的制度设计得以缓和。因为在卑告尊的情形下,卑幼面临“干名犯义”的法律难题和坐视尊长受刑的道德诘难。法律提供了自相矛盾的行为模式,看似不能逻辑自洽,但这种两难境地,使行为人的选择实现了家国利益的两全。这一作用在司法案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自首制度在诸种法律价值之间不作妥协的同时,又发挥了发现犯罪和实现刑罚的实用效果,道德主义与实用主义并行不悖。
尊长告卑幼的案件主要包括父告子和父代子自首两种情形。乾隆年间,李作良因盗窃衣物等三个案件被杖责和监禁。其间李乘机逃脱后又从染铺盗窃八匹白布,此次被捕后被发配到广东充军。乾隆三十六年(1771),李因思念父母,再次逃脱,在中秋节夜里逃回家中。父亲李海知道其子有罪,便秘密嘱咐邻居代为看守,自己到县府告诉县官,并帮助抓获其子。按照清律,发配逃脱应判死刑,亲属首告效果等同于罪人自首。负责该案的官员奏请判其斩首死刑,他认为该犯多次盗窃,被发配后自己逃回,属于玩法,因而不能因其父首告而从宽。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旨,虽然犯人逃回家是不知悔改,但其父首告,按照法律可以宽减,因而应当从宽,仍然发配到广东。但该旨也警告犯人,此次免死已是法外开恩,只此一次,如果发配后再次逃跑,即使父兄首告,也不再宽减,并称这样办理更符合人情法理,之后的类似案件也都要照此办理。另一案例与本案情节类似,且被引作定案依据。周新淋盗窃后强奸物主,其叔父周歧山盘问了解情况后,到官府报告了事实,周新淋也对此供认不讳。因盗窃强奸,按照例的规定本应斩立决,但其叔父出首与犯人自首效果相同,因此免去所因盗窃之罪,按强奸罪判斩监候“斩监候”。以上案件中,犯罪者都因亲属告发自首而免于死刑。
父代子自首在司法实践中也同样获得了从宽处理。王廷吉向王敷恩借钱不被应允,想要强行借去其放在炕边的一千文钱,争执中王廷吉拿菜刀砍死了王敷恩。事后,王廷吉携赃逃回家中。其父王尔富看到他身上有血迹,还带有钱,就向他询问,王廷吉敷衍不说。第二天,王尔富听说王敷恩被杀害,料定凶手是自己的儿子,就向县官自首,之后王廷吉对事实供认不讳。依照当时的法律,杀人获得钱财,视为强盗,而强盗杀人不在自首范围内。因此王廷吉被判斩立决。但刑部审核后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的自首免所因之罪,应免除杀人所因的图财之罪,按照谋杀罪判决斩监候。本案中,由于自首情节,原判的立即执行死刑亦被改判为缓刑。此外,对于共同犯罪的家庭成员,一人自首则全家可减轻刑罚。于刘氏想要娶王于氏为儿媳,说媒不成,就带着儿子和工人抢夺王于氏回家。还没有办完婚礼,于刘氏就听说官兵前来查缉。由于畏惧,于刘氏跑到村外等候官兵并自首。司法官判决时认为,虽然一家人共同抢夺妇女,但于得成是听从母亲命令,工人们也听从雇主。根据亲属出首、犯人减免的判例,一家人都因于刘氏自首而被认定为自首,一律获得减免。
卑幼告发尊长的案件则尤能够体现前文提到的制度智慧。徐允武以五十两银子私和长子命案,次子徐仲威因兄弟冤死,将此事告发,但没有提到父亲收受赃银。地方官依照法律判徐允武杖责一百,徒刑三年。但刑部认为,该案并非一般关系,而是父子兄弟案件,应当权衡情法,合于人伦。徐仲威为兄弟澄清冤屈,成全了兄弟手足情谊,但也导致父亲因行迹败露被判处徒刑,于父子名义上有所损伤。徐仲威既然不能容忍兄弟死于非命,就更不应该忍心父亲遭受刑罚。如果按照原来杖徒徐允武的判决,不仅徐允武受难,徐仲威也会于心不安。因而,根据亲属自首如本人自首、子告父属“干名犯义”的规定,判决徐允武因其子“相告言”,而按自首免罪,徐仲威按“干名犯义”杖责一百,徒刑三年。这样,既成全了徐仲威的兄弟情谊,也使其与徐允武的父子恩义无所亏欠。
犯法的父亲丝毫无伤,揭露真相的儿子却无辜受刑,这一案件的处理尽管与“罪罚相当、罪责自负”等现代正义观念相悖,但契合于古代的法律体系和立法精神。法律为维护骨肉亲情的家族利益,规定亲属犯罪应当容隐,如果违反,就犯了“干名犯义”之罪;同时,法律又维护惩治犯罪的国家利益,规定自首免罪,亲属为首则罪人免罪。这样,就出现了如果选择遵守后者,就会违反前者的矛盾情形。也就是说,在父亲犯罪的情况下,儿子有两种选择:一是遵守容隐的规定,不揭露犯罪的事实,最后只能眼看着父亲被审判处刑而无能为力;二是告讦父亲犯罪,使得父亲可以因自首免罪,但代价是自己将因告诉行为被按“干名犯义”处罚。如此一来,对于家庭,次子虽因揭露犯罪身陷囹圄,却既可雪兄弟死于非命之冤情,又代父自首免除父亲之刑罚,不违孝道人伦。此案的最终判决考虑到当事人的特殊关系,实现了法律与伦理的兼顾与平衡。
父子兄弟为首的案件不止上述这种卑告尊的特别形式,在普通的为首案件中,犯罪者也依照律文和先例获得减免。犯人殴伤缌麻服叔致死,被押审途中逃脱,经过案犯的父亲自首被抓获。由于先例中没有押解审判途中逃脱的案例,司法官最后比照“一人越狱,半年内如系有服亲属拿首者,照本犯自首,仍依原拟罪名完结例”,依照“殴本宗缌麻尊亲属死者斩律”判斩监候,秋后处决。乾隆三十五年(1770),太平县军犯黄佑窃盗、“临时拒捕”伤人,被判决发边远充军。后他在发配途中逃回,本应按照先例“积匪滑贼发云贵两广充军,如脱逃被获,请旨即行正法”判死刑。但其母带同投首,符合“罪人自首”“法各减等”的规定,援引逃军姬三、王伦自投之案,将黄佑依照“杀伤人、盗首闻拿自首”例,拟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从以上案件的审判可以看出,司法官按照自首相关条文的规定,将亲属的告发行为解释为有利于犯罪者的自首行为,即为首,并使犯罪者因此获得刑罚减免。总体而言,我国传统立法体系和司法实际都致力于维护家族团结,通过司法实现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的法律统合。
——选自蒋正阳《改过自新:清代以来自首制度的表达与实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0月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