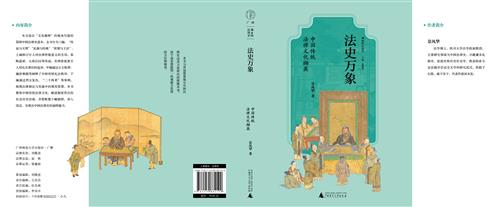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5-09-01
定 价:79.00
作 者:景风华 著
责 编:亢东昌
图书分类: 法律史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法律/法律史
开本: 32
字数: 170 (千字)
页数: 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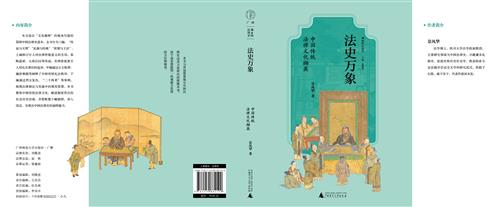
一部简明中国法律史读本,聚焦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解读制度背后的社会历史语境。全书以“传说与天理”“礼制与经典”“世情与王法”三部分,生动展现中国法律史的复杂面相。从皋陶造狱、大禹泣囚等神话切入,追问古人对法律终极意义的关切;透过公主称谓、嫡庶差异等规定,揭示礼法社会的运行规则;并借烈女复仇、“二十四孝”等案例,展现情与法的现实调和。书中尽可能多地捕捉在不同文化面相上的法律史碎片,并用诸多文物照片及古籍插图为读者提供生动直观的认知,致力于使本书成为对中国法律史怀抱兴趣者的入门读物。
景风华,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法律史,兴趣兼及礼制史、家庭史和历史社会学。
上 编 传说与天理
法律之祖:皋陶造狱与神兽决疑
大禹泣囚:传统司法的仁政基因
天命玄鸟:图腾崇拜与刑名从商
秦人尚六:数字中的天命密码
秋后问斩:天人之道与司法时令
人鬼秩序:传统法的幽冥镜像
中 编 礼制与经典
公主与帝姬:称谓背后的礼法规则
继承顺位:宗法制下的嫡庶难题
三年之丧:五服与法律的不解之缘
屈原之妻:文艺作品中的婚姻误区
《春秋》决狱:儒家经义的司法实践
《麟趾格》:法典命名中的政教之学
下 编 世情与王法
烈女赵娥:中国式经典复仇
“新律”出世:魏明帝曹叡的法律人生
族诛的缝隙:缘坐制度中的出嫁女
“恶毒”的继母:孝子故事背后的家庭法
明代契约:世情小说中的法律万象
清代儿童杀人案:年龄与刑罚的平衡之道
后 记
走进异彩纷呈的传统法世界
如果说历史是一具包罗万象的万花筒,其魅力不在于停留在过去的静止画面,而在于观察者每一次旋转圆筒时,各不相同的文明碎片在时光棱镜的折射下所呈现出的变幻莫测的多样性,那么中国法律史尤其如此。早在19世纪末,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盖在中文,物有是非谓之理,国有禁令谓之法,而西人则通谓之法”;“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译,学者审之。”因此,当我们拿着中国历史的万花筒去观察西学体系中law的对应物时,就不能只追踪刑制典章这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而要将对正义的理解、对恰当举止的评判、创建合作纽带的方式、定分止争的办法等隐藏得更深的文化碎片尽收于眼底。
这些恰恰是进入中国法律史情境的真正难点。当我们成为手持万花筒的观察者时,作为观察对象的历史镜像实际上就会成为“他者”—这本是人类学上的术语,用以指代同“我”存在文化异质性的原住民群体,因此人类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理解他者”。然而,文化异质性并不仅仅因为地域阻隔而产生,所谓“过往即异域”,纵然是在一个宣称文明从未断绝的国度中,过往时空中的价值体系、认知模式与生存经验同样构成了与当下存在本质差异的“他者世界”。当我们在一个“祛魅”的环境中将现代国家治理之下的权利义务分配模式视作理所当然时,传统时代的不少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也许只能落得“奇葩”二字的评价。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法律是嵌在文化当中的,甚至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那么,对传统法律的文化解释就能够成为跨越时空异域的桥梁,使我们进入自成体系的文化操作系统内部,观察古人如何在他们编织的意义之网上安放自身孜孜以求的秩序感。
这本小书是以文化解释的视角写就的简明中国法律史读本。在尽可能多地捕捉浮动在不同文化面相上的法律史碎片,用通俗的语言串联起中国法律史的主要知识点之外,本书还试图理解古人的理解,对特定制度赖以存续的社会和文化语境进行深度诠释,并用诸多文物照片及古籍插图为读者提供生动直观的认知,致力于使本书不仅可以成为对中国法律史怀抱兴趣者的入门读物,还可以为修习中国法律史的本科同学提供理解上的助益。
全书共分为三编。上编“传说与天理”在辽阔的宇宙图景中探讨古人对法律之终极意义的关切。正所谓“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中华民族的神圣历史描摹了治世的愿景,古来圣贤的所言所行树立了良法的标杆,王朝的命运和人世的秩序都被无垠的自然之道包容。
中编为“礼制与经典”。经典即神圣文本,是人类世界最早的理性化成果,它通过对“应当”的诠释,在丛林世界中率先打开了规则的大门,并持续对后世的任意性权力产生制约作用,是位阶最高的法律渊源。礼则通过将内心确信与行为守则合二为一的方式来塑造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从而缔造了独具特色的礼法中国。
下编“世情与王法”最终进入实体法的制定与实施环节。律典内部的逻辑结构、统治者的意志、政治需求、社会文化氛围、风俗民情……法律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在各种力量的角逐、各种思想的碰撞中进行平衡调适并试图在当时的情境下做出最佳选择,体现了一种现实的智慧。
当然,以上内容远不足以涵盖中国法律史的丰富性。本书与其说想要展示中国法律史这具万花筒内的图像本身,毋宁说更想提供一些观察万花筒的方法和视角。这样终有一日,读者们也能通过转动自己手中的万花筒,看到更加异彩纷呈的传统法的世界。
与以个案讲法律不同,本书侧重于以浅显而准确的文字展现法律史背后的文化史,让读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书中深入阐释了中华法系中的两组核心关系。
一是礼与法的关系。自汉代以来,法律便开始了儒家化的过程。魏晋南北朝以后,礼与法实现深度融合,“法律儒家化” 成为主流趋势。曹魏新律首次将“八议”入律,直接将礼所推崇的“尊尊”“贤贤”原则转化为法律特权,使贵族、贤臣等依礼享有的特殊地位获得法律认可;《唐律疏议》规定,“嫡、继、慈母,若养者,与亲同”,将礼所规定的 “继母如母” 纳入法律,规定继母与亲母在量刑中地位一致,实现了“礼的伦理”与“法的规则”的统一。
二是情与法的关系。今人面对的道德难题,古人同样遇到过,如子女为父母报仇,法律该如何判决?儿童犯了命案,法律又该怎么判决?继母虐待继子女,是否与生母同判?正是在这些棘手的难题中,中国古代法律的智慧尽显。如汉代的“亲亲得相首匿”制度,既认可“父子相隐”的亲情,又通过法律明确了“子匿父母,妻匿夫,勿坐;父母匿子,罪殊死,需上请”的范围,不让亲情无限突破法律底线;又如清代秋审制度中,“可矜”“缓决”类目中专门纳入“情”的考量:15岁以下少年犯若“被年长欺凌反击杀人”,归入“可矜”而减流;而除谋杀、故杀之外,15岁以下犯罪儿童,基本被归入“缓决”而监禁,既体现了“矜弱”“恤幼”之情,又通过逐级审转复核,保证了法律严肃性。
由此,法律不再是冷冰冰的法条,而是现实的考量和人性的温度。
继承顺位:宗法制下的嫡庶难题
在古装剧中,总少不了“宅斗”与“宫斗”题材,而嫡庶之分,则被视为导致这些钩心斗角的家庭结构性矛盾。因此,我们需要从西周这一礼制的成熟完备阶段开始,探究到底何谓嫡庶之制。
在此之前,我们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古人是闲得没事干,才对同父所生的亲兄弟进行区分,好引起他们之间的矛盾吗?如果不是的话,区分嫡庶到底为了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西周的宗法制谈起。宗者,尊也,弟敬兄之义,即在以同一先祖为源头、依照男性世系繁衍而成的宗族团体的同辈兄弟之中区分宗子与宗人,形成统率与服从关系,以便更好地进行宗族内部的事务管理和秩序建构。
依照《礼记·大传》的说法,宗法制下的宗族团体可分为大宗和小宗两个谱系: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
“百世不迁之宗”即为大宗。它是以本宗先祖为开端,以先祖的后子以及后子的后子代代相袭而形成的大宗子单线条传承体系。在理想状态下,这条直线可以延伸至百世、千世,乃至万世,所以叫作“百世不迁之宗”。
“五世则迁之宗”则为小宗。它是以自己为基座,向上数四代至高祖,然后分别梳理出继高祖、继曾祖、继祖、继祢四个小宗支系的正统继承人,也就是自己所需尊奉的小宗子。由于小宗最远只溯及高祖,所以到自己的下一代时,随着高祖发生变化,小宗支系也会产生变更,这就是“五世则迁”以及“祖迁于上,宗易于下”的道理。
无论是大宗子还是小宗子,理解它们的关键都在于一个“后”字。后子亦称嗣子,大约可以翻译成现代汉语中的“继承人”。但在传统语境中,“继承人”的含义要丰富得多,它意味着“正宗”的血脉传承、香火延续、家族荣耀与身份地位的接力。所以“后子”一词非常具有仪式感,它的祭祀意义与身份意义远大于财产意义。
而且,在所继之人为王侯公卿时,后子不仅能继承该支系的祭主之位,还因承袭父爵成为领地的新一任领主。其余未能成为宗子的儿子们则从宗子那里受封一片采邑,成为宗子的臣属。由此,宗子与宗人的宗族关系转化成了政治上的主臣关系,宗法制与分封制达成统合,形成了最为彻底的家国一体的政治统治秩序。
既然宗子如此重要,每个人又只能从自己的诸多儿子中挑选一位作为宗子(若无亲生子,则过继兄弟的儿子为后),那么当一名贵族妻妾成群、子孙满堂时,他该如何从众多儿孙中间挑出那个唯一的宗子?
想必大家早已知晓正确答案,挑选宗子的原则即为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又称立子立嫡之制,它是依照诸子的出生先后和生母身份,形成通往宗子道路上的次位排序。由此我们可以澄清两个问题:
第一,嫡长子继承制只是手段,成为宗子才是目的。故而从宗法的终极视角来说,只有那个能够承袭父亲身份的独一无二的正统继承人才是嫡子,其余的儿子不管生母是谁,都会成为庶子。
第二,生母的身份决定的是儿子们成为宗子的顺位而非资格。嫡长子继承制的含义是说嫡长子是通往宗子道路上的第一顺位,并不是说只有嫡长子才能成为父亲的正统继承人。倘若正妻无子,庶长子就可以依照顺位名正言顺地成为宗子和嫡支,并不需要电视剧中“过给正妻”“记到正妻名下”等毫无礼法依据的多余操作。
那么具体而言,在传统中国,儿子们的身份继承顺位究竟是怎样的呢?这问题可就复杂了,连古人都存在相互冲突的观点。典籍中明确提到的立嗣原则有以下三条:
大(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左传》
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公羊传》
父死,立嫡子;嫡子死,立嫡孙。—《五礼通考》
总结起来分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如果嫡妻有子,则在嫡出之子当中取其年龄最长者。至于该子是否贤能,或者是否有比嫡长子年岁更大的庶子存在,则一概不论。只有在嫡长子有废疾的情况下,才可以舍之而取其他。这一点几乎毫无疑义。
第二,嫡长子去世且没有留下嫡孙,正妻还有其他儿子,那么就从剩下的嫡出之子中再取一位年纪最长的。这一点也没什么问题。
第三,嫡长子虽然去世,但遗有嫡孙,且嫡妻还有其他儿子的情况下,立嫡孙还是立其他嫡出之子就成为主要矛盾。
按照《公羊传》的说法:“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这里的“质家”和“文家”,一般被认为是不同时期的“礼”的特点。比如殷商偏重“质”,周代偏重“文”,春秋又变周之文,从殷之质。但从根本上来说,“质”与“文”是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学说对于“礼”的不同侧重。质家亲亲,最为重视的是“质朴”的血缘亲情,因此以儿子为先;文家尊尊,最为重视的是上一代与下一代的传承,因此以孙子为先。毕竟在“文家”看来,只有嫡长子才属于本宗正统,其他嫡出之子虽然比起庶出之子要“正”一些,但毕竟仍属旁支,如果嫡长子遗有嫡孙,说明正宗有后,是以不可绝正统而厚旁支。
如果说周代属于“文家”,按照后世王朝纷纷向周礼看齐的态度,“嫡子死,立嫡孙”才是正统,只要嫡长子有儿子,其他嫡出之子都得靠边站。而且依照《仪礼》,如果嫡孙承嗣,那么在祖父去世的时候,嫡孙需要按照儿子的礼节服三年之丧,这在礼学上被称为“承重孙”。
但是立嫡孙的“文家”规则在现实中执行得并不顺利。究其原因,除了中国人对儿子的重视,大概还有继承人不宜过于年幼等现实层面的考虑。于是,南朝梁武帝长子昭明太子去世后,依礼应立昭明太子之嫡长子为皇太孙,但梁武帝思虑再三,还是选择册立昭明太子的同母弟为皇太子。此事虽在朝野引起不小的争议,但结果无可更改。
唐代律令中的立嗣规则是“嫡妻之长子为嫡子”,其后的顺位依次为:
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无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子;无庶子,立嫡孙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孙。曾、玄以下准此。(《唐律疏议·户婚》)
此条更近似于折中或者混搭。它虽然将嫡孙列为第二顺位来昭示对周礼的尊重,但正如条文中的“嫡子”仅指嫡长子,“嫡孙”更是被最狭义地定义为嫡长子的嫡长子。而嫡长子的其他儿子,哪怕亦是嫡出(嫡孙同母弟),其顺位甚至都落到了他的庶出叔叔之后。
王安石变法时进一步规定,如果有爵可传,方采用“嫡子死,立嫡孙”之制,如果是没有爵位的一般士大夫或庶民,在嫡长子去世之后按照人之常情由其他儿子依次承嗣就好,没必要由嫡孙承重。
在《红楼梦》当中,贾政的嫡长子贾珠去世之后,次子宝玉成了贾府公认的“凤凰”,而贾珠之子贾兰完全是个小透明。赵姨娘也认为只要害死了宝玉,自己的儿子贾环就会成为继承人,完全没把贾兰这号人物考虑在内,似乎说明儿子(哪怕是庶出之子)的继承权优先于孙子已成社会普遍观念。
第四,如果嫡长子去世,无嫡孙又无其他嫡出之子,或者嫡妻无出,则不得不考虑庶出之子。这时,主张“立长”的《左传》就同主张“立贵”的《公羊传》发生了冲突。
按照《左传》的说法,“立妾子之长,则无间于贵贱”,即不管生母是哪一位妾室,只需从一众庶出之子中拎出那个年龄最大的即可。如果有两人年纪相当,则选择更加贤能的那位;如果两个人各有长处,难以取舍,就在宗庙里卜一卦,听听祖先的意思。
如此简单明了方便易行,强迫症患者表示满意。唯一的问题是,“年钧”是什么情形?鉴于有学者认为,过生日的习俗应该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才逐渐在中国流行起来的,那么此处所谓的年纪相当,更可能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年甲计岁法,同年出生而已。不过,即便出现同日所生的双胞胎的情况,也完全可以用该条解决,所以网络传言由于无法从双胞胎中选择继承人,在双胞胎出生时必须弄死一个的说法并不能成立。
而关于“立贵”,何休在对《公羊传》所作的注疏中讲道:“礼,適(嫡)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嫡姪娣;嫡姪娣无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无子,立左媵姪娣。”
念起来有点像绕口令。要解释这个问题,须从西周的婚姻制度谈起。据《左传·成公八年》记载:“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也就是说,诸侯从另一诸侯国迎娶夫人,与女方同姓的其他诸侯需要派出两名姑娘“媵之”,而这三位姑娘又各有两名姪娣“从之”。如此一来,诸侯结一次婚,就可以得到九位贵族姑娘,即“一娶九女”。这九名同姓的姑娘即使来自不同族支,但归根到底也算姐妹宗亲。这样远在异国他乡也好相互扶持,只要其中任何一人生下儿子,都是姐妹团所有成员的共同依靠。但是她们之间依然存在身份位阶排序,即:嫡夫人﹥右媵﹥左媵﹥嫡夫人的姪娣陪嫁团﹥右媵的姪娣陪嫁团﹥左媵的姪娣陪嫁团。
而且,一个姪娣陪嫁团内部也得有个高低贵贱之分才是。对此,《公羊传》的说法是:“质家亲亲,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没错,“质家”和“文家”又出现了。质家亲亲,以关系同自己最为亲近的妹妹为先;文家尊尊,以小自己一辈的侄女为先。
如此看来,“立贵”比“立长”复杂得多,它要求在媵妾当中做出严格的身份位阶排序,然后以生母的身份作为选择宗子的第一标准,长幼的标准只适用于同母的兄弟之间。但是这样不仅麻烦,还有个潜在风险:由于先秦的姪娣陪嫁制在后世逐渐消失,媵妾的贵贱不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男方的宠爱,这种由“爱继”而引发的上位争宠恰恰是立嗣制度最为反对的。此外,在媵妾中详细区分贵贱也被认为意义不大。《左传》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公羊传》的立贵原则:“非嫡嗣,何必娣之子?”后世亦有礼学家发出质疑:“均妾庶也,而立其母之贵者可乎?”所以,无论从发展的眼光、实用的眼光还是学理的眼光来看,认同“立长”的礼学家都更多一些。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嫡长子继承制仅限于身份继承,这种宗人服务于宗子的身份制度在本质上是严格分封制下的产物。随着后世分封制的解体与大一统帝制统治之下一君万民的新秩序的建立,中国形成了与此种新政治结构相匹配的财产继承制度—诸子均分制,在小宗谱系内部的亲属网络中辨别不同亲属之间的亲疏、尊卑与长幼关系才是帝制时代家族秩序的核心。除皇室之外,嫡子的意义基本被局限于家族祭祀方面,历代律典仅有“立嫡违法”这一则条文与嫡庶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讲,当下的古装剧如此执着于嫡庶,实则是对中国帝制社会的理解有所偏颇。
——选自景风华《法史万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撷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9月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