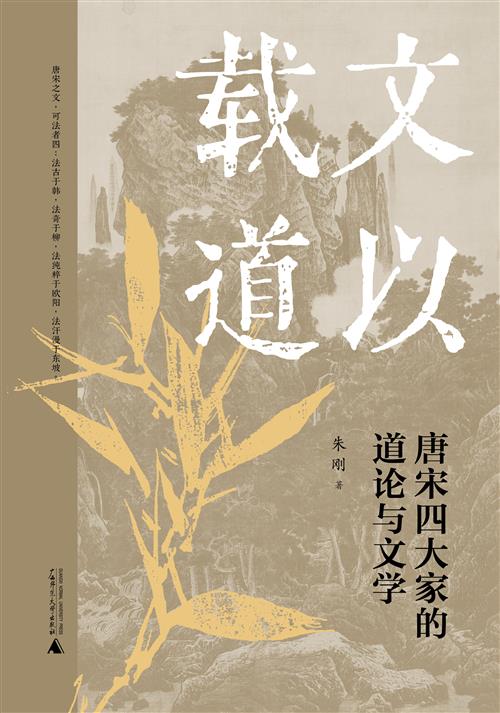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5-09-01
定 价:75.00
作 者:朱刚 著
责 编:周莉娟
图书分类: 文学理论
读者对象: 文学爱好者
上架建议: 文学/文学理论
开本: 32
字数: 240 (千字)
页数: 3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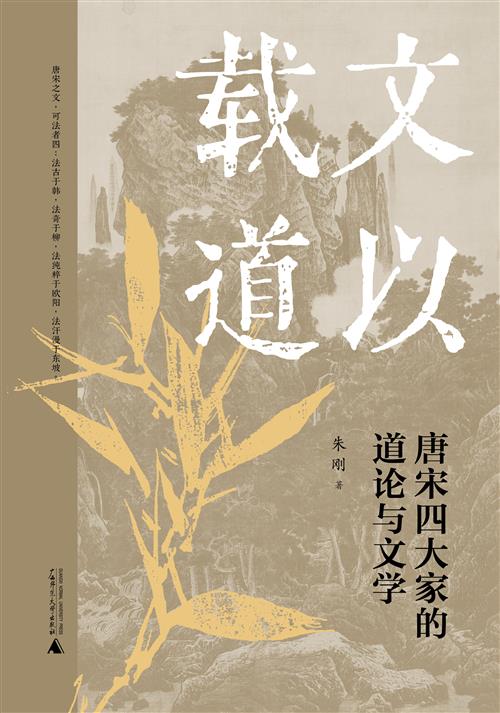
韩柳欧苏一脉相承的“道”是什么?他们又如何影响了理性精神与抒情传统的分野?
本书以道学为核心,梳理了从柳宗元、韩愈、欧阳修至苏轼的道学传承和文学创作,刻画了他们作为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的立体面相,由此解读唐宋两代的文学复古运动。作者围绕“文以载道”这一命题,辨析时代变革中的古文、骈文、诗、词各文体的发展,由此折射唐宋道学的发展线索。全书以史实为依托,借助哲学、政治史、思想史的视角,见证儒家道学如何复兴,又如何重塑士大夫精神。
朱刚,文学博士,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苏轼研究会副会长、《新宋学》主编。著有《宋代禅僧诗辑考》《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中国文学传统》《唐宋诗歌与佛教文艺论集》《苏轼十讲》等。
引 言
第一章 道学的兴起
第一节“中兴”思潮:道学兴起的时代背景
第二节超越“礼”的“道”:“道”概念的来源
第二章 从啖助到柳宗元的“尧舜之道”
第一节 啖助的《春秋》学
第二节 “尧舜之道”的社会历史意义
第三节 柳宗元的道论
第三章?韩愈《原道》的研究
第一节 道统论
第二节 “定名—虚位”论
第四章?欧阳修的文化功绩及其“至理”学说
第一节 “斯文有承,学者有师”
第二节 “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
第五章?苏学:自由与审美的道
第一节 “苏学”的历史地位
第二节 “苏氏之道”的三个层面
第三节 “苏氏之道”的审美内涵
第六章?“道”与各体文学
第一节 “文以载道”
第二节 “以文为诗”
第三节 “以诗为词”
附录? 傅璇琮先生“日晷文库”原序
再版前言
此书原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题为《文以载道——韩柳欧苏的道学与文学》,1996年底在复旦大学完成答辩,蒙导师王水照教授推荐,傅璇琮、吴先宁先生垂顾,收入“日晷文库·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改为今题,于1997年10月由东方出版社初版。
近年有一些师友嘱我修订再版,但当年提供给出版社的犹是手写稿,自己手头并无电子文本,不便修订,于是一拖再拖,迁延不决。现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张洁编辑协助,据初版录成了电子文稿,在此基础上加以修订,就方便多了。修订的主要对象是全书的注释。我们当年写学位论文,对引文出处的注释还不如目前这样规范,既然再版,自须按目前的学术规范重新处理。新世纪以来,唐宋文学的研究进展很快,二十多年前的旧著,即便我自己也能发觉许多错误不当之处,本不该再以敝帚示人,但考虑到学术进展是同行们逐步取得,无论小大,俱为历史,若径直改写旧著,深恐涂抹了进展的轨迹,或误后学,所以对于正文,除明显的错字漏词外,基本未加修订,仍存其旧。
实在感觉有必要加以说明的,则在注释中略予提及。总之,这次再版与初版相异的就是注释而已,未能积极创新,请求读者原谅。除了对出版社的好意,要再次表示感激外,此时此刻不能自已的,是对傅璇琮先生的怀念。
2023年 10月 3日
在朱刚教授看来,“文以载道”的实质是在文学中贯注理性精神,折射士人独立与文学自觉互为表里的历史现实,韩愈“长江秋注,千里一道”、欧阳修“容与闲易”如“秋山平远”、苏轼“万斛泉源,随地涌出”等文学盛景,就是文学中贯注理性精神的成果。
那么文学艺术一再强调的感性又如何安置呢?朱教授以苏轼的学生、高敏感人秦观为例,论证愁困的“词心”其实是宋人损之又损而不能化解的块垒,是人生非理性冲动的最后浓缩处。词心是秦观痛苦的渊薮,也是他的生命力所在,更是文学史的宝藏。
与秦观的内耗形成更鲜明对比的是韩愈,韩愈年轻时,曾三次上书宰相告饥寒、求汲引,这在后世一些士人看来丢脸的行动,其实有完备的“道学”体系支撑,这个体系可追溯至先秦“名实论”,深合儒家天人之辨和伦理观传统。韩愈的告饥寒求汲引,是对实施礼乐刑政的官员的监督规范,其干谒求职之道,也比后来理学家的“饿死道”更高级自洽。
士人的道学理论,不仅塑造了他们的文章气象,也确立了他们为官的气节,朱教授在苏轼的文章中提炼出作为抽象的“自然之总名”的“道”,从传世篇章《赤壁赋》引入,论证“盈虚者如代,而卒莫消长也”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终始”内涵一致,进而论证苏轼及其门生的大节观与其道学理论的内在一致性。本书论理磅礴浩荡,又处处圆融自洽,朱教授自身的写作也是在“于文学中贯注理性精神”的传统中吧。
本书底本是朱刚教授的博士论文,编辑读罢的第一感觉和豆瓣上很多初代读者一样——这是一部Dream Dissertation(梦之博士论文)。在上述种种出色的格局、观点和功夫之上,书中零星闪现的理想主义理论设计和“炫技”,洋溢着作者考据的快乐、思辨的快乐、表达的快乐。
总之,中国古代文论中并无“载道”与“言志”的对立;唐宋古文家讲“文以载道”,其“道”实指本其“所学”而独自树立的一家之言,与“言志”恰为同义;而唐宋古文大家之“所学”,虽有不出儒道之范围的局限性,却更重在自出新意。因此,“文以载道”的实质,是要求在文学创作中贯注理性精神。理性精神在文学领域的崛起,当然与宋学“主理”的倾向一致,它有可能给文学带来一些损失,因为理性思维可能会过滤掉某些诗性的智慧,但从更广的历史视野来看,它标志着我国先人在思维领域的一次革命,也标志着他们对文学的思考进入了一个更为自觉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文以载道”的主张,不仅没有抹杀文学的独立性,反而增强了文学的独立性。因为文学的真正独立,并不系于某种“纯文学”之观念,而是根本地来自士人立说持论的独立精神,这种精神,只能在一个士气甚盛的时代才会被认可为当然。从中唐士人激于世变,奋发自立始,到北宋时代,士气之高涨为历史上所罕见,其间虽隔了唐末五代宋初的一段“论卑气弱”之时期,但一直有人与衰颓的风气相抗争,至欧阳修、范仲淹一出,以“道”自立的士风又被激扬起来,终宋之世,蔚为大观。所以,文学的盛衰,并不像周作人虚构的那样,由“载道”与“言志”两种对立的文学观所导致,而是由士气之盛衰所决定。士气盛则文盛,“道”对于宋代文学的繁荣,是通过它激发士气来贡献其作用的。
唐宋古文的兴起,是古文运动的成果;唐宋道学的兴起,是儒学复古运动的成果。这两个运动本是同一个,所以,道学与古文可谓孪生的兄弟,在以后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也没有失去血肉的联系。道学的演进,表现为“道”概念之含义的不断丰富,从“善”而推究到“真”,又走向“美”,这个过程在韩、欧、苏三家道学上表现得极为典型;古文的发展,则表现为不同的艺术风格的相继出现,因为此种“成体”“载道”之古文是以“道”为灵魂的,所以“道”的含义的丰富,亦必对于艺术风格之形成产生影响,这里仍取韩、欧、苏三家为例来说明。
钱锺书先生《谈艺录》论李贺诗歌的风格,用了很多比喻,并将李贺与韩愈、苏轼对比:
此非昌黎之长江秋注,千里一道也;亦非东坡之万斛泉源,随地涌出也。此如冰山之忽塌,沙漠之疾移,势挟碎块细石而直前,虽固体而具流性也。
这些比喻都极为精彩,深得谈艺之三昧。钱先生在这里提及韩、苏,是拿他们做比照,来凸现李贺诗歌的独特风格,但所用的两个比喻,却极形象地概括了韩、苏古文的艺术特征。“长江秋注,千里一道”,是形容韩文气势之盛大,浩浩荡荡,一泻千里,内容既丰富,而行文亦充满力度。这当然与韩愈自己的艺术追求相符合,《答李翊书》所谓: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这种“气盛言宜”的境界,是其学养到了一定程度的产物,而“长江秋注”的艺术风格,则与其所表现的思想内容相统一。欧阳修的文章风格跟韩愈不同,这在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有很好的比较说明:
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
他指出韩愈文中含有大量的险怪内容,而其盛气足以驾驭之,使人震慑,不敢迫视。欧阳修的文章就不同了,他充满自信,平易地讲说着,语气委婉而道理穷尽,一点儿不感到困难,有一副“容与闲易”的态度。欧阳修虽然也主张行文要有“气”,但是他的“气”比较委婉平和,不像韩愈那样高潮迭起,要把读者一下卷进去;他是以更为理性的态度来渐渐引导读者走向他的结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而不是以气势来挟带人。欧阳修的古文,奠定了宋代古文流畅婉转、平易自然的总体风格,他曾经通过曾巩指点王安石,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要王安石别模仿孟子、韩愈的行文风格,而以自然为追求的境界。这说明,欧阳修的古文风格,是他自觉追求的结果。清代的魏禧在《日录论文》中把欧文比喻为秀丽的风景:“永叔如秋山平远,春谷倩丽,园亭林沼,悉可图画。”的确,欧文很像这样的风景画。
至于苏轼的“万斛泉源,随地涌出”,此语本是他对自己文章的评述,见于《自评文》一篇。那意思是说他蓄养充沛,悟性通达,故能随意挥洒,触处生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而表现一切内容都能得心应手,姿态横生。对于这样一种写作的自由境界,后人当然叹为观止,但只能形容,而很难从文法上进行总结,刘熙载《文概》说:
东坡文只是拈来法,此由悟性绝人,故处处触著耳。
盖其过人处在能说得出,不但见得到已也。
东坡最善于没要紧底题说没要紧底话,未曾有底题说未曾有底话,抑所谓“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耶?
这些话说得都不错,但一个学习苏文的人恐怕很难从这里找到门径。苏文的确多“拈来法”,的确能表达自如,也的确善于随题生发,但若学习者照此去做,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拿着一个题目随意说去,那恐怕并不能写得好。倒是从后人学习苏文失败的教训中,我们可以窥见苏文的长处。《日录论文》说学苏易流于“衍”,《文概》说“东坡文虽打通墙壁说话,然立脚自在稳处”,这说明苏文于表面上的泛衍外,内中自有精奥者存。据李之仪《庄居阻雨邻人以纸求书因而信笔》一文记载,苏轼作文时,并非提起笔来随兴而成的,他每每研墨甚久,下笔甚迟;据何薳《春渚纪闻》卷七“作文不惮屡改”条记载,苏轼对于自己的诗文,也不以一时快笔为定,而是勤于修改的。据此来看,苏轼写作时,运思颇为精心。他少年时的文章,仍有推求、经营的痕迹,高下抑扬,务为绚烂;中年以后,笔力足以称意,才达到了随物赋形,收放自如,而浑然无迹的境界;但到晚年万里南迁之后,可能是受柳宗元诗文影响的缘故,又转为精纯,不大再放笔驰骋,往往寥寥数语,而精神矍铄,光彩照人,使弟子们叹服其略无老人的衰惫之态,原来寓于泛衍之中的精奥到这时才脱颖而出。因此,苏轼的行文自如,本出于好学深思,其“万斛泉源,随地涌出”的艺术风格,是由刚健明锐的理性力量操纵而就的。他非但比韩、欧更为博大,实亦更为精深,非但更为自由,实亦更为果决。
这样,韩、欧、苏三人的艺术风格之形成,不仅出于他们个人性格上的偏好,而且无一不与各人的学养、自觉的追求和理性的思考相关。我认为,他们在道学上的不同造诣,是与他们不同的文风相一致的。韩愈的“道”是一种文化价值之“善”,它对于人们的影响力来自列圣相传的权威性,和某种拯溺救亡、力挽颓波的奋发感,以及“善”本身具有的激发正义感的作用。这样的“道”,被认为是由先圣传下来,不幸中绝,需要人们重新高举这个旗帜,把它光大起来的。所以,韩愈主张学“道”的人必须养成浩然之“气”,学养并重,以盛气来行文,才能带动读者进入圣人之道。于是,他的文风便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欧阳修虽也有激昂慷慨之语,但因为他的“道”已从文化价值更推本于自然、人情之“真”,以“至理”的面目出现在文章里,所以,他不必借气势压人,而可以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说道理,“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这样,他的文风便会平易自然,流畅婉转,而更具理性之风范。至于苏轼,他的“道”已是造化中所蕴含着的“美”的“无尽藏”,这种“道”无处不在,所以触处皆春;再加上他的“性命自得”的通达境界,远大的“器识”和越来越深刻的对人生的反思,最终觉醒为主体“性”的高扬,于是他的文风便不但有“万斛泉源,随地涌出”的挥洒之妙,并且能以理性的思致为其精神,一步步脱落华饰,现出气骨。如果我们以韩、欧、苏三家为道学和古文的三个发展阶段,那么,我们便能看到道学和古文同步发展的景观。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