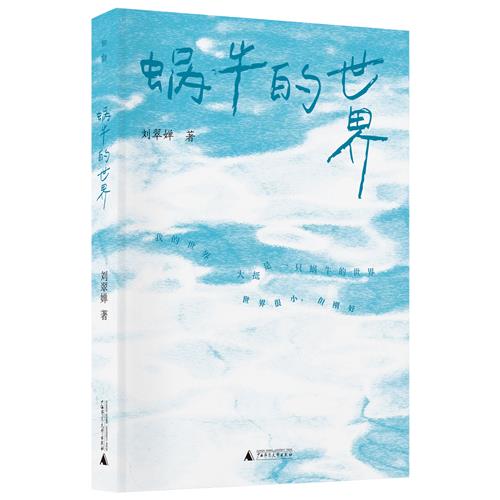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5-08-01
定 价:45.00
作 者:刘翠婵 著
责 编:邹婧
图书分类: 中国现当代随笔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文学/中国现当代随笔
开本: 32
字数: 130 (千字)
页数: 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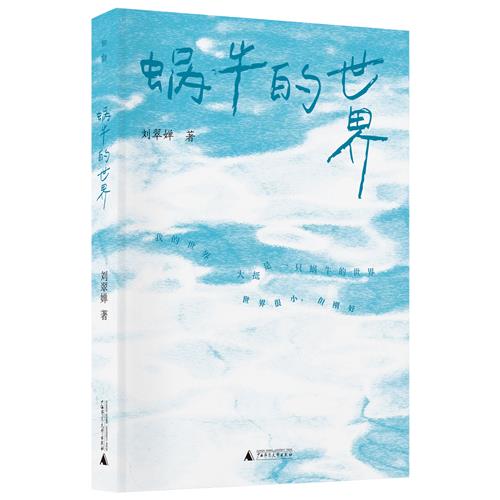
一个人要攒下多少生活的尘埃,才终于懂得人生的底色?
五个散文专辑,集结作者不同阶段的生命切片。从海岛漂到海岛,从渔船摇到山路,天各一方的至亲、漂流远方的好友、生之多艰的乡邻、萍水相逢的路人,无数的羁绊与重叠的宿命,一路走来的所失所得,伴着南方岛屿的海风和潮声,拼凑起一个人存在的世界。“我的世界,大抵是一只蜗牛的世界”“我飞不起来,只能仰望,只能想象,只能告别”。
刘翠婵,福建霞浦人。用文字呼吸的“蜗牛”。作品曾刊于《福建文学》《散文选刊》《南方人物周刊》等,入选《福建文艺创作60年选 ? 散文》《福建优秀文学70年精选 ? 散文卷》《2011年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100篇》。曾获福建省优秀文学奖。
第一辑 时时刻刻
木 菊
远远的台湾 近近的台湾
背包里有一只煎鱼
远 去
时时刻刻
倒 影
我哥刘伟雄
穿过风
在隐秘的水边
真先生
第二辑 伤 逝
伤 逝
山路又远又长
初春叙事
亲亲故乡草
清明乡间
庄稼开花
第三辑 尘的世
尘的世
不辞而别,或永别
野猪进村
从凌晨两点开始的日子
骨头坏了
路 人
扫 尘
银杏树下
第四辑 且行且温暖
太姥蓝
霞浦:慢游 漫游
嵛山岛:瓷器一样的时光
枫行杨家溪
山城老时光
东冲颜色
蝴蝶飞过
风从海上来
阳朔的雨 池上的云
细节里的台湾
半月里往事
神在人间
茶来茶去
春来黄花
且行且温暖
第五辑 所有的夜晚都会过去
在机场等候
愿你在天堂有爱人——给安徒生
没有星辰,也没有大海
啥叫好
宽 心
向内的疼痛——读谢宜兴的诗
剩在人间的凛冽——读汤养宗关于清明的诗
带着桃子的书去台湾
所有的夜晚都会过去——《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读后
天堂,有时只是一个村落
有诗的光亮也有草木的葳蕤
—刘翠婵和她的散文
一
这世间美好的文学是值得捧在手心里的。有些人热
闹地写着,名满天下,文章锦绣;有些人安静地写着,
默默无闻,文章也芬芳。无论热闹抑或安静,殊途同
归,莫不指向美好而智慧的缪斯女神。
于我这个职业阅读者而言,我更钟情于那些偏居一
隅、默默写作的人,他们没有累人的文学声名,也没有
疲于应酬的文学圈层,只有认真而纯粹地写着,日复一
日地写着。往往,他们的笔端更容易捕捉到那只时隐时
现于云端的文学神鸟,他们的写作更容易带给我们文学
的惊喜。钱锺书先生说显学易成俗学,作文章亦如此,
名家易成俗家。文学的本质多在于“隐”和“悟”—
隐于市或隐于野,低调而安静,一生体悟,一心琢磨,
写出那种充沛、智慧、灵动的文字来。
这里,我想谈的是刘翠婵和她的散文。翠婵住在海
边小城霞浦,素颜朝天,默默而纯粹地写着,如田间劳
作的农人一般,日出日落,不疾不徐,一丝不苟,心灵
手巧,写下了一篇篇闪动着诗的光亮、涌动着草木葳蕤
般生机勃勃的文字。我要感谢这些文字,它们让我品尝
到了文学的万千滋味。
二
写散文的刘翠婵,本质上是个诗人,或者说她的写
作表现出浓郁的诗性特质:对世间人事敏感、细腻,且
具洞察力,有悲悯之情;讲究词语和句子的节奏和气
息,自然流畅,文白镶嵌,有雅韵,语言上精挑细拣如
沙河里敬业的淘金人;她的文章篇幅都不长,多用短句
子,从句子到篇幅都有诗的精练。
黑格尔认为艺术的最高形式是诗。这里的诗,既指
诗歌体裁,也指艺术的造诣—诗性。昆德拉将诗性定
义为一部作品所能“接受的最高苛求”,他提出“小说
是关于存在的一种诗性思考”。那么,散文的诗性呢?
当然指散文的抒情性,语言的诗意化,更深层的是指散
文的灵性、轻逸之美,从语言到内容再到题旨的朴素、
脱俗与深刻。本质上,诗性是作品艺术性高低、强弱的
刻度,是艺术的终点站。
我以为,翠婵的写作为“散文的诗性”这一美学话
题提供了文本范例。这也让她的散文从众多冗长、乏
味、迟钝的散文中脱颖而出,有了自己的样子和情态:
用精练灵动的语言进入平常生活和起伏人生(分离的亲
情、远去的故乡、海岛的记忆、街坊的邻里等等),发
现并赋予它们别样的美感和精神力量,此即诗性。诗性
的光亮从她的文字中闪烁出来,不仅照亮了她的写作,
也照亮了散文这一文体。
仅以开篇之文《木菊》为例。“不知孤苦是不是最
苦的苦”,“从没把她与花联系起来,故去十多年后,
想起天上的祖母,始知木菊就是花,虽寻常,却有异
质,如她风雨一生”……这些句子很有诗性,简练,朴
素,读时有强烈的韵律感,是生活的结晶体,既是人事
的一种总结又是一种敞开,阅读的吸引力由此生成。写
祖母之作汗牛充栋,易乏味,但读过翠婵笔下的《木
菊》之后,觉得这位祖母必须写,因为作者写出了一位
我们熟悉又陌生、平常又卓越的大众祖母。此文最大
的诗性在于书写的异质化。一是写一位祖母经历的异
质化。她活了 93 岁,一生只两次远行,每一次都是天
涯海角般的远行,细节的独创性让祖母的人生故事充满
叙事张力。二是写一位祖母精神的异质化。她吃尽人生
苦,却一辈子活得硬气,作者写道:“想来祖母所有的
硬气,都用来抵抗世道的坚硬。”文章巨大的情感空间
和精神空间在这一刻释放开来,打动了我,我觉得这是
一位品性无比美丽的祖母,她身上散发着诗性光芒。
赋予经验和现实巨大而神秘的美感和力量就是一种
诗性的达成。
所谓散文的诗性,即“超越一切之上寻找美”(昆
德拉语)的意图。无疑,翠婵的散文拥有这种写作意图
和叙事美德。
三
翠婵写了乡间的草,写了海岛的风,有时写得小心
翼翼—有节制地寻找那些暗含着生命力的细节;有时
写得汪洋恣肆—任压抑的情感恣意迸发。无论哪一种
写法都暗含着生命力的坚韧和勃发。
她写道:盛开的草,漫山遍野站着,站成村庄一季
一季的依靠。
她写道:风忽而在山腰上漫游,惹起草浪连连,汹
涌着追逐着奔向山的尽头。
风吹草木,万物葳蕤。这成为我读完翠婵全部散文
之后留在脑中的一个阅读意象。为何会如此?大约因为
翠婵散文呈现出的流动感和生命力打动了我,它们如葳
蕤的草木一般,在文字间或“漫山遍野站着”或“汹涌
着追逐着”。
这是散文充满生机活力的表征。
散文写作的触角伸达之处,无非情感(亲情、乡
情)、历险(经历、经验)、论说(哲理、思考)、文史
(文化、历史)等几样,问题在于,如何把情写出真、
把经历写出险、把理写透、把文史写晓畅,才是散文之
职责。
翠婵的散文也没有离开这些题材,家族故事,故乡
记忆,城市生活,人物小记,诸如此类,但是她的散文
成功地避开了南朝范晔所说的“事尽于形,情急于藻,
义牵其旨,韵移其意”(意思是叙事流于表面,急于言
情而忽略文彩,辞不达意影响主题表达,过分注重音律
而妨碍文意)的写作险滩。翠婵的散文写作如在阳光下
晾晒被子,把漫长的岁月挤去水分,把繁复的人事撑捋
平整,把人生的感知晾晒开来。
翠婵说:“我的世界,大抵是一只蜗牛的世界。”但
是写作,让她把“一只蜗牛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宽广无
边的世界,那里是心灵的世界。因为她的文字里,不仅
有诗的光亮,也有草木的葳蕤。
翠婵的散文有了自己的艺术个性和辨识度,她的散
文会被更多的读者读到和喜欢。我期待她在写作上走得
更远,继续默默而纯粹地写下去。
石华鹏
(文学评论家、《福建文学》常务副主编)
2024 年 10 月 12 日? 福州黎明街
翠婵内敛,是那种感性与理性平衡的作家。越是到后来,她越惜墨如金,她的温情和悲悯,都藏在平静的叙述和平淡的文字后面。唯有细品,才能感受到她笔下的好处和妙处。
——邱景华(学人、诗歌研究者)
我一直在想象这样的散文:天真的、透明的。事物是新鲜的,眼睛和文字也是新鲜的。翠婵的散文提供了这样的初步样板。她在时时提醒我们,有一种可能性:她的文字不是从文字中,而是从事物、从感官中生长出来的。
——陈健(评论家)
刘翠婵的散文虽然数量不多,但她真诚地感受着土地上的众生相,在克制的书写中摆脱了一己悲欢的小情绪,看到时代变迁背后那个更为广大的艺术世界,从而打通了“小我”经验与“广大”经验之间的精神通道,成为众多读者的阅读期待。
——许陈颖(宁德市作协副主席)
在尘的世上,还有多少这样的蜗牛,驮着沉重的壳,活着,走着,缓慢但步履不停,捡拾一路走来的点滴碎片,拼凑起一方天地,刚好安身立命。
蜗牛的世界微不足道,只有乡间的草、海岛的风、卑微坚韧的凡人、悲喜交织的日常、一地鸡毛的生活,但芥子须弥,秋毫泰山。无数细碎的日常里就藏着生活的真相。
木菊,不是花,是我的祖母。
在人世九十三年,祖母只有过两次远行。一次从海岛到山区,一次从大陆到台湾。
祖母第一次远行时,已经六十岁。
1971 年除夕前日,祖母随一家人被遣离乡,舟车颠簸两日才辗转来到一个叫丁步头的地方。寒冷的冬夜,没有一户人家可以一口气收留七口人。次日,好心的村人合计,把牛牵出牛栏,铲走牛粪,撒上草木灰,牛栏就是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了。年迈的祖母和我们在牛栏里度过异乡的第一个春节。从此,他乡成故乡。
祖母生性倔,脾气烈。花甲之年经此周折,她的脾气变得更烈,以致至死不说异乡话,只说老家的福州话。村人总是用当地方言呼她“阿婆”,她一概以福州话回应。“硬”得村里人都有点怕她,有时他们会善意地嘀咕:阿婆真坏。
为了一棵竹子,祖母硬气得让村里村外的人都见识了她的“坏”。到村里次年,在村人的帮助下,家里有了一座属于自己的小房子,只是远离村人的房子,孤单地立在山边。父亲在门前屋后种下很多树,以及两丛麻竹。种竹是为遮风,也为砍柴时自家就有现成的竹篾捆柴火。有阵子,竹子老是被邻村的人偷偷砍倒做篾条。祖母气不过,有一天终于撞到一个偷砍竹子的人,她用故乡话直骂得那人灰溜溜地逃走。祖母一骂出名,但自此竹子却是安全许多。
祖母嗜烟。七十多岁时,她居然把烟戒了,起因是与父亲因抽烟起争执。当时抽的是水烟,母子共用一个水烟筒。一次,父亲劳作回来,发现烟板抽没了,暴脾气的父亲顿时发火。其实,那把烟筒并不是祖母和父亲专用的,过路的村人偶尔在家里歇个脚,也会抽上几口。那天路过的村人多了几个,就把烟抽没了。祖母听不得父亲的埋怨,硬硬地撂下一句话:“这辈子再也不抽了。”以为只是气话,但祖母第二天果真就不再抽烟,之后竟一口都没抽过。至于酒,祖母倒是一直喝到老,喝酒之风也硬朗。她不习惯小酌,很少就着菜喝,喝时少与人言语,小半斤酒,几口就饮尽,饮尽就离桌。
印象中,祖母有时硬得没有道理。古稀之时,姑姑病逝。消息从海岛传来,祖母如常扫地喂鸡煮饭拔草,她甚至没回海岛。偶尔,祖母会一边喂鸡食一边喃喃说:“人都死了,回去又有啥用……人要死有什么法子,早点死就少受罪……”她说给鸡鸭牲畜听,说给穿过院子的风听,说给柴堆上的猫狗听,却独独不说给人听。只是有时,在昏暗的屋角,祖母会摩挲着姑姑买给她的发簪出神,在无人处撇去眼角的泪湿。祖母有句口头禅——“好死不死”。难时苦时,她用这句话骂别人,也用这句话骂自己,似乎恨不得把自己咒死。
硬气的祖母在八十多岁的时候,遇上台湾开放探亲,她无论如何都要去台湾看大儿子。在山里过了二十多年,祖母的活动范围大抵是从家到一百多米远的桥头、三十多米远的水井,但是谁也无法阻止祖母人生中的第二次远行。
当时还未直航,从霞浦到福州,福州又深圳,深圳过关到香港,香港飞台北,台北又基隆……山一程水一程,小脚的祖母一步也没落下。深圳过关时,在汹涌的人潮中,白发的祖母又硬上了,不让二哥背她,执意自己走过去。苦过千山万水,这日思夜想的一步,祖母是怎么也不愿被背过去的。
不知孤苦是不是最苦的苦。
山中的日子,父母要下地劳动,孩子们要去上学,大多时候,祖母都是一个人守着孤零零的房子。无人言语的日子,收音机就成为最好的陪伴。祖母喜欢听戏,黄昏时咿咿呀呀的唱戏声从匣子里传出来的时刻,就是无人的世界里最热闹的场景。听多了,祖母也会哼几段,若是她哼了,定是暂时忘了现世的苦。
那时每天上下午都会有一趟来自县城的班车,在村口停几分钟。大约车到的时间,祖母就会到树下,张望着村口停车的方向。班车要是没停,她会念叨:“今天又没人……”虽然下车的都是陌生人,但看见有人下车,也成了祖母的念想。多少年里,祖母总是这样一个人在树下张望着。祖母很老的时候,满屋都是从外头捡回来的厚纸皮、小木板,母亲一回回把房间收拾妥当,没多久,祖母又捡新的摞在床底和房角,这些无用的东西,也许是她孤苦中莫名的陪伴。
想来祖母所有的硬气,都用来抵抗世道的坚硬。
……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