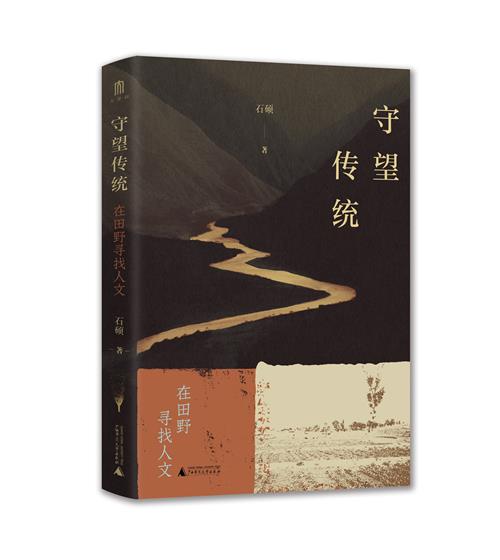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5-07-01
定 价:69.00
作 者:石硕 著
责 编:倪小捷
图书分类: 历史随笔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历史/历史随笔
开本: 32
字数: 260 (千字)
页数: 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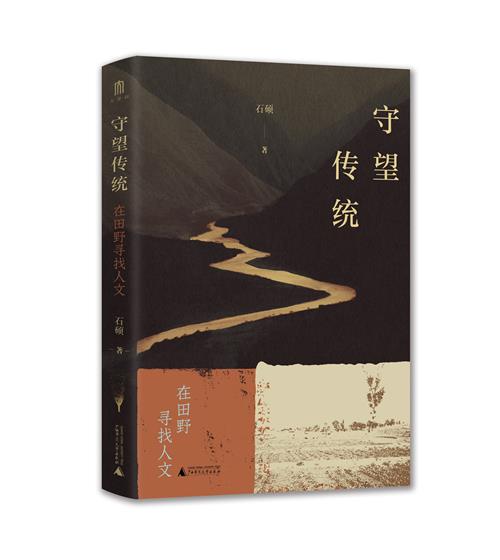
本书是一部踏遍山河写成的学术散记,凝聚了作者多年民族学研究与田野考察成果。全书分为 “大地经纬”“文明长河”“生命学问” 三篇,涵盖三江源人文地理、民族交流、城市历史、学人与教育多元主题,实证分析雪域高原生态、康定与成都城镇景观等自然人文风貌,对三苏祠礼制空间等建筑遗存进行历史考古,解读藏彝走廊族群迁徙、茶马古道等文化路线,从自然到文明再到生命,多维展现中国西南地域文化底蕴,揭示文明演进逻辑。作者以轻松笔触,采用散文化表达,将学术思想与个人感悟融合,传递对传统文化的守护与再发现。
石硕,1957年生,四川成都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涉及中国民族史、藏彝走廊、藏族史、汉藏关系史等领域。出版《青藏高原的历史与文明》《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等10余部学术专著,发表论文近两百篇。
上篇? 大地经纬——望天地
三江源:一个观察天人之际与生命意义的视角 3
318国道:中国大地上的一条美丽项链 11
雪域高原的世界奇观:石渠松格嘛呢石经城 15
漫谈藏族及其文化 20
方言多样性与经济活力——浙江经济的文化解读 48
“西出折多”有“燕尾” 56
茶在汉、藏之间 63
融通汉藏民心的“大先生” 69
相处之道:藏彝走廊对中国民族交往的经验与智慧 89
中篇? 文明长河——通古今
打箭炉:一座有“故事”的边城 99
从民族读杭州的背影 117
成都:一个延续两千年的民族协作传统——成都在汉藏民族交往中的地位与特点 121
如何分辨“历史”与“历史学” 138
传说与历史记忆:主体人群与边疆人群如何“与共”?——从“庄蹻王滇”和“打箭炉”说起 143
“亡秦者胡也”与秦筑万里长城——读李济先生《中国民族的形成》有感 158
释《老子》“见小曰明”——兼谈马一浮论读书的“明”与“昧” 165
苏东坡给我们留下什么? 172
下篇? 生命学问——见众生
人类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181
围炉夜话:如何做中国民族史研究?——马长寿、周伟洲治民族史的启示 206
记民族学家李绍明的为人与为学——李绍明先生十年祭 224
一件难以忘怀的事 234
问世间,情为何物? 238
年轻人看我们,比我们看他们要清楚 245
我对教师角色的点滴感悟 251
赠给历史系毕业生的三句话 255
自序
本集子的出版,于我而言,意义非同寻常,是我写作生涯的一种拓展,俗话叫“换频道”——这是我第一本“学术散记”。
和以往出版的诸多学术专著或论文集不同,这部集子有两点让我喜欢:一、无须板着“学术”的面孔,行文轻松、自由;二、无须考虑为科研考核增加筹码之类,写作时心灵比较自由、洒脱。
集子所收文章主要有三个来源:
第一,多年来,应一些刊物之邀如《中国国家地理》等写的文字。刊发后便置之脑后,未再理会。
第二,虽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但比较通俗,有可读性,读来亲切,接地气。
第三,近年东跑西跑,有一些见闻和感触,随手记下,积少成多,也不在少数。
因长期做学术研究,秉性难移,这些文字或多或少带有些“学术”“思想”的痕迹与味道,称其为“随笔”似不太妥帖。一位学界高人阅后称它为“学术散记”,我觉得很准确。其实,这些文字的写作比较随性,知识、思想、感悟、认知、情调尽在其中,随笔挥洒,轻松自如,见微知著,是我很喜欢的一种写作。
读清样时,心中掠过一丝疑虑:读者会喜欢这些没实际效用,供茶余饭后打发时光的文字吗?不得而知。不知谁说过,作品一旦完成,就和作者没什么关系,就像母鸡下蛋,人们只会品评蛋的好坏,并不关心生蛋的母鸡。所以,这些文字究竟如何,留给读者评判。
石硕
2024年8月27日于江安花园
《守望传统:在田野寻找人文》是一本融汇学者石硕多年民族学研究与田野考察的学术散记,如果你是《中国国家地理》的爱好者,那一定不容错过。书中不仅呈现了壮美的松格嘛呢石经城、“跑马溜溜”的康定、故事深厚的打箭炉,还有成都、杭州鲜为人知的一面。这是一场穿越青藏高原的广阔旅程,一场跨越古今的自在探索,更是一次对汉藏文化的追寻。
你会从其对广阔世界的深切关怀中受益良多,领略到“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传统与现代交融互补”的文化内涵。揽天地于怀,通古今之变,照见众生百态。相信读完这本书,你会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中华民族以及我们的文化魅力。
这是一篇把地名传说写成民族交往史的精彩长文,是能够反映本书内容主旨的代表性选篇。作者从康定“跑马山”“打箭炉”两则耳熟能详却经不起考证的“误读”切入,层层剥笋:藏语“帕姆山”如何被汉人听成“跑马山”、藏语“打折多”怎样在汉人移民口中变出诸葛亮“造箭”故事,并衍生出根本不存在的“郭达将军”。文章揭示,这些看似荒诞的附会,其实是清代汉人移民把异乡“变故乡”的心理工程:借藏族神山、地名,植入自身文化符号,既缓解思乡焦虑,又达成与藏民的“共享—求同—互尊”。作者更以“锅庄”贸易形式为例,呈现汉藏双向浸润的日常细节,反驳单向“汉化”旧说。
——编者按
打箭炉:一座有“故事”的边城
“故事”一词,颇值得玩味。从字面上看,它是指过去的事,但实际含义则要丰富和有意味得多。我们常说的“讲故事”或某 人某事“有故事”,这里的“故事”,大多指一些有内涵、有趣味 的情节或事情。
记得一次与几位学界朋友吃饭聊天,一位曾做过大学校长、颇有见识的朋友提出一个让人称奇的观点:判断一个学者成熟与否,标准很简单,看他是否“有故事”。结论是,一个“有故事”的学者才是成熟的学者。他举了一个例子,他做校长的学校有一位著名前辈学者,早年留学哈佛大学,是国内某领域开拓者,桃李满天下。在一个轻松的场合,有同事笑问他在家中地位,该先生说:“我家的大事由我定,小事由夫人决定。”同事接着问:“你家哪些是大事?”该先生答道:“我家就没有大事。”大家听完哄然一笑。朋友说这就是“故事”。并说据他留心观察,大学里的一些著名学者,大都伴随着这样一些私下为人们津津乐道、不 断传播的“故事”。当时听完就罢了,并未怎么往心里去。但闲下来细思,却慢慢品出其中一些道理。“故事”大多指一些有趣味、有意义且超乎寻常的事,能做出有“故事”的事、说出能成 为“故事”的话之人,或许具有某些不同寻常的智慧与见识。我想,这大约是产生用是否“有故事”来判断一个学者成熟与否这 一认识的原因吧。
如此看来,常言说的“有故事”,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词。因为“故事”往往意味着是否有趣和有意义。有趣和有意义的事不 仅令人长见识,更能启迪人的智慧。所以,古今中外,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莫不喜欢“故事”,喜欢“有故事”的人、事和地方。
提到康定人们并不陌生,一首广为传唱的《康定情歌》已让这座位于成都平原之西的边城闻名遐迩。康定处于传统的汉、藏分布边缘,也是汉、藏民族的接合部,是一座兼具汉、藏文化特点并有着浓郁特色的边城。康定给人的印象是喧嚣、拥挤但又充 满活力。在纵贯城市中心的繁华地段,一条清澈、奔腾、喧嚣的 河流以极快的流速穿城而过,这在中国的城市中恐怕独一无二, 是康定城最独特的一道风景。但若论康定之魅力,却不在自然,不在于其地为交通咽喉,也不在于《康定情歌》所唱“康定溜溜的城”,而在于它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先从康定的跑马山说起。《康定情歌》第一句歌词是: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这句简单、悠远的歌词,激起人们对康定的无限遐想。20世纪 90年代初,我第一次去康定,朋友带我去登跑马山,当时还没有索道,山很陡,但树木葱茏,风景极佳,我们沿着陡斜的山间小 路一路上行,狭长形的康定城全貌逐渐清晰地尽收眼底。当终于到达目的地,却发现被称作跑马山“跑马”的地方并非辽阔、空旷之地,更不是飘着“一朵溜溜的云”的一望无垠的草原,而只是一个山间小平坝,完全不适合“跑马”或“赛马”之类。或许为了与“跑马山”名称相符以满足游客的期望,小平坝上确有商家弄了两匹马在坝子上转圈,这主要成为小朋友或部分成年游客的娱乐项目。下山路上,朋友告诉我,很多外地游客和朋友到康定,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地去上跑马山。对跑马山,康定人有一个很诙谐的总结:“不上跑马山会遗憾,上了跑马山也会遗憾。”“不上跑马山会遗憾”比较好理解,因为不上跑马山,就无法兑现我们被《康定情歌》所激发起来的对跑马山的无限遐想。但上了跑马山才发现,这并非人们想象的辽阔、空旷的跑马之地,故也会遗憾。
下山后,我一直困惑于一个并不适合跑马的山为何会被称作“跑马山”。专业习惯使我忍不住去查阅资料,一查才知道,所谓跑马山,当地藏族人原称“帕姆山”,“帕姆”(phag mo)又作“金刚亥母”,是藏传佛教中一位重要本尊,被尊为女性本尊之首。“帕姆山”乃藏族人的一座神山,因清代管辖康定一带的明正土司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在山腰台地供奉山神,当时康定汉人 已较多,汉人遂依其音将“帕姆山”称为“跑马山”,这才有了 《康定情歌》唱的“跑马溜溜的山”。
对这则故事,一般多认为是由汉、藏民族之间的“词语误读”所引起,是汉人将藏族人所称“帕姆山”读作了“跑马山” 的一个有趣味的误会。从表面上看,这大体没有错。这也是我最 初的认识。但后来,有关这类故事的一系列令人惊奇的发现,让我改变了看法。我发现,所谓“误读”,其实是一个错误判断。
先从康定的地名说起。康定原来并不叫“康定”,而叫“打箭炉”。今天康定城区仍叫“炉城镇”,系“打箭炉”地名的孑遗。“打箭炉”地名由何而来?今作为康定门户的泸定桥头矗立着一尊高大石碑,这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泸定桥落成时, 康熙皇帝亲自为泸定桥落成撰写的一篇碑记,全称是《圣祖仁皇帝御制泸定桥碑记》。碑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打箭炉未详所始,蜀人传汉诸葛武乡侯亮铸军器于此,故名。这说明,至少在泸定桥落成时已有“打箭炉”这一地名。且碑记中特别提到“蜀人传汉诸葛武乡侯亮铸军器于此”,这是对“打箭炉”地名含义的诠释。也就是说,“打箭炉”得名是因为诸葛亮铸军器(“造箭”)于此,而且此说法出自“蜀人”。这是我们从康熙碑记中得到的信息。
那么,“打箭炉”真是因诸葛亮“造箭”于此而得名吗?查阅史料才发现,“打箭炉”的地名早在明代已经出现。《明实录》中记载了一件事,洪武十五年(1382年),元朝时曾任四川分省左丞相的剌瓦蒙(应为蒙古人)派一名叫高惟善的使臣前往明都城应天,目的是把元朝所授银印上交明朝,以示“弃元投明”,归顺新王朝。记载中提及高惟善一行是“自西番打煎炉长河西来朝”。“长河”指大渡河,“长河西”则指大渡河之西。文中提到了“打煎炉”这一地名。这一事件在《明史》中也有记载,称高 惟善是从“其地打煎炉”来朝,确证“打煎炉”是一地名。可见,《明实录》《明史》中已出现了“打煎炉”地名。
清初,蒙古和硕特控制康区之时爆发了“三藩之乱”。割据云南的吴三桂势力延伸至滇西北,且与西藏多有来往,引起清廷不安。为此,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廷发了一道谕令,要求派员加强对“打煎炉”一带的侦察和防御。此谕令中,把“打煎 炉”写作“打折卢”。由此可见,在康熙《御制泸定桥碑记》以前,仅写作“打煎炉”和“打折卢”,并无“打箭炉”的写法。
那么,“打煎炉”或“打折卢”是何意?显然,无论是“打 煎炉”还是“打折卢”,均不存在汉文字面的含义。可以肯定,二者均源自藏语地名的译音,属汉字记音的地名。对此,民国时期学者已有一致看法:该词“系藏语‘打折多’之译音”。藏语称两水交汇处为“多”(mdo)。打煎炉正好处于源自折多山之折曲(折多河,曲为“河”)与源自大炮山之大曲(打曲,即今 雅拉河)交汇处,故被藏族人称作“打折多”(dar rtse mdo)。所以,明代和清代早期文献中出现的“打煎炉”或“打折卢”,正是藏语“打折多”的译音。
“打折多”在明代兴起主要与两个背景有关。第一,从明中叶起,青藏道因受西北蒙古诸部威胁,屡遭劫掠,明朝为“隔绝蒙番”,从明中叶起规定涉藏地区僧俗朝贡使团一律须经由川藏道往返,川藏道必经打箭炉,这使打箭炉的交通咽喉地位开始凸显。第二,明末蜀乱及张献忠入蜀,使蜀人大量西迁避险。避险的蜀人大量越过大渡河,进入打箭炉一带。这使汉藏茶叶贸易市场逐步从大渡河东岸向西岸转移,打箭炉作为汉藏新兴茶叶贸易中心的地位开始确立。
为何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廷谕令中尚称“打折卢”,时隔26年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却变成了“蜀人传汉诸葛武 乡侯亮铸军器于此”的“打箭炉”呢?原因是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1700年当地发生蒙古营官杀害明正土司事件,为维护当地政治秩序,清朝发动“西炉之役”,从蒙古和硕特部手中夺取了对打箭炉的直接控制权。二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在大渡河上建成了泸定铁索桥。这两个因素造成大批蜀地汉人涌入打箭炉。正在此背景下,“打折多”开始变成了“蜀人传汉诸葛 武乡侯亮铸军器于此”的“打箭炉”,故“打箭炉”的称呼显然 出自迁入当地的蜀地汉人的“发明”。
既然“打箭炉”是因“汉诸葛武乡侯亮铸军器于此”得名,该传说在蜀人中就被继续演绎。于是产生了诸葛亮曾派一名叫“郭达”的将军在当地造箭,郭达将军死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在打箭炉城中建起了“郭达将军庙”等一系列传说故事。为配合这些传说故事,使之更真切,城边的一座山被命名为“郭达山”,城中也就出现了一座“郭达将军庙”。
“郭达”何许人也?遍查《三国志》等史籍,诸葛亮麾下及同时代并无一位叫郭达的将军,可见“郭达”并非真实历史人 物,而是出自虚构。既然“打箭炉”是一个望文生义附会而来 的地名,何来“郭达”其人?稍做调查才知道,“噶达”(mgar ba)原是当地护法山神的名称,所谓“郭达山”原是当地的“噶达”神山,城中的所谓“郭达将军庙”,当地藏民称“噶达拉康”(mgar ba lha kang),是敬拜“噶达”山神的庙。有意思的是,有关噶达山神的来历,据当地藏族人的传说,很久以前,一铁匠在西藏习法,奉命来打箭炉,修成正果,幻化为铁匠化身的神。藏语“噶达”正是“铁匠”之意。于是,噶达山神的“铁匠”身份成为汉人衍生郭达将军“造箭”传说的蓝本,也成为衔接汉藏传说、信仰的一个关键环节。
以上这些,均是打箭炉兴起过程中,因大量汉人移民进入而 出现的独特文化现象。毫无疑问,无论是“打箭炉”地名,还是“郭达山”和“郭达将军庙”,均出自汉人移民的主观建构。那么,这些主观建构有什么作用?对此,开始我不甚了了,亦未深究,只觉得这些“故事”很有趣。直到2017年我在雅安一个藏茶 厂的宣传栏上看到这样一段文字,才恍然有所悟:“雅安”是藏语,意思是牦牛的尾巴。如果把青藏高原比作一头牦牛,雅安就是这头牦牛的尾巴。由此可见雅安是当时涉藏地区的边沿。三国时,诸葛亮南征与孟获交战,就 在雅安。七擒七纵使孟获心服口服,双方商定,孟获退一箭之地。谁料这一箭却从雅安“射”到了200多公里以外的康定。这是诸葛亮谋略过人,早已暗中派人在康定安炉造箭,然后将所造之箭插在一个山顶上,孟获吃了哑巴亏,无奈还雅安于蜀国,退到了康定以西,所以康定会取名为“打箭炉”。 藏茶厂老板祖辈均从事藏茶生产,他是第七代传人。若按30年为 一代计,大体可上溯至乾隆时期。他称此传说系祖辈所传。因清代藏茶主要经打箭炉销往涉藏地区,此传说当年在打箭炉地方流传甚广。这是一个典型的民间传说版本。“退一箭之地”是发于诸葛亮征南中的传说,将其移植于打箭炉实属荒谬,但这个移植对我们理解当年进入打箭炉的汉人移民为何会围绕“打箭炉”地名附会诸多传说却十分关键,这些传说实际上在强调和隐喻一个事实:打箭炉并非“异乡”,早在诸葛亮时代就已是汉人的地界。这样做并非要和藏族人争地盘,而是对汉人移民可以起到化“番地”为“故乡”、化“陌生”为“熟悉”的心理作用。打箭炉的汉人移民主要来自蜀地,诸葛亮是蜀地家喻户晓的人物, 也是典型的汉人符号,把自己最熟悉的文化符号带到新的环境,是移民化解、疏导客居异域“思乡之愁”和弱势心理的一剂良方。对“打箭炉”地名的塑造并演绎诸葛亮时在此“造箭”“让一箭之地”和“郭达将军”等传说,对汉人移民来说正有着这样的功能。
我国是一个史学传统深厚的国度,因传统史学对史实真实性的强调往往远大于史实意义,故清代民国的文人学士多从传统史学立场出发,认为这些故事纯属“齐东野语”、荒谬不经,多持不屑与排斥态度。如清末黄懋材认为:“(打箭炉之名)附会无稽。愚按:唐宋之世,吐蕃入寇,斯为要道,或尝造箭于此,至于丞相南征,由巂入益。程途各别,非所经行也。”任乃强也指出:“清乾隆时,始有人捏造武侯遣将军郭达造箭于此之说。世多仍之,荒谬之甚矣。”从其所用“附会无稽”“捏造”“荒谬之甚”等词语看,他们对这类传说故事明显持负面看法。在缺乏人类学及现代学术视野的条件下,这些看法原无可厚非,但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却影响了后人对“打箭炉的故事”背后之意义的思考和探索。
其实,历史从来就包含“真”和“伪”两个部分。前者指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后者指经过历史当事者或前人主观建构而呈现的历史事实。两者一个真、一个假,一个客观、一个主观, 但都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上,前人遗留下来的那些明显属于主观建构的传说、附会,看似荒诞不经,却往往蕴含丰富的思想资源、观念和意义,同样是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的重要史实和素材。例如二十四史帝王本纪中,有大量关于各朝帝王尤其是开国皇帝出生前后出现种种祥瑞的记述,它们明显出自附会。从传 统史学观点看,肯定是“伪”。但这“伪”既是古人所造,也是当时历史的一部分。重要的是,古人为何附会?这些附会有何功能?它们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根植于什么样的思想观念与社会土壤?这些都是更具意味的问题,对理解当时社会及其思想观念同样是重要的史料。
毫无疑问,清代以来汉人围绕“打箭炉”进行的一系列主观建构,是近代汉藏大规模杂糅、交融背景下出现的一个生动而有趣的文化案例。此案例非由专家设计,而是出于民间的自发,甚至可以说是民间自发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的产物,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其所包含的文化策略、智慧,尤其是其带来的巨大效果,却着实令人惊叹。细细思量,该文化案例至少蕴含了有关民族交融与文化整合的两个重要规则:
一、通过“借用”达成“共享”和“求同”。汉人的一系列主观建构并非出于“误读”,而是集体意识下的“有意附会”。这种借用藏族人的地名、山神名来植入自己的文化因素的做法,既能满足汉族移民自身的心理需要,又能达成与藏族人“共享”,并通过“共享”与藏族人“求同”。这实在是与藏族人进行文化整合的高超策略和民间智慧。我想,这也许正是汉人绝不“另起炉灶”,一定要借用藏族人已有概念来说事儿的原因。
二、在“共享”和“求同”过程中,给对方以足够的尊重。 汉人尽管称“噶达拉康”为“郭达将军庙”,却接受“郭达神像 着藏式服装、骑山羊”的藏式样貌;尽管称“将军会”,但抬神像出巡者必为藏族青年。也就是说,汉人在“借用”和“共享”的过程中,对藏族人的信仰始终予以尊重和维护。如此,才最终形成汉藏同祀一庙(藏族人的“噶达拉康”亦同时为汉人之“郭 达将军庙”)、共敬一人(藏族人之山神“噶达”亦同为汉人之“郭达将军”),正是有了这种宗教感情的融通,才发展出藏汉民众同祀共欢、汉藏文化充分整合的“将军会”。
当然,有一点不容忽视,汉人的主观建构之所以能在汉藏文化整合及与藏族人互动上产生巨大效果,与藏族人的主观愿望有直接关系。打箭炉是因汉藏茶叶贸易而兴,从泸定桥建成以后,逐渐成为新的汉藏茶叶交易中心。汉人将茶从雅安运到打箭炉,卖给藏族人,再由藏族人将茶叶销往青藏高原各地。但是,打箭炉汉藏茶叶交易却不是通过沿街集市来进行,而是采取了一种独 特交易方式——以“锅庄”为中心的贸易方式。这里所谓“锅 庄”,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锅庄”舞蹈,而是指一种特殊的进行汉藏茶叶贸易的客栈。汉商将茶叶运到打箭炉后,入住固定的自己所熟悉的“锅庄”客栈,茶包也堆放在“锅庄”里,马也由“锅庄”照看喂养,汉商及其随员在“锅庄”里不仅吃住免费,还会受到热情周到的款待,他们只需要告诉锅庄主自己这批茶的销售价格。锅庄主即为其八方寻找买主,买主找好后,双方 进行交易,锅庄主按事先的约定“抽头”(提取佣金),藏商派人 将茶叶运走。这是汉藏茶叶的主要交易方式。过去打箭炉曾有48 家锅庄,锅庄主最初均为藏族人(后来才有汉人“锅庄”),且多 为女性,她们大都热情干练,熟知汉藏文化及习俗,人情练达且善于沟通,穿梭和游说于藏汉客商之间,如鱼得水,八面玲珑,人缘甚佳,成为汉藏客商之间特殊的联系纽带和润滑剂。这种以锅庄客栈为中心的汉藏茶叶贸易方式,不但是以信誉为基础,也以汉藏之间的情感沟通为纽带,是一种“和气生财”的典范。所以,这种以锅庄客栈为主的汉藏茶叶贸易的方式,不但造就了大批像锅庄主一样在藏汉商人之间如鱼得水、应付自如的“媒人”,也使打箭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普遍呈现出汉藏民族及文化相互濡染、相互接纳的情形。民国时期对这方面情形已多有记叙,如称当地汉人子女多有“习于穿蛮装的”,“在这地方生长的小孩,差不多没有一个不会说蛮话、唱蛮歌的。其中有的一口蛮话,和康人没有分别”。又记康定藏族人则多能说汉话,“富家生活也很优裕,家里用具,多同汉人”。事实上,打箭炉能够形成汉藏同祀一庙、共敬一人并在宗教感情融通基础上发展出藏汉民众同祀共欢的盛大“将军会”,正是以汉藏民族及文化的相互濡染、相互接纳为其社会土壤。
对康定的汉、藏混一情况,民国时曾有人发出“多数康人已经汉化,或是少数汉人已经康化”的感慨。其实,这是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以“汉化”作为汉族与少数民族交融之最终结果的一种思维范式,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打箭炉的故事”生动地证明民族间的交融与文化整合从来是双向性的。该案例揭示了民族之间交融与文化整合的三个核心要素——相互需要、相互求同、相互尊重。历史上,汉人进入边疆地区并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交融与文化整合,是造就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途径。但过去人们容易站在汉族中心立场,往往习惯于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融和文化整合简单归结为所谓“汉化”。这种认识的偏颇与局限性不言而喻。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早已提出应注意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文化影响的双向性,他指出:“民族与民族接触之时,相互影响吸收和采借经常是双方面的事。汉族文化固然影响少数民族,但其间接受他们文化影响的也应不在少数。”顾颉刚先生亦指出:“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汉人的一定比较汉人原有的多得多。”其实,民族的交融与文化整合是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并非简单的什么“化”或“谁化谁”所能概括。当下,提倡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这正是基于民族平等观念的科学、客观表述,它表明民族交融的结果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对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接触,我们应跳出“汉化”“夷化”的窠臼与思考范式。以上是“打箭炉的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
节选自石硕《守望传统:在田野寻找人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7月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