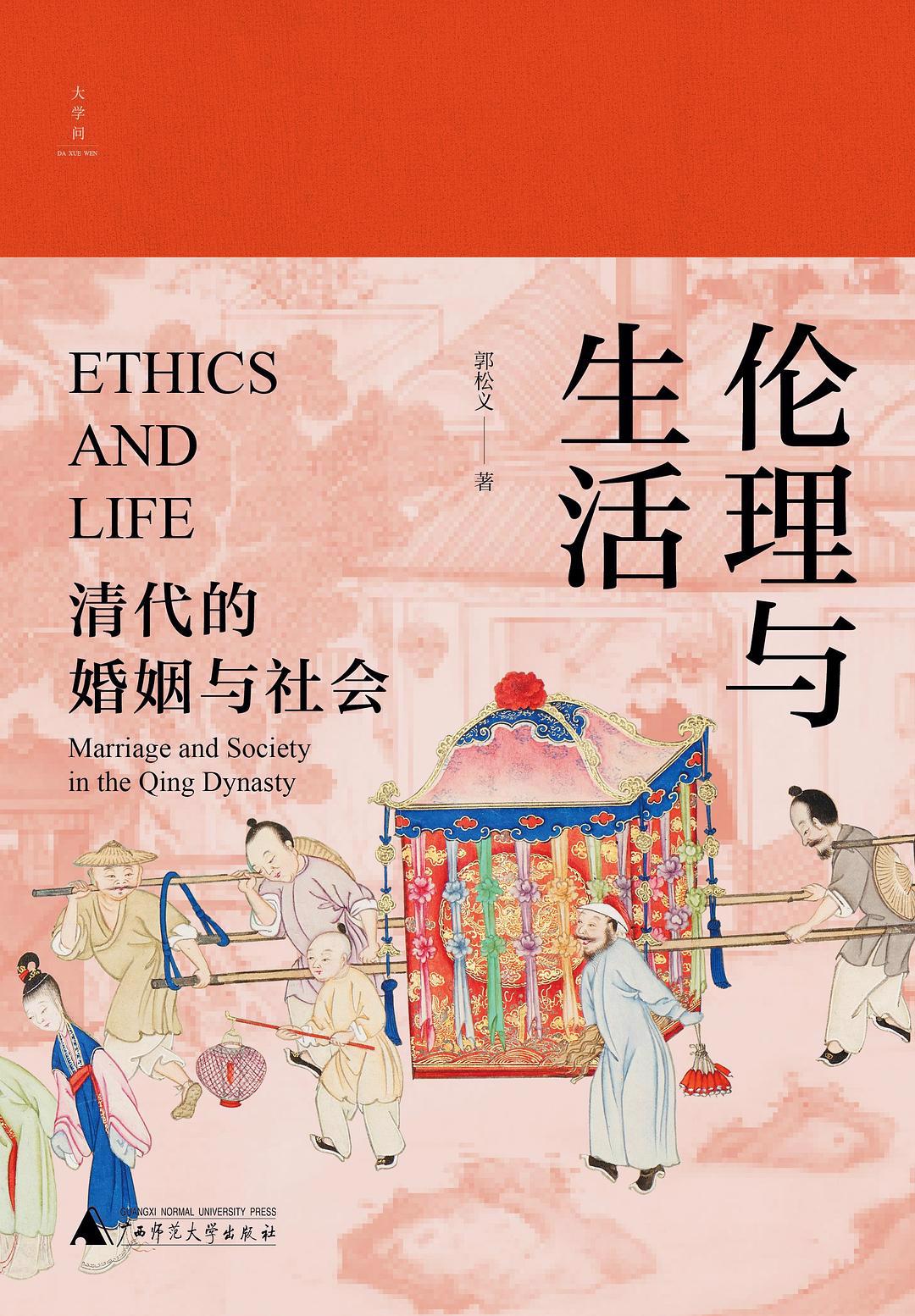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5-05-01
定 价:98.00
作 者:郭松义 著
责 编:邓进升
图书分类: 社会学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社会科学/社会学
开本: 16
字数: 500 (千字)
页数: 6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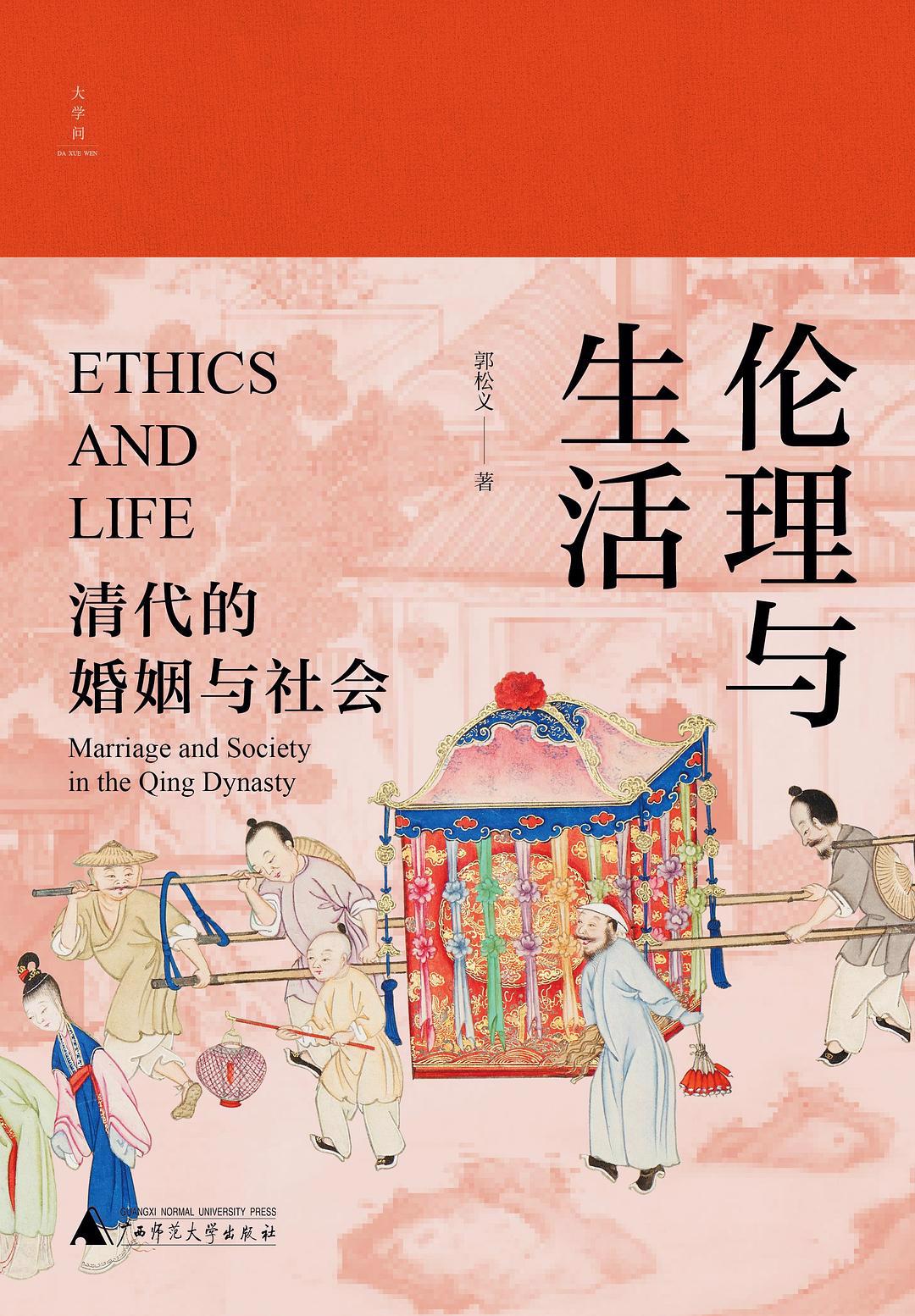
本书稿是一部专门研究清代婚姻与社会的学术著作。作者采用历史学、社会学的考订分析、个案研究、抽样统计等方法,借助伦理学、心理学的研究理论,使用了统计学量化处理的手段,汇集了方志、族谱、年谱、档案等前人未经采用的历史资料,对清代婚姻关系作了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全面的研究与考察。内容涉及婚姻地域圈、婚姻社会圈、婚龄、童养媳、入赘婚、妾、节烈妇女和贞女、妇女再嫁等问题。论述全面、资料丰厚,是一部富有创见的高质量专著。
郭松义,浙江上虞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清史研究室副主任、社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务; 1995年退休。主要科研成果:《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清代全史》《中国史稿·第7册》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目前承担国家清史工程课题《农业志》。
绪 论
第一章 婚姻社会圈( 上)
第一节 择偶的等级和界限
第二节 嫁娶必论门户的习俗
第三节 表亲婚和士绅中的世婚制
第四节 从族谱资料考察婚姻的社会圈
第二章 婚姻社会圈( 下)
第一节 结婚论财之风的滥觞
第二节 婚嫁和溺婴
第三章 婚姻地域圈
第一节 几组不同资料的统计分析
第二节 家庭生活面与通婚地域的关系
第三节 人口流动和婚姻地域圈
第四章 婚 龄
第一节 男女婚嫁各有其时
第二节 聘定以及聘与婚的时序间隔
第三节 从数字抽样看婚龄
第四节 大量早婚者的存在
第五节 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和不同阶级的婚龄差别
第六节 夫妻年龄差
第七节 幼男娶长妇的习俗
第八节 “婚嫁愆期”辨析
第五章 童养媳
第一节 童养媳婚姻的普遍性
第二节 领养原因和领养形式
第三节 童养媳的领养年龄和婚龄、婚仪
第四节 养媳在童养期间的身份和地位
第五节 从55宗案例看童养媳婚姻的婚姻质量
第六节 关于童养婿
第六章 男子入赘
第一节 入赘的原因
第二节 赘婿的身份和地位
第七章 妾
第一节 妾的来源和社会地位
第二节 纳妾的理由
第三节 纳妾与财势
第四节 妾的地位的改变和妾生子女的身份
第八章 节妇、烈女和贞女
第一节 清朝政府的贞节表彰制度
第二节 旌表人数的迅速增长
第三节 备受压抑的寡妇生活
第四节 贞女
第九章 寡妇再嫁
第一节 寡妇再嫁的动因及其他
第二节 寡妇转房
第三节 妇女再嫁与地区、门第之间的关系
第十章 出妻、卖妻、典妻与妇女的拒嫁和弃夫他嫁
第一节 出妻
第二节 卖妻和典妻
第三节 妇女的拒嫁和弃夫他嫁
第十一章 婚外性关系
第一节 卖淫和嫖娼
第二节 403例男女私通案例分析
第三节 男女同性恋及其他
第十二章 离 婚
第一节 夫妻离异的法律规定
第二节 提出离婚的原因
第三节 离异诉求中的角色分析
第四节 离婚的实践
第五节 离婚后妇女的归宿
附 录
一 方志所见清代妇女初婚年龄表
二 文献所见清代存在童养媳婚姻的州县厅
三 苦志守节申报册式
四 清历朝实录所载历年旌表节烈妇女人数
引用文献与书目
重要人名和专有名词索引
后 记
新版后记
绪论(节选)
一
在《礼记正义》中有这样两句话:“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婚礼,万世之始也”;又说:“婚姻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有了婚姻,才有夫妻和比较确定的父母、子女关系,由此形成一个个代相传承的、大小不同的家庭。众多的家庭组成一个社会,于是又有民族和国家。所以,社会学家把婚姻、家庭和性,看成人类初级社会圈。婚姻又是一种社会行为,从配偶的选择,婚姻的确定、延续乃至破裂,既与个人,亦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环境有密切关联。婚姻质量的高低,以及男女成婚比例的大小等,又影响着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所以无论哪个国家、民族乃至家庭,都把规范男女婚姻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并为此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和必须遵行的道德约束。
我们讨论的清代婚姻关系,属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范畴。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指导婚姻行为的重点,不是男女个人的爱情和幸福,而是对上孝事父母尊长,以及繁衍教养子女。这是传统礼法的要求,也符合当时人们对婚姻的基本期盼。由于传统中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所以婚姻又有其严格的等级界限,并形成了许多成文不成文的规定。首先是良贱不得通婚;又如不同等级、不同集团存在不同的婚姻圈子。盛行于中上层家庭的门第婚,以及由门第婚发展而来的世婚制便应运而生。在这里,婚姻体现为财产和权力的结合,并将之延伸到政治和经济领域。
其次,男女择偶婚配,权在父母等长辈手中,这也是传统婚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明律》和《清律》都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若夫亡携女适人者,其女从母主婚。”除少数特殊者例外,没有父母等长辈做主的婚姻,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有人写诗说:“父母之命礼经传,婚姻私订南词有。”(后一句也有作“私订婚姻小说有”)男女自订婚姻,只有在戏台和小说里,反映了人们对自由的爱情生活的向往,才被大胆地加以说唱和描绘,在现实生活中却不可想象。
最后,当婚姻成立后,夫妻间名义上是平等的,即所谓妻者齐也,与夫齐体。但同时又有夫为妻纲之说,有的更明确指出:“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既然嫁人后,女子以服从丈夫为天职,这就注定了夫妻关系在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在此原则指导下,丈夫可以名正言顺地纳妾,借着名义“出妻”,妻子在很大程度上不但只能消极忍受,而且要为丈夫守贞持节,甚至不惜以身相殉,以表示从一不二。
上述的婚姻原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十分森严的时代特点的反映,是对妇女所要求的“在家则为贤女,既嫁则为贤妻,嫁而生子则为贤母”的道德准则在婚姻和夫妻关系中的体现。在他们看来,只有遵循上述原则,婚姻才有规度,夫妻关系才能稳定,最后达到家和万事兴的目的。
由于清代是我国帝制时期的最后一个朝代,古代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经过长期积累、发展,已经十分成熟,反映在婚姻关系上,不但全盘承袭了上述三条原则,而且在某些方面更趋于严密,择要而言:
一是更加强调婚姻的契约规定。婚嫁需凭婚书,在我国早已有之,但口诺为信的做法仍在民间流行,至清代还是如此。为了加以规范,清朝的《会典》和《律例》同时明载:男女订婚,“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又定,“招婿须凭媒妁,明立婚书”。有时男女两家要先出具请书、允书,待确认后,再开婚书。按官方颁行的婚书格式包括:籍贯,父祖三代姓名,男女行次、年庚,以及主婚人、冰媒见证人亲押。有的家族为了表示隆重,在受聘、成婚时,还要具帖到祠堂或祖宗牌位前焚香禀告。及至清朝晚期,国家更明确规定,婚书由政府发放,使其完全纳入法律的规范之中。
强调婚姻以契约为凭,而且不断趋于规范化:一方面固然表现了双方家长、家族对子女、对本族男女终身大事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统社会后期,由于矛盾交织,各种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其中就包括了婚嫁方面的纠纷。强调婚嫁凭证,为的是在调解和官府审判时有据可依,实乃时代变化使然。
二是加强了对节妇、贞女的表彰。我国自宋以降,政府对贞节妇女的表彰就一代盛于一代,及至清朝,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国家旌表贞节,目的是强化妇女终身不二的婚姻伦理观,要求妻子永远忠诚于丈夫。在清朝政府的大力倡导下,不但受旌人数急剧上升,迄清末,已累计达百万之众,超过明朝很多很多倍,甚至比以往所有朝代的旌表总和还多,更为重要的是,在一片渲染声中,有人对如何做妻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清廷下诏对夫死妻子从殉的烈妇旌表做法实行“永永严禁”,理由是人命为重,轻生从死,事属反常,似乎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其实却别有深意。正如雍正帝胤禛所说:女人除了要尽妻责之外,还负有尽孝道和尽母责的重任,即需要代亡夫孝养公婆、教抚子女,治家立业。殉夫尽管壮烈,却是在逃避责任,所以不能旌表。再比如为了加重婚姻为承嗣的宣扬,清朝政府不但在法律上规定丈夫无子即可以出妻纳妾,而且动员舆论,把妻子主动为丈夫纳妾生子,作为妇女的至高美德予以褒扬。与此相反,对于妇女再嫁却极力贬斥,再嫁之妇不得随丈夫受封;儿子做官,推恩封赠,也不得及再醮母亲。有的家族还规定,女子再嫁无子嗣,在名分上只当以妾论,甚至不得写进族谱。如此等等,都说明在成婚后的夫妻关系中,妻子的义务就是服从再服从,这具体体现了“妇人伏于人”的伦理观。
但是在清代,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这就是与统治者倡导的婚姻伦理观相背离的倾向也在滋长。导致这一变化的因素,是传统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调节作用的加大。清代商品经济虽然在总体上仍归于传统经济,但从本质而言与传统经济格格不入,而且必然要在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中表现出来。具体到婚姻关系,最直接的反映便是嫁娶论财之风的蔓延。嫁娶论财,说白了亦即买卖婚姻,世界各民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当时的中国亦不例外,只是在士绅阶层中,论财在礼法的掩盖下显得并不直露。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受到贱视的商贾之家因拥有财富而显赫起来。他们不满原先的法律束缚,率先冲破藩篱,以奢华为时尚,甚至攀附阅阀,出现以厚币缔姻高门的现象。此种现象凸显于明朝中叶,到清代其势头已不可抑制。婚姻论财对于传统的门第婚以及以门第婚为基础的世婚制造成了冲击,也促使原先按等级制原则确定的婚礼制度产生裂变。正像当时有人说的:“今皂隶之家往往具仪卫,执事夹道,鸣金传呼,恬不为怪也。俗竞奢僭,尚为之坊哉。”原来只有贵族品官才有资格享受的待遇,竟落到连归于贱籍的皂隶之家也可张扬于道的地步,相对凝固的关系被打进一个楔子。随着楔子的深入,缝隙也在变宽变深。从冲破等级制这一点看,婚姻论财,亦有其积极的一面。
婚嫁论财风气的蔓延也带来消极的内容。比如因女家苛索聘金,男家只得汲汲于妆奁的丰厚,加上婚礼讲排场,致使中人之家穷于应付,贫者则婚娶失时或不得良配,这也会给婚后的夫妻和家庭关系失和造成口实,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自婚嫁竞尚华侈而溺女之风遂盛”。把溺女与婚嫁论财之风相联系,这也是明清以来,特别是清代社会变化中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如果说过去溺婴是基于贫穷,又重税难当,多系下层民众所为,那么因不堪婚嫁负担而溺婴者,就不仅限于下层民众了,不少中等小康家庭,甚至少数富有者也牵涉在内,使参与溺婴的层面更加扩大了。由于所溺多系女婴,在溺婴之风严重的地区,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矛盾亦更趋尖锐,给男子择偶造成新的困难。清代童养媳婚姻的普遍化,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们为制止溺婴、补救日后婚娶困难所作的努力。至于清代文献中不断见到的夺寡、抢醮行为,尽管粗暴且触犯禁律,但多数亦系事出无奈,是男多女少、室女难聘所致。此外,屡屡见于政府案卷的丈夫出妻、卖妻和租典妻子,以及妇女背夫他嫁等行为的增多,也多与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相关。
二
由于婚姻的道德规范,以及在此规范下制定的法律条文,体现的主要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而各阶级、阶层所处的地位和条件不同,又决定了他们在对待这些规范和条文时,往往会有各种差异,于是便出现了在同一种情况下,因阶级不同,结果亦不一样的情况。仍以妇女的守节和再嫁为例。在清代,作为道德的主导方面和政府规定的旌表制度,对寡妇守节无疑是极力提倡的,许多女子也自觉不自觉、甘愿不甘愿地为此而献出个人的青春和希望。前述庞大的受旌队伍便是最好的证明。可是若深究人们对守节的态度,则可明显看到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别。
绅士家庭把受旌看成家门的荣誉,妇女们自幼受此熏陶,视贞节为性命,从整体环境到个人的思想活动,全被传统礼教俘虏?即使年轻守孀,乃至已聘未婚而聘夫早亡,也要挣扎着去做节妇、贞女。据我接触到的资料,绅士家庭虽不乏年轻寡妇,有的甚至还不到20岁,却无一例再嫁的。然而这种做法,在下层百姓中的反响就颇不相同了。诚然,下层妇女也有守节不嫁的,有的也受到了旌表,但是有很多人不顾伦理束缚,选择了再嫁之路,特别是年轻无子女的寡妇,比例还相当大。根据我对某些族谱资料的抽样,30岁以前寡妇的再嫁率竟占到总数的58.33%。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有“夫死鲜守节”;“夫死妇多再醮,鲜有从一而终者”,或“妇人不以再嫁为耻”的情况。
在寡妇再嫁中,还有一种叫叔就嫂的转房婚,亦即民族学家所称的收继婚。如兄死,嫂转嫁于小叔,也有弟死,弟妹转嫁与伯兄的。依照清朝的法律,寡妇再嫁虽不被提倡,却无禁条,可是对寡妇转房,则以伦理攸关,定男妇俱绞。律令昭昭,按理小民应无敢有再犯者,可是在民间不少地区,仍相当广泛地存在着转房的习俗,有的甚至还被写进族谱的族规中,得到家族的认可。再比如同姓为婚,亦被清律禁止:“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杖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但是,也有百姓不惜触犯刑律和背上有违人伦的包袱而与同姓结亲。
为什么不同阶级的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会有如此大的差别?这里既有道德宣传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不同生活环境造就的。在中上层人士中,特别是少数上层官宦之家,他们既是三从四德的倡导者、鼓吹者,自然也应该是实践者。他们用牺牲妻女们青春的代价来换取家门的荣耀,并以此作为社会的表率。可是下层百姓不行,他们本来生活贫困,尤其是小家女子,一旦失去丈夫,往往就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靠山。她们夫家不足倚,娘家不得归,只要不想殉死,选择再嫁就成为苟延生活的重要出路。正如人们所说:“家贫窭,无以为活,始不得已而再嫁”;更悲惨的还有:“夫骸尚未入木,而此身已有所属,衣棺各项即指妇措办。”是现实的生活迫使她们选择再嫁。
至于寡妇转房,对于未婚的小叔或亡妻的大伯,等于是少了一笔开销而能圆成家之梦,对寡嫂、寡弟妹则意味着既不致子女分离、家庭破碎,又有了新的依靠,所以尽管渎伦,仍为下层百姓所默许。至于同姓为婚,更多是反映了百姓生活圈的狭窄。他们不像当官或有钱者交际广泛,可以突破一区一隅,有机会向更多的人提亲相偶,而只能局限于几里、几十里范围之内,假若恰恰又是聚族而居的大姓,同姓为婚便很难避免。总之,是生活环境决定着对道德的取舍。在现实生活面前,僵死的伦理便显得无力了,何况这种伦理本来就充满着对人性的压抑。
在清人的婚姻行为中,也有一些并不牵涉伦理问题,更谈不上触犯禁律,可是在上层和下层之间同样存在着区别。以婚龄为例,据测定,清代全国男子平均初婚年龄为20—21岁,女子为17—18岁。若按不同等级排列,就明显地呈现出差别。据抽样资料,在上层绅士家庭,女子初婚年龄与全国平均婚龄差别不大,,男子却要低2岁左右。上层男子除少数例外,绝大部分在20岁前已经成婚,而下层贫民男子有一半多是在21岁后才结婚的。在女子中,尽管平均婚龄差别不大,可在15岁以前(含15岁)的低婚龄中,两者仍有不同。绅士家庭占20.22%,下层贫民为29.76%,较绅士家庭高出近10个百分点。对于这种情况,有人归结说:“大抵富家结婚男早于女,贫家结婚女早于男。”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早婚早育早立业的思想根深蒂固,但因婚嫁需要可观的开销,富家子弟有能力做到,对下层贫民却是件大难事,这就形成不同阶级男子在婚龄上的差别。至于下层女子平均婚龄偏低,除了与社会上男女性别比例不协调有关外,在很大程度上亦出于早嫁可省去一口吃食的观念。
童养媳婚姻和入赘婚本来是一种流行于下层百姓中的婚姻形式,特别是入赘婚,因赘婿地位低下,即使下层百姓也多不屑于此。即或如此,在一些绅士家庭,仍有选择童养媳和入赘婚的。绅士家庭的童养媳婚姻,多数是在原先聘定的基础上,因一方要外出做官、举家远迁,或因家里出现变故,需要将聘妻提前送领到夫家,是为了两家方便而采取的做法。入赘也一样,或基于婚娶方便,或为了就近照看,多数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排。做丈夫的既可住在妻家,也可随时将妻子领返自家;既无入赘契约,更不牵涉赘婿的身份问题。所以尽管同是童养媳和入赘女婿,但目的和性质完全不同。
编辑推荐一:
在清代等级森严的传统社会里,统治者强调“门当户对”,对人们的择偶有严格的规定和制度,但那些成文的或不成文规定与制度都被人们遵守吗?清朝政府加强对节妇烈女、贞女表彰的同时,却为何又出现许多寡妇再嫁的例子呢?在清代男性多于女性的地区,为什么又多出现溺女婴的现象?这些问题又衍生了哪些社会问题?与统治者倡导的婚姻伦理观相背离的倾向不断滋长的原因何在?
郭松义先生翻阅数千种稀有文献,采用历史学、社会学的考订分析、个案研究等方法,以及借助伦理学、心理学等理论,通过研究清代的婚姻关系,描绘了一幅伦理道德、法律制度、人情秩序交织交融、错综复杂的社会史。
编辑推荐二:
在清代的婚姻关系中,有些地区有一种叫作“拉帮套”的同居关系。它是指妻子在丈夫以外,还有一个或几个非正式关系的男人,在丈夫同意或默许的情况一起生活。帮套与本夫以兄弟相称,与主妇以叔嫂或伯兄弟妹相称。出现这种同居关系,主要是因为当地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这迫使当地人采取各种方式互助合作,彼此扶持以求生存。
在清代,有些地区男多女少,存在大批鳏旷者的同时却又大量出现溺女婴的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直接推手是婚嫁论财之风,主要原因则是贫穷。因为在清代,少女从许嫁办妆奁起,出嫁后有三朝、满月、令节新年、家属生日,娘家都要有馈赠;然后怀孕有催生礼,生育后弥月、周岁、上学,也少不了要赠送;再就是女婿分家的索取,女儿归宁私取母家所有,携之而归;等等,真是数不尽的应付。正是此种习俗、此种观念支配下,人们溺婴,怎么会不首先选择溺女婴下手?
……
本书通过大量的案例与事实,具象描述了清代伦理道德与生活实践的矛盾与复杂。
编辑推荐三:
在清代,一纸婚约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伦理与生活的博弈?
寡妇再嫁是“失节”还是生存智慧?商贾联姻如何突破阶层壁垒?
这些问题在《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中得到了深刻而鲜活的解答。
本书聚焦清代婚姻制度与社会伦理关系,通过婚姻这一切口,透视清代社会的伦理秩序、性别权力与道德文化。作者不限于清代婚姻制度的条文规范,从民间实践切入,揭示伦理规范在真实生活中的复杂落地过程。同时综合利用刑科题本、地方志、契约文书、族谱、文人笔记等文献资料,为我们还原了普通民众的婚姻生活细节。如书中剖析童养媳现象时,不仅援引《大清律例》的禁令,更通过地方诉讼档案展现民间如何变通执行;通过徽州商人家族的联姻账簿,分析婚姻如何成为资本积累与社会地位攀升的“隐形杠杆”,挑战“士农工商”的固化等级观念;书中也指出清代民间对官方伦理并非全盘接受,如华北农村普遍存在的“典妻”现象,实为贫困家庭在道德与生存间的妥协,官府往往默许此类“非礼”行为。
这不仅是一部关于婚姻的历史之书,更是一把打开传统中国社会伦理迷宫的钥匙,为理解传统中国婚姻伦理冲突提供了深刻历史镜鉴。
清代妇女的守节与再嫁并存,是伦理道德与社会现实冲突的缩影。地区经济、家族门第、年龄与子女等因素共同塑造了清代妇女的选择。尽管统治阶层通过旌表制度强化贞节观,但底层民众的生存逻辑和实际需求使得再嫁成为普遍现象。
——编者按
妇女再嫁与地区、门第之间的关系
在第八章我们谈了清代妇女的守节,这一章又谈妇女的再嫁。这实际上是两个对立、相互矛盾的问题。但在清代却是如此显眼地同时存在着。当然,作为道德的主导方面,由于清政府的大力倡导和众多文人学士的鼓噪,以及与之相配合的一套法律定规,从一而终被确立衡量妇女品行的重要标准,很多妇女也自觉不自觉、甘愿不甘愿地以此作为准绳,乃至献出青春和幸福。有清一代,仅被朝廷旌表的节妇人数就超过百万,至于志书存名由地方表彰或受到文人称颂的,亦不亚于此数。这么多节妇受表彰,不但以前朝代所没有,而且在同期其他表彰活动中,也名列前茅。这说明,清朝政府的宣传、倡导是做得成功的,同时也显现了宋明理学那套妇女贞洁观,在经过几百年不断修饰包装,已经十分完备,具有了很大的蒙蔽性。
其实所谓从一而终,这只是男子对女子所发出的要求,在男子拥有三妻四妾可以不受谴责的情况下,却要求女子从一而终,这不但不公正,也是对女权的粗暴践踏。不仅如此,它在维护道德原则旗号下,实际上把许多本来难以娶妻的贫苦男子的权利也给剥夺了,或大大增加了他们娶妻的难度。说到底,从一而终的道德标准,只对有权有钱的男子有利,反映了少数特权者的私利。由此它必然会导致道德规范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并产生相互背离的现象。我们列举的大量促使寡妇再嫁的事实,便是最好的证明。
不过,由于各个地区、家族、家庭乃至本人的情况各不相同,所以在具体看待或选择守节或再嫁上,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大致在农村,特别是偏远新移民区,由于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等种种缘故,寡妇的再嫁率很高。相反,在一些中心地区,尤其像江浙和京师周围,受传统道德说教影响较深,舆论压力较大,妇女守孀比例就相对要大得多。至于家族、家庭,则受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政治地位高,又是世家望族,有较丰厚的族产、家产,能对寡母孤儿提供一定生活条件的,对寡妇再嫁控制从严,守孀的比例便大,反之则小。有的学者根据族谱资料,对19个家族的孀妇再嫁人数作了统计,见表9—2。(表格略——编者)
由于妇女再醮有损家族门庭,所以多数族谱无此栏目,即使像上述19个家族,我也怀疑记录是否完整。即便如此,仍可提供参考,从表中看,妇女改适比例最高的是广东香山张氏;其次是福建永春郑氏、湖南衡阳魏氏;再就是番禺凌氏、浙江南浔周氏、南海黄氏。在不满1%的6个家族中,除1个是湖南,1个是广东外,另4个都在江浙文化发达地区,这间接说明边缘区的妇女再嫁率要高于中心区。遗憾的是表中缺少北方地区和偏远区。不过我们通过其他记载,亦可略见一二。
福建邵武县“远乡之民,往往有夫死不逾时而再醮者,其人亦悍然娶之而不顾”;
台湾,“夫死而再醮,或一而再,再而三,白首嫠妇,犹字老夫,柏舟之誓,盖亦鲜矣”;
湖南祁阳县,“至穷檐小户……中年破镜者亦多改节另嫁”;
湖南道州,“妇人不以守节为重,不幸而嫠,劝嫁者踵至”;
湖南宁远县,“孀妇不以再适为耻”;
浙江定海县,“年少之妇一醮再醮,恬不为怪,谓之广眷属”;
浙江汤溪县,“妇怼未亡之夫,面目未改,顿事他人,恬不为留”;
浙江景宁县,“夫死,妇多再醮,鲜有从一而终者”;
四川彭山县,“至夫死改醮,离婚更嫁,则唐宋以来,此风久著,故家大族亦不废也”;
四川石柱厅,“夫死鲜守节”;
山西朔平府,“既谓妇不耻廉,名节甚轻,竟有守志多年,忽思改醮者”;
保德州,“妇人不以再嫁为耻,虽儒家子亦娶以为偶”;
陕西,“陕西风气,男乐于娶二婚,女不必专一姓,由来久矣”;
奉天昌图府,“女子夫死再瞧(醮)者有之……不以为怪,盖陋俗也”。
从以上所举的例子中看出,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在人们的观念中,并不把妇女再嫁当成是奇耻大辱之事。
关于妇女再嫁与家庭、家族的关系,根据我对五十余部族谱的考察。凡有功名的绅宦之家,无有一例再嫁。这表明再嫁与家庭经济有重要关联外,亦与家庭的政治地位以及受传统礼教熏陶关系密切。处于这类家庭中的妇女,在精神思想上所接受的束缚,远比一般平民百姓要更加严重。
最后,我们用数字统计的办法考察一下妇女再嫁的年龄和有无子女的关系。湖南《两湘续修陈氏族谱》(民国本)共记录了41名再醮妇女,内14人守孀时年龄不明,另27人分别是:
19岁及以下 8人 占29.36%
20—29岁 10人 37.04%
30—39岁 5人 18.52%
40—49岁 3人 11.11%
50岁及以上 1人 3.7%
从记载中见到,30岁以前守孀妇女的再嫁率,占到全部的66.6%。咸丰《衡阳王氏族谱》共载孀妇21人,明确记录守孀年龄的18人,她们中最小的是18岁,最大59岁。剩下3人虽无具体年龄记载,但从丈夫去世年龄推断(丈夫去世年龄分别18岁和35岁,另1人系副室,丈夫38岁死),除1人可能超出30岁外,另两人,1人在20岁以下,1人不过二十几岁,将其归类,便是:
19岁及以下 3人 占14.29%
20—29岁 7人 33.33%
30—39岁 5人 23.81%
40—49岁 4人 19.05%
50岁及以上 2人 9.52%
从陈、王两个家族来看,30岁以前(不包括30岁)守孀妇女的再嫁率占到总数的58.33%,即超过一半。
这些妇女再醮前拥有子女的情况,陈氏家族的41人中,无子女者20人,占48.78%;有子者8人,占19.51%;有女者10人,占24.39%;有子有女者3人,占7.32%。王氏家族21人中,无子女者9人,占42.86%;有子者2人,占9.52%;有女者6人,占28.57%;有子有女者4人,占19.05%。再醮妇女中,无子无女的占了很大的比重。
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区)《洪氏宗谱》,载录了11个再嫁妇女,除了19世洪清利妻邹氏生有一子;15世洪梅扬妻张氏曾生有2子,后一死一卖;17世洪章之妻王氏生一子金全早卒。余下8人都没记载生有子女,而且上述3人中,张氏和王氏实际上等于没有子女。
又据四川《蓉城叶氏宗族全谱》所记10名再嫁妇女,除了两名是副室,两名继配,其余均属元配。她们中4人没生育子女,4人生有1子,1人生有2子,1人2子1女。无子无女的占40%。谱中没有记录再嫁年龄,但从丈夫去世年龄推测(19岁去世2人,26岁去世1人,31岁死2人,32岁1人,33岁1人,41岁1人。其中41岁和33岁去世的丈夫,其妻均系继配,另2个副室,丈夫的年龄未计),她们守孀时年龄大概在18—19岁到30来岁之间。
当然无论是陈氏家族或王、洪、叶等家族,都只能说是个案资料,不过透过信息,再结合前面的某些例证,大体可作如此推断:孀妇的再嫁年龄。多数在30岁以前,30—35岁,比例也不小,以后迅速递减,50岁及以上,除特殊者外,便很少见到了。从有无子女方面看到,以无子无女的再嫁比例为最大。女儿出嫁后,又牵涉将来的养老,加上本宗不足仗恃,也是促发再嫁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有子或有子有女的,因负有抚养责任,精神上已有所依托,舆论方面的压力也大些,再嫁相对要少多了。但是也有这样一种情况,即年轻守寡、子女幼小,维持生活不易,公婆和父母家又无法依靠,那只好冲破压力再嫁了。
在清代,尽管妇女从一而终的思想“村农市儿皆耳熟焉”,旌表节妇的人数也达到空前的境地,但仍不能抑制寡妇择夫再嫁,这再次证明,把清代妇女的守节和再嫁并列起来进行讨论,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只看到清统治者和文人学士们所热衷宣传的伦理准则,看到相当一部分妇女对“从一而终”的信条显现得如此诚惶诚恐,并伏帖地为之献身的种种事实,而没有看到它的另一面,特别是众多下层民众从现实出发,蔑视准则,同情并支持寡妇再嫁的强大行动,那就是不全面的了。事实上,真正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正是在当时并不受到倡导,可却具有活的生命的后一种情况。
节选自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版。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