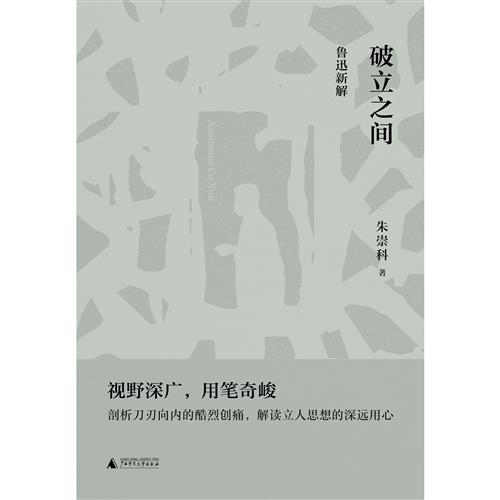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4-12-01
定 价:69.00
作 者:朱崇科 著
责 编:梁文春,冉娜
图书分类: 文学理论
读者对象: 文化研究者
上架建议: 文学/文学理论
开本: 16
字数: 400 (千字)
页数: 4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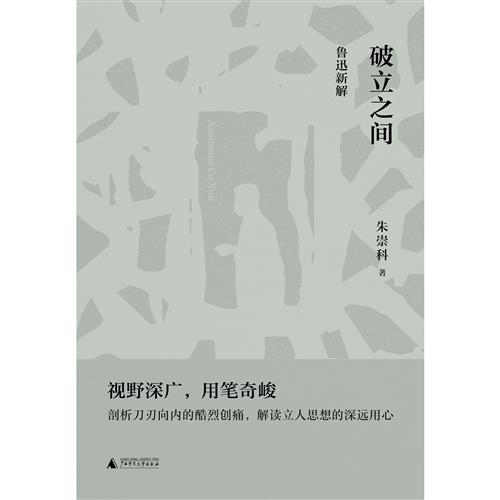
本书是一部关于鲁迅的学术研究著作。作者用奇峻而深切的笔触,细致入微地剖析了处于破立之间,进行韧性战斗的“解剖者鲁迅”的思想。所谓“破”就是对旧土壤之上的人、事、物进行筛检、剖析与重估,尤其是侧重对国民劣根性及其生成机制的猛烈批判和韧性战斗。毫无疑问,对自我的解剖和重构也位列其中,甚至首当其冲。而“立”则是重申和践行“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尤其指向“立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并指向在此基础之上的“立国”。在这个过程中,“解剖者鲁迅”一直把自己架在火上直至燃烧成火烬。这既是个案自我的浴火重生,同时也借助自己的千锤百炼温暖了他所心心念念的他者,从而铸就了“民族魂”的连缀性和相通性。
朱崇科(1975—),山东临沂人,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教授兼系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2005),旋即以“百人计划”副教授人才引进执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2005—2011),2007—2008年任美国巴德学院(Bard College)交换教授,2011年12月—2016年4月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教授,2013年2—7月任中国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教授,2015年2—7月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海内外刊物发表论文250余篇。著有《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鲁迅小说中的话语形构》《广州鲁迅》等10余部论著。
绪?论 / 1
第一章?《野草》诗学 / 9
[ 第一节 ] 《野草》中的自我裂合与整饬 / 11
[ 第二节 ] 《野草》中的“故事新编”/ 30
[ 第三节 ] 《野草》中的临界点设置 / 53
[ 第四节 ] 《野草》中的梦话语 / 71
[ 第五节 ] 《野草》中的“潜在”过客话语 / 88
第二章?《野草》系统 / 101
[ 第一节 ] 《野草》中的国民性空间 / 103
[ 第二节 ] 《野草》中的“立人”维度 / 115
[ 第三节 ] 《野草》中的笑 / 134
[ 第四节 ] 《野草》中的植物系统 / 147
[ 第五节 ] 《野草》中的动物谱系 / 161
第三章? 话语凝练 / 177
[ 第一节 ] 论鲁迅小说中的教师话语 / 179
[ 第二节 ] 鲁迅小说人物命名中的解 / 构辩证 / 191
[ 第三节 ] 鲁迅小说中的创伤话语 / 207
[ 第四节 ] 论鲁迅作品中的寡妇话语 / 224
[ 第五节 ] 鲁迅小说中的英雄话语 / 237
第四章? 主题展演 / 251
[ 第一节 ] 鲁迅“中间物”再辩证:进化的中间物 / 253
[ 第二节 ] 后殖民鲁迅:主体性建构视野下的逆袭与正道 / 270
[ 第三节 ] 汉语修行与现代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力提升 / 286
[ 第四节 ] 论鲁迅在狮城的赓续 / 305
[ 第五节 ] 论“王润华鲁迅”的生成及理路 / 322
第五章? 重读新颜 / 337
[ 第一节 ] “立人”的“出悌”切入与多维验证:重读《弟兄》/ 339
[ 第二节 ] 论《故乡》的“意绪秀异”/ 352
[ 第三节 ] 论《故乡》中鲁迅“感受结构”的演绎 / 366
[ 第四节 ] 底层游民之“承认的政治”/ 381
[ 第五节 ] 从“立人”到“立国”的尝试隐喻及其破灭 / 398
参考书目 / 414
致? 谢 / 421
绪 论
大家耳熟能详的《藤野先生》里曾写到对鲁迅倍加关照的藤野先生与鲁迅的一段精彩交流: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从以小见大的角度思考,这其实精妙呈现了(传到日本的)西方解剖学(文化)与晚清帝国文化劣习的遭遇和交锋,也似乎注定了对一个西医学生必然包含的身份——“解剖者”的强调与确认,当然也有其对自身落伍及劣根性的尴尬回应姿态。
实际上,晚清留学生鲁迅在实际参与尸体解剖时,还是面临了不能为外人言的文化冲击。在1904年10月给蒋抑卮的信中,鲁迅写道:“解剖人体已略视之。树人自信性颇酷忍,然目睹之后,胸中亦殊作恶,形状历久犹灼然陈于目前。”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藤野先生给鲁迅解剖学课程的分数恰恰是他在日本仙台医专就读时的最低分——59.3分。解读的面向可以复杂多元,但有些解读把鲁迅弃医从文的要因归结为得分偏低、无力继续学业,明显是错误的认知。作为“解剖者”的鲁迅,显然还有更复杂的文化指向:向外的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以及向内的自我审核。换言之,也就是“废墟重建”与“刀刃向内”相结合。作为新文学文化解剖隐喻学的杰出代表,“解剖者鲁迅”富含了重述与再论的宏阔空间。
“解剖者鲁迅”并非只是一个医学形象,尽管“小医医病,大医医国”的理念是历史悠久的医学理念和文化传统之一,但“解剖者”也契合特立独行的鲁迅破传统、立规矩的追求——他长期坚守的显然是一种探寻特征的精神与繁复文学实践。与此相关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话语:“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但这只能算是其中复杂缠绕的一个精彩面向。
实际上,“解剖者”是一个非常开放、多元而又指向未来的理念与实践。从宏阔的层面思考,解剖的方向包含了“破”与“立”的辩证。所谓“破”就是对旧土壤之上的人、事、物进行筛检、剖析与重估,尤其是侧重对国民劣根性及其生成机制的猛烈批判和韧性战斗。毫无疑问,对自我的解剖和重构也位列其中,甚至首当其冲。而“立”则是重申和践行“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尤其指向“立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并指向在此基础之上的“立国”。在这个过程中,“解剖者鲁迅”一直把自己架在火上直至燃烧成火烬。这既是个案自我的浴火重生,同时也借助自己的千锤百炼温暖了他所心心念念的他者,从而铸就了“民族魂”的连缀性和相通性。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两者中,“破”的一面往往会被过度强调,这是因为鲁迅的笔锋犀利、批判的覆盖面广且往往不留情面,但实际上破立之间自有丰富的辩证。这一点在回到个体审视时,往往会更加凸显。榨取精华的当儿剔除了糟粕,同时又注入了新的元素,谱写出新的篇章。从宏阔的意义上说,鲁迅的所有创作都和破立并存的“解剖”息息相关;从微观的意义上说,在不少经典文本、意象、话语中,这一点都可谓得到了集中体现,尤显突出。
很多时候,作为后来人的我们从传统中找寻可再生资源时,往往容易心生骄矜。不少古代人习惯厚古薄今,而今人似乎因为添加了后顾者视角而有了“事后诸葛亮”式的自大,“鲁迅式现代性”恰恰可以反衬出这种虚荣的虚妄与误置。比如骄傲于自古有之的民族主义分子会认为古人所言的“一日三省吾身”就等于现代意义上的“解剖”,实则不然。简单举例来说,《野草》中,鲁迅对自我的思考主要可分为整体上的分裂式串合、自我剖白、自我复仇、自我悬置以及经典个案中的自我审视,明显超越了古代文化中哪怕是最丰富的自我的边界与层次。
近些年来,作为“中间物”的我一直努力尝试在鲁迅研究领域有所推进和突破,哪怕微不足道,也可算是一面张扬创新欲望的旗帜。然而兜兜转转几经尝试,最终发现其实并未突破“解剖者鲁迅”的范畴。比如焦点之一是论述《野草》,在主题上既论及了不少人论述的国民性空间,同时又触及其“立人”维度。不仅如此,还通过“笑”、动物、植物系统等加以聚焦和辨析。当然,作为一部自我之书,《野草》的解剖诗学令人印象深刻甚至叹为观止,为此我勠力探勘了其间的“故事新编”策略、临界点设置、梦话语梳理以及有关虐审与裂合的整体操作。
《野草》中鲁迅选择以相对隐晦的方式和梦的技艺谨慎地传递内心的繁复、痛苦和幽深,同时不惜创设出令人目瞪口呆的临界点存在,并对这种难以直说的苦衷、哲学思想或复杂情愫进行了再现。从此意义上可以说,《死火》《影的告别》《死后》的主要角色都有一种相似性,那就是身份、自我主体的裂合、对话以及与此相关的彷徨性。但如果再度进行细分,所谓“临界点设置”,一方面是物理层面的,另一方面则是精神和心理层面的。看似互不相干,但其实二者往往鱼水交融、密不可分,并同时带来了神奇的效果和可能的悖论。
《野草》中的梦话语有其独特品格:一方面是其梦诗学的精彩创制,既遵循梦的相关特征同时又利用强烈的主体介入人工筑梦;另一方面,他的梦话语意义指向又可以继续深挖,其中既有个体梦,呈现出鲁迅对弗洛伊德等人的性欲说的借鉴与反拨,以及他以梦修复创伤、弘扬英雄气质的关怀,同时也有国族梦,彰显出鲁迅对个体现代性的张扬与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此外,鲁迅还有更高远的宇宙视野,他的梦话语中不乏超越时代和现实的未来反思与指涉。
《野草》中存在着一个过客话语 / 系统,它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前过客(尤以《求乞者》为中心)、过客(代表文本《过客》)和后过客(《死后》)。通过这些文本,鲁迅深入反省了过客的诸多层面——坚守、彷徨、疲惫、堕落、决绝、非功利,等等。从上述话语系统中,我们不难看出鲁迅既为同行者又为自己所提供的反抗绝望的道路的复杂性、决绝性和暧昧性。从诗学层面角度思考的话,这三篇代表性文本恰恰也是对话及对话性丰富的实践。
在小说的有关话语操练中,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彰显出“解剖者鲁迅”犀利的批判性,比如其间的“创伤”“寡妇”与“教师”主题,等等。考察鲁迅小说文本中的教师话语,可以发现鲁迅在小说书写中主要呈现出两种风格:同情式剖析与入木式批判。前者涉及了作为谋生职业中教师的个体变异以及为师的艰辛,后者则批判了伪现代的卑劣与旧传统的僵化。相较而言,鲁迅在有关散文的书写中,对这一话题主体褒扬更多,因为其中贯穿了“立人”的现代性教育理念及有关角色形塑,同时鲁迅也从“破”的角度进行了独特的反思与高度警醒,从而呈现出有破有立、双管齐下的深入思考。
类似的,“创伤话语”亦然。鲁迅少年丧父、生活从小康堕入困顿、赴日留学走异路中有颇多艰辛,而后的兄弟失和的打击、与多人笔战、长期患病,等等,鲁迅一生经历的创伤体验并不少,在其文学生产中,“创伤话语”亦屡屡可见。他在对“创伤”的小说再现中,呈现出的“创伤”的挫败性惯习(habitus)(布尔迪厄语):一方面指向了传统致人挫败的杀伤力;另一方面则说明现代转换中亦有类似惯习。鲁迅亦有“复仇创伤”的书写实践,他强调反抗遗忘和自奴的同时,亦有攻击性乃至同归于尽的复仇理念。而在其作品中,亦有“疗治创伤”的书写,其中也是悖论重重。
同时,我也认真爬梳了鲁迅小说创作中关于人物命名的张力。拥有小说命名权的鲁迅的小说人物命名可谓别有洞天,呈现出丰富的话语张力:在严谨正名(名正言顺)的实践中,他再现了“旧”的刻板与顽固,也彰显了“新”的希望与没落;在无名 / 共名的命名实践中,以洋文命名国人本身既有无处可逃的尴尬又借之呈现出可能的含混与丰富,而共名背后既有麻木单一,又可能有民间力量的反拨;在《故事新编》中,他又有“去名”的操作,企图呈现出他更繁复而深刻的思考——依靠旧传统,即使是神仙圣贤也未必能够适应新时代,而批判国民劣根性从不该停止脚步。
除此以外,我也认真思考灌注新素质的可能性。比如鲁迅在小说中对“英雄”的再现与强调,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民族的脊梁”。鲁迅在小说中的“英雄话语”有其独特追求:一方面是状描与剖析英雄气质,如其个性与创造,实干与牺牲,借此实现对“新人”的强调 / 再造和“立人”思想的再现;另一方面他也可以以同情之笔抒写并自我投射英雄,尤其是迟暮之感。当然他也批判了某些劣根性,其中既有对借助英雄的符号化使用的批判,又有对滥权的伪英雄的描写。
毫无疑问,鲁迅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宝藏,具有极强的时空穿透力和借鉴延伸性。从国内语境来看,探讨汉语修行与现代中国文学文化自信力提升的关系问题涉及汉语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它包括语言及其背后相关文化的丰富、淬炼以及创造性提纯,也包括文体形式创新的可行性,还涉及意义建构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范式更新的宏大议题。经由鲁迅个案,其卓越实践和丰富内涵帮助和引导我们进行深入而开阔的思考——我们必须尊重汉语修行过程中语言发展的专业性、精神性与超越性;我们必须立足当下中国,认真汲取古今中外的文化资源与精神创制,重新审视我们自身的缺憾、劣根性,汰除杂质、推陈出新;我们必须继续全面开放、引育并举,尊重个体的独创性与涵容其可能的缺陷,最终才能另立新宗。
放眼海外,非常令人震撼的是,鲁迅个案几乎是所有现代、后现代理论的最佳落脚点之一。其中,后殖民理论遭遇鲁迅以后也会产生新的可能性与误读。“后殖民鲁迅”作为鲁学中相当热门的论题之一彰显出有关理论与个案分析对话的繁复张力和有益联结,在不同时空都有相当精彩的实践。在东南亚地区赫赫有名的学者、作家王润华的相关书写,犀利地反映出曾经的殖民地子民“逆写”的合法与急切,也偶有伤及中国的矫枉过正的操作。但作为“南洋”诗学的建设者,他对作为精神资源和中国文化象征的鲁迅的挪用与警醒又令人同情且深思。北美学者刘禾的实践既有清醒的棒喝、反问与提醒,同时又有剑走偏锋的偏执和悖论。实际上认真回归鲁迅本体,他本人也有对殖民主义的深入理解,“香港借助”与“上海补偿”功能各司其职,展现出其丰厚、锐利与不断发展着的伟大。
真正的鲁迅传统,哪怕只是在文学层面也从未断绝,比如新加坡优秀作家英培安就是鲁迅传统在狮城的赓续。此外,“王润华鲁迅”不是一个单纯概念的新造,而是一个安放到东南亚语境以及王润华个体思想经历之后的认真总结。其研究理路清晰、新意盎然、风格独具,有其迷人风采。按照历时性发展,大致可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去蔽:独特发声;第二,跨越:国界与疆域;第三,回归:壮大本土。当然“王润华鲁迅”也有其可能的限制,比如相对新颖但略显清浅,多点透视但偶尔散漫。
同时,本书也是我对鲁迅的自我认知和规律思考的结晶。比如“中间物”其实也可以有新的再确认——鲁迅“中间物”的话语论述模型主要有三种:历史的中间物、价值的中间物和生命哲学论,但也各有缺点。不容忽略的是,鲁迅的“中间物”的使用是有其谱系的,也有繁复的意义指向,我们必须回到其不同文本的原初语境中才能有更准确的判断与逻辑推演。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概括鲁迅“中间物”的话,那应该是“进化的中间物”,这里的进化显然不是线性演进的机械进化论,它可能推进,也可能退化,又可能多种类型并存;它不只是历史的,又不能窄化为价值判断,偶尔还可能回环;它就是在进化中的,既有古,又有今,但也指向未来。
我素来特别强调文本细读理念下对鲁迅的文本进行立体多元的新解读,实际上不只是为了追求新的可能性,努力一点一滴靠近鲁迅,同时也是为了成为一种有意义和价值的自圆其说。《弟兄》一文在我看来不乏对“立人”的多维验证,它通过空间诗学以“出悌”作为切入点探讨了“立人”的可能性及其限制。鲁迅通过家庭、梦境、公司三种空间来探讨其中的兄弟情谊与文化抗衡、精神焦虑与物质压迫、生死吊诡与对比表演,具有超越性追求和浓厚的现实关怀——宣泄焦虑、平复自我、刻画人性以及重新“立人”。
《故乡》作为鲁迅的经典名作,其意义指向相当繁复,可以理解为一种鼎立并合关系。其主题蕴含至少可以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作为老中国的隐喻 / 寓言,既有宏观图像描述,又有个体荏弱状描,同时也引发了读者对变革的反思或冲动;第二,揭示其间对隔膜 / 国民劣根性的人为制造机制,一方面是精神奴化,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动物驯养;第三,绝望的反抗与反抗绝望之间的意绪的复杂辩证。同时,其中的“情感结构”何尝不是一个民族游子“出走—回归—再出走”的中年落寞、努力探求与无尽悲哀的诉说?重审《故乡》,它既反映出民国时期国民们的相通劣根性与可能隔膜的精神感受,结合鲁迅文学生产的自身特征,又反映出“小我”的颠沛模式,同时并置了填充 / 攫取模式。但无论如何,“立人”“立国”都更多是悲剧。从此角度看,《故乡》更是鲁迅抚慰自我、记录思想、反思自我及国家的生产性文本。
类似的《伤逝》中也有对从“立人”到“立国”有意实践的预设与挫败。他以爱情作为切入点,反衬出现实压迫的强大,既批判了抱残守缺的惯习,又指出“新人”们谋生乏力。若从精神资源角度思考,其中亦不乏个体提升的悖论,子君和涓生分别呈现出自动停滞和被动停滞的风格。当然,如果从“新人”“立人”的空间转换角度思考,也可以探勘其间大小社会的张力以及新人内部相当明显的隔膜,而这一切却未必和空间的优化成正比。
《阿Q正传》是鲁迅最精彩的自我与他者合二为一的“解剖”实践之一。从意义的指向上看,它既有其时代特征,又有其开放性和未完成性,很多时候它的中性指向(而非单纯批判)意义范围被严重压缩,同时它也有新时代的延展性。即便是回到相对窄缩化的国民性批判视角进行挖掘,它本身也是一种近乎最大公约数模型的构筑,其中既有游民类型的聚焦与分层处理,亦有鲁迅小说中常见的其他不同类型角色身份与时空连缀语境中的宏阔联动,需要用“超时代”与“去阶级”的眼光加以审视或观照。《阿 Q 正传》其实书写了一个无名游民的辛酸挣扎、强作狂欢与满地破碎。
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鲁迅式“解剖”的文本实践是遍地开花的,在他的古体诗、散文、译文和杂文中都不乏此类操作,期待有心人继续开掘。从此角度看,鲁迅不只是从精神资源化用上为广大读者指向了未来,他之于鲁学及其研究者的提升亦然。创新创造才是对大师最好的继承。
当我细读朱崇科教授这部《破立之间:鲁迅新解》时不禁感慨万千,让我再度确认2001年大力推荐他拿“杰出学者奖学金”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的理由坚持与正确远见。当时新加坡已决定建构国际一流大学,而中文系的师生,必须有潜力“越界跨国”,跨越民族国家的区域界限,跨越学科、文化、方法、视野的边界,同时也超越文本,进入社会及历史现场,回到文化/文学产生的场域,甚至有时也有必要打通古今,进出现代与古代之间,重新解读现代与古典文学。
如今,20多年过去了,朱崇科教授这部《破立之间:鲁迅新解》涵容广阔,从诗学、话语、空间、系谱、系统、中间物、赓续、生成、演绎与重读等层面与方法生发出关于鲁迅的诸多新解,一再证明我们已经实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当年要打造国际一流大学的学术文化之预设。作为崇科的博士导师,与有荣焉,同时也欢迎大家不吝指正。
——王润华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资深教授兼中华语言文化学院院长)
★出入古今,越界跨国,全新视角解锁全新鲁迅。向远处看,望见鲁迅思想的超前与阔远;往深处看,窥见鲁迅思想的深邃与温情。
★回到历史现场,还原一个处于破立之间,坚持韧性战斗的解剖者鲁迅形象:一面是向旧垒反戈一击的决绝,一面是刀刃向内的抉心自食,一面是废墟重建的深远用心。
★独特深广的视角,奇峻雄健的文笔,细致入微地烛照鲁迅幽微内心的同时,又以鲁迅的思想观照当下现实。
无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