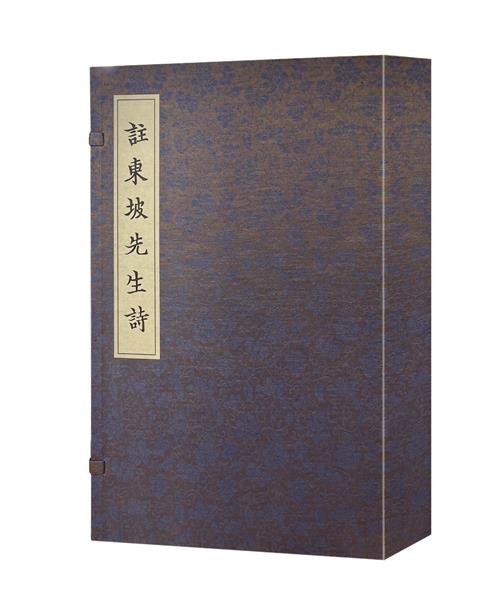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3-05-01
定 价:1380.00
作 者:(宋)施元之,顾禧,施宿 编注
责 编:王琦,朱时予,杨磊
图书分类: 中国古诗词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仿真
开本: 12
字数: 95 (千字)
页数: 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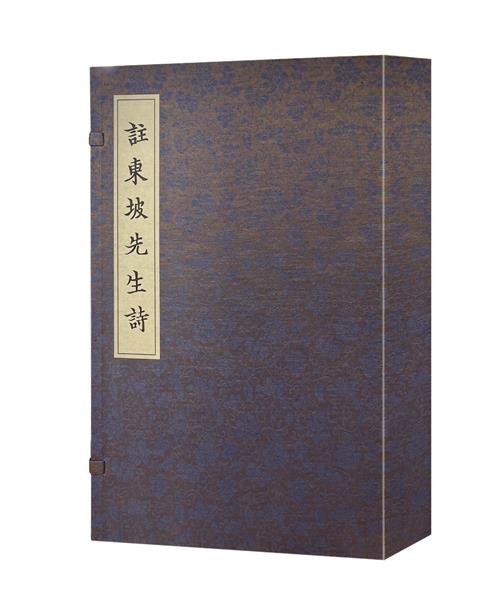
宋刻《注东坡先生诗集》四十二卷。宋苏轼撰,施元之、顾禧、施宿注,宋嘉泰淮东仓司刻本。存一卷(卷四十一)。此本从中国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本析出。原卷四十一、四十二为近代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所藏,分别赠予其两名子女,后分别被国图和韦力收藏。韦力藏本前几年与台北藏本合璧出版,反响甚大。此本俗称“焦尾本”,虽仅一册,但书中明安国、毛晋,清宋荦、揆叙、翁方纲递藏,以及众名家之印记累累,依稀可见当年大家藏书之风貌。整体仿真制作。
苏轼(一〇三七至一一〇一),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汉族,眉州眉山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无
宋嘉定六年淮东仓司刻本《注东坡先生诗》(翁方纲旧藏“焦尾本”卷四十二)
——代前言
宋代有许多苏轼诗歌的注本,其中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是题为王十朋编纂的《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直到明末清初,苏诗注本以此书最为通行。该书汇集了此前几乎所有的苏诗注,网罗宏富,但注释不标出处,分类杂乱。
宋代另有一部由施元之、顾禧、施宿编注的《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年谱》一卷(以下简称《注东坡先生诗》),由于流传不广,长久以来沉晦不彰。直到清代康熙年间,宋荦购得此书的宋刻残本,经补辑整理,改以《施注苏诗》之名,雕版印行,这部罕见的宋代苏诗注本,才重又化身千百,广传于世。
遗憾的是,参与整理《施注苏诗》的邵长蘅、顾嗣立、宋至、李必恒等人,对施、顾原注肆意增删,妄改臆断,导致全书从内容到形式,都大异于宋刊本的原貌。《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四指出:
元之原本注在各句之下,长蘅病其间隔,乃汇注于篇末。又于原注多所刊削,或失其旧。后查慎行作《苏诗补注》,颇斥其非,亦如长蘅之诋王注。然数百年沉晦之笈,实由荦与长蘅复见于世,遂得以上邀乙夜之观,且剞劂枣梨,寿诸不朽,其功亦何可尽没欤?
四库馆臣肯定了宋荦、邵长蘅等人刊印稀见宋本的功劳,但对其刊削原注、毁失宋版旧貌的错误做法,也实事求是地给予了严厉批评。以“佞宋主人”自称的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对《施注苏诗》刊削宋版尤为不满,甚至斥其“可覆酱瓿”。而更多的学者,都为见不到宋刻原本而深感遗憾。
宋刻《注东坡先生诗》笺注精审,版印精美,是宋本中的上品。惜存世珍罕,仅有几部历经名家递藏的残本流传。该书在元明两代踪迹难觅,自清康熙年间《施注苏诗》印行以来,即备受学界关注。
本次影印的是国家图书馆藏翁方纲旧藏“焦尾本”——宋嘉定六年(一二一三)淮东仓司刻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卷四十二(《和陶渊明诗》)。
一、成书与刊刻
《注东坡先生诗》正文四十二卷,前三十九卷为编年诗,卷四十收翰林帖子及遗诗;卷四十一、四十二为“和陶诗”。其苏诗编年,完全依照宋代通行的《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但分卷与之不同,每卷卷首均有编年提纲。《东坡年谱》一卷由施宿编撰,其中诗目是施宿自行编年的,所编诗目的序次、篇章数量与正文诗注并不相同。
全书注文分为两类。一是诗句注(以下简称句注),即对诗句的注释。二是诗题注(以下简称题注),即置于标题之后的注释,题注又分为题下注和题左注——题下注位于标题之下,文字多行者,注文与标题齐平,较正文低三字;题左注位于标题左侧,另起一行,比标题低两字。句注与题下注的内容为典故、成语、地理、名物等;题左注内容则以解析苏轼所处时代的人物、掌故、朝政时局,以及作诗的主旨为主。另有少量记载东坡某诗墨迹的注释,以及对典故、地理、名物等的注释。
《注东坡先生诗》的编撰历经三十余年,是施氏父子两代人共同完成的杰作。正文四十二卷约于淳熙三年至嘉泰元年(一一七六至一二〇一),由施元之、顾禧完成初稿;自嘉泰二年至嘉定二年(一二〇二至一二〇九),施宿又增补了一部分注文,并作《苏轼年谱》一卷。
施元之(一一〇二?—一一七九?),字德初,吴兴(今属浙江湖州)人。绍兴二十四年(一一五四)进士,乾道二年(一一六六)为秘书省正字;乾道五年(一一六九)任秘书省著作佐郎,兼国史院编修,除左司谏;乾道七年(一一七一)任职衢州,曾知赣州。其三衢“坐啸斋”是当时著名的刻书坊。
顾禧,字景藩,或作景蕃,吴郡(今属江苏苏州)人。少纵游任侠,后折节读书,工诗文,曾注杜甫、苏轼诗。绍兴年间,以遗逸荐举,力辞不应,于邳村筑“漫庄”,自号“漫庄”,又号“痴绝”,隐居五十年,享高寿而终。
施宿(一一六四—一二二二?),字武子,元之子。绍熙四年(一一九三)进士,庆元初,知余姚县。后为绍兴通判,主持编撰《会稽志》。嘉定间,知吉州,后提举淮东常平仓,刊刻《注东坡先生诗》于仓司。施宿长于金石之学,曾于嘉定六年(一二一三)刻王顺伯《石鼓诅楚音》。章樵《古文苑注》卷一《石鼓文》云:“周宣王狩于岐阳,所刻《石鼓文》十篇,近世薛尚功、郑樵各为之音释,王厚之考正而集录之,施宿又参以诸家之本,订以《石鼓》籀文真刻,寿梓于淮东仓司,其辨证训释,盖亦详备。”
施元之、顾禧完成初稿后,施宿做绍兴通判时,延请当时已告老还乡的著名诗人陆游为本书作序,陆游序成于嘉泰二年(一二〇二),收入《渭南文集》卷十五。
施宿作注和编撰年谱的时间,大致为嘉定元年(一二〇八)春夏间至嘉定二年(一二〇九)中秋。不过,他的准备工作应该始于陆游作序之后不久,即于嘉泰二年(一二〇二)开始搜集资料。经过几年资料的积累,又综合施元之晚年搜集的部分资料,即施宿序所谓“先君末年所得未及笔之书者亦尚多有”,施宿终于完成了对《注东坡先生诗》注释的增补。施宿作注周详细密,用力颇深,且态度认真,书已刊刻,还在不断添改。
嘉定五年至六年(一二一二至一二一三),《注东坡先生诗》刊刻于淮东仓司,是施宿出任淮东仓司仓曹时主持刊刻的,由善写欧体字的傅穉手书上板。该书使用公款雕印,书板一直收存于淮东仓司。五十年以后,景定三年(一二六二),郑羽任提举淮东常平茶盐司长官时,看到这部书的板片已有部分模糊不清,便着手修补重刻,这就是景定修补本。该本末有郑羽的跋文:
坡诗多本,独淮东仓司所刊,明净端楷,为有识所宝。羽承乏于兹,暇日偶取观,汰其字之漫者大小七万一千五百七十七,计一百七十九板,命工重梓。他时板浸古,漫字浸多,后之人好事必有贤于羽者矣。景定壬戌中元,吴门郑羽题。
《注东坡先生诗》传本稀少,且非全帙,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该书的认识。关于三位著者及其注文、该书的编撰时间、刊刻年代等问题,清代以来,众说纷纭,以注释苏诗闻名的“注苏五家”——邵长蘅、查慎行、翁方纲、冯应榴、王文诰,以及郑元庆、阮元、余嘉锡等众多学者,都表达过不同的观点。直至近代以来,这些问题仍不断吸引学者予以研究、探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施宿自序、跋文和《东坡年谱》在日本的一个旧抄本内被发现,《注东坡先生诗》的诸多疑点豁然冰释。现结合新见资料及各家研究成果,就该书的编刊等问题,略作阐述。
《注东坡先生诗》的著者是谁?这个问题在清代就曾经存在误解,有些学者甚至不清楚作者有几人。翁方纲得到宋荦旧藏宋版《注东坡先生诗》残书以后,曾手书跋文感慨道:
卷前题云“吴兴施氏”“吴郡顾氏”,今相沿称“施注”,而不知有“顾”久矣!
可见某些错误认识,竟源自于《施注苏诗》题名“施注”之失。
其实,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对该书著者已说得明明白白:
《注东坡集》四十二卷,《年谱》《目录》各一卷。司谏吴兴施元之德初与吴郡顾景蕃共为之;元之子宿从而推广,且为《年谱》,以传于世。
施元之、施宿父子的生平,长久以来也鲜为人知。近人陈乃乾曾于《宋长兴施氏父子事迹考》序言中为此感言:
自宋迄今,致力于是书者或校或补,与夫考证题跋,无虑数十家,而于施氏父子之事迹莫能详悉。所引者惟《直斋书录解题》与《癸辛杂识》数行,知元之以进士官司谏,及其子宿为淮东仓司,以刻《苏诗》被弹去官而已。呜呼!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陈乃乾遍查南宋人文集及郡县方志,搜辑施氏父子行事,编成《宋长兴施氏父子事迹考》(《学林》一九四一年四月第六辑)长文。据该文所考,施元之、施宿父子不仅学识渊博,交游广泛,且都热衷于刊刻。正是施氏父子的共同努力,才有了《注东坡先生诗》的编纂和成功刊刻。
三位注释者各自所做的笺注工作是哪些?清人对此亦有不同看法:郑元庆认为“句解是元之笔,诗题下小传低数字,乃武子补注”;冯应榴认为“诗题下似亦有元之注”;王文诰、阮元、余嘉锡则认为施元之注人物时局,顾禧注典故,施宿只是在二人基础上略加增补。(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二《施注苏诗》)
从卷端题署和《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看,施元之显然是编撰《注东坡先生诗》的初始发起者及主要注释者。陈乃乾指出:“元之注《苏诗》致力最深。惟何年写定,无明文可考。”(《宋长兴施氏父子事迹考》所收罗愿《水调歌头·中秋和施司谏作》词下按语)。关于施元之开始笺注苏诗及其完成的时间,阮元推测“应在淳、绍之时”,此判断并无错误,但时间跨度太大,精准性不足。
施宿序说:
东坡先生诗,有蜀人所注八家,行于世已久。先君司谏病其缺略未究,遂因闲居,随事诠释,岁久成书。然当无恙时,未尝出以示人。后二十余年,宿郡佐会稽,始请待制陆公为之序。
根据邓广铭《辛稼轩年谱》,辛弃疾任江西提点刑狱时,曾于淳熙三年(一一七六)弹劾时任赣州知州的施元之,施因此离职,闲居在家。故施元之应在淳熙三年(一一七六)闲居之后开始注释苏诗。“然当无恙时”,指的是施元之在世之时,按此语义,下面的“后二十余年”句,显然是说直到他死后二十多年,施宿才请陆游作序。
陆游序文末题“嘉泰二年正月五日山阴老民陆游序”。正月五日属一年之初,从施宿请序到陆游写成序言,需要一定的时间,故施宿向陆游请序的实际时间,应该在嘉泰元年(一二〇一)。由嘉泰元年(一二〇一)上推“二十余年”,便可大致推定施元之的卒年。
陈乃乾《宋长兴施氏父子事迹考》将施元之的卒年定为淳熙元年(一一七四),显然有误,王水照《评久佚重见的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三年第三辑)认为施元之“去世当比淳熙四年更晚”。
从施元之闲居的淳熙三年至嘉泰元年(一一七六至一二〇一),共二十五年。假设施宿所说的“二十余年”只有二十年,即施元之卒于淳熙八年(一一八一),留给其作注释的时间有五年;假设是二十二年,那就只有三年时间。就“二十余年”的可能性而言,推测施元之卒于淳熙五年(一一七八)或六年(一一七九)之前,似较妥当。
《注东坡先生诗》洋洋四十二卷,释文极多。“岁久成书”,似是在说注释工作花费了较长时间且全书终于完成。但实际上,施元之从闲居到去世,时间并不太长。如果施元之卒于淳熙六年(一一七九),那他注释书稿的时间应不足三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独立完成全部注释工作,难免令人生疑。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施元之完成书稿以后,生前为何“未尝出以示人”?除非其未能完成书稿的注释或者是对自己的注释不够满意,否则他的行为实在有悖于常理。
施宿十三四岁时父亲去世,成年以后,又长年在外做官,对于父亲注诗工作的认识和了解都很有限。直到嘉泰二年(一二〇二)读到陆游所写的序文,才意识到父亲的书稿实际未能按其理想得以完成。施宿的序点明了施元之“未尝出以示人”的原因:
而序文所载在蜀与石湖范公往复语,谓坡公旨趣未易尽观遽识,若有所谨重不敢者。宿退而念先君于此书用力既久,独不轻为人出,意或有近于陆公之说。而先君末年所得未及笔之书者亦尚多有,故止于今所传。宿因陆公之说,拊卷流涕,欲有以广之而未暇。
原来,当时陆游看到的只是一个未最终完成的初稿,施元之还有许多“末年所得未及笔之书者”没有写进书稿里,这才是“先君于此书用力既久,独不轻为人出”的真正原因。我们有理由推断,施元之应该是带着很大的遗憾去世的,因为他在闲居的有限之年,只作了典故、成语、风土山川等常规注释,完成初稿,而最初计划和构想的一些与陆游观点相近的内容,如对当时人物、时局的解析等,尚未如愿写进书稿。
经过陆游序的点拨、启发,施宿才真正认识到父亲所追求并意欲完成的这部书稿的重要价值,他感激涕零,并由此产生了继承父志、增补完成全部书稿注释工作的决心,开始着力搜集苏轼经历、交往人物、掌故、时局等方面的资料,为全书增加了大量补注。
据郑骞《宋刊施顾注苏东坡诗提要》(严一萍、郑骞编《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一),台北:艺文印书馆,一九八〇年)统计研究,在现存三十六卷(合并现存残本,并剔除重复卷次)中,施宿所作题左注有三百五十余条,计五万两千五百七十余字,篇幅相当可观。题左注中有十三条施宿自称其名,其余各条与此十三条的文笔体裁,完全相同;题左注中有关神宗、哲宗两朝的政见观点,与施宿自序中持论相同;题左注中多处论述苏轼墨迹石刻和其他法书名画,与施宿的金石学专长吻合。
施宿在主持刊刻该书的时候,并没有在卷端署自己的名字,只是在序言中说明自己增补注文,“各附见篇目之左”。虽然施宿尽力突出父辈之名,对自己的贡献只在不起眼的序言中做了说明,但施宿的低调并不能掩盖题左注的耀眼光芒。全书的注文中,最重要、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部分正是施宿所作的题左注。
施宿注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施宿距离东坡时代不远,熟悉史事,更因为施宿的政治立场与苏轼一致,都反对王安石熙宁变法,他对苏轼深怀敬意,同情苏轼的坎坷遭遇。同时,施宿对待苏轼的态度比较公允,并没有一味“佞苏”和阿私附和,而是坚持自己独立的见解,难能可贵。
施宿为作此注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力颇深。他结合朝政时局,深入分析苏诗的写作背景,对读者理解和领悟苏轼的真实旨意,提供了积极的帮助;同时也为后人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宋史资料,如对卷十四《送李公择》、卷四十一《饮酒二十首》、卷四十一《岁暮作和张常侍》所作注释等。
清人对施宿的题左注评价甚高。张榕端《施注苏诗序》云:“又于注题之下,务阐诗旨,引事征诗,因诗存人,使读者得以考见当日之情事,与少陵诗史同条共贯,洵乎有功玉局(苏轼曾提举玉局观。——撰者注)而度越梅溪(王十朋,号梅溪。——撰者注)也。”邵长蘅《注苏例言》云:“《施注》佳处,每于注题之下多所发明,少或数言,多至数百言,或引事以征诗,或因诗以存人,或援此以证彼,务阐诗旨,非取泛澜,间亦可补正史之阙遗,即此一端,迥非诸家所及。”王文诰亦谓“最要是题下注事”。
《注东坡先生诗》的刊刻版式颇有特点。依照宋代刻书惯例,诗歌注本的版面形式特征是诗歌题目、正文采用大字,注文一般小字双行。题注置于诗题之下,诗文注随诗句注于各诗句之下。该书除了常见的题注和句注,还出现了罕见的标注于诗题左侧的题左注。根据施宿自序:
宿因先君遗绪,及有感于陆公之说,反覆先生出处,考其所与酬答赓倡之人,言论风旨足以相发;与夫得之耆旧长老之传,有所援据,足裨隐轶者,各附见篇目之左。
由此可证,列于“篇目之左”的题左注,都是施宿所作的注释。
从书籍刊刻的角度来说,题左注的出现,正是从版面形式上明显区分不同著者的一种独特方法,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清晰地展示题注和句注均为施元之、顾禧初稿的原注,而题左注则是施宿后来所作的补注。
另外,题注和句注是施元之、顾禧共为之,但二人如何合作?各自做了哪些工作?仅看文字内容,则难以区分。郑骞等学者认为施元之、顾禧同时合作完成,根据卷端署施元之、顾禧之名,陆游序提到顾禧,判断施元之退休回家之后,“施家住在湖州,距离顾禧的家乡苏州很近,通信会面都很方便,正是合作的好机会”(《宋刊施顾注苏东坡诗提要》第五节《施顾注的完成刊印与流传》)。不过,这个貌似顺理成章的结论,却没有想象中那么无懈可击。以当时的交通状况,湖州与苏州距离虽不太远,但要真正交流、沟通、合作,也不会特别容易。从陆游序说施宿“先人司谏公所注数十大编”以及施宿《后序》的记述可以判定,施元之是《注东坡先生诗》的创始作者,顾禧则属于后来加入的次要性的第二作者。陆游序先说施元之“历岁久,用工深”,之后夸赞“又助之以顾君景蕃之该洽”,显然对作者也是分了主次的。“该洽”大意是更为恰当、妥帖、完善,即是说顾禧的注释使此书显得更好了。如果施元之、顾禧二人开始即一起合作注释苏诗,陆游如此赞誉顾禧,显然对施元之有些不够尊重,更何况他面对的是施元之之子施宿。但如果是对后继加工、修订者的工作给予称赞,那就显得十分自然而顺畅。
通过陆游的话,也许可做出这样的推测,即顾禧并非初始就是与施元之一起注释苏诗的合作者,而极可能是施元之去世之后,施宿请顾禧对父亲原稿进行整理、加工、修订。准确地说,顾禧只是审稿和修订者。据陈鹄《耆旧续闻》卷二,赵右史家有顾禧《补注东坡长短句》真迹。正因为顾禧之前曾为《东坡乐府》做过补注,对于苏轼诗词中的时事、掌故比较熟悉,故施宿邀请顾禧帮助整理、修订父亲施元之注释的初稿。
出于审稿人的责任,更出于对苏轼诗歌的热爱,顾禧增改了许多注释,只可惜他所作的补注,大多未见署名,被淹没于书稿中了。翁方纲指出:“今注中尚有数处存顾氏姓名,卷二十《橄榄》诗注,卷三十四《立春日戏李端叔》诗注,而学者莫之详也。”(翁方纲《苏诗补注》卷八)。其中卷二十《橄榄》“已输崖蜜十分甜”注文:
《本草》:“崖蜜,又名石蜜,别有土蜜、石蜜。”《归叟诗话》曰:“范景仁云:‘橄榄木高大难采,以盐擦木身,则其实自落。’”顾禧注云:“记得《小说》:‘南人夸橄榄于河东人云:“此有回味。”东人云:“不若我枣。比至你回味,我已甜久矣。”’”枣,一作柿。
卷三十四《立春日小集戏李端叔》“须烦李居士,重说后三三”注文:
延一《广清凉传》:无著禅师游五台山,见一寺,有童子延入。无著问一僧云:“此处众有几何?”答曰:“前三三、后三三。”无著无对。僧曰:“既不解,速须引去。”顾禧云:“此诗方叙燕游而遽用后三三语,读者往往不知所谓,盖端叔在定武幕中,特悦营妓董九者,故用九数以戏尔。闻其说于强行父云。”
由此可见,顾禧对一些时事比较了解,他的补注较原注有了深化。而此两条补注,正说明施元之与顾禧的注释工作有先后之分,顾禧是一位审稿者,是后来才加入整理、补注此书的工作的。
《直斋书录解题》未提及《注东坡先生诗》的刊印时间和地点。关于其刊刻时间,清代学者也有不同观点。宋荦、翁方纲等根据陆游嘉泰二年(一二〇二)序推定该书刻于嘉泰二年(一二〇二),如“公诗故有吴兴施氏元之注四十二卷,元之子宿推广为《年谱》,而陆放翁序之,宋嘉泰间镂版行世。”(《施注苏诗》宋荦序);“施氏《注东坡诗》四十二卷,镂版于宋嘉泰间”(邵长蘅《题宋本施注苏诗》),“据《渭南集》,是书之刻在嘉泰二年壬戌时”(顾廷龙抄本《宋椠苏诗施顾注题跋钞》翁方纲题记)。冯应榴则认为该书刻于嘉定年间,“施德初卒年无考,而乾道七年尚官衢州。其子武子嘉定间始刊其父所注”(《苏文忠公诗合注·凡例》)。在这两种观点中,“嘉泰说”一直占主流,近代以来各家目录多将其著录为嘉泰刻本。
其实,该书卷三十八《次韵郑介夫诗》题左注,有“嘉定六年赐谥忠介”之语,足证刻书时间不可能早于嘉定六年(一二一三)。至施宿跋文被发现,该跋落款“嘉定六年中秋日,吴兴施宿书”,说明施宿于嘉定六年(一二一三)刊刻该书确凿无疑,而以陆游序之年份确定刊刻时间则失之草率。
关于其刊刻地点,也有不同的说法。宋周密《癸辛杂识》:“宿尝以其父所注坡诗刻之仓司,有所识傅穉,字汉儒,穷乏相投,善欧书,遂俾书之锓板,以赒其归。因摭此事,坐以赃私。”(《癸辛杂识》别集上“施武子被劾”条)
现存宋景定三年(一二六二)印本中郑羽跋文,正好与《癸辛杂识》互相印证,说明该书刊刻于淮东仓司。
而《四库全书总目》所谓“嘉泰中,宿官余姚,尝以是书刊版。缘是遭论罢,故传本颇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四《施注苏诗》),显然对其刊刻时间和地点均做误判。
明末清初钱谦益曾收藏过一部嘉定刊《注东坡先生诗》全本,惜毁于绛云一炬。《绛云楼书目》卷三著录:“宋板《东坡诗集施注》四十二卷,又《年谱》《目录》各一卷。”钱谦益又作《跋东坡先生诗集》(《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五)。钱谦益应该是清代唯一见过全本的学者,他的跋语是比较客观可靠的,现录其跋如下:
吴兴施宿武子增补其父司谏所注东坡诗,而陆务观为之序。务观序题嘉泰二年,是书刻于嘉定六年,又十二年而后出。故其考证人物,援据时事,视他注为可观。然如务观所与范致能往复方云,不知果无憾否?诗以纪年为次,又附《和陶》一卷。坡诗尽于此矣,读者宜辨之。
钱谦益对该书刊刻年份的著录和判断,恰好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日本发现旧抄本的可靠性。
二、《追和陶渊明先生诗》
《和陶诗》又名《追和陶渊明先生诗》,是苏轼晚年自编的一部诗集,主要收录其晚年居惠州、儋州时追和东晋诗人陶渊明的诗作。
苏轼一生坎坷,遭贬于海南以后,写下了许多追和陶渊明的诗歌。如居惠州时所作《和陶归园田居六首》,有诗序云:
始,余在广陵和渊明《饮酒二十首》,今复为此,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
苏轼对其所作和陶诗极其重视,亲自将这些诗作结集出版。他在写给弟弟苏辙的信中说:
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其为我志之。
(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
陶诗看似朴素,实则华丽;貌似平淡,实则意味深邃。苏轼追写《和陶诗》,不单是对陶诗艺术的欣赏,更多的是思想行为上的追随。正如苏轼所说:
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俯仰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
苏轼博学多识,才气横溢,堪称千古奇才。其一生虽遭遇无数艰难困苦,却能以旷达的人生态度面对逆境,超然物外、与世无争。在这一点上,苏轼和陶渊明很相似。黄庭坚曾有诗曰:
渊明千载人,东坡百世士。
出处固不同,风味要相似。
据《郡斋读书志》,苏轼著作南宋时已有《东坡前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集》四卷、《应诏集》十卷,共七集行世。现存宋黄州刻“东坡七集”本之《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集》四卷,即反映了《东坡和陶诗》的初始面貌。
《注东坡先生诗》前四十卷的各卷内容均在卷前标明,题作“诗××首”(如卷三题“诗四十五首”),卷四十一、四十二《和陶诗》,卷前分别题作“《追和陶渊明诗》五十四首”“《追和陶渊明诗》五十三首”。卷前题署的不同,说明前四十卷来源于《东坡前集》《后集》;卷四十一、四十二《和陶诗》,来源于四卷本《和陶诗》。
卷四十一收录的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表明当时收录在《和陶诗》之内的苏轼追和陶渊明诗是一百零九首。但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一所收《子瞻追和陶渊明诗引》与此句文字有异,作“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因此,清代学者对《和陶诗》收诗是否“一百有九”颇有怀疑,王文诰认为是一百二十四首,查慎行认为是一百三十三首。
依据我国台湾图书馆藏宋黄州刻本《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集》目录(该目录以诗题为记,同一诗题有两首以上者标明数字,再除去陶诗原作及苏辙和诗)统计,共收苏轼和陶诗一百零七首,外加末尾的和《归去来辞》《桃花源》二赋,总计一百零九首。因此,《注东坡先生诗》的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所谓的“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无疑属于原始提法,应该正确无误。
关于《注东坡先生诗》卷四十一、四十二的所收诗数,需要略作说明。依据目录,卷四十一实收诗五十四首无误;卷四十二据目录诗题统计作五十三首,但其中《和杂诗十一首》漏刻第七首“蓝桥近得道,常苦世褊迫”一诗,故实际收诗五十二首。两卷合计,实际收诗一百零六首。又以《注东坡先生诗》目录诗题核之黄州本,施顾本较黄州本缺少《和东方有一士》《和刘柴桑》二首。
综上所述,施顾本和陶诗较黄州本缺诗三首:《和东方有一士》、《和刘柴桑》、《和杂诗十一首》之第七首。依常理看,施顾本所缺三首,最有可能像《和杂诗十一首》之第七首那样漏刻或漏抄所致,但也不能排除其他原因。
施顾本《和陶诗》与黄州本所收内容有明显的区别——施顾本惟有苏轼和陶渊明诗;黄州本收录陶渊明、苏轼、苏辙三人诗作,在每首陶渊明原诗之后,接录苏轼和诗及苏辙再和诗。
据黄州本卷二目录,《移居二首》《和刘柴桑》二诗应以先后顺序出现,正文却出现混乱,陶渊明《移居二首》原诗之后,接刻的不是苏轼《和移居二首》,而是陶渊明《和刘柴桑》原诗。黄州本每版二十行(半叶十行,行十六字),此叶首行刻陶渊明《移居二首》尾句“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第二至九行插刻陶渊明《和刘柴桑》原诗,第十行起接刻苏轼《和移居二首》诗并引,直至下叶第九行止,十行起顺接陶渊明《岁暮作和张常侍》原诗。除了此叶,其他各叶内容顺序均与目录相合无误。因此,据黄州本目录统计,苏轼《和陶诗》是一百零九首,但其正文漏刻了《和刘柴桑》一首,实际收录一百零八首。
由此可以断定,黄州本漏刻了苏轼《和刘柴桑》原诗,施、顾著《和陶诗》的底本极有可能据黄州本过录。对于印本书出现的此类错误,如果不够细心,较难发现问题所在。所以,施顾本缺失此诗,更有可能是“因错就错”。即便发现了问题,倘若是代为抄书的书手,也很有可能因莫名所以而选择放弃过录此诗,以避免混乱。这样的做法,对于一个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的书手来说,尚可看作是负责而又较为合理的选择。
三、现存宋刻残本
宋代《直斋书录解题》首次著录《注东坡先生诗》,《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四《经籍》七十一著录沿袭之,仅个别字改动。之后元明两朝几乎未见提及。清初以后,该本遂成为凤毛麟角般的存在。
《注东坡先生诗》目前存世的仅有四部残本:黄丕烈旧藏本、嘉业堂旧藏本(缪荃孙旧藏本)、翁同龢旧藏本、翁方纲旧藏本。除了翁同龢旧藏本是景定三年(一二六二)郑羽补刊本,其余均为嘉定原刻本。
黄丕烈旧藏本存二卷(卷四十一至四十二,卷端题“卷上”“卷下”,即《和陶渊明诗》二卷),二册,现藏国家图书馆。该书经清季振宜、周锡瓒、黄丕烈、汪文琛、汪士钟、杨氏海源阁递藏,有周锡瓒跋、黄丕烈跋并题诗、潘奕隽题诗。民国以后,归著名藏书家周叔弢先生,由周叔弢先生捐赠予国家图书馆。
嘉业堂旧藏本(缪荃孙旧藏本)存四卷(卷十一至十二、二十五至二十六),四册,现藏国家图书馆。各册有“刘承乾印”“翰怡”“翰怡欣赏”“张叔平”“诗外簃藏书”“徐伯郊”“徐伯郊藏书记”“伯郊”“伯郊所藏”“吴兴徐氏”“人间孤本”“文靖世家”等印,据此可知,此本原为嘉业堂旧藏,后经张叔平、徐伯郊之手,归于国家图书馆。据《藏园群书题记》,此本原为缪荃孙艺风堂旧藏,后归嘉业堂。
常熟翁同龢旧藏本存三十二卷(卷三至四、十一至十八、二十一至四十二),三十四册。此本曾经清怡亲王府收藏,有同治间翁氏题跋、潘祖荫跋,光绪间沈曾桐题识等。钤“安乐堂藏书记”“常熟翁同龢藏本”“同龢私印”“郑盦”“说心堂”“龙自然室”等印。此书曾由翁氏后人携往美国。一九八〇年,翁同龢玄孙翁万戈先生将该本付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出版;二〇〇〇年,该书由海外回归祖国,入藏上海图书馆;二〇〇四年,《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此本。
在四部宋刻本中,以翁方纲旧藏本最为著名,该本存卷较多,递藏经历曲折,留下不少书林佳话。该本系明嘉靖时期安国、毛晋汲古阁藏嘉定刻本的残本,入清后归徐乾学。康熙年间为商丘宋荦购入,仅存三十卷(目录下半卷,卷三至四、七、十至二十二、二十四至二十五、二十七至三十四、三十七至三十八、四十一至四十二),宋荦命邵长蘅、李必恒等删补、翻刻为《施注苏诗》,成为通行本。康熙五十四年至五十六年(一七一五至一七一七),该本归于揆叙,到了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内阁学士翁方纲在北京购得该本,翁方纲因此自号“苏斋”,并给自己的书室取名“宝苏斋”。每年农历十二月十九苏东坡生日,翁方纲都要招集亲朋好友、硕儒名彦至家中,展示此书,焚香祭拜,设宴鉴赏,三十年如一日。翁方纲和其他乾嘉以来名流如桂馥、阮元、何绍基等人的手跋、题识、观款尽留书上;又有翁方纲四十岁小像、顾莼泥金绘梅花、东坡生日消寒图等,堪称宋版书中至为名贵者。
翁方纲之后,道光六年(一八二六),该书归吴荣光。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潘仕成得之,清道光、咸丰间,归汉阳叶名澧,光绪中邓振瀛收藏,光绪末年,湘潭袁思亮在京为官时,以三千金之价购此书于邓氏,一时轰动京城。不料数年之后,位于北京西安门外的袁宅失火,火势猛烈,延及该书。袁思亮痛惜宝书,几欲以身赴火,与之俱焚,幸为家人拼死冒火救出。但此书过火竟未全毁,大部分得以幸存,如有神物护持,成为清代书林的传奇。稍遗憾的是,该书多册书口、书脑受损严重,各卷内容及题跋也有所损毁,后人因此称之为“焦尾本”。
袁思亮得书之前,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湖北学政王同愈曾见此书,并将首函的题记、图章等抄录一过,包括翁方纲、吴荣光、阮元、英和、顾莼、桂馥、何绍基、法式善、石韫玉、李文藻、钱坫、邵懿辰、曾国藩、陆费墀、冯应榴等六十余人的题记以及东坡笠屐图等。宣统元年(己酉,一九〇九)冬,章钰借得王同愈的抄本誊录一份。王同愈抄本于宣统三年(辛亥,一九一一)佚失于赣江;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顾廷龙先生抄录了章钰的录副本。之后,章氏的重抄本亦下落不明,顾廷龙先生的抄本便成孤本。顾廷龙先生的抄本《宋椠苏诗施顾注题跋钞》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影印出版,保留了翁方纲旧藏本在成为“焦尾本”之前的部分原貌。
民国时期,此“焦尾本”为不同藏家收藏,经历了不同的递藏路径。其中十九卷又三分之一[目录下半卷、卷三至四、七、十至十三、卷十四(三分之一)、十五至二十、二十九、三十二至三十四、三十七至三十八],二十册,经潘宗周、蒋祖诒、张泽珩递藏后,归台湾图书馆。该本钤有“大明锡山桂坡安国民太氏书画印”“毛晋书印”“汲古得修绠”“子晋”“谦牧堂藏书记”“商丘宋荦牧仲考藏本”“苏斋”“苏斋墨缘”“提督江西学政关防”“潘仕成印”“潘氏德畬珍赏”“藏之海山仙馆”“曾在潘德畬家”“伯夔”“刚伐邑斋”“吴兴张氏图书之记”等印。
另两卷(卷四十一、四十二)即《和陶渊明诗》,则初为著名藏书家陈清华(字澄中)于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冬在上海以重金购得。卷四十一钤“商丘宋荦收藏善本”“谦牧堂藏书记”“苏斋”“海山仙馆”“仕成”“祁阳陈澄中藏书记”“荀斋”等印,卷四十二钤“毛晋”“汲古主人”“商丘宋荦收藏善本”“谦牧堂藏书记”“翁方纲”“苏斋”“南海吴荣光书画之印”“祁阳陈澄中藏书记”“荀斋”等印。四周均有火烧痕迹。此二卷残本由陈清华带往香港,后至美国。陈晚年将此二卷分给子女,卷四十二归其子陈国琅,卷四十一归其女陈国瑾。卷四十二后经嘉德国际拍卖公司斡旋,于二〇〇四年由海外回归祖国。卷四十二之册连同陈清华其他珍贵藏书共二十三部入藏国家图书馆;不久,另一册(卷四十一)为私人藏书家韦力购得。
值得一提的是,“焦尾本”卷十六存于台湾图书馆,其首叶却被国家图书馆收藏。在国图收藏的嘉业堂旧藏本卷十二末附有“焦尾本”卷十六首叶一纸。上部及书口处焦损,有“大明锡山桂坡安国民太氏书画印”“毛晋之印”“商丘宋荦收藏善本”“谦牧堂藏书记”“苏斋墨缘”“苏斋”“荷屋”“筠清馆印”“德畬”“潘仕成”“叶志诜”“海山仙馆主人”等印,应属“焦尾本”散出之零叶。残叶“注东坡先生诗卷第十六”卷端题署清晰完整,正文首为“诗四十八首”(起在彭城,尽守吴兴),下第一首诗为《云龙山观烧得云字》,与目录卷第相合。据该残叶的国图采访编号,该“焦尾本”残叶入藏国图的时间早于嘉业堂本。嘉业堂本入藏之后,可能为了更好地保存此残叶,避免丢失,遂根据卷次顺序将该叶装订在嘉业堂本卷十二之末,与其卷十二合为一册。
二〇〇四年,《中华再造善本》将嘉业堂本与黄丕烈旧藏本一并影印出版,《中华再造善本提要》之《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所言“前四册曾为翁方纲苏斋旧藏”(《中华再造善本提要·唐宋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第六二八页)即指嘉业堂本。其实,此四册嘉业堂本与翁方纲无关。嘉业堂本使人联想到翁方纲的信息有两个,一是上述的“焦尾本”卷十六首叶,二是每卷末均钤有“苏斋”印。该印尺寸比“焦尾本”所钤“苏斋”印大(嘉业堂本印长约四点八厘米,宽约二点八厘米;“焦尾本”印长约二点四厘米,宽约一点八厘米),但印章形制、字形都很相似。经过仔细甄别,该“苏斋”印并非翁方纲印章(此问题不是本文重点,不赘述)。所以,嘉业堂本并未经翁方纲收藏。
二〇一二年,台湾出版单位将台湾图书馆所藏的焦尾本十九卷与韦力先生所藏的一卷(卷四十一)一并影印出版,名曰“《注东坡先生诗:焦尾本》”。
本次影印国家图书馆所藏一卷(卷四十二),则存世的“焦尾本”全部影印出版,供社会各界使用。
李坚
二〇二三年一月
《注东坡先生诗》一卷,为“续宋本丛书”仿真系列中一种。宋苏轼撰,宋施元之、顾禧、施宿编注。宋嘉定六年(一二一三)淮东仓司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翁方纲旧藏本,俗称“焦尾本”。此本书品宽大,历经众名家收藏,最早成为苏东坡生日祭书会之本,书中题咏、画作网罗了清代士林名流,各卷前后遍钤印记,几无隙地;瓷青纸上泥金题跋、绘花,别具风采,彰显东坡品格。此本又遭火焚而不毁,其经历亦称传奇。
宋嘉定六年淮东仓司刻本《注东坡先生诗》(翁方纲旧藏“焦尾本”卷四十二)
——代前言
宋代有许多苏轼诗歌的注本,其中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是题为王十朋编纂的《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直到明末清初,苏诗注本以此书最为通行。该书汇集了此前几乎所有的苏诗注,网罗宏富,但注释不标出处,分类杂乱。
宋代另有一部由施元之、顾禧、施宿编注的《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年谱》一卷(以下简称《注东坡先生诗》),由于流传不广,长久以来沉晦不彰。直到清代康熙年间,宋荦购得此书的宋刻残本,经补辑整理,改以《施注苏诗》之名,雕版印行,这部罕见的宋代苏诗注本,才重又化身千百,广传于世。
遗憾的是,参与整理《施注苏诗》的邵长蘅、顾嗣立、宋至、李必恒等人,对施、顾原注肆意增删,妄改臆断,导致全书从内容到形式,都大异于宋刊本的原貌。《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四指出:
元之原本注在各句之下,长蘅病其间隔,乃汇注于篇末。又于原注多所刊削,或失其旧。后查慎行作《苏诗补注》,颇斥其非,亦如长蘅之诋王注。然数百年沉晦之笈,实由荦与长蘅复见于世,遂得以上邀乙夜之观,且剞劂枣梨,寿诸不朽,其功亦何可尽没欤?
四库馆臣肯定了宋荦、邵长蘅等人刊印稀见宋本的功劳,但对其刊削原注、毁失宋版旧貌的错误做法,也实事求是地给予了严厉批评。以“佞宋主人”自称的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对《施注苏诗》刊削宋版尤为不满,甚至斥其“可覆酱瓿”。而更多的学者,都为见不到宋刻原本而深感遗憾。
宋刻《注东坡先生诗》笺注精审,版印精美,是宋本中的上品。惜存世珍罕,仅有几部历经名家递藏的残本流传。该书在元明两代踪迹难觅,自清康熙年间《施注苏诗》印行以来,即备受学界关注。
本次影印的是国家图书馆藏翁方纲旧藏“焦尾本”——宋嘉定六年(一二一三)淮东仓司刻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卷四十二(《和陶渊明诗》)。
一、成书与刊刻
《注东坡先生诗》正文四十二卷,前三十九卷为编年诗,卷四十收翰林帖子及遗诗;卷四十一、四十二为“和陶诗”。其苏诗编年,完全依照宋代通行的《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但分卷与之不同,每卷卷首均有编年提纲。《东坡年谱》一卷由施宿编撰,其中诗目是施宿自行编年的,所编诗目的序次、篇章数量与正文诗注并不相同。
全书注文分为两类。一是诗句注(以下简称句注),即对诗句的注释。二是诗题注(以下简称题注),即置于标题之后的注释,题注又分为题下注和题左注——题下注位于标题之下,文字多行者,注文与标题齐平,较正文低三字;题左注位于标题左侧,另起一行,比标题低两字。句注与题下注的内容为典故、成语、地理、名物等;题左注内容则以解析苏轼所处时代的人物、掌故、朝政时局,以及作诗的主旨为主。另有少量记载东坡某诗墨迹的注释,以及对典故、地理、名物等的注释。
《注东坡先生诗》的编撰历经三十余年,是施氏父子两代人共同完成的杰作。正文四十二卷约于淳熙三年至嘉泰元年(一一七六至一二〇一),由施元之、顾禧完成初稿;自嘉泰二年至嘉定二年(一二〇二至一二〇九),施宿又增补了一部分注文,并作《苏轼年谱》一卷。
施元之(一一〇二?—一一七九?),字德初,吴兴(今属浙江湖州)人。绍兴二十四年(一一五四)进士,乾道二年(一一六六)为秘书省正字;乾道五年(一一六九)任秘书省著作佐郎,兼国史院编修,除左司谏;乾道七年(一一七一)任职衢州,曾知赣州。其三衢“坐啸斋”是当时著名的刻书坊。
顾禧,字景藩,或作景蕃,吴郡(今属江苏苏州)人。少纵游任侠,后折节读书,工诗文,曾注杜甫、苏轼诗。绍兴年间,以遗逸荐举,力辞不应,于邳村筑“漫庄”,自号“漫庄”,又号“痴绝”,隐居五十年,享高寿而终。
施宿(一一六四—一二二二?),字武子,元之子。绍熙四年(一一九三)进士,庆元初,知余姚县。后为绍兴通判,主持编撰《会稽志》。嘉定间,知吉州,后提举淮东常平仓,刊刻《注东坡先生诗》于仓司。施宿长于金石之学,曾于嘉定六年(一二一三)刻王顺伯《石鼓诅楚音》。章樵《古文苑注》卷一《石鼓文》云:“周宣王狩于岐阳,所刻《石鼓文》十篇,近世薛尚功、郑樵各为之音释,王厚之考正而集录之,施宿又参以诸家之本,订以《石鼓》籀文真刻,寿梓于淮东仓司,其辨证训释,盖亦详备。”
施元之、顾禧完成初稿后,施宿做绍兴通判时,延请当时已告老还乡的著名诗人陆游为本书作序,陆游序成于嘉泰二年(一二〇二),收入《渭南文集》卷十五。
施宿作注和编撰年谱的时间,大致为嘉定元年(一二〇八)春夏间至嘉定二年(一二〇九)中秋。不过,他的准备工作应该始于陆游作序之后不久,即于嘉泰二年(一二〇二)开始搜集资料。经过几年资料的积累,又综合施元之晚年搜集的部分资料,即施宿序所谓“先君末年所得未及笔之书者亦尚多有”,施宿终于完成了对《注东坡先生诗》注释的增补。施宿作注周详细密,用力颇深,且态度认真,书已刊刻,还在不断添改。
嘉定五年至六年(一二一二至一二一三),《注东坡先生诗》刊刻于淮东仓司,是施宿出任淮东仓司仓曹时主持刊刻的,由善写欧体字的傅穉手书上板。该书使用公款雕印,书板一直收存于淮东仓司。五十年以后,景定三年(一二六二),郑羽任提举淮东常平茶盐司长官时,看到这部书的板片已有部分模糊不清,便着手修补重刻,这就是景定修补本。该本末有郑羽的跋文:
坡诗多本,独淮东仓司所刊,明净端楷,为有识所宝。羽承乏于兹,暇日偶取观,汰其字之漫者大小七万一千五百七十七,计一百七十九板,命工重梓。他时板浸古,漫字浸多,后之人好事必有贤于羽者矣。景定壬戌中元,吴门郑羽题。
《注东坡先生诗》传本稀少,且非全帙,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该书的认识。关于三位著者及其注文、该书的编撰时间、刊刻年代等问题,清代以来,众说纷纭,以注释苏诗闻名的“注苏五家”——邵长蘅、查慎行、翁方纲、冯应榴、王文诰,以及郑元庆、阮元、余嘉锡等众多学者,都表达过不同的观点。直至近代以来,这些问题仍不断吸引学者予以研究、探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施宿自序、跋文和《东坡年谱》在日本的一个旧抄本内被发现,《注东坡先生诗》的诸多疑点豁然冰释。现结合新见资料及各家研究成果,就该书的编刊等问题,略作阐述。
《注东坡先生诗》的著者是谁?这个问题在清代就曾经存在误解,有些学者甚至不清楚作者有几人。翁方纲得到宋荦旧藏宋版《注东坡先生诗》残书以后,曾手书跋文感慨道:
卷前题云“吴兴施氏”“吴郡顾氏”,今相沿称“施注”,而不知有“顾”久矣!
可见某些错误认识,竟源自于《施注苏诗》题名“施注”之失。
其实,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对该书著者已说得明明白白:
《注东坡集》四十二卷,《年谱》《目录》各一卷。司谏吴兴施元之德初与吴郡顾景蕃共为之;元之子宿从而推广,且为《年谱》,以传于世。
施元之、施宿父子的生平,长久以来也鲜为人知。近人陈乃乾曾于《宋长兴施氏父子事迹考》序言中为此感言:
自宋迄今,致力于是书者或校或补,与夫考证题跋,无虑数十家,而于施氏父子之事迹莫能详悉。所引者惟《直斋书录解题》与《癸辛杂识》数行,知元之以进士官司谏,及其子宿为淮东仓司,以刻《苏诗》被弹去官而已。呜呼!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陈乃乾遍查南宋人文集及郡县方志,搜辑施氏父子行事,编成《宋长兴施氏父子事迹考》(《学林》一九四一年四月第六辑)长文。据该文所考,施元之、施宿父子不仅学识渊博,交游广泛,且都热衷于刊刻。正是施氏父子的共同努力,才有了《注东坡先生诗》的编纂和成功刊刻。
三位注释者各自所做的笺注工作是哪些?清人对此亦有不同看法:郑元庆认为“句解是元之笔,诗题下小传低数字,乃武子补注”;冯应榴认为“诗题下似亦有元之注”;王文诰、阮元、余嘉锡则认为施元之注人物时局,顾禧注典故,施宿只是在二人基础上略加增补。(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二《施注苏诗》)
从卷端题署和《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看,施元之显然是编撰《注东坡先生诗》的初始发起者及主要注释者。陈乃乾指出:“元之注《苏诗》致力最深。惟何年写定,无明文可考。”(《宋长兴施氏父子事迹考》所收罗愿《水调歌头·中秋和施司谏作》词下按语)。关于施元之开始笺注苏诗及其完成的时间,阮元推测“应在淳、绍之时”,此判断并无错误,但时间跨度太大,精准性不足。
施宿序说:
东坡先生诗,有蜀人所注八家,行于世已久。先君司谏病其缺略未究,遂因闲居,随事诠释,岁久成书。然当无恙时,未尝出以示人。后二十余年,宿郡佐会稽,始请待制陆公为之序。
根据邓广铭《辛稼轩年谱》,辛弃疾任江西提点刑狱时,曾于淳熙三年(一一七六)弹劾时任赣州知州的施元之,施因此离职,闲居在家。故施元之应在淳熙三年(一一七六)闲居之后开始注释苏诗。“然当无恙时”,指的是施元之在世之时,按此语义,下面的“后二十余年”句,显然是说直到他死后二十多年,施宿才请陆游作序。
陆游序文末题“嘉泰二年正月五日山阴老民陆游序”。正月五日属一年之初,从施宿请序到陆游写成序言,需要一定的时间,故施宿向陆游请序的实际时间,应该在嘉泰元年(一二〇一)。由嘉泰元年(一二〇一)上推“二十余年”,便可大致推定施元之的卒年。
陈乃乾《宋长兴施氏父子事迹考》将施元之的卒年定为淳熙元年(一一七四),显然有误,王水照《评久佚重见的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三年第三辑)认为施元之“去世当比淳熙四年更晚”。
从施元之闲居的淳熙三年至嘉泰元年(一一七六至一二〇一),共二十五年。假设施宿所说的“二十余年”只有二十年,即施元之卒于淳熙八年(一一八一),留给其作注释的时间有五年;假设是二十二年,那就只有三年时间。就“二十余年”的可能性而言,推测施元之卒于淳熙五年(一一七八)或六年(一一七九)之前,似较妥当。
《注东坡先生诗》洋洋四十二卷,释文极多。“岁久成书”,似是在说注释工作花费了较长时间且全书终于完成。但实际上,施元之从闲居到去世,时间并不太长。如果施元之卒于淳熙六年(一一七九),那他注释书稿的时间应不足三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独立完成全部注释工作,难免令人生疑。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施元之完成书稿以后,生前为何“未尝出以示人”?除非其未能完成书稿的注释或者是对自己的注释不够满意,否则他的行为实在有悖于常理。
施宿十三四岁时父亲去世,成年以后,又长年在外做官,对于父亲注诗工作的认识和了解都很有限。直到嘉泰二年(一二〇二)读到陆游所写的序文,才意识到父亲的书稿实际未能按其理想得以完成。施宿的序点明了施元之“未尝出以示人”的原因:
而序文所载在蜀与石湖范公往复语,谓坡公旨趣未易尽观遽识,若有所谨重不敢者。宿退而念先君于此书用力既久,独不轻为人出,意或有近于陆公之说。而先君末年所得未及笔之书者亦尚多有,故止于今所传。宿因陆公之说,拊卷流涕,欲有以广之而未暇。
原来,当时陆游看到的只是一个未最终完成的初稿,施元之还有许多“末年所得未及笔之书者”没有写进书稿里,这才是“先君于此书用力既久,独不轻为人出”的真正原因。我们有理由推断,施元之应该是带着很大的遗憾去世的,因为他在闲居的有限之年,只作了典故、成语、风土山川等常规注释,完成初稿,而最初计划和构想的一些与陆游观点相近的内容,如对当时人物、时局的解析等,尚未如愿写进书稿。
经过陆游序的点拨、启发,施宿才真正认识到父亲所追求并意欲完成的这部书稿的重要价值,他感激涕零,并由此产生了继承父志、增补完成全部书稿注释工作的决心,开始着力搜集苏轼经历、交往人物、掌故、时局等方面的资料,为全书增加了大量补注。
据郑骞《宋刊施顾注苏东坡诗提要》(严一萍、郑骞编《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一),台北:艺文印书馆,一九八〇年)统计研究,在现存三十六卷(合并现存残本,并剔除重复卷次)中,施宿所作题左注有三百五十余条,计五万两千五百七十余字,篇幅相当可观。题左注中有十三条施宿自称其名,其余各条与此十三条的文笔体裁,完全相同;题左注中有关神宗、哲宗两朝的政见观点,与施宿自序中持论相同;题左注中多处论述苏轼墨迹石刻和其他法书名画,与施宿的金石学专长吻合。
施宿在主持刊刻该书的时候,并没有在卷端署自己的名字,只是在序言中说明自己增补注文,“各附见篇目之左”。虽然施宿尽力突出父辈之名,对自己的贡献只在不起眼的序言中做了说明,但施宿的低调并不能掩盖题左注的耀眼光芒。全书的注文中,最重要、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部分正是施宿所作的题左注。
施宿注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施宿距离东坡时代不远,熟悉史事,更因为施宿的政治立场与苏轼一致,都反对王安石熙宁变法,他对苏轼深怀敬意,同情苏轼的坎坷遭遇。同时,施宿对待苏轼的态度比较公允,并没有一味“佞苏”和阿私附和,而是坚持自己独立的见解,难能可贵。
施宿为作此注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力颇深。他结合朝政时局,深入分析苏诗的写作背景,对读者理解和领悟苏轼的真实旨意,提供了积极的帮助;同时也为后人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宋史资料,如对卷十四《送李公择》、卷四十一《饮酒二十首》、卷四十一《岁暮作和张常侍》所作注释等。
清人对施宿的题左注评价甚高。张榕端《施注苏诗序》云:“又于注题之下,务阐诗旨,引事征诗,因诗存人,使读者得以考见当日之情事,与少陵诗史同条共贯,洵乎有功玉局(苏轼曾提举玉局观。——撰者注)而度越梅溪(王十朋,号梅溪。——撰者注)也。”邵长蘅《注苏例言》云:“《施注》佳处,每于注题之下多所发明,少或数言,多至数百言,或引事以征诗,或因诗以存人,或援此以证彼,务阐诗旨,非取泛澜,间亦可补正史之阙遗,即此一端,迥非诸家所及。”王文诰亦谓“最要是题下注事”。
《注东坡先生诗》的刊刻版式颇有特点。依照宋代刻书惯例,诗歌注本的版面形式特征是诗歌题目、正文采用大字,注文一般小字双行。题注置于诗题之下,诗文注随诗句注于各诗句之下。该书除了常见的题注和句注,还出现了罕见的标注于诗题左侧的题左注。根据施宿自序:
宿因先君遗绪,及有感于陆公之说,反覆先生出处,考其所与酬答赓倡之人,言论风旨足以相发;与夫得之耆旧长老之传,有所援据,足裨隐轶者,各附见篇目之左。
由此可证,列于“篇目之左”的题左注,都是施宿所作的注释。
从书籍刊刻的角度来说,题左注的出现,正是从版面形式上明显区分不同著者的一种独特方法,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清晰地展示题注和句注均为施元之、顾禧初稿的原注,而题左注则是施宿后来所作的补注。
另外,题注和句注是施元之、顾禧共为之,但二人如何合作?各自做了哪些工作?仅看文字内容,则难以区分。郑骞等学者认为施元之、顾禧同时合作完成,根据卷端署施元之、顾禧之名,陆游序提到顾禧,判断施元之退休回家之后,“施家住在湖州,距离顾禧的家乡苏州很近,通信会面都很方便,正是合作的好机会”(《宋刊施顾注苏东坡诗提要》第五节《施顾注的完成刊印与流传》)。不过,这个貌似顺理成章的结论,却没有想象中那么无懈可击。以当时的交通状况,湖州与苏州距离虽不太远,但要真正交流、沟通、合作,也不会特别容易。从陆游序说施宿“先人司谏公所注数十大编”以及施宿《后序》的记述可以判定,施元之是《注东坡先生诗》的创始作者,顾禧则属于后来加入的次要性的第二作者。陆游序先说施元之“历岁久,用工深”,之后夸赞“又助之以顾君景蕃之该洽”,显然对作者也是分了主次的。“该洽”大意是更为恰当、妥帖、完善,即是说顾禧的注释使此书显得更好了。如果施元之、顾禧二人开始即一起合作注释苏诗,陆游如此赞誉顾禧,显然对施元之有些不够尊重,更何况他面对的是施元之之子施宿。但如果是对后继加工、修订者的工作给予称赞,那就显得十分自然而顺畅。
通过陆游的话,也许可做出这样的推测,即顾禧并非初始就是与施元之一起注释苏诗的合作者,而极可能是施元之去世之后,施宿请顾禧对父亲原稿进行整理、加工、修订。准确地说,顾禧只是审稿和修订者。据陈鹄《耆旧续闻》卷二,赵右史家有顾禧《补注东坡长短句》真迹。正因为顾禧之前曾为《东坡乐府》做过补注,对于苏轼诗词中的时事、掌故比较熟悉,故施宿邀请顾禧帮助整理、修订父亲施元之注释的初稿。
出于审稿人的责任,更出于对苏轼诗歌的热爱,顾禧增改了许多注释,只可惜他所作的补注,大多未见署名,被淹没于书稿中了。翁方纲指出:“今注中尚有数处存顾氏姓名,卷二十《橄榄》诗注,卷三十四《立春日戏李端叔》诗注,而学者莫之详也。”(翁方纲《苏诗补注》卷八)。其中卷二十《橄榄》“已输崖蜜十分甜”注文:
《本草》:“崖蜜,又名石蜜,别有土蜜、石蜜。”《归叟诗话》曰:“范景仁云:‘橄榄木高大难采,以盐擦木身,则其实自落。’”顾禧注云:“记得《小说》:‘南人夸橄榄于河东人云:“此有回味。”东人云:“不若我枣。比至你回味,我已甜久矣。”’”枣,一作柿。
卷三十四《立春日小集戏李端叔》“须烦李居士,重说后三三”注文:
延一《广清凉传》:无著禅师游五台山,见一寺,有童子延入。无著问一僧云:“此处众有几何?”答曰:“前三三、后三三。”无著无对。僧曰:“既不解,速须引去。”顾禧云:“此诗方叙燕游而遽用后三三语,读者往往不知所谓,盖端叔在定武幕中,特悦营妓董九者,故用九数以戏尔。闻其说于强行父云。”
由此可见,顾禧对一些时事比较了解,他的补注较原注有了深化。而此两条补注,正说明施元之与顾禧的注释工作有先后之分,顾禧是一位审稿者,是后来才加入整理、补注此书的工作的。
《直斋书录解题》未提及《注东坡先生诗》的刊印时间和地点。关于其刊刻时间,清代学者也有不同观点。宋荦、翁方纲等根据陆游嘉泰二年(一二〇二)序推定该书刻于嘉泰二年(一二〇二),如“公诗故有吴兴施氏元之注四十二卷,元之子宿推广为《年谱》,而陆放翁序之,宋嘉泰间镂版行世。”(《施注苏诗》宋荦序);“施氏《注东坡诗》四十二卷,镂版于宋嘉泰间”(邵长蘅《题宋本施注苏诗》),“据《渭南集》,是书之刻在嘉泰二年壬戌时”(顾廷龙抄本《宋椠苏诗施顾注题跋钞》翁方纲题记)。冯应榴则认为该书刻于嘉定年间,“施德初卒年无考,而乾道七年尚官衢州。其子武子嘉定间始刊其父所注”(《苏文忠公诗合注·凡例》)。在这两种观点中,“嘉泰说”一直占主流,近代以来各家目录多将其著录为嘉泰刻本。
其实,该书卷三十八《次韵郑介夫诗》题左注,有“嘉定六年赐谥忠介”之语,足证刻书时间不可能早于嘉定六年(一二一三)。至施宿跋文被发现,该跋落款“嘉定六年中秋日,吴兴施宿书”,说明施宿于嘉定六年(一二一三)刊刻该书确凿无疑,而以陆游序之年份确定刊刻时间则失之草率。
关于其刊刻地点,也有不同的说法。宋周密《癸辛杂识》:“宿尝以其父所注坡诗刻之仓司,有所识傅穉,字汉儒,穷乏相投,善欧书,遂俾书之锓板,以赒其归。因摭此事,坐以赃私。”(《癸辛杂识》别集上“施武子被劾”条)
现存宋景定三年(一二六二)印本中郑羽跋文,正好与《癸辛杂识》互相印证,说明该书刊刻于淮东仓司。
而《四库全书总目》所谓“嘉泰中,宿官余姚,尝以是书刊版。缘是遭论罢,故传本颇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四《施注苏诗》),显然对其刊刻时间和地点均做误判。
明末清初钱谦益曾收藏过一部嘉定刊《注东坡先生诗》全本,惜毁于绛云一炬。《绛云楼书目》卷三著录:“宋板《东坡诗集施注》四十二卷,又《年谱》《目录》各一卷。”钱谦益又作《跋东坡先生诗集》(《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五)。钱谦益应该是清代唯一见过全本的学者,他的跋语是比较客观可靠的,现录其跋如下:
吴兴施宿武子增补其父司谏所注东坡诗,而陆务观为之序。务观序题嘉泰二年,是书刻于嘉定六年,又十二年而后出。故其考证人物,援据时事,视他注为可观。然如务观所与范致能往复方云,不知果无憾否?诗以纪年为次,又附《和陶》一卷。坡诗尽于此矣,读者宜辨之。
钱谦益对该书刊刻年份的著录和判断,恰好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日本发现旧抄本的可靠性。
二、《追和陶渊明先生诗》
《和陶诗》又名《追和陶渊明先生诗》,是苏轼晚年自编的一部诗集,主要收录其晚年居惠州、儋州时追和东晋诗人陶渊明的诗作。
苏轼一生坎坷,遭贬于海南以后,写下了许多追和陶渊明的诗歌。如居惠州时所作《和陶归园田居六首》,有诗序云:
始,余在广陵和渊明《饮酒二十首》,今复为此,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
苏轼对其所作和陶诗极其重视,亲自将这些诗作结集出版。他在写给弟弟苏辙的信中说:
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其为我志之。
(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
陶诗看似朴素,实则华丽;貌似平淡,实则意味深邃。苏轼追写《和陶诗》,不单是对陶诗艺术的欣赏,更多的是思想行为上的追随。正如苏轼所说:
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俯仰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
苏轼博学多识,才气横溢,堪称千古奇才。其一生虽遭遇无数艰难困苦,却能以旷达的人生态度面对逆境,超然物外、与世无争。在这一点上,苏轼和陶渊明很相似。黄庭坚曾有诗曰:
渊明千载人,东坡百世士。
出处固不同,风味要相似。
据《郡斋读书志》,苏轼著作南宋时已有《东坡前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集》四卷、《应诏集》十卷,共七集行世。现存宋黄州刻“东坡七集”本之《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集》四卷,即反映了《东坡和陶诗》的初始面貌。
《注东坡先生诗》前四十卷的各卷内容均在卷前标明,题作“诗××首”(如卷三题“诗四十五首”),卷四十一、四十二《和陶诗》,卷前分别题作“《追和陶渊明诗》五十四首”“《追和陶渊明诗》五十三首”。卷前题署的不同,说明前四十卷来源于《东坡前集》《后集》;卷四十一、四十二《和陶诗》,来源于四卷本《和陶诗》。
卷四十一收录的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表明当时收录在《和陶诗》之内的苏轼追和陶渊明诗是一百零九首。但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一所收《子瞻追和陶渊明诗引》与此句文字有异,作“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因此,清代学者对《和陶诗》收诗是否“一百有九”颇有怀疑,王文诰认为是一百二十四首,查慎行认为是一百三十三首。
依据我国台湾图书馆藏宋黄州刻本《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集》目录(该目录以诗题为记,同一诗题有两首以上者标明数字,再除去陶诗原作及苏辙和诗)统计,共收苏轼和陶诗一百零七首,外加末尾的和《归去来辞》《桃花源》二赋,总计一百零九首。因此,《注东坡先生诗》的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所谓的“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无疑属于原始提法,应该正确无误。
关于《注东坡先生诗》卷四十一、四十二的所收诗数,需要略作说明。依据目录,卷四十一实收诗五十四首无误;卷四十二据目录诗题统计作五十三首,但其中《和杂诗十一首》漏刻第七首“蓝桥近得道,常苦世褊迫”一诗,故实际收诗五十二首。两卷合计,实际收诗一百零六首。又以《注东坡先生诗》目录诗题核之黄州本,施顾本较黄州本缺少《和东方有一士》《和刘柴桑》二首。
综上所述,施顾本和陶诗较黄州本缺诗三首:《和东方有一士》、《和刘柴桑》、《和杂诗十一首》之第七首。依常理看,施顾本所缺三首,最有可能像《和杂诗十一首》之第七首那样漏刻或漏抄所致,但也不能排除其他原因。
施顾本《和陶诗》与黄州本所收内容有明显的区别——施顾本惟有苏轼和陶渊明诗;黄州本收录陶渊明、苏轼、苏辙三人诗作,在每首陶渊明原诗之后,接录苏轼和诗及苏辙再和诗。
据黄州本卷二目录,《移居二首》《和刘柴桑》二诗应以先后顺序出现,正文却出现混乱,陶渊明《移居二首》原诗之后,接刻的不是苏轼《和移居二首》,而是陶渊明《和刘柴桑》原诗。黄州本每版二十行(半叶十行,行十六字),此叶首行刻陶渊明《移居二首》尾句“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第二至九行插刻陶渊明《和刘柴桑》原诗,第十行起接刻苏轼《和移居二首》诗并引,直至下叶第九行止,十行起顺接陶渊明《岁暮作和张常侍》原诗。除了此叶,其他各叶内容顺序均与目录相合无误。因此,据黄州本目录统计,苏轼《和陶诗》是一百零九首,但其正文漏刻了《和刘柴桑》一首,实际收录一百零八首。
由此可以断定,黄州本漏刻了苏轼《和刘柴桑》原诗,施、顾著《和陶诗》的底本极有可能据黄州本过录。对于印本书出现的此类错误,如果不够细心,较难发现问题所在。所以,施顾本缺失此诗,更有可能是“因错就错”。即便发现了问题,倘若是代为抄书的书手,也很有可能因莫名所以而选择放弃过录此诗,以避免混乱。这样的做法,对于一个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的书手来说,尚可看作是负责而又较为合理的选择。
三、现存宋刻残本
宋代《直斋书录解题》首次著录《注东坡先生诗》,《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四《经籍》七十一著录沿袭之,仅个别字改动。之后元明两朝几乎未见提及。清初以后,该本遂成为凤毛麟角般的存在。
《注东坡先生诗》目前存世的仅有四部残本:黄丕烈旧藏本、嘉业堂旧藏本(缪荃孙旧藏本)、翁同龢旧藏本、翁方纲旧藏本。除了翁同龢旧藏本是景定三年(一二六二)郑羽补刊本,其余均为嘉定原刻本。
黄丕烈旧藏本存二卷(卷四十一至四十二,卷端题“卷上”“卷下”,即《和陶渊明诗》二卷),二册,现藏国家图书馆。该书经清季振宜、周锡瓒、黄丕烈、汪文琛、汪士钟、杨氏海源阁递藏,有周锡瓒跋、黄丕烈跋并题诗、潘奕隽题诗。民国以后,归著名藏书家周叔弢先生,由周叔弢先生捐赠予国家图书馆。
嘉业堂旧藏本(缪荃孙旧藏本)存四卷(卷十一至十二、二十五至二十六),四册,现藏国家图书馆。各册有“刘承乾印”“翰怡”“翰怡欣赏”“张叔平”“诗外簃藏书”“徐伯郊”“徐伯郊藏书记”“伯郊”“伯郊所藏”“吴兴徐氏”“人间孤本”“文靖世家”等印,据此可知,此本原为嘉业堂旧藏,后经张叔平、徐伯郊之手,归于国家图书馆。据《藏园群书题记》,此本原为缪荃孙艺风堂旧藏,后归嘉业堂。
常熟翁同龢旧藏本存三十二卷(卷三至四、十一至十八、二十一至四十二),三十四册。此本曾经清怡亲王府收藏,有同治间翁氏题跋、潘祖荫跋,光绪间沈曾桐题识等。钤“安乐堂藏书记”“常熟翁同龢藏本”“同龢私印”“郑盦”“说心堂”“龙自然室”等印。此书曾由翁氏后人携往美国。一九八〇年,翁同龢玄孙翁万戈先生将该本付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出版;二〇〇〇年,该书由海外回归祖国,入藏上海图书馆;二〇〇四年,《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此本。
在四部宋刻本中,以翁方纲旧藏本最为著名,该本存卷较多,递藏经历曲折,留下不少书林佳话。该本系明嘉靖时期安国、毛晋汲古阁藏嘉定刻本的残本,入清后归徐乾学。康熙年间为商丘宋荦购入,仅存三十卷(目录下半卷,卷三至四、七、十至二十二、二十四至二十五、二十七至三十四、三十七至三十八、四十一至四十二),宋荦命邵长蘅、李必恒等删补、翻刻为《施注苏诗》,成为通行本。康熙五十四年至五十六年(一七一五至一七一七),该本归于揆叙,到了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内阁学士翁方纲在北京购得该本,翁方纲因此自号“苏斋”,并给自己的书室取名“宝苏斋”。每年农历十二月十九苏东坡生日,翁方纲都要招集亲朋好友、硕儒名彦至家中,展示此书,焚香祭拜,设宴鉴赏,三十年如一日。翁方纲和其他乾嘉以来名流如桂馥、阮元、何绍基等人的手跋、题识、观款尽留书上;又有翁方纲四十岁小像、顾莼泥金绘梅花、东坡生日消寒图等,堪称宋版书中至为名贵者。
翁方纲之后,道光六年(一八二六),该书归吴荣光。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潘仕成得之,清道光、咸丰间,归汉阳叶名澧,光绪中邓振瀛收藏,光绪末年,湘潭袁思亮在京为官时,以三千金之价购此书于邓氏,一时轰动京城。不料数年之后,位于北京西安门外的袁宅失火,火势猛烈,延及该书。袁思亮痛惜宝书,几欲以身赴火,与之俱焚,幸为家人拼死冒火救出。但此书过火竟未全毁,大部分得以幸存,如有神物护持,成为清代书林的传奇。稍遗憾的是,该书多册书口、书脑受损严重,各卷内容及题跋也有所损毁,后人因此称之为“焦尾本”。
袁思亮得书之前,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湖北学政王同愈曾见此书,并将首函的题记、图章等抄录一过,包括翁方纲、吴荣光、阮元、英和、顾莼、桂馥、何绍基、法式善、石韫玉、李文藻、钱坫、邵懿辰、曾国藩、陆费墀、冯应榴等六十余人的题记以及东坡笠屐图等。宣统元年(己酉,一九〇九)冬,章钰借得王同愈的抄本誊录一份。王同愈抄本于宣统三年(辛亥,一九一一)佚失于赣江;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顾廷龙先生抄录了章钰的录副本。之后,章氏的重抄本亦下落不明,顾廷龙先生的抄本便成孤本。顾廷龙先生的抄本《宋椠苏诗施顾注题跋钞》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影印出版,保留了翁方纲旧藏本在成为“焦尾本”之前的部分原貌。
民国时期,此“焦尾本”为不同藏家收藏,经历了不同的递藏路径。其中十九卷又三分之一[目录下半卷、卷三至四、七、十至十三、卷十四(三分之一)、十五至二十、二十九、三十二至三十四、三十七至三十八],二十册,经潘宗周、蒋祖诒、张泽珩递藏后,归台湾图书馆。该本钤有“大明锡山桂坡安国民太氏书画印”“毛晋书印”“汲古得修绠”“子晋”“谦牧堂藏书记”“商丘宋荦牧仲考藏本”“苏斋”“苏斋墨缘”“提督江西学政关防”“潘仕成印”“潘氏德畬珍赏”“藏之海山仙馆”“曾在潘德畬家”“伯夔”“刚伐邑斋”“吴兴张氏图书之记”等印。
另两卷(卷四十一、四十二)即《和陶渊明诗》,则初为著名藏书家陈清华(字澄中)于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冬在上海以重金购得。卷四十一钤“商丘宋荦收藏善本”“谦牧堂藏书记”“苏斋”“海山仙馆”“仕成”“祁阳陈澄中藏书记”“荀斋”等印,卷四十二钤“毛晋”“汲古主人”“商丘宋荦收藏善本”“谦牧堂藏书记”“翁方纲”“苏斋”“南海吴荣光书画之印”“祁阳陈澄中藏书记”“荀斋”等印。四周均有火烧痕迹。此二卷残本由陈清华带往香港,后至美国。陈晚年将此二卷分给子女,卷四十二归其子陈国琅,卷四十一归其女陈国瑾。卷四十二后经嘉德国际拍卖公司斡旋,于二〇〇四年由海外回归祖国。卷四十二之册连同陈清华其他珍贵藏书共二十三部入藏国家图书馆;不久,另一册(卷四十一)为私人藏书家韦力购得。
值得一提的是,“焦尾本”卷十六存于台湾图书馆,其首叶却被国家图书馆收藏。在国图收藏的嘉业堂旧藏本卷十二末附有“焦尾本”卷十六首叶一纸。上部及书口处焦损,有“大明锡山桂坡安国民太氏书画印”“毛晋之印”“商丘宋荦收藏善本”“谦牧堂藏书记”“苏斋墨缘”“苏斋”“荷屋”“筠清馆印”“德畬”“潘仕成”“叶志诜”“海山仙馆主人”等印,应属“焦尾本”散出之零叶。残叶“注东坡先生诗卷第十六”卷端题署清晰完整,正文首为“诗四十八首”(起在彭城,尽守吴兴),下第一首诗为《云龙山观烧得云字》,与目录卷第相合。据该残叶的国图采访编号,该“焦尾本”残叶入藏国图的时间早于嘉业堂本。嘉业堂本入藏之后,可能为了更好地保存此残叶,避免丢失,遂根据卷次顺序将该叶装订在嘉业堂本卷十二之末,与其卷十二合为一册。
二〇〇四年,《中华再造善本》将嘉业堂本与黄丕烈旧藏本一并影印出版,《中华再造善本提要》之《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所言“前四册曾为翁方纲苏斋旧藏”(《中华再造善本提要·唐宋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第六二八页)即指嘉业堂本。其实,此四册嘉业堂本与翁方纲无关。嘉业堂本使人联想到翁方纲的信息有两个,一是上述的“焦尾本”卷十六首叶,二是每卷末均钤有“苏斋”印。该印尺寸比“焦尾本”所钤“苏斋”印大(嘉业堂本印长约四点八厘米,宽约二点八厘米;“焦尾本”印长约二点四厘米,宽约一点八厘米),但印章形制、字形都很相似。经过仔细甄别,该“苏斋”印并非翁方纲印章(此问题不是本文重点,不赘述)。所以,嘉业堂本并未经翁方纲收藏。
二〇一二年,台湾出版单位将台湾图书馆所藏的焦尾本十九卷与韦力先生所藏的一卷(卷四十一)一并影印出版,名曰“《注东坡先生诗:焦尾本》”。
本次影印国家图书馆所藏一卷(卷四十二),则存世的“焦尾本”全部影印出版,供社会各界使用。
李坚
二〇二三年一月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