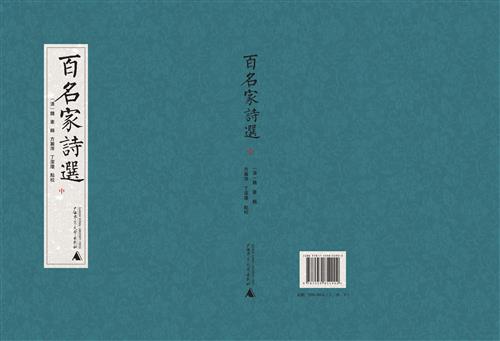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2-10-01
定 价:398.00
作 者:(清)魏宪辑;方丽萍、丁洁琼点校
责 编:刘艳艳,闫曦
图书分类: 史料典籍
读者对象: 文化研究者
上架建议: 历史/史料典籍
开本: 32
字数: 855 (千字)
页数: 14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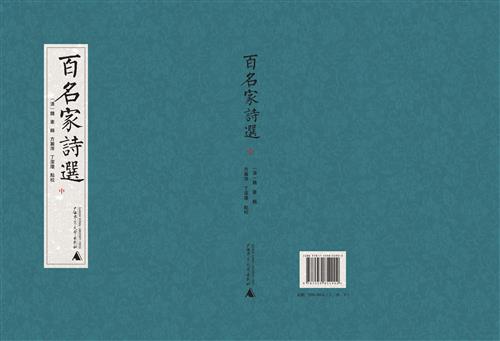
《清代诗歌总集丛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清诗歌总集文献整理与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拟收清代诗歌总集11种,加以点校整理。
《百名家诗选》为其中一种,亦名《皇清百名家诗选》,共89卷,魏宪辑。全书选录了清初(1623-1672年)91位诗人诗作,此书迄今未有点校本出版。此次点校以清康熙魏氏枕江堂刻本为底本,以清康熙二十四年圣益斋本、和聚锦堂印本为主要参校本。同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前言,对作者生平、文学主张、版本异同、诗学价值等做出全面的介绍与评价,确保文献整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魏宪,字惟度,清顺治间庠生。曾任兵部郎和广西按察使(一作左布政使)等职。
方丽萍,玉林师范学院教授、博士。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项,参与完成省社科联项目两项。
丁洁琼,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毕业文学硕士,青海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讲师。
前 言
凡 例
目 录
御製昇平嘉宴詩序
御製麗日和風被萬方
登選姓氏(以得詩之先後為次)
卷一 魏裔介
卷二 李 霨
卷三 王崇簡
卷四 龔鼎孳
卷五 梁清標
卷六 王 熙
卷七 錢謙益
卷八 吳偉業
卷九 曹 溶
卷十 申涵光
卷十一 曹申吉
卷十二 佟鳳彩
卷十三 楊思聖
卷十四 戴明說
卷十五 沈 荃
卷十六 陳廷敬
卷十七 王士祿
卷十八 王士禛
卷十九 曹爾堪
卷二十 施閏章
卷二十一 嚴 沆
卷二十二 宋 琬
卷二十三 張永祺
卷二十四 梁清寬
卷二十五 范承謨 范承斌 范承烈
卷二十六 魏裔魯
卷二十七 孔胤樾
卷二十八 郜煥元
卷二十九 陳寶鑰
卷三十 柯 聳
卷三十一 毛 逵
卷三十二 馮如京
卷三十三 程可則
卷三十四 周令樹
卷三十五 李衷燦
卷三十六 傅為霖
卷三十七 程 雲
卷三十八 嚴曾榘
卷三十九 顧大申
卷四十 陸求可
卷四十一 周體觀
卷四十二 王日高
卷四十三 范 周
卷四十四 王紫绶
卷四十五 竇遴奇
卷四十六 王追騏
卷四十七 李贊元
卷四十八 紀映鐘
卷四十九 劉六德
卷五十 黃茝若
卷五十一 宋 翔
卷五十二 馮雲驤
卷五十三 申涵盼
卷五十四 袁 佑
卷五十五 毛升芳
卷五十六 梅 清
卷五十七 計 東
卷五十八 趙 威
卷五十九 孟 瑤
卷六十 程啟朱
卷六十一 楊輝斗
卷六十二 成 光
卷六十三 黃 伸
卷六十四 黃 任
卷六十五 張祖詠
卷六十六 張鴻儀
卷六十七 張鴻佑
卷六十八 劉友光
卷六十九 戴其員
卷七十 李念慈
卷七十一 陸 輿
卷七十二 沈道映
卷七十三 朱 驊
卷七十四 孫 郁
卷七十五 劉元徵
卷七十六 楊州彦
卷七十七 楊思本
卷七十八 劉維禎
卷七十九 王澤弘
卷八十 丘象升
卷八十一 葉雷生
卷八十二 宗元鼎
卷八十三 毛師柱
卷八十四 黃之鼎
卷八十五 曹玉珂
卷八十六 吳學炯
卷八十七 釋大依
卷八十八 釋讀徹
卷八十九 魏 憲
附錄
成性
孔興釪
吳偉業序
凡例
題跋
鄧之誠跋
鄭振鐸跋
一
魏憲,字惟度,號兩峰居士,別署兩峰、枕江堂主人、竹川釣叟、虛舟漁史等,福建福清人。著有《枕江堂集》(詩十卷、文一卷),編有《詩持》《補石倉詩選》《燕台送別詩》等詩歌總集。
萬曆《福州府志》[(明)潘頤龍等掌修:《福州府志·人文志》卷十七,萬曆二十四年刻本。]、康熙《福清縣志》等載魏憲曾祖文焲為嘉靖二十三年(1544)進士,曾任兵部郎中,歷任知府,分守嶺西副使轉廣西按察使等,有文集《石室私抄》(九卷)[(清)李傳甲修、郭文祥纂:《福清縣志》卷六,清康熙十一年刻本。]。魏憲父名賢訒(1577-1650),字獻可,號仁者。天啟二年(1622)“始鐸富春”,崇禎元年(1628)“擢定海令”。次年即憤然於“有司”構陷而辭官返鄉。魏賢訒為人剛直爽快,“吾生平以意氣過激,不得大用”,臨終囑令兒孫“慎之”[(清)魏憲:《枕江堂文集·贈文林郎仁者五府君行狀》,康熙癸丑有恒書屋刊。]。魏憲“為人豪爽,刻苦問學,肆力於詩。……以詩交海內”[(清)郭柏蒼,楊浚輯錄:《全閩明詩傳》卷三十八,《萬里朝九·董養河》;鄭傑等輯錄:《全閩詩錄》第4册,福建省文史研究館整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19頁。],待人謙恭和善,與清初詩壇诗人、選家,如錢謙益、吳偉業、魏裔介、周亮工、施閏章等都有交往。
魏憲生年,學界有幾說:柯愈春先生認為大致是在“萬曆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1611-1615)之間”[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3頁。],陸林先生推斷“當生於天啓四年(1624)”[陸林:《知非集——元明清文學與文獻論稿》,合肥:黃山書社,2007年,第428頁。],黃浩然先生斷魏憲生於天啟六年(1626)[黃浩然:《魏憲研究》,南京師范大學2009年碩士學位論文。另:魏憲生於天啟六年(1626),卒於康熙二十二年(1682)冬後,這一觀點亦見於鄧曉東博士論文《清初清詩選本研究》(南京師范大學2009年博士學位論文)。]。《補石倉詩選》中有魏憲康熙二十二年(1683)冬編選胡介祉詩的材料,可斷定魏憲卒於康熙二十二年冬後。
“甲午之役,余誤副車。滙(原文即此字)白夫子監厥事,爲歎息者久之。至以詩相慰,留寓白門,爲襄《詩持》之選。”[(清)魏憲:《百名家詩选·佟鳳彩》卷一二。]甲午年是順治十一年(1654),這一年魏憲鄉試落榜,之後再沒有參加過科举,故文獻大都稱其為“順治間庠生”。他一生四處游歷,“所至皆交結當地名士以采詩”,曾在北京、江蘇南京、江蘇蘇州、江蘇常州、江蘇揚州、安徽宣城、河北大名、河南濮陽、山東東明、安徽蒙城、河南開封、河南商丘多地盘桓。游历期间,魏憲一方面與當地詩人交游唱和,一方面將所得之詩編選、刊印。魏憲本人詩作也入選其他选家詩選中,且都被給予較高評價。如與他同時期的鄧漢儀(1617-1689)所編《詩觀》選其詩五首,且評其《雲屏》有“壯句”“寫得蒼茫有氣”;《光明頂》“字字精煉,筆有奇光”[(清)鄧漢儀撰,陸林、王卓華輯:《慎墨堂詩話》,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433、992頁。];卓爾堪(康熙時人,生卒不詳)《遺民詩》選其詩四首,鄭傑(約1750-1800)《國朝全閩詩錄初集》卷五選其詩兩首,徐世昌(1855-1939)《晚晴簃詩匯》選其詩六首。詩歌外,“惟度於古文詞,若誌、序、銘、記,以及傳奇各體,動筆千百言,無不原本於漢唐,浸淫於子史”[(清)魏憲:《枕江堂詩集·孔胤樾序》,康熙癸丑有恒書屋刊。];魏憲詞作,《全明詞》《全清詞》中均有收錄,所作《芙蓉屏傳奇》在當時有一定影響[(清)魏憲:《百名家詩選·趙威》卷五八,《讀魏惟度芙蓉屏傳奇有感》。]。
儘管卓爾堪、鄭傑等均將魏憲視作遺民詩人,但入清時魏憲只有十八歲,且參加了順治十一年(1654)的鄉試。因此番鄉試落榜,魏憲终生未得仕進,所以稱其為明遺民恐不合適。
二
《百名家詩選》已知版本三種:(一)康熙十年(1671)魏氏枕江堂本;(二)康熙二十一年(1682)聚錦堂本;(三)康熙二十四年(1685)聖益齋本。
三個版本基本情况如下:
枕江堂本。左右雙邊,半頁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單黑魚尾,下書口鐫“枕江堂”三字。卷前有吳偉業序、凡例(八則),其後為登選姓氏(九十一家,含各卷所選詩人姓字、籍貫、選詩總頁數、小引頁數等信息)。如“魏裔介,石生,貞庵。直隸柏鄉人,詩二十六、引二”,表示魏裔介詩在卷內占二十六頁,小引兩頁[《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此中數字解讀為選詩數,誤。參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36頁。]。其後依次為小引、書名、選家、四位參選者姓字、籍貫,本卷詩人姓字、籍貫,入選詩歌。枕江堂本吉林大學圖書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日本神户市立中央圖書館有藏,《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據吉林大学圖書館藏本影印出版。
聚錦堂本。左右雙邊,半頁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單黑魚尾,下書口鐫“枕江堂”三字。內封右刻“閩中魏惟度彚輯”,中刻“皇清百名家詩”,左刻“聚錦堂藏板”。卷前為《御製昇平嘉宴詩序》與《御製麗日和風被萬方》詩,其餘和其他兩本基本相同。此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湖南省圖書館、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有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藏稀見叢書彙刊》所影印均為聚錦堂本,前者據湖南省圖書館藏本影印,後者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影印。
聖益齋本。內封右刻“閩中魏惟度彚輯”,中刻“國朝百名家詩選”,左刻“詩持廣集 聖益齋藏板”,天頭刻“康熙乙丑年鐫”。左右雙邊,半頁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單黑魚尾,下書口鐫“枕江堂”三字。此本登選姓氏有一百〇一家,十家名後有“嗣刻”二字[嗣刻者為葉芳藹、馮雲驌、汪琬、徐乾學、龔章、尤侗、倪燦、陳維崧、黃虞稷、吳朔十家。],卷前為《御製昇平嘉宴詩序》與《御製麗日和風被萬方》詩,後基本與其他兩本同。國家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有藏。國家圖書館藏本上有鄭振鐸手跋。
經比勘,以上三個版本在版式、內容上基本相同,實為一個版本系統。“枕江堂”是魏憲的室名,刊印過《詩持》《補石倉詩選》及《杜律詹言》等著作。“聚錦堂”是自明至清末在南京一直都很活躍的書坊,版刻書籍很多,醫書、詩選、小說等一應俱全。刻印過劉勰的《楊慎庵先生批點文心雕龍》,湯顯祖評《花間集》等著作[瞿冕良编著:《中國古籍版刻辭典》,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515、920頁。]。“聖益齋”可見資料很少,《歷代名人室名別號辭典》認為與枕江堂一樣也是魏憲的刻書室名[池秀雲編:《歷代名人室名別號辭典》,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25頁。],所刻書籍只有兩種,一是《百名家詩選》,二是順治十六年(1659)刊刻的《詩法入門指規》二卷,金陵陳美發輯,日本內閣文庫有藏。
三本均無評點,但個別卷內偶見夾註,如卷三十三程可則《銅鼓歌金公絢宅作》一詩“醉擊華堂聲陸續”句下小字夾註:“《晉書》諸獠並鑄銅為鼓,初成,懸庭中,置酒招同類。有富豪子弟來者,執金銀釵扣鼓,釵竟遺主人,名納鼓釵”;“詔置宣德稱奇珍”句下註:“《漢書》伏波征交趾,得駱越銅鼓,改鑄馬式上之,詔置宣德殿門”。卷八十還保留了幾首詩後的小記。
除卷八十九魏憲本人詩為“同學諸子公選定”外,其他卷均列有四位參選者,如卷一魏裔介詩是“宣城施閏章愚山、含山李衷燦梅村、黃岡程啟朱念伊、無錫顧貞觀華峰參”。大多數的入選者也多少不等地參與了其他卷的編選工作,如宋琬參編了梁清標、王熙、戴其員、沈道映、王澤弘的詩,王士禛參與了毛師柱詩的編訂;施閏章參與了魏裔介、陸求可、葉雷生、宗元鼎詩的編訂;吳偉業參與了吳學炯詩的編訂,曹爾堪參與了陸求可、沈道映、劉元徵、宗元鼎詩歌的編訂等。孔胤樾參編最多,參與了二十六卷(近三分之一)的編選工作,吳學炯參與了十三卷的編選。
清代姚觀元所編《清代禁毀書目(補遺)》載乾隆間《百名家詩選》“內有錢謙益、龔鼎孳詩,應剷除抽禁,餘書仍行世”。
三
《百名家詩選》三種版本雖屬一個版本系統,但彼此間存在一些差異,而這些差異導致我們對此書的版本判定出現不少問題。
首先是此書的版本來源及三個版本間的關係不清。三本有同有異:
第一,名稱有別:枕江堂本名《百名家詩選》,聚錦堂本為《皇清百名家詩》,聖益齋本作《國朝百名家詩選》;《中國古籍善本總目》著錄時間及依據不同:枕江堂本作康熙十年的依據是吳偉業序,聚錦堂本是御製詩及序的創作時間[康熙二十一年(1682)上元節,康熙與群臣(九十三人)柏梁聯句,康熙作序。四庫《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三十五收此詩及序,題作《昇平嘉宴同群臣賦詩用柏梁體》(並序)。參見(清)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升平嘉宴同群臣赋诗用柏梁体(并序)》卷三十五。],聖益齋本是封面上“康熙乙丑年鐫”字樣。體例不同:枕江堂本有吳偉業序、凡例,無御製詩序及詩。聚錦堂與聖益齋本有《御製昇平嘉宴詩序》及《御製麗日和風被萬方》詩,無吳偉業序,亦無凡例。
第二,登選姓氏(目錄)有細微差異。三本均收九十一人。各本均存在登選姓氏與卷內選人不完全對應的情况。三個版本均將卷八十七釋讀徹、卷八十八釋大依二人次序顛倒;聚錦堂本與聖益齋本目錄為馮如京,卷內為柯聳。聖益齋本目錄與卷內不同處最多。除上列外還有:卷三十二“成性”收馮如京詩,卷五十“馮雲驤”收黃茝若詩,卷五十二“孔興釪”收馮雲驤詩。這就導致聖益齋本比其他二本多出馮如京、馮雲驤詩而少孔興釪、成性詩。
第三,小引問題。陳融《颙園詩話》稱“人一小引,皆自作”[謝正光,佘汝豐編著:《清初人選清初詩匯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36頁。]。全部以“魏子曰”開篇,主要介紹本卷詩歌的由來、編者與本卷詩人的交往、得詩渠道,對入選者詩歌、人品的評價,以及對一些詩歌問題的看法。除卷八十九魏憲本人小引為陸輿(雪樵)撰外,其他均應為魏憲所作。三本小引均不全,枕江堂本、聖益齋本缺八卷小引[分別為:卷六王熙、卷九曹溶、卷三十柯聳、卷四十陸求可、卷五十八趙威、卷六十八劉友光、卷七十七楊思本、卷七十八劉維禎。],聚錦堂本另缺曹爾堪、陳寶鑰、黃茝若三人小引,共缺十一篇。聖益齋本馮如京、馮雲驤卷皆有小引,但與此書其他小引形製不同,為駢文,沒有魏憲與之交游的信息。馮如京小引與清陳維崧《佳山堂詩集序》(《陳檢討四六·卷五》)中部分文章內容大量重疊,馮雲驤篇內也存在與《陳檢討四六》部分文章相似文句。三本卷八十六小引與其他小引體例不同,題為《秋雨堂詩集原序》,乃魏憲為吳學炯《秋雨堂詩集》所作序言,從《枕江堂詩文集》中直接移入,未更換標題,但加上了与其他小引一致的“魏子曰”三字。
第四,刻印質量問題。三本中,聖益齋本最為精細,錯誤較少。聚錦堂本最為粗糙,有字體、字形不統一的現象,如卷二十三張永祺第十五、十六頁,卷三十一毛逵第一、二頁,卷三十八嚴曾榘第一、二頁,卷三十九顧大申第九、十頁,卷六十程啟朱第一、二頁,卷七十一陸輿第十五、十六頁,卷七十三朱驊第一、二頁內字體與其他部分字體明顯不同。卷三十一缺自《招燕》至《小孤山》的六首詩。入選詩人字號、籍貫錯誤,錯別字也比較多;枕江堂本未見內封,個別版心處有“補石倉詩選”字樣。
四
通過以上對照,《百名家詩選》中出現了與魏憲編選的另外兩部詩集《詩持》《補石倉詩選》相關的信息,要弄明白《百名家詩選》的本來面目,我們必須要釐清幾個關係。第一是與《詩持》《詩持廣集》的關係,第二是和《補石倉詩選》之間的關係。
《販書偶記》著錄“《詩持》一集四卷、二集十卷、三集十卷,閩中魏憲評選,康熙辛亥枕江堂刊”,“《詩持》四集一卷,東冶魏憲評選,康熙十九年枕江堂刊”;《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著錄大體相同,多版本信息:“《詩持》一集四卷、二集十卷、三集十卷、四集一卷,清魏憲編。清康熙魏氏枕江堂刊本,九行十八字。一至三集康熙十年刊,四集康熙十九年刊。”可知《詩持》四集共二十五卷,前三集彙刻于康熙十年(1671),四集刊刻於康熙十九年(1680)。《詩持》今藏清華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其內封右刻“閩中魏惟度先生評選”,中刻“詩持全集”,左下刻“枕江堂藏板”。四周單邊,半頁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單黑魚尾。集内各卷上書口鐫“詩持一集”,版心中按卷數鐫“卷之一(二、三、四)”,下書口鐫“枕江堂”三字。版式與《百名家詩選》基本相同。四集分別有自序、凡例、目錄。目錄後為書名、卷次、評選者、參閱者、詩人姓字籍里、詩作及評點。《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三十八冊收錄此書。
《詩持》一集《自序》落款時間為“康熙辛亥中秋前五日”,枕江堂本《百名家詩選》吳偉業序時間為“康熙辛亥夏日”。這也就意味着《詩持》前三集與《百名家詩選》的編選、刊刻可能是同步進行的。魏憲為什麽同時進行兩部型性質相似詩集的編選呢?
第一,《詩持》前三集的編選、刻印歷時較長。《詩持一集》是“總二十三年之風雅”,選詩斷限是“甲子至丙戌”,即天啟四年(1624)至順治三年(1646),“僅得兩卷”,“刻於潭陽”[(清)魏憲:《詩持一集·凡例》,譚陽即今福建潭陽漳州漳浦縣。],時間當在康熙五年(1666)前。因魏憲於康熙五年抵京師,“紙貴一時,板亦漫滅”,已着手補刻一集。《詩持二集》“始自都門,成於白下”,計劃收錄“丁亥至今日”,即順治四年(1645)至康熙七年(1668)詩[(清)魏憲《詩持二集·凡例》。];魏憲於康熙七年到南京,因此,補刻的《詩持一集》與新編《詩持二集》應刻印於康熙五年到七年(1666-1668)間。魏憲後來又調整了計劃,《詩持二集》“大約皆選甲子以後(天啟四年1624)詩”,“意在總六十年風雅,為一代全書”。康熙九年(1670)他“攜近代詩三百有餘家至雲間”,與“暘谷傅先生論定”,終“自夏徂冬,六閱月始編”《詩持》一至三集(最新增修版)。至康熙十年(1671),《詩持》已歷“三刻矣”[(清)魏憲《詩持三集·自序》。]。因此,魏憲這裡所說《詩持一集》實指《詩持》前三集(最新增修版),此序作於三集彙刻後。編訂於嘉慶二十一年(1816)的《江蘇詩徵》在卷四十六《贈魏惟度》詩下有註曰:“惟度,閩人……輯《詩持》初、二集、《皇清百名家詩鈔》行世” [王豫,字應和,又字柳村,江蘇江都人,約生於1762年,卒於1820前後,編有《江蘇詩徵》一百八十三卷。其生平見於《清史列傳》卷七三。《江蘇詩徵·贈魏惟度》卷四十六,詩下註:“王屋云:惟度,閩人,僑居白下。輯詩持初二集、皇清百名家詩鈔行世。”王豫編《江蘇詩徵》,清道光元年焦山海西庵詩徵閣刻本,全詩如下:“騷人卜築枕江流,洗耳投綸有唱酬。六代鶯花憑醉眼,二陵風雨入羈愁。早看王謝傾玄麈,未許蕭梁傍選樓。千古瀼西人不見,草堂今在古皇州。”],這可能意味着《詩持三集》尚未刊印時,《皇清百名家詩》已在市面上流行開。《清史稿·藝文志》著錄魏憲著作兩部,“《詩持》十卷,《廣集》八十九卷。[《清史稿·志一百二十三·藝文四·總集類》卷一百四十八,載:“詩持十卷,廣集八十九卷,魏憲編”。]”徐世昌也曾言“惟度嘗選國朝詩爲《詩持》,凡三集。又别采百家,號《詩持廣》。” [(清)徐世昌著,傅卜棠編校:《晚晴簃詩話·魏憲》卷三十三,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93頁。]《詩持廣集》的卷數與《百名家詩選》完全相同,且有“百家”之說。在聖益齋本的封面上,也有“詩持廣集”四字。這是否預示着《詩持廣集》與《百名家詩選》本就是一本書?魏憲從順治十一年(1654)開始編選《詩持》,“以得詩先後為次”,随选随刻,至康熙十年(1671)《詩持》“三刻”完成,歷時十七年。十七年間,魏憲“閱稿四百餘家,得詩三千餘首”,僅編出二十四卷書(詩持前三集),“有集已成而增益者,業難更定”,有“新編較勝於前”的,更加“不忍遽棄”,於是便出現“仍以再見三見為例”之事[(清)魏憲:《詩持三集?凡例》,清康熙枕江堂刻本。]。如此的編排與刻印方式决定了《詩持》的編撰過程本身就是一個不斷調整思路,不斷發現不足的過程,所以才會《詩持一集》起初只有兩卷,很快就有四卷的修訂、增訂版。在時間、材料都充足,前編詩集滿是遺憾的情况下,魏憲很可能順手將《詩持》容納不了或感情上割捨不去的內容一併收入《詩持廣集》中,以圖後續再編出一部容量較《詩持》更大的詩集。
第二、將《詩持》(前三集)與《百名家詩選》入選詩人對照後會發現,《百名家詩選》選錄詩人近一半出現在《詩持》前三集中。《百名家詩選》小引提及《詩持》與《百名家詩選》關係之處多達11次[分別為:卷二李霨、卷十申涵光、卷十二佟鳳彩、卷十九曹爾堪、卷三十一毛逵、卷三十三程可則、卷三十四周令樹、卷三十九顧大申、卷五十七計東、卷八十丘象升、卷八十五曹玉珂。],都涉及到這兩部選集之間的關係。如卷三十一毛逵小引說:
近代匪石君緝太虛、雪堂、巨源、茂先、于一、士業,博庵。諸君子擅東南之譽,余《詩持》之選,固已論次之矣。壬子寓衛,錦來毛先生憑太守程念伊寄示近集數種……余因論次是集……
選《詩持》時,魏憲未見毛逵詩。毛逵後來委託程啟朱將“近集數種”寄示,毛逵詩才得以入選是集。這是《詩持》與《百名家詩選》的第一種關係:從無到有。
陳寶鑰詩代表第二種情况:在兩部詩集中完全相同。《詩持》前三集共選30首(一集選7首、二集選15首、三集選8首),《百名家詩選》卷二十九選30首,所選詩作完全相同。
第三種情况是完全不同,以王崇簡、周體觀、釋大依等人選詩為代表的。《百名家詩選》所選詩歌無一首與《詩持》相同。無論是完全相同還是完全不同,第二、第三種情况在兩部詩集中並不普遍。
最常見的是第四種情况:由少到多。先看卷三十三程可則小引:
丁戊之際,余寓白門得先生佳什,登《詩持》二、三集中,業已借光紙貴。近復得八家詩于五鹿,多先生長安之作,拔其尤者,先付剞劂。
《詩持》(前三集)收錄了程可則的五首詩。後來魏憲得到八人詩集,其中有程可則作於長安的新詩,於是又將其中特別優秀的詩選入計60首,其中與《詩持》相同的只有兩首。
程可則詩是比較極端的由少到多的例子,更多的是《百名家詩選》比《詩持》略有增加。如吳偉業詩,《詩持》選30首(二集22首,三集8首),《百名家詩選》選33首,30首全同,增加了3首。再如傅為霖詩,《詩持》前三集選27首,《百名家詩選》共選33首,其中27首全同,增加5首。王熙、沈荃、戴明說、楊思聖、嚴曾榘等人的選詩都屬於這一類情况。這是《詩持》與《百名家詩選》中最常見的現象。
在計東小引、丘象升小引中,魏憲表示過《詩持》選詩過少的遺憾[“余過白門,訪恕老堂。堂中人善月旦,首推甫草才名,口詠數詩見示,已梓予《詩持》之選矣。近輪蹄息魏、楚中,王先生來視學,復傳甫草數詩至。雖較恕老堂口授者略廣,余終不能無恨少也。”(《百名家詩選》卷五十七計東小引);“曩余選《詩持》,僅登其數首,不無恨少。近始得其《嶺海集》,古體取材昭明,長句希蹤太白,近體以少陵為主,佐以王、孟,故音節、聲響、意象、丰神,無之不飛揚欲動,真可束天下于法之中,游天下于法之外,譬大塊噫氣,吹萬不同,寧僅為黍谷之暖已哉……”(《百名家詩選》卷八十丘象升小引)]。在《百名家詩選》卷三十九顧大申小引下有這樣一段話:
近策蹇入都,路出大名,奕聞太守新擁五馬賁予寓,坐談之頃,即以見山為詢,意以余《石倉》之選不得先生佳篇為憾事。遂遍搜行篋,《鶴巢全集》久為上官大夫竊去。因取余《詩持》暨徐松之《雲山酬倡》內所載,合梓以傳。
魏憲與顧耿臣相遇後論詩,顧耿臣(字奕聞,嘉善人)認為魏憲還沒有選到顧大申(字見山)的好詩,他手頭本有顧大申的別集,但被“竊去”,魏憲只好將《詩持》已選之詩加上徐松之唱和集中顧大申所作合併刊刻。
綜上所述,從編訂《詩持》第一集開始,魏憲就源源不斷地得到許多新的詩作,於是他在編訂《詩持》的同時,將從各種渠道新得到的新詩編入一部新的詩集,作為對《詩持》的擴充、增加。
而在聖益齋本的封面上,恰恰有醒目的“詩持廣集”字樣。顯然魏憲在重修《詩持》一集、編訂二、三集的過程中,將已經入選、未能入選《詩持》以及新獲得的詩歌一併編入了《詩持廣集》中,以擴大出一部容量較《詩持》大許多的詩集。如此,《詩持廣集》與《詩持》前三集刊刻時間也應當是大致同步的,即康熙七年至康熙十年(1668-1671)間。
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麽人們在談論魏憲時,很少談及《詩持廣集》,而魏憲本人又為何從不提及《百名家詩選》呢?
首先應當考慮的是經濟原因。魏憲本人並沒有足够的財力獨立編詩,他需要“射利”以維持生計。“利”之來源,可言說的,是外界的資助,魏憲說了很多,如《詩持》(一集)得佟國器資助,《詩持》(三集)是傅為霖“捐冰俸相資”,《詩持》(四集)獲佟鳳彩助刻。有沒有不可言說的(不好意思、不屑等)其他渠道?二集的刻印經費從哪裡來?為什麽我們沒有見到《詩持二集》的贊助者?是魏憲為《詩持廣集》重定“異名”,還是魏憲為“射利”將《詩持廣集》的書板貨與書商,而書商認為《詩持廣集》的名頭不够大,在刊刻時選了幾個更搶眼、更響亮的詞(百名家、國朝、皇清)為書名。鄭振鐸曾對此有過懷疑,“百字係後來挖改,疑非原來書名”。這也就能說清為什麽聖益齋本封面上有《詩持廣集》字樣,且人數最接近百(九十一家加嗣刻十家,除去魏憲本人,恰為百家)。故聖益齋本很可能是最接近《詩持廣集》原貌的本子。枕江堂本則與聖益齋本近似,而流傳最廣的聚錦堂本應是書坊補刻本,質量粗糙,缺失小引最多、文字錯誤也多、鐫刻字體不一。清人法式善曾言“余見憲輯自魏裔介訖憲凡九十一家。所列葉方藹十家目已芟去。殆後人重刻本耳。卷前恭載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御製昇平嘉宴詩”,即是聚錦堂本[(清)法式善撰、涂雨公點校:《陶廬雜錄》卷三,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59年,第78頁。]。
至於為什麽聖益齋本內封有“康熙乙丑年鐫”,而聚錦堂的補刻斷限為康熙二十一年?第一,目前可以確定的是《百名家詩選》一書最初名為《詩持廣集》,後不斷更名,《國朝百名家詩選》《皇清百名家詩》皆是。冠有魏憲刻書室名“聖益齋”之《國朝百名家詩選》出現應當在聚錦堂補刻《皇清百名家詩》之前。在謝正光《清初人選清初詩匯考》一書中有哈佛燕京圖書館庋藏《皇清百名家詩》的書影,上有“康熙七年聚錦堂刻本”字樣,這很可能說明《百名家詩選》聚錦堂本補刻時間大致在康熙七年(1668),而聖益齋本的出現應在聚錦堂本出現之前不遠。
《百名家詩選》與《補石倉詩選》的關係也是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
在枕江堂本《百名家詩選》版心出現了七處“補石倉詩選”字樣[具體位置為:吳序第一頁、卷四龔鼎孳第二十九頁、卷十二佟鳳彩第八頁、卷二十五范承謨第一頁、卷三十七程雲小引第一頁、卷七十一陸輿第十七頁。]。研究者們據此推斷《百名家詩選》即《補石倉詩選》,並將枕江堂本的刊刻時間定為吳偉業作序的康熙十年(1671),認為枕江堂本《百名家詩選》可能是最早的刻本。這個結論還需要進一步辨析。
《補石倉詩選》所補乃明代曹學佺《歷代石倉詩選》(亦名《十二代詩選》)。曹學佺(1574-1646),字能始,號石倉,與魏憲同為閩人。其《歷代石倉詩選》上起古初,下止於明,共506卷。魏憲“悉照石倉舊本,廣及昭代,上溯啟禎,補宗伯曹能始先生未竟之業”,以“接十二代宗工”,成一時“盛事也”。
《補石倉詩選》現存版本有康熙十年(1671)魏氏枕江堂刻本、嘉慶間孫氏度森堂印本。前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六十七卷、國家圖書館藏十四卷(國圖十四卷均見於社科院文研所六十七卷內)。此本未見內封,版式為左右雙邊,半頁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單黑魚尾。書前有康熙十年(1671)吳偉業序,凡例(八則),目錄三帙。目錄首行題“補石倉詩選”,次行題“第幾帙姓氏”、“以得詩之先後爲次”,後為詩家姓字、籍貫,每帙六十八家,共204家。目錄後依次為小引、書名及卷次(補石倉詩選、卷之、墨釘)、選家、四位編選者、詩人、選詩。上書口鐫“補石倉詩選”;版心中鐫詩家姓氏及卷次(如申鳧盟、卷之,但卷之下基本無卷數而是墨釘);下書口鐫頁數及“枕江堂”。
後者南京圖書館藏三十二卷。是書內封分左中右三欄:右刻“福清魏憲惟度輯選 中牟孫志道性山重訂”,中刻“重訂補石倉詩選”,左下刻“度森堂藏板”。無吳序、凡例及目錄,只有孫氏自序。在孫氏序言中,魏憲於“康熙中,膺大中丞聘,因至中州”,並且“與一時賢士大夫游”,最終“遂成此編,付之梓人,惜僅三十二家”[(清)魏憲輯、孫志道重訂:《重訂補石倉詩選》,清康熙間枕江堂刻嘉慶間度森堂本。]。根據此本各家小引紀年來看,此三十二卷編選活動時間大致在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間。由於此本中卷四黃淳耀見於社科院文研所藏本目錄第一帙第四位,可見此三十二卷也是《補石倉詩選》中的一部分。然而此本選人無一與《百名家詩選》同。
將《百名家詩選》與《補石倉詩選》進行對照,社科院文研所藏本與枕江堂本《百名家詩選》除版式基本相同,卷前吳序、凡例完全一致外,現存六十七卷文獻有六十三卷與《百名家詩選》高度重合。魏憲為何要再次重複勞動,“克隆”與《百名家詩選》(《詩持廣集》)幾乎一模一樣的總集?這是否說明《百名家詩選》就是《補石倉詩選》?
康熙十年(1671)魏憲在《詩持》三集最終彙刻時言“余是選既峻,即有補石倉之舉……有志千秋者,乞以全稿郵寄白下,共商剞劂。”說明此時《補石倉詩選》還未開始編選,魏憲利用凡例正為其新書徵稿[李鵬:《中國古代圖書出版行銷研究》,北京:學習出版社,2013年,第236頁。],及至康熙十一年(1672)魏憲仍說“壬子春暮,謀續《石倉》之選”[(清)魏憲:《百名家詩選?孔胤樾》卷二十七,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聖益齋本。],但枕江堂本《百名家詩選》與《補石倉詩選》皆有吳偉業所作序言,而且魏憲在吳偉業卷前小引中說“迨辛亥維夏,相遇虎丘,謀《補石倉》之選,先生贈序,過為揄揚”,看來吳偉業序言的確是為《補石倉詩選》所作,但吳偉業於康熙十一年初即去世,他為何要為一部尚未具雛形的詩選作序?由於在《詩持》與《百名家詩選》(《詩持廣集》)中,魏憲的編選活動呈現出既重複又增補,且不斷擴大選人選詩規模之特徵,因此首先要考慮的是他直接將已成型之《百名家詩選》(《詩持廣集》)作為了《補石倉詩選》的藍本,並決定以此為基礎繼續編選另一部新的“擴大集”,使其成為“接十二代宗工”之“盛事”。因此吳偉業看到的很可能是《百名家詩選》(《詩持廣集》)。再者四庫提要曾稱“憲以曹學佺有《十二代詩選》,止於天啟,因選是集(《百名家詩選》八十九卷)以補之”,但又于王澤弘《鶴嶺山人詩集》提要中稱“前三卷皆題已刻詩若干首,蓋皆澤宏舊作,嘗為魏憲錄入石倉詩選者”[(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卷一百八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646頁。
],館臣為什麽認為《百名家詩選》是補曹學佺《石倉詩選》,為何又認為王澤弘舊作收入了《補石倉詩選》呢?《百名家詩選》中選王澤弘一百三十三首詩,然而《補石倉詩選》中王澤弘僅列於目錄,並未見其詩。若《百名家詩選》是由《補石倉詩選》修改而成,為何王澤弘詩不見於《補石倉詩選》?說明館臣所見亦是《百名家詩選》,而非《補石倉詩選》。值得注意的是,王澤弘《鶴嶺山人詩集》附注有言“冠以少作,刻入《補石倉詩選》者一百二十三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五十三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第344-345頁。],此語與提要相合,可知館臣所見並非《補石倉詩選》。且《鶴嶺山人詩集》言此一百二十三首詩皆出於《補石倉詩選》,既如此,由《補石倉詩選》修改而成的《百名家詩選》怎麽會比原本多出十首詩作[《百名家詩選》多出十首詩為:《鐵佛寺訪謝有客》《江上漫興》《落花詩其一》《程穆倩山人招飲》《贈李二夢珠》《望九華》《自題小像》《雨後游西山作其二》《岸動二首》。]?由於《鶴嶺山人詩集》是王澤弘第六子王材振於康熙末年在金陵整理刊刻而成[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集部》卷五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166頁。],故其所言《補石倉詩選》很可能是以《百名家詩選》王澤弘卷為基礎刻出的《補石倉詩選》,所以在篇目及文字上有一些出入和刪改。
《補石倉詩選》中與王澤弘情况類似者共有十七人[名列《補石倉詩選》目錄,卻未見其詩者:曹溶、成性、傅為霖、陸求可、毛升芳、計東、程啟朱、楊輝斗、黃伸、張鴻儀、劉友光、李念慈、朱驊、楊州彥、劉維禎、王澤弘、馮雲驤(僅見於聖益齋本)。],如此看來,魏憲至少是準備將《百名家詩選》中的八十二位詩人作為《補石倉詩選》的基礎,但實際上魏憲僅將六十五人的文獻移入《補石倉詩選》中,並做了極其細微的改動,如增張永祺詩五首,張祖詠、戴其員詩各一首,增王熙、柯聳、趙威三人小引,大多數詩人的文獻都維持了《百名家詩選》中的原樣。究其原因,概因魏憲已將全部精力投入到擴大《補石倉詩選》的工作中了。結合《百名家詩選》卷五十七計東《天雄旅次以詩代柬寄魏惟度》、卷七十四孫郁《閩中魏惟度同江右吳星若過訪以補石倉詩選見惠即贈》兩首詩中記載交游情况及其他卷小引紀年來看,魏憲從康熙壬子(1672)至癸丑(1673)這一時間段起開始頻繁活動于濮陽、天雄等地,而《補石倉詩選》的編選大致是始於這一區間,而且此時魏憲很可能已將《百名家詩選》部分文獻及新選文獻合併後改題為《補石倉詩選》,故《百名家詩選》中頻現魏憲“補石倉”事業之名[出現十四次,與詩持十一次相當。分別見於卷八吳偉業、卷二十施閏章、卷二十六魏裔魯、卷二十七孔胤樾、卷二十九陳寶鑰、卷三十五李衷燦、卷三十九顧大申、卷四十八紀映鐘、卷五十三申涵盼、卷五十六梅清、卷五十七計東、卷七十二沈道映、卷七十四孫郁、卷八十九魏憲。]。而且從孫郁詩題看,《補石倉詩選》似乎已經刻成,但這若是《補石倉詩選》全集,僅從體量上就是一筆十分厚重的饋贈。第一,孫郁與魏憲沒有特別交情,以《補石倉詩選》全集為贄,太重;第二,孫郁也並非當時的文壇泰斗或詩界領袖,不存在魏憲以此集求引的可能;第三,孫郁此詩寫得很是輕鬆,絲毫看不出受大饋贈的感激。因此,魏憲贈與孫郁的,應該是旋得旋刻的《補石倉詩選》的某一卷或某幾卷。
據上述信息可知,魏憲從康熙十一年起(1672)主要活動區域在河南、河北兩地。在這期間,他的交際面不斷擴大,得詩越來越多,《補石倉詩選》的規模也越來越大,而在《百名家詩選》各家小引中,康熙十二年(1673)以後的紀年就沒有出現過了,而是集中出現于南圖藏度森堂本《補石倉詩選》詩人小引中,區間大致在康熙十三年(1674)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魏憲入梁時間大致為康熙十四年及其後。《詩持四集?自序》稱“余乙卯游梁,大中丞佟公假館艮嶽之側”;南圖度森堂《重訂補石倉詩選》楊士元小引稱“丙辰入大梁”、毛際可小引稱“丙丁間游大梁”、宋法祖小引稱“壬戌游大梁”。]。而據此本來看,康熙二十二年冬魏憲仍然還在編選《補石倉詩選》,且最終卒於開封[(清)沈傳義、黃舒昺:《新修祥符縣誌?人物》卷十七,清光緒二十四年。“過梁買宅居焉。卒,厝柩南薰門外,游者多瀝酒吊。”]。因此南圖藏本所選三十二人自然不會與《百名家詩選》相同。
《補石倉詩選》是以《百名家詩選》(《詩持廣集》)為藍本編選而成的其他證據有,前文述《補石倉詩選》中未見選詩的詩人中,還包括僅見於聖益齋本《百名家詩選》目錄的徐乾學。這說明魏憲在編選《百名家詩選》時因未能得徐氏文獻而將其列於嗣刻,並計劃於《補石倉詩選》中再選,然而也未能成功。《補石倉詩選》若刻有徐乾學詩,《百名家詩選》又何必將其列於“嗣刻”之中?再如《百名家詩選》還有十一人逸出《補石倉詩選》目錄[《百名家詩選》有,而《補石倉詩選》目錄無的詩人為:劉六德、張鴻佑、楊思本、丘象升、葉雷生、宗元鼎、毛師柱、曹玉珂、釋大依、馮如京、魏憲。],其中有僅存於聖益齋本《百名家詩選》中的馮如京。聖益齋本著錄時間為康熙二十四年(1685),如果《百名家詩選》從《補石倉詩選》修改而來,為何《補石倉詩選》中並無馮如京?這也再次證明康熙二十四年(1685)聖益齋本《國朝百名家詩選》可能是在原版封面上添加時間後刷印而成,並非原刻。而枕江堂本《百名家詩選》吳序、凡例及個別卷版心處之所以出現未挖净“補石倉詩選”字樣,可能是書商作偽所致。《百名家詩選》成書在《補石倉詩選》之前,且盛名已久,二者內容高度近似,書商不能區分二者之關聯,為射利,將《百名家詩選》與陸續出現的《補石倉詩選》個別詩卷拼接而成,加之吳序、凡例,刪除封面,以充全貌。這也再次印證了《百名家詩選》三本中為何只有枕江堂本卷前有凡例,且與《補石倉詩選》一模一樣。况且此凡例中第五、七則分別與《詩持二集》第四則、《詩持三集》第三則相同,這很可能說明魏憲因《詩持》前三集體例完備,故並未作《百名家詩選》凡例,而是待《百名家詩選》基礎上擴大《補石倉詩選》後,再作凡例。
如果對《百名家詩選》版本出現時間進行重新界定,一種推測是冠有魏憲刻書室名的聖益齋本最接近《詩持廣集》(《百名家詩選》)的原貌,其質量最好,出現時間也最早,魏憲將書版轉售他人後,保留了該集初名《詩持廣集》的同時,為擴大影響又冠名《國朝百名家詩選》。後聚錦堂得到此板,進行補刻,並大肆出版發行,使《皇清百名家詩》大行於世,廣泛流傳。
然而迄今為止,我們也看不到全本的《補石倉詩選》留存,根據魏憲最後的活動軌跡來看,此書最終未能峻刻,於是《清史稿·藝文志》等材料言及魏憲成就時就只知《詩持廣集》或《百名家詩選》而不知《補石倉詩選》了。
綜合前文所述,我們可以清晰的總結出魏憲整個編選計劃制定、執行、調整、再執行的一個較為符合邏輯的軌跡,也能更為合理地解釋魏憲如此“不憚煩”[鄧之誠先生為其所藏康熙二十一年本《皇清百名家詩》所作手跋。],一而再、再而三地編選同類性質,且詩人及作品大量重疊的詩集到底為何?除鄧之誠先生所言“蓋以此書射利”的可能外,魏憲在持續三十年的時間中只專於一事,三部總集所反映的清初詩壇面貌也越來越清晰、全面。
第一,編選《詩持》雖牛刀小試,但目標明確,選詩時間上先後進行了三次調整,最終確定為“總六十年風雅”(1624-1684),《詩持》前三集編訂刻印期間積累了一定經驗,但不系統、不完善,於是要“廣”,同步將已入選、未入選、新得“國朝”詩人大部分詩歌編入《詩持廣集》。
第二,《詩持》峻刻,《廣集》已備,魏憲又圖以“石倉舊版”接“十二代宗工”之“盛事”。然而,《百名家詩選》中只選部分“國朝”詩人,尚有勝朝及《百名家詩選》未選國朝詩人待選,於是計劃一併置入《補石倉詩選》中,以成巨著。
最後,可以說《百名家詩選》的本來面貌實為一部承前啟後、承上啟下之作,它既是《詩持》之“廣集”,又是《補石倉詩選》之“基礎”。且此作在流傳過程中,傳播、影響遠超《詩持》與《補石倉詩選》。正因如此,它為魏憲帶來了名利上的巨大收穫,也使他與此書始終陷於巨大爭議之中。
五
下面我們再談談魏憲的詩學思想及其在選詩上的反映。
與中國詩論喜探源溯流一樣,魏憲選詩,每以某人詩似前代而加以讚譽,如“寢食三唐,沐浴漢魏”“不啻唐虞之賡歌、成康之陳頌、有皋蘷、周召風焉”類;他評吳偉業的詩是“陶冶于漢、魏而潤澤于盛、初,根荄於德性而煥發於典籍”;評劉元徵是“敦厚也似陳拾遺,韶秀也似王氾水,沉鬱頓挫也幾幾乎比肩浣花野老矣”;說丘象升詩“古體取材昭明,長句希蹤太白,近體以少陵為主,佐以王孟,故音節、聲響、意象、豐神無之不飛揚欲動”;申涵光詩“詞典旨溫,情深景肖,不减漢唐風裁”。但他同時也肯定承襲中的“變”,如王崇簡詩“皆澤于古而出以娟秀之容,和平之氣,不斤斤摹擬三唐,而三唐不能外焉”;說王追騏詩“新穎雋逸,不屑屑步趨古人”;龔鼎孳的詩更是“其調高而逸,其詞婉而麗,其托旨也遙深,取材也精確,浸淫於六朝而不沾六朝之氣,沉酣于三唐而不貌三唐之容,即起應劉、嵇、阮、韋、孟、杜、李諸君子,相與角技一堂”。魏憲認為“變”應適度,“一變而新創,再變而雕鏤,三變而險僻,則牛鬼蛇神輩得操入室內之戈以與我爭,而詩道傷矣”。
魏憲推重先秦、漢魏詩歌的清剛勁健,但也不排斥鍛煉技巧、凝練詩歌韻致的六朝及晚唐。他在評宗元鼎詩時說:
今人言詩,古體動稱漢魏、黃初以降,若不屑者。定九獨不廢六朝。今人言詩,近體動稱初盛,大曆以還若不屑者。定九獨不廢中晚。蓋今人為詩,多以郛郭,而定九以神韻。今人為詩,多以剽襲,而定九以研精也。至主客評其《芙蓉集》為青春鸚鵡、楊柳樓臺,極得陰鏗、何遜之體,意得處往往欲逼二謝絕句,尤得樊川、玉溪諸家之妙。
“青春鸚鵡”“楊柳樓台”,以古代批評最常用的意象批評法予宗元鼎詩歌風格以形象把握,又採用類比批評法,以殷、何、大小謝及小李、杜來描述宗元鼎詩歌的風格。魏憲認為只要能得“妙”處,入詩境,皆是好詩,反對“詩有正始,以《三百篇》為宗。吾楚未入風,安能媲響”之說,認為“楚無風而有騷,今以為經,繼經而有詩,今以為史,幾與雅、頌並列,且詩之盛也,莫楚若矣”。從整體來說,魏憲選詩還是多以現實主義傳統為主,風格多沉厚、頓挫,輔以楚辭、六朝、晚唐中的浪漫主義表達與風格的清麗、婉約。
魏憲主張詩歌創作要打破成規,遠離近習。他評宋翔“不屑屑於近人之習,且不屑屑于古人之規,縱筆所如,意先之必以創,詞隨之必以新,創也、新也。”要求詩人之詩要“率真”,因為“人不真,惡能詩?有意為之,則偽矣。詩不真,惡足傳?有意為之,則僻矣。惟無意於為真而真詩見,真人並見者,斯其人非常人,其詩亦非常詩。”而且詩人只有“率真”才能擁有超然灑脫,不為世俗所累之“性情”,“性情”的培養還需得“江山之助”,如“少陵入蜀後詩益工,謂其獲山水之助。則生長於蜀者,宜盡能詩矣。”詩人得“江山之助”後,不僅可以作詩,還可以“臨帖作字”,盡顯“丰采骨力”或“以詩文作丹青,寄其性靈。”只有如此,人之“真情”,詩之“真情”就能得以自然流露、準確表達。魏憲認為“真情”的表達和流露同時也應該是詩歌的作用,即“詩為心聲”,不平則鳴,相輔相成。
六
魏憲選詩,重詩人品節,“是選以人為重。人以品節為主,或理學紹古,或經濟匡世,或正色廟廊,或敦行草野,皆兩間正氣、一代偉人。衡量之間,寧嚴不濫。事緣實著,人以類從。”[《百名家詩選·凡例》。]《百名家詩選》中入選詩人或為賢臣能吏,在安邦治國、紓解百姓苦難方面兢兢業業;或行吟草野,品行高卓,足以規范周邊,輝耀後世者。魏憲不同意嚴羽的“別才”“別趣”說,認為“詩以適於用者為大”[《百名家詩選·黃伸》卷六十三。]並將“適用”分為“經世”“居身”“接物”三類。[《百名家詩選·竇遴奇》卷四十四,“不知舍理與學而言詩,雖有別趣、別才,終不可以入道。古聖人以詩為經,蓋經者,常也,常行之謂道。道之所在,可以經世,可以居身,可以接物。比興之體,觀感繫焉,匪細故也”。]由此出發,魏憲選了很多的“載道”“適用”之詩,從中可見到深沉的歷史反思、尖銳的現實批判,以及波譎雲詭的清初的歷史,如他本人模仿杜甫《哀江頭》而作的《哀城東》,即在強烈的今昔對比中將家鄉福清的現實予以展現:“壞垣破壁亦無存,萬瓦鱗鱗何須計。百族流離自昔無,男為奴僕女為隸”。李念慈的《剛成屯》、楊思本的《閱旅庵難民圖志哀》、孟瑤《康熙元年六月出郭觀郡伯程念伊先生决衛河水灌城池歸而感事有作》、陸求可的《水災三載困苦已甚秦陲河堤未築辛亥春水猶漲民之饑也殆云極矣皇上心焉念之捐漕米十萬石遣戶部侍郎田公賑濟》均屬此類。這些詩,寫出了百姓的苦難,也表達了身處亂世士人的憤激、憂慮與悲憫,如“從來兵寇也如林,十六年來太不禁”[《百名家詩選·楊思本》卷七十七,《閱旅庵難民圖志哀》。],“明明天子國,鞠為戎馬場”[《百名家詩選·楊思聖》卷十三,《追憤五百字》。]。毛師柱《田父詞》“人生筋力百可用,慎莫歸種江南田”宛然可見杜甫的“歎息腸內熱”。
《百名家詩選》中有很多今天的文學史不很重視的奉贈、唱和詩。這類題材並非全無價值。結合其他抒懷之作,我們讀到了《百名家詩選》社會政治批判外的另一面:士人的風雅。他們憑吊古跡、宴飲清歡,深夜青燈攤書的快樂,友人突然造訪的驚喜,親朋的辭世,生活的艱辛……幾乎所有生活的日常與波瀾都在其中有所反映。“漢法三章懸日月,宦途九折比江河”“興來風雨千張掃,望去蒼茫一管枯”。諸如此類的詩歌能令我們無限接近清初士人的語境,體味到他們年復一年“日常消耗”中的牢騷與抱怨,他們作為讀書人精神的堅守,以及他們對社會政治、自身命運、前途的思索。此外,我們還能從中發現清初士人所開拓的新的審美領域,也能看到清初詩壇的潮流與趨勢。如魏憲創 《八居詩》[分別為:樓居、廛居、山居、岩居、水居、村居、船居、茅居。]後,出現了一個小小的《八居詩》創作高潮,魏裔魯、程啓朱、楊輝斗、戴其員等紛紛進行同題創作。他們以各自不同的視角展開了清人對於居處的想像,也進行着詩藝的競技。再如楊輝斗對各種精細聲音的描繪(《剪刀聲》《桔槔聲》《砧聲》《鐵馬聲》《欸乃聲》)。范周創作了幾種系列詩,如“花”系列:霜花、雪花、浪花、酒花、鏡花、雨花;韻部系列:《雁字詩》(一東、二冬、四支、六魚、七虞、十一真、十三元、十一尤、十二侵)、《落花詩》(一東、二冬、三江、四支、五微、六魚、七虞、八齊、十灰、十一真)等,也很有意思。這些均反映了清初詩人在詩藝方面的努力及成效。
《百名家詩選》還能令我們瞭解當時人的交游,看下面這段話:
余以衰老多愛憐後學。見微慧者,撫之、策之、激之、濯之,不啻飢渴者之於食飲,寒暑者之於衣巾也。旁有忌者,議之、方之、怪之、毀之,余初不顧也。閱數歲,或盡棄,其生平竟背謬余所期。向之議且毀者,復快且謔矣,而余復不顧也。[《百名家詩選·釋大依》卷八十七,《示牧愚上座引》。]
儘管這是出自僧人之口,但其中所顯示的前輩對後學無任何希求的純淨的欣賞與提攜令人感喟,也從一個側面見出清初大致的社會風氣。其他再如應舉詩、落第詩、思鄉、返鄉詩等等,都在為今天的讀者展開清初廣闊的社會空間的同時,也將我們拉回到他們當年生活“現場”,令我們看到劇烈的社會動蕩後,清初士人所遭遇的艱難以及他們的堅守與堅持。
作為一個來自福建的選家,魏憲選詩顯示了鮮明的地域視野。小引中常有對地域與詩歌流派及文學群體、文化活動的介紹,如江左三大家、燕台七子、天雄三才子之類。一些即便在當時可能都微不足道的小詩派、小活動,魏憲也將它們記錄下來,如編選了《五鹿詩選》的五鹿社等。魏憲还有很多反映獨有地域文學、文化歷史的詩歌。“山川若無高士跡,臺觀芳草亦空留”[《百名家詩選·李贊元》卷四十七,《任城太白樓》。],謫仙樓、荆軻故居、“保定道中拜漢昭烈關壯繆張桓侯廟”“柴市”(北京府學西,文天祥死節處)。地方的歷史文化傳統及清初人對這些傳統的理解和認識在這些詩歌中得到了相對集中的呈現。
“君寓胥江湄,嘯歌著詩史。”[《百名家詩選·計東》卷五十七,《天雄旅次以詩代柬寄魏惟度》。]魏憲要接續曹學佺的《明詩選》,編選一部反映清初詩壇狀况的一代“詩史”,必然要照顧到編選對象的全面性、豐富性、多樣性。內容上,社會批判、民生疾苦,文士風雅,詠懷詠史、奉贈唱和,覆蓋面很廣,也有一定的深度。形式上呢,也豐富多樣。古體、近體、樂府,應有盡有。長篇、短章,各有千秋。儘管較之唐宋詩,清詩在整體藝術水準上有一些差距,但《百名家詩選》中,依然選到了不少在描摹物態,勾畫性靈、記錄歷史的神妙之作,也有很多在藝術上臻於完美的篇章。如下面這首:
新婦思母家,頻歸又畏禮。咨且姑嫜前,微言衣當洗。[《百名家詩選·曹玉珂》卷八十五,《新妇》。]
因此,這個意義上,《百名家詩選》凡例中所宣稱的“是集所載,不問存沒,一以佳篇為主”(《凡例》)的主觀目標基本達到了。
七
清人是如何評價這部詩集的呢?
屬嘉慶間侯官人鄭傑(約1750-1800)如是說:
惟度嘗選本朝《百家詩》,入選者多顯官,列己於末,而秀水朱竹垞(彝尊)檢討不與焉。檢討有詩云:“近來論詩多序爵,不及歸田七品官。直待書坊有陳起,江湖諸集庶齊刊”蓋指此也。又嘗選《詩持》三集,凡平日與己唱和者,美惡悉登,頗為蕪爛。
魏憲不以詩而以“位”選詩,以私人交情選詩,導致編出的詩集“蕪爛”。趨炎附勢、自我標榜,沒有公心,鄭傑對同鄉魏憲似乎一點兒也不講情面。鄭傑此說影響極大,詩話著作[朱則杰文章梳理出了一個系列:鄭傑《註韓居詩話》——徐祚永《閩游詩話》——楊鐘羲《雪橋詩話》——陳融《颙園詩話》——錢仲聯《夢苕庵詩話》——鄧之誠《皇清百名家詩跋》。見朱則杰、李迎芳《清代詩歌中的若干本事问题》,浙江社會科學,2004年第2期。此外還有郭柏蒼《竹間十日話》、梁章钜《三管詩话》。]全部跟着講,目錄學著作也受其影響。如乾隆年間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百名家詩選》八十九卷,福建巡撫采進本……今觀所選諸人,大抵聲氣標榜之習,至葉方藹以下十人未得其詩,而先列其目,益見其不為論詩作矣。[(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771頁。]
“未得其詩,而先列其目”是聖益齋本的情况,可以不論。“不為論詩作”——從根本上否定了魏憲的選詩水準。此後,“標榜聲氣”成為黏在《百名家詩選》上的標籤。但它也說此書“可寶貴者,清初詩人如丘象升《嶺海集》、吳學炯《秋雨堂詩集》等今皆未見,藉此選可略窺原集之一斑。”[實則遠不止此二集,如孔胤樾無別集,詩歌全賴此書存。]但作為一本權威的目錄學著作,《總目提要》點明了《百名家詩選》在保存文獻方面的價值。
相較而言,鄭振鐸對《百名家詩選》的評價比較中肯:
此類書在三十年前為學人爭取之目標,今則知音絕稀。實則論述清初詩者,此書仍是第一手材料之一也。”“每家有一小序,足資知人論世之助。”“憲自附其詩於後,不脫明人積習。所選未必皆可觀。然其中詩集不傳者居多。賴此,得窺豹一斑。[鄭振鐸著:《西諦書話》,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第253頁。]
作為文獻學家、藏書家的鄭振鐸對《百名家詩選》的來源及流傳十分熟悉,認為此書保存了清初詩的第一手資料,提示小引提供了諸多考訂作家籍里、仕宦、生平、交游、作者所處時代等資料。“未必皆可觀”,言下之意是選出的並不都是好詩。[嚴格地說,配得上“皆可觀”的詩選是微乎其微的,考查角度不同,各種缺憾、錯誤都難以避免。]可以說,鄭振鐸是充分肯定此書的。
1999年出版的《中國詩學大辭典》承《四庫全書總目》思路,只是“大抵”沒了“此書之編意在標榜聲氣。”[本詞條為王学泰撰,見傅璇琮等主编:《中国詩学大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77頁。]
《總目提要》寫就的兩百餘年後,《續修四庫提要》出版,收了《百名家詩選》,同樣也有一提要。它將“顯宦(官)”與“標榜聲氣”勾連,落實為“打秋風”:
魏憲,字惟度,……所選詩人,除二僧外,多為顯宦,似藉選詩之名,行打秋風之實。魏憲及同預選政之吳學炯亦得列入,選己詩且多達三十四首[本提要作者誤將“編選姓氏”中該詩集每位詩人選詩所占頁數為選詩數量。],他人多不及此數。此舉與其輯《詩持》時多錄他人贈己之作同出一轍,難逃自我標榜之譏。……多平平之作,實難當“名家”之稱。而未選朱彝尊詩,尤為遺珠。[傅璇琮主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百名家詩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36頁。]
魏憲的人品及所編詩集質量被完全否定了。
《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藏稀見叢書彙刊》收錄了聚錦堂本《皇清百名家詩》,曰:
魏憲選詩,多為達官顯宦。而清初最重要的一些詩人,如顧炎武、屈大均等遺民,朱彝尊、毛奇齡官位不顯,皆未能入選。即使入選者,如吳偉業、王士禎的某些名篇,或涉時忌,或揭露民間疾苦,亦在擯除之列。但此書作為清前期詩歌的重要選本,還是選了不少好詩,自有參考價值。[黃秀文,吳平主編《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藏稀見叢書彙刊·前言》,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6年,第6頁。]
指出遺漏的其他清初重要詩人,沒問題。但認為擯除了涉“時忌”的及揭露民間疾苦的“名篇”,就站不住了。因為“名篇”是一複雜而主觀的判斷,對清詩名篇的共識還在繼續討論,逐漸形成共識的過程中。同時,本文前部分所舉已經證明,此書中並不乏觸“時忌”“揭露民間疾苦”的詩。與鄭振鐸一樣,也承認它“選到了不少好詩”,有“參考價值”。
七
現代學術背景下,我們當充分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但也不必全受其拘限。回歸文本,回歸語境,持“瞭解之同情”的“瞭解”,與古人“同情”,不求全責備,不回避問題,盡量給此書一個真實、客觀、公正的評價。
第一,詩選本身。本文前面已有陳述,摒除“涉時忌”及“揭露民間疾苦”詩作應屬沒有認真閱讀具體作品的誅心之論;確實不能說是清初詩壇的全貌,遺漏了一些重要詩人,但還是選到了不少好詩。
第二,選家本人。我們注意魏憲的身份:底層知識分子,無權無勢,需要生存,自然就期待着有熱心同道的資助,利用可資利用的人際資源。以隱士的道德標準要求選家魏憲,是不合適的。憑魏憲交往對象中有“顯官”就斷定他“聲氣標榜”“打秋風”自然更欠妥。何况,他交往的這些所謂的“顯宦”,全部是經過了科舉選拔,有很好的文學功底與趣味的士人,一起談談詩,寫寫詩,偶爾給生活無着的魏憲以經濟的幫助,一如當年嚴武資助杜甫,怎么能轻言其“打秋風”?而且,魏憲以“枕江堂”之名刊刻書籍出售,應該也有勞動所得,不會全靠給人編詩“打秋風”為活計吧!
自然,還需要深入到“多為顯宦”的問題,用數字說話。入選八十九位詩人,以一生經歷最高官位計算,五品及以上五十二人[入選詩人的品階根據《清史稿》、地方通志等资料进行統計,数据如下:一品十二人,二品八人,三品四人,四品十三人,五品十五人,六品二人,七品六人,八品一人,無品階、未入仕二十九人。],過半數。考慮幾個因素:很多不是直接交往;有一些入選者在魏憲選詩時已經辭世;剩餘魏憲與之有交集的,顯然不會統一處他官職的最高位。綜合考慮這些因素,即便“多為顯宦”勉強能成立,但“聲氣標榜”尤其是“打秋風”之說過於刻薄。
第三,選詩語境。先看下面這段文字:
遴選一代之詩,工程是很浩大的,對選家的識見、交游和財力的要求都很高,所以多數選家都是以自己交游所及的范圍,或為懷念故舊,或為標榜聲氣,編選同人的作品。[傅璇琮,蔣寅主编:《中國古代文學通論》清代卷,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12頁。]
清人選當代詩,就“交游所及范圍”選是普遍作法。鄧漢儀自稱他的《詩觀》“選數多寡,實非有意,皆因其卷之繁簡,地點之遠近然”,有遺漏、不典型,也難免多親友故舊。應該說,清人選清詩,大致如此。但人們對《詩觀》的評價較高,沈德潛稱“足備後人採擇”,徐世昌讚“其中遺集罕傳者,頗賴以得梗概”[分別見於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徐世昌《晚晴簃詩匯》。]。為什麽《百名家詩選》遭遇的卻是百年一貫的苛評呢?“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誚。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劉勰《文心雕龍·程器》。]。“文士以职卑多誚”,一介布衣,無寸官半職,活該“多誚”?
我們還需要注意魏憲本人的話:
柏鄉魏相國之《觀始》《溯洄》二集,顧茂倫之《驪珠》《英華》《詩鈔》,田髴淵之《高言集》,陳伯璣之《詩慰》,鄧孝威之《詩觀》,徐松之之《雲山酬唱》,多不勝述,俱見博採苦心,業已行世,是選不敢雷同以滋物議。[魏憲《百名家詩選·凡例》。]
魏憲不願意重複別人的勞動,不沿襲其他選家。它遺漏了幾位在我們今天看來十分重要的詩人。但有情可原,一是魏憲所生活的年代,選家只能選自己“够得着”的人和詩;二是因為他想有所創新,所編選詩集有獨特性。
當我們將《百名家詩選》的選詩與其他清人選清詩進行比較後,我們甚至可以說《百名家詩選》是一部較好的“論詩之作”。沈德潛的《國朝詩別裁集》刻印晚於《百名家詩選》九十年,好評如潮。兩部詩集都選了宗元鼎,沈德潛稱他“最重風調,而性情因之以出”“集中七言絕句,尤近中晚唐人”,選詩六首,七言絕句三首。《百名家詩選》選有宗元鼎三十四首詩,称他“避地東原,藏書百卷,鴻妻驥子,衡門蕭然”,詩歌風格接近六朝與中晚唐。在對宗元鼎詩歌風格的判斷及最擅詩體這兩個關鍵問題上,二人完全一致。二人所选七言絕句均最多,沈德潜是占比百分之五十,魏憲是十一首,三分之一;再如《百名家詩選》卷五十選黃茝若詩十七首[具體為:《暮春過李弘甫郊居》《早春詠雪和孔心一觀察韻郜凌玉學憲修郡誌成旋里送別》《登岱二首》《登東昌光嶽樓》《探梅》《夜雪》《百泉》《送別曹顧庵歸里》《七夕立秋》《社集喜曹顧庵太史至分韻》《雨中蓮開遲竇德邁不至却寄》《游成八公野圃同劉印心》《雪霽》。],道光己亥年(1839)刊印的《國朝畿輔詩傳》卷十六選黃茝若詩四首[分別為《登東昌光嶽樓》《送別曹顧庵歸里》《送趙秋水歸里》《探梅》,有兩首贈人歸里詩。]。四首詩魏憲選了三首,獨無《送趙秋水歸里》。一方面,可說兩書的選詩傾向大致相同,也能见出魏憲選詩,可能有更審慎、更細致的去取考慮。
《百名家詩選》的文獻價值还得益于其刊刻時间。彼时文祸未開,忌憚相對較少,再加上刊刻之後不怎么被重視,流傳不廣,一些詩歌的本來面貌得以保存下來。如施閏章的《先祖母生日述感》中的“商飆忽已至,朱明猶未畢”兩句,“朱明”表示夏天。此句到《愚山先生詩集》變為“炎序”,顯然是不想讓人聯想、引申生出歧義。再如吳偉業《鴛湖曲》“畫閣猶存老兵坐”,《梅村集》作“畫閣偷窺老兵怒”“人生快樂終安極,年去年來增嘆息”,《梅村集》為“人生苦樂皆陳跡,年去年來堪痛息”。有的時候是詩句的刪减,再如卷九曹溶的《武林遇何芝函侍禦舉子彌月因述往事以志悲喜》,《敬惕堂詩集》少四句,改一處[《靜惕堂詩集》無“西川方阻兵,劍閣樹牙纛”“茂草聚都宮,簪紳日煩促”四句。“潼關賊莫當”改為“潼關賊滔天”。]。這些刪减和修改,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形式的考慮,但更多的則應該有更深層的社會政治原因。所有這些差異,可資校刊、考訂外,也值得分析、研究。
綜上,《百名家詩選》是一部尚未得到充分重視,具有較高文學、文獻價值,值得閱讀和深入研究的一部清初詩選。
本书选用精善之本作为底本,并参校重要异本,经过严谨校勘与详尽注释,既保留了原作的古朴风貌,又为现代读者扫清了阅读障碍。无论是诗歌爱好者还是学术研究者,都能从中汲取灵感,感受古典诗歌的深邃意境与永恒魅力。翻开本书,仿佛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共赏诗词之美。
選清詩觀始集作
人心釀世運,世運變人心。盛衰既遞轉,治亂亦相尋。群生天地間,激蕩成謳音。鴻纖既異致,雅俗判高深。聖主闢文運,群賢慶盍簪。篇什多古風,聲價重球琳。寧敢繼絕筆,所願正哇淫。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