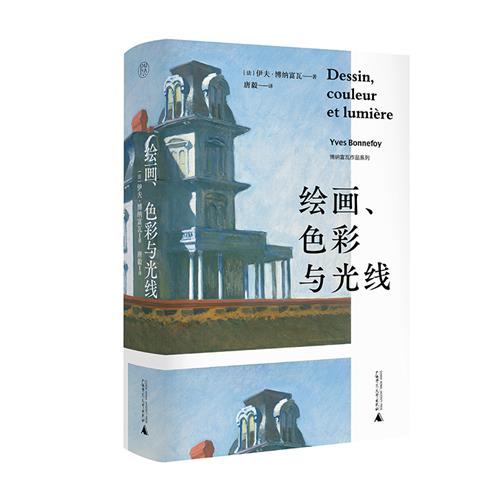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5-02-01
定 价:68.00
作 者:(法)伊夫·博纳富瓦 著;唐毅 译
责 编:吴义红,孟繁强
图书分类: 文学评论与鉴赏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人文·思想·艺术评论
开本: 32
字数: 198 (千字)
页数: 3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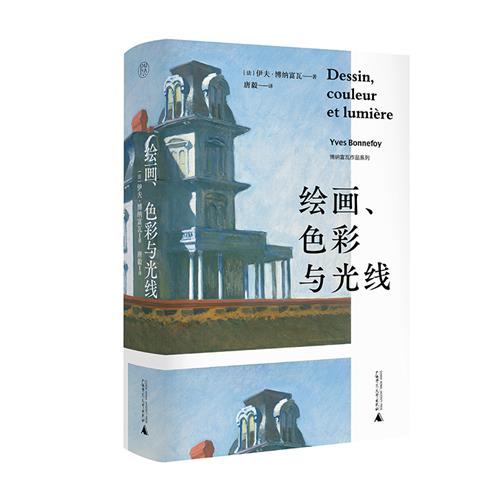
《绘画、色彩与光线》是法国著名诗人、评论家博纳富瓦撰写的一部有关绘画、摄影、音乐的评论集,收录十余篇文章,重点评论西方艺术发展史上几位重要的画家、雕塑家、摄影家、音乐家。从曼特尼亚到埃尔斯海默,从霍珀到布列松,从贝多芬到贾科梅蒂,既描绘出艺术家们的日常生活细节,又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肯定了他们的艺术成就,也清晰地揭示出其问题症结和前进方向。博纳富瓦站在诗学理论的高度上评论画家和诗人的作品,目光如炬,切中要害,在探寻现代性的种种表现的同时,也深入表述了自己的诗学和美学主张。
作者简介:
伊夫·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1923—2016),法国著名诗人、评论家和翻译家。他的创作宗于波德莱尔、瓦雷里、马拉美以来的象征主义传统,又融以现代艺术的创新活力,被认为是20世纪法国现代诗歌的最后一座高峰。他一生创作诗集几十部,曾获得法兰西学院诗歌奖、龚古尔诗歌奖、卡夫卡文学奖、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并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译者简介:
唐毅,文学博士,讲师,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硕士毕业于湘潭大学法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般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各一项,主持兰州交通大学青年基金和校级教改项目各一项。
艾蒂安·迪朗 / 001
关于肖像画的评论 / 023
安德烈亚·曼特尼亚 / 049
从委罗内塞到戈雅 / 073
“夜晚的色列斯,来自亚当·埃尔斯海默” / 095
1630年之争:《阿什杜德的瘟疫》和《强掳萨宾妇女》 / 107
阿卡迪亚的牧人 / 141
一个世界尽头的提埃波罗 / 181
莫扎特心中的世界 / 207
雷茨沙漠和地点的体验 / 235
油墨层下的色彩 / 253
爱德华·霍珀:生命存在的光合作用 / 275
乔治·德·基里科 / 309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 315
贾科梅蒂的愿望 / 331
贾科梅蒂:两个时期的问题 / 353
附录:《变化无常的诗》 / 370
书目注释 / 374
作者的其他主要作品 / 377
无
博纳富瓦不仅给了我们风景,还给了我们艺术品——自从读了他的作品后,我对于乌切洛、尼古拉·普桑、戈雅、拉文纳的墓地或罗马式建筑的看法已经改变,或者说,他提供了这种看法。他最好的散文经常邀请人们在那些伟大的作品中沉思。
——斯蒂芬·罗默
博纳富瓦是20 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将我们语言的精确度和美感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弗朗索瓦·奥朗德
除了完全没有任何装腔作势或做作之外,最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博纳富瓦那种精神上的宁静和安详。
——约瑟夫·弗兰克
博纳富瓦是法国当代文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六十多年的文字生涯使他的诗歌作品和诗学著述兼具深邃的历史感和深刻的思想性。
——唐毅
博纳富瓦《绘画、色彩与光线》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艺术史知识,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观看和思考方式。博纳富瓦启发我们:艺术批评不应停留在形式分析和历史考据层面,而应该是一种涵盖美学体验、哲学思考和诗意想象的综合性思维活动。这本书不仅可以让读者学会如何欣赏一幅画、一件艺术作品,还可以学习如何从多个角度思考,从画家的笔触、色彩、构图等技法层面,到画家想要表达的对生命、存在等永恒命题的探讨。
艾蒂安· 迪朗
I
乍一看,艾蒂安·迪朗的《沉思录》(Méditations)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也没有什么能重振自宗教战争结束以来诗歌所缺乏的活力,那场战争同样使七星诗社的梦想破灭。在1600—1610年间,沙龙迅速增多,娱乐趣味、文字游戏、附庸风雅优先于形而上学的志向和敢于思辨的勇气——而这不正是此书所呈现的东西吗?人们很容易察觉书中那些精雕细琢的讽刺、内容贫乏的夸张以及流于表面的主题,后者看上去既没有新意,也毫无希望:诗人爱得狂热,他的情妇却显得冷淡,她表示拒绝,他本应放弃,但他仍执着追求。的确,这份执着具有某种奇特之处,迪朗自己也对此感到诧异,他几乎从中发现一个错误,他似乎在努力确定这个错误的性质。但是,当这些诗歌以如此枯燥乏味的方式提出该问题时,我们为何还要把这个微不足道的问题放在心上?然而,正当人们想要放弃阅读时,他们却被拉了回来,仿佛迄今为止看起来不过是翻版的事物、一些空洞的符号,变得更加密集,形成一个场所,由此不断变得空虚。人们预感到,文字的空洞本身就是意识产生的对象,它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自相矛盾地成为一种尚不确定却寻求深化的经验的充实。
有什么发现足以解释这种趣味的复苏呢?首先,正如心理学家所指出的那样,这位女士的强硬态度——“比磐石还坚硬,比地狱更凶猛”——并非一种性格特征;这位女士自身也不是我们世界的存在,她甚至在小说或戏剧里发生了变异:在戴利娅的子孙后代中,她应被置于一个由“漂亮的眼睛”和“波浪形”头发来模糊呈现的人类形象与一个即使不算神圣也是超验性的在场或不在场的中间。在此书第一首优美的诗作《不在场之诗》(Stances à l’Absence)中,迪朗直截了当地向冥界发难:他说,同那些罪恶的灵魂因被上帝放弃而感受到的痛苦相比,他们的罪恶不值一提;又因为他告诉我们,他自己承受的正是这种缺失带来的痛苦,故而他所爱之人配得上那些最高尚的比喻。此外,她被称作乌拉尼亚,作为司掌天文和几何的缪斯女神,这使她与浩瀚宇宙空间里的上帝的数字联结在一起——那个空间远在我们地球之所的上方——即使她的信徒注定要忍受更大的忧郁。《沉思录》中的乌拉尼亚并不是一个缺乏普通欲望的真实女性,这只会使她更强烈地出现在同样需要她的言语之中,她象征着一种更难定位又更为广大的不在场。这种不在场可能会掏空并清除尘世经验中的一切形象,进而对一切词语和一切言语产生影响。这实际上令人深思。从修辞层面上讲,诗歌的“空虚”绝非单纯的写作平庸,而是一种直觉;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对现实乃至对上帝的批判,这一批判也许在迪朗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在矫揉造作的夸张手法和陈词滥调中开始,随着焦虑的蔓延,它逐渐变得更有意义。
我相信人们可以证明——根据种种迹象,但我不会强调这些迹象——迪朗最初进行诗性思考时所谈及的,正是从符号中隐退的存在,是对那些被认为以知识或爱情为保障的虚幻对象的发现,是当他看到这一发现、这种对世界秩序的破坏一直延伸到上帝本身时产生的思想混乱。《沉思录》是对诗的一种侵袭,这种诗最初可能仅仅表现为一个简单的游戏,基于一些平淡无奇的目的,通过对表象和价值的质疑,它们在那场由马基雅维利或蒙田推动的巨大危机中幸存下来。而在这方面,这部作品不是一本简单的小书,它不是在一个更伟大艺术的废墟上迅速繁殖的杂草,而是标志着直到昨天还认同象征网络之信仰的更大衰退,这个网络长久以来一直在宣扬绝对性。
II
迪朗的诗远不止于此,因为在《沉思录》之外,他在《变化无常的诗》(Stances à l’Inconstance)中恢复了冷静。一首诗刹那间就以思想的活力和美妙的图像令人如此信服,它理所应当被视为我们语言中最优美的篇章,而且我们还应思考,为何它胜过甚至超越这本书的所有其余部分。
诚然,正如我所说,《不在场之诗》已经具有崇高之处,而诗集中的任何诗节都胜过其他体裁,也许是因为“沉思”需要持久的时间和雄浑的气势,这正是十四行诗所缺少的。但是突然间,抽象的东西消失不见,词语重新获得重量,言语重新具有重要性,它们揭穿空虚,由此书中第一次以既精确又无限的方式提出一个观点:人们只能对此加以证实,因为思想得以深化、变得激进,从此以后不仅以人类而且以宇宙为对象。在这一关键时刻,戈莱(Gaulée)重新对此展开研究。
恢复冷静——首先这种意识是对最初诗歌之肤浅的否定和超越,从而达到形而上学的高度。人们可能犹豫,不敢相信先前的沉思包含的疑惑远不止针对一个特定的形象。无论如何,这是从此必须得承认的一点,因为《变化无常的诗》对乌拉尼亚的否认,在任何场所和生活的任何层面上,从海岸上的波浪到天空中被称作上帝的看似恒定的火光,都是对一切稳定性和一切本体论意图的否定。这首令人惊奇的诗作是对深渊的发现与证明,从自然或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看,这个深渊将在我们创造的所有艺术品中展开,而它一直延伸到底部,在总是转瞬即逝的表象之下,那里只有元素,或更确切地说只有原子。可见,迪朗延续了卢克莱修的理念。从逻辑上讲,这首诗似乎同样是将从前那颗过于恒定的心凝聚到一种毫无保留地欢迎所有经过之物的伦理观上,只要欲望与之相连。
如今,迪朗指出,不稳定性是那些被视为世界秩序和意义的稳定数据之物的不断变化,是唯一真实的“本质”。它是由空气和水构成的——海风吹散波浪,使它成为泡沫之柱——暴风雨就在这里,来主持这些婚礼,暴风雨也就是火。至于第四元素,也许更加值得信赖,在迪朗经常提及的那些“磐石”中,但是
如果沉重的大地在其底部受到束缚,
那是因为各种原子的运动
由此,从总体上看,没有任何东西被用来预防那些是或看似是源于崩溃、重启、遗忘以及改变的事物,这个时代称之为“变化”。不稳定性是宇宙的灵魂,不过是昼夜交替、四季轮换,而在天空中,还有行星的运转。它“神圣的威严”对人类具有同样的力量,人们也许会认为那里栖居着永恒的光芒。因为“我们的精神仅仅是风”,它只有以幻想抑或假象的形式才拥有稳定性。事实上,我们难道不是由自然界中无故旋转的四种元素组成,特别是火——欲望之火?
但艾蒂安·迪朗的发现并不局限于这种智力上的虚无主义,他恢复冷静也不单纯是逃避眩晕,面对瞬间空旷的天空,让自己献身于每时每刻万物的非持久性所引起的欲望之中。诚然,《变化无常的诗》似乎是对欲望的辩护,使其运动性成为世界虚无的唯一真实的反映,进而使之成为唯一的行动准则而非一种谎言。不过,迪朗还告诉我们,这一宇宙的灵魂,不稳定性,被埃俄罗斯想象成“这个世界的第二本质”,这就提出了第一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并且在一种明显的矛盾之下,令人意识到思想的其他层次。“第一”本质是或曾经是什么?既然人们只能得出结论,认为这确实仍是传统世界的秩序,是古希腊—基督教的宇宙秩序——迪朗难道不是说如此“伟大”而又“美丽”之物并非任何别的东西,而是天空的形象吗?——如何在作为第一本质的形式的持久性之诱惑和对万物不稳定性的忠实之间实现调和呢?
III
在我看来,这是简单可行的方式,是迪朗思想中最特别的方面,同时也使《变化无常的诗》变得丰富起来。实际上,从本体论上讲,同时赋予这两种“本质”以同样客观的真实性是不可想象的,当人们认识到一系列的解读时,这种双重假设就不再自相矛盾了,而其中一种,“第一本质”是美妙的,非常美妙,瞬间变得令人着迷,然后永远无法忘怀,但人们必须意识到它仍是幻想。总之,言说者对这个世界的感知的一种表达是美,另一种是真。我认为,对迪朗而言,在这个圈套空间的美与真之间被开掘出的是一条迄今很少被人探索的道路,即对言语的存在本身的思考,它与事物的存在相对立。
我们换一种说法。第一本质是天空的有序形象,是神圣之永恒的表现,它是空间,是受制于空间的时间。在这个精确而稳定的结构中,确实存在一种“变化”的地方——这一众所周知的“境况”可以破坏任何计划,挫败任何预言——但这样一种不稳定性仅仅是世间原罪的影响之一,它对真正信徒的灵魂的作用比对自然的终极存在的作用更大。在造物主的本体论中,存在作为规律的担保人,依然在永恒中与自我保持一致。然而,迪朗察觉到一切都只是在变化的宇宙之中,这种永恒在何处拥有其场所呢?他难道不应该确定,也许只有在词语里,只有在它们本真的层面上,无限地保持同自身的一致,以至于让人以为它们所命名的事物也是如此?天空、星宿,无论它们看上去多么恒定,如若人们探寻其存在,也只不过是一些幻景,人们在其中仅仅发现原子的运动。只是因为构思它们的语言的恩赐,它们才在一致性和美感方面存在并保持强大。
然而,以这种方式思考问题,显然不为宗教乃至哲学所接受。要认识到我们的表象具有实质性,这无疑对社会是有益的。而且也很容易设想出一些体系,它们至少会有一个好处,就是让人相信它们在现象和梦想中并无十足理由就界定的那些本质是永恒的。但是,在永恒运动的原子哲学之上,迪朗补充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正好也否定了思想意识的伎俩,同时揭示了在我们的表象和概念中,与在情感或事物中一样,存在一种不可控制却很深刻的不稳定性。“我们的精神仅仅是风”,我已引用这句话,但现在必须要看到,它还适用于比普通生活的抉择和痴迷更多样的东西。
我很乐意描绘我轻盈的思想,
但是,想到这一点,我的思想就已改变,
迪朗如是写道,这比现代物理学的“不确定性原理”或解构主义的考察还要早。任何思想都依赖于思考它的词语,正如我们所说,人们只能通过揭示或领会对事物的过度能指来对其加以阐释,换句话说,即所指拥有的虚幻之物。事实上,这就是关于词语的思考——在现象的非持久性与精神的轻盈之间——并视其为唯一的真实,尽管它本身也随着另一种形式的“变化”而沙沙作响。“美妙思想的精神”,不稳定性,也是并且尤其可能是一种清醒,如今这种清醒知道语言同样也是“真实的”——在其自主性上,在其作为骰子的存在中,那些骰子在摇杯中晃动,即将从杯中掉落,空白页上的星宿——正如它简化的表象是短暂而虚幻的一样。《变化无常的诗》是一首对语言的赞歌,它取代了上帝的位置。
IV
伴随这种没有上帝的语言,出现了一种新的结合。的确,在这些词语中,存在避而不见,思想因在事物中没有支点而纷繁杂乱,欲望更加自由地依附于一种引诱它的表象,哪怕只在一瞬间,这让它过剩的力量得以消耗,而这就是一种快乐。当对真理的表达背离,只在它们的位置上留下怀旧情绪或虚无主义,欲望的词语至少具有渴望终止的特点,它们对其加以浇灌。在无限的可变性之中,在普遍的不在场之中,这不就像一个在场的片刻,转瞬即逝却更加令人感动吗?除了人们早已意识到的毫无节制的享乐主义,这种即时的、充分的却又虚空的认同——就像玫瑰之美——它在神学时代被抑制、被禁止,如今在完全是“美妙思想”的精神里得以重新绽放。
在精神上——艾蒂安·迪朗继续思索——他知道如何成为一位诗人。作为一种哲学,作为一种语言理论,《变化无常的诗》显然更是一种诗学;这种诗学信任言语,在那其中言说只会显现为缺失,确切的原因正在此。为什么对乌拉尼亚保持忠诚是徒劳无益的甚至是一种错误呢?因为在词语的所指意义中,它不是布满星辰的天空,也不是世界的固定秩序,而只是一种言语的轮廓,是人们将其想象为绝对的幻景。正是由于人们太过长久地信任它,以至于它只是一种空虚,欲望在其中迷失——由此产生讹误——这种欲望表现为一条道路。但是,如果人们揭露它的专横,专注于言语业已形成的新图像,即使承受语言的重负,一切感性经验的财富也将被奉献给存在于生命个体中的活力。艾蒂安·迪朗的诗学,是要让欲望直抵它所喜爱的一切。那么,会不会诞生一种尚不为人知的诗,它比兰波还要早,更不用说超现实主义?无论如何,这位处于路易十三时代的诗人——正如波德莱尔所言,诗在那个年代奄奄一息,只为在查理十世时期重获新生——将在《变化无常的诗》的结尾处以三节诗表现它,我只能引用这三节诗,尽管它们几乎家喻户晓。
那时,空气的女儿,浑身有一百根羽毛,
她让我摆脱农奴的身份,获得自由,
我给你的礼物是我死后的遗体,
是我的改变的爱情,它冷清的火焰,
以及那个曾阻止我的顽皮的物体。
我给你的礼物是一幅奇幻的画作,
爱情和游戏将在其中手牵着手,
遗忘,希望,狂热的欲望,
背弃的誓言,忧郁的性情,
女人与风会在其中一起被看见。
海沙,暴风雨,云彩,
火焰在空气中制造雷鸣般的热量,
闪电的火焰在被看见以前早已消失。
天空的绘画在我们看来是陌生的,
将作为这幅神圣画作的色彩。
这就是艾蒂安·迪朗对那位“无处不在却无一所在的女神”所描绘的景象,并由此表达了一些观点。一方面,从此很清楚的是,除非放弃新柏拉图主义者所谓的理念,否则就不可能有诗。由戴利娅或奥利弗制造的心智的东西和超验的事物,也只不过是一团“荒凉的火焰”,一种被认为极其危险的诱惑。在对“现在”的肯定中,数个世纪的纠缠就此结束,这个“现在”既是完全真实的瞬间,也是人们在无限之中自我完成的馈赠,一种令人痴迷的消耗。
另一方面,这个“现在”是一幅画。“浑身有一百根羽毛”——所有的颜色,所有的虹彩——不稳定性首先是表象本身,当这一表象在“变化”的旋风中凭借自我消散而再次惊艳地重获新生时,眼睛这一最为迅速的感官能够首先回应它,进而显现出感官直接性的财富。诗如画,已经重复了许多个世纪,新柏拉图主义理应终结——它的美学是迪赛诺,它的介质是米开朗琪罗式的白色大理石或意大利矫饰主义的冷色调——诗才会给予它的姊妹——也从后者处获得回报——存在于感官之中的无限。这是一种充满潜力的新艺术?“天空之画”,染红,撕裂,在那个社会,在公园夜晚的宴会——德鲁埃的一些画作——的确已从它们的活力中流露出图森·杜布勒伊式的羞怯或贝朗热式的紧张的虔诚。不,这并不是在古典主义的冒险中发生的事情。但——我是否太急于拉近关系了?——这些“暴风雨”和“云朵”让我想起阿雷蒂诺写给提香的信,讲述他看到的夕阳混合着火光,在威尼斯天边的色彩,装饰着迪朗所说的“幻想的”建筑物。阿雷蒂诺对提香说,您画这个,更多的是为了通过您的艺术使无常的自然永存。永存,消耗:在这两种诱惑的脊线上,西方一直在追寻,有时几乎已经找到——在刹那间变得太晚之前——一幅意识到瞬间之存在的画作。
这一瞬间,这幅“幻想的”画作,因为一切都在瞬间发生改变,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一个看似经久不衰的思想范畴,迪朗毫不犹豫地将其描述为“神性”,在一句美妙的诗里赋予这个词语以全部的重量。上帝已死,正如《变化无常的诗》中已经说过,但神性依旧存在,它仅仅是那个出现、消失、蜕变的东西:它“是”,为什么不呢,词语不再假装表象具有实质。迪朗问道:诗是什么?如此接近世界上变化无常的事物,以至于这种非持久性本身就显露出实质,成为快乐;由此,诗歌将成为一种新的神圣的写作。
V
我们不可低估这份快乐、这种新的神性,以及赋予诗的几近神秘的角色。即使以《变化无常的诗》写于22世纪为由,也无法否认它至少已经预感到了尼采对元素力量的认同以及对酒神的皈依,这一皈依使得含义和价值的偏移成为“真正的生活”的空间。
但反过来,我们也不要急于认为,在1615年左右这一大胆的思想就已成为一种广为流传的观念。无论智力上的放纵在自我掩饰方面拥有何等技巧,这也只不过是某些地位显赫的智者的状况,它难道不更倾向于主张理性并领会自然规律,而不是那些仍然流于宗教范畴的对上帝的否定?一个叫瓦尼尼的人,在迪朗之后的几个月同样被处死;作为布鲁诺的接班人,他也许达到了直觉上的相同广度。而在那些自称为诗人的人中间呢?诚然,在那些年不计其数的韵律中,幻想的纠缠无处不在。但很多时候,对一个极其冷漠的情妇来说,“一切会过去的想法”通常只会轻易导致“活在当下”的念头。即使是泰奥菲勒·德·维奥——人们无法原谅他关于艾蒂安·迪朗之死的卑劣的十四行诗,他只想玩弄诡计——也只是以这样平庸的方式成为“美妙的思想”。而变化的直觉比瞬间的享乐主义更加深刻,多数时候人们并无更大的勇气对其加以言说。在那个反宗教改革的时代,上帝无所不在。与《沉思录》同一时期,拉塞佩德(La Cépède)、沙西涅、拉扎尔·德·塞尔夫创作并发表作品,更不用说奥比涅:他们仅仅消极地思考非持久性,比如必须战胜的混乱,期待罗马的巴洛克响起一声雷鸣。而在那些很少拥有信仰或很少笃信宗教的地方,是意志在起作用,正如高乃依很快就证实的那样。
事实上,在诗人中,唯一可能影响迪朗思想的激进主义者,就是马莱伯,后者意识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能指优先现象;但在其别的逻辑中,只有稳定形式的吸引力更好地显现并占据上风。马莱伯确认,尽管词语在事物层面上没有一点可靠性,也没有什么能使言语提防变化,词语却能够听令于国王的权力,变得明确而恒定,国王制定价值观,指定道路,选取并强行规定生活方式。这位主管者的身份从君主那里窃取而来,它从总体上监督君主,由此提出更正、清理并修剪语言,好比修葺一座法式花园,最终从一整个世纪的言语场中赶走真正的本质。这项工作同样存在于绘画之中,因为它的监督针对的是可见与可想象之物。但由于这幅画缺乏生命力,迪赛诺冒着沦为寓意画的风险,再次占了上风。
VI
迪朗是孤独的。同样因诗而孤独,他的诗似乎是通过骤然的灵感而成熟的,就像他临死时那样。而由于认识到这种独特性确保其在诗学争论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今天应归功于他的,就是反思他的直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真实的。换言之,他从虚幻经验的结果中得到了什么?在我们的道德存在中,在埃俄罗斯或尼普顿那里,一切都不过是沙堆的城堡;倘若不是在存在之中,难道不是在语言里有一些东西来回应这种创建的需求吗?人们也在其他作家身上和无可辩驳的诗歌里发现了这一需求。
总之,对那些赞赏《变化无常的诗》的人来说,这个时刻令人联想到言语创建之物同它所命名之物一样多,汇聚之物同分散之物一样多,由此形成一个场所,它拥有记忆和期限,如同镜子一样,除了云朵,什么也没有映照其上。这是一个产生感情的场所,一个唤醒一致性的场所,它意味着言说者不能再像动物一样单纯忠实于连续的冲动,也不能沉迷于梦想的乐趣而没有迅速意识到一些形象在消失,这些形象在其世界意识中却是必不可少的。的确,应该要理解“变化”:否则在言说者之间就只剩思想意识了。但要竭力在其中立足。如果不是懂得拒绝变化,确切地说,通过确定绝对,通过一个拒绝非持久性的人或事物,这种言语在我们周围延伸的场所,那么迪朗在乌拉尼亚时期证实的具有顽强存在意愿的爱又是什么呢?对于这类问题,我只浅尝辄止,它们在《变化无常的诗》的最后一节也没有得到解决,而最后的诗节赞美一种双重的不稳定性,即情人的变化无常以及情妇的变化无常;但关于“美”,“美好的思想”再次给它披上了庄严、崇高而神圣的外衣,正如它在乌拉尼亚身上看到的那样。不,这些问题绝不是借助矛盾修辞法就能最终解决的。相反,它们对此感到愤怒不已。
但这些问题至少已被提了出来,或许仅仅出于这个原因,《变化无常的诗》的作者可以被称为伟大的诗人:因为伟大的诗就是彼此燃烧——就像在电弧之中——最自发的敏感性与智力的净化活动。为了让言语在这个危机时期完成更新,这两个积极的源头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一结合发生的层面上,一些作品之间的联系显现出来,尽管还存在一些距离;以迪朗为例,虽然我刚刚还说他是孤独的,他却在美妙的神圣对话中与其他诗人或画家重新交谈。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我想到那个大约十年后做了许多事情的人,但他逃亡到另一个城市,为了那些我们深知作为重大十字路口的世纪的决定。我是否说过迪朗没有近亲?诚然,尼古拉·普桑在1618年已经24岁,他可能住在巴黎,但他远离诗歌,尽管他与马里诺相识,也一定没有接触过《变化无常的诗》,更不知道是谁在沙滩广场的木柴堆上被火刑处死。他很快就前往意大利,游览威尼斯,在那里发现提香并为之折服,在自己身上感到更大的狂热——已经更为现代——那种肉欲感,那种对统一性的追求,那种对光的无限激情,而在罗马,这些将会是他真正追求的最早画作,包括《鲁特琴女演奏者的酒神》(Bacchanale à la joueuse de luth)。为什么提及这幅画呢?因为在我看来,简单地说,没有其他画能更好地说明迪朗想要在肉欲和性欲的时刻加入惊恐的愿望——在这个广阔的天空中,正好是那些“在被看见以前早已消失”的“闪电的火焰”。但画出《鲁特琴女演奏者的酒神》的普桑已经构想出《狄安娜和恩底弥翁》(Diane et Endymion)或《诗人的加冕》(Couronnement du poète):而对欲望和爱的思考,还有何时比我们唯一真正的古典主义的创立时期进行得更好呢?迪朗的诗学直接指向普桑的道德批判,并通过这样的领会而变得丰富,这得付出超越的代价。精神的历史只有在顶点处才会焕发光彩;而一位年轻诗人作为不公和草率的受害者,他的诗篇也许就是这样的顶点之一。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