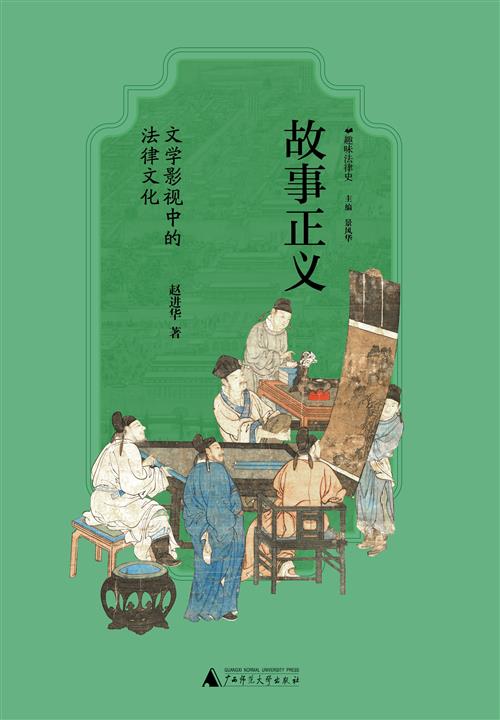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5-03-01
定 价:68.00
作 者:赵进华 著
责 编:蔡楠
图书分类: 法律普及读物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法律/法律普及读物
开本: 32
字数: 245 (千字)
页数: 3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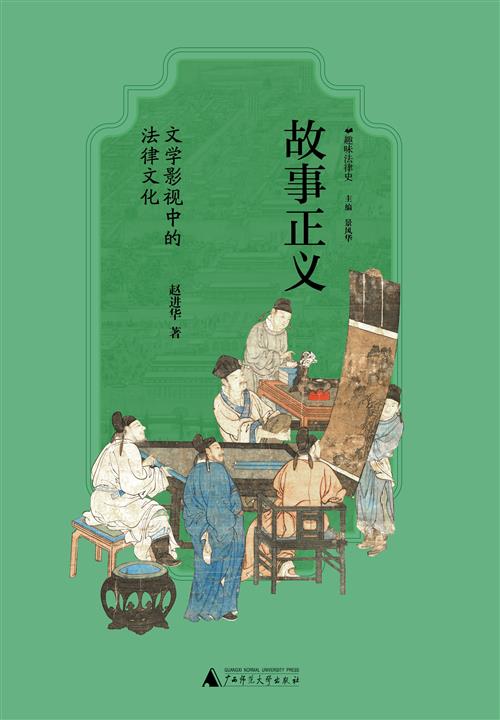
本书以经典文学作品和热门影视剧为研究素材,以法律史和法律文化为学术底色,发掘经典文学影视作品中的法治元素,解开其中不为人知的法律文化谜题。如通过《聊斋志异》《醒世姻缘传》《红楼梦》等探讨中国古代与身份、婚姻、家庭有关的法律建制和法律实践;借助影视剧《清平乐》《鹤唳华亭》《长安十二时辰》等探讨中国古代与政治、行政有关的法治安排和法律实践。本书在解读文学经典的同时普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让读者可以具象化地走近古人的法律世界,体会古人的法律情感和法治理想,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文化内涵,也更深入地理解传统法律文化。
赵进华,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法律文化、比较法律文化、经济法学。曾在《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检察日报》等专业报刊发表若干文章,并在《东北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导言 1
壹
在古代,表兄妹到底能不能结婚? 11
十三妹的身份是妾吗? 22
姻缘如何能醒世? 37
严法能奈悍妻何? 53
宋朝男人为何钟情娶小姨子? 66
公主为什么不幸福? 85
裘千尺为什么想不通? 101
贾宝玉挨打反映了什么? 112
贰
为什么说宋朝是中国古代法治的顶峰? 125
范仲淹的好友尹洙因何而死? 139
君主该不该使诈术? 149
太子为什么多不得善终? 156
林九郎是法治派吗? 163
古人为什么喜欢敲登闻鼓? 170
匿丧为什么行不得? 182
夏竦为何没能获谥“文正”? 194
叁
中国古代的理想法官是什么样子的? 203
包公是靠什么断案的? 211
宋江浔阳楼题诗被定谋反冤枉吗? 221
为亲复仇难题如何解? 234
大宋提刑官为何那么牛? 245
宋慈的父亲为何自杀? 256
中国古代的“宰白鸭”是怎么一回事? 265
提利昂的审判为何能打动人心? 276
肆
在古代,庸医会是什么下场? 287
“伤人最少”的侠义之道有什么问题? 294
冤案的逻辑是什么? 305
反杀凶徒何罪之有? 317
世间有天生犯罪人吗? 324
分歧终端机具有何种隐喻? 332
古墓派为何如此另类? 341
正义为何令人困惑? 356
后记 362
导?言
除了存在于人类共同的想象之外,这个宇宙中根本没有神、没有国家、没有钱、没有人权、没有法律,也没有正义。
——《人类简史》
法律与文学研究属于法理学的一个分支,在法理学研究的大家庭中,法律与文学研究即便算不上一枝独秀,至少也是独树一帜、楚楚动人了。
法律与文学研究的繁荣兴盛来自于作为异质学科的法学和文学的交互滋养和彼此启发,反映出法律与文学之间天然的紧密联系。
一方面,文学是法律得以表达自身的基本工具。现实世界中,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离不开文学的加持。最能说明这一事实的证据是,举凡伟大的法典无不代表着当时文学的最高水准,所以司汤达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才要每天读上几页《法国民法典》,以寻找语言的灵感。而曾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卡多佐也坦承:“在司法判决的荒野上,文学风格不仅不是一种罪恶,只要运用得当,它甚至具有积极的益处。”
另一方面,法律(尤其是司法)是文学叙事的重要对象。文学以揭示人性、映射现实为使命,而法律不仅是现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约束人性的重要制度性力量。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古往今来那些伟大的诗人、剧作家、小说家都如此地偏爱法律题材。不少经典的文学作品触及法律命题,或者本身就是纯粹的法律故事,例证不胜枚举,西方的有《安提戈涅》、《威尼斯商人》、《悲惨世界》(又名《法律的命运》)、《审判》等戏剧小说,中国的则以流行于明清之际的一系列公案文学如《包公案》《施公案》《狄公案》为代表。
法律与文学研究将文学的视角引入法理学的思考,从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以感性调和理性,从而拓宽了法理学研究的视野,也丰富了法理学研究的内容。罗宾·维斯特曾提示我们:“文学包含有关法律的真相,而这种真相并不易于在非叙事的法理学中被发现。”到了冯象笔下,这层意思揭示得更为显豁:“要弄懂中国老底子的政法手段,光读《唐律疏议》《资治通鉴》《名公书判清明集》是不够的,搞不好还被蒙了;不如听那门子讲一遍‘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的‘护官符’来得切中肯綮,纲举目张。”
诚如冯象所言,想要对中国传统法制和古典法理有更真切的了解,学者实在有必要好好读一读《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金瓶梅》等古典文学名著。在这些久负盛名的现实主义作品中,读者不仅可以发现大量鲜活的古代法制史料,其中有不少甚至可以补典籍记载之不足,而且可以具象化地走近古人的法律世界,体会古人的法律情感和法治理想。
能够为法律教学和法学研究提供营养的其实不限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西游记》《聊斋志异》《封神榜》《镜花缘》何尝没有价值?有读者就从《西游记》的字里行间读出了猪八戒的法律意识和权利观念,而描写唐僧身世的一节文字《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则反映出中国古代为亲复仇传统的强大,再看唐僧师徒投身艰苦卓绝的取经事业以赎前衍的故事逻辑,其“将功折罪”的法律寓意再明显不过。至于《聊斋志异》,其中描写司法或法律的篇章真正不少,如《席方平》《胭脂》《太原狱》《诗谳》《考城隍》皆是,其间既有对政治黑暗、司法腐败的揭露和鞭挞,也借由幽冥审判和因果报应表达了作者对公道正义的向往和呼唤。
再把眼界拓宽,除了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戏曲、杂文、诗词歌赋乃至民间文学,无不可以成为法学研究取资利用的素材。清人赵翼有《题白香山集后》诗云:“风流太守爱魂消,到处春游有翠翘。想见当时疏禁网,尚无官吏宿娼条。”提示我们,白居易的诗作是考证中国古代官吏宿娼禁令制度的绝佳证据,而后来学者以文证史的研究路数或者正取资于此。
读诗的这层好处折射出文学作品的法律教益价值。借由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帮助,读者不仅可以把握法律的当下,而且得以窥探法律的前身,甚至能够预见法律的未来。科幻文学的法律预测功能最为突出,不少优秀的科幻小说不乏对未来人类社会法治状况的设想。如《三体》中“青铜时代”号审判记录显示,为当代人所珍视的无罪推定原则在危机纪元被部分推翻了。日本科幻小说《百年法》则大胆地设想了人类实现“永生”后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引导读者思考代际义务的正义性以及“由法律来规定人何时死亡”的正当性问题。
将文学资源引入法律教学和法学研究不仅有理论上的必要,而且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乐趣。喜欢听故事、讲故事似乎是人类的天性,文学作品(包括影视作品)总是可以轻松地调动人们的情绪,乃至触及人们的灵魂深处。经验告诉我们,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可能都要归因于童年时代童话故事的熏陶。
若是按照《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的说法,故事的发明或讲故事的能力的形成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正是通过讲故事,人类建立起共同的想象,从而可以实现复杂的社会分工和协作。在这个意义上,几乎全套的政治法律制度都隶属于这种“共同的想象”,从而与故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很多国家的宪法都有序言,宪法序言的故事属性尤其明显。以我国现行宪法的序言为例,其中较长篇幅的历史叙事在交代宪法诞生的历史背景和宪法由来的同时,阐明了革命和法治二者之间深刻的历史联系,从而使国民获得法治意识形态层面的教益。
对于司法实践,讲故事同样重要。在张扣扣杀人案中,被告辩护律师在洋洋洒洒的辩护意见中,一开篇就大胆断言:“这是一个血亲复仇的故事。”而据学者们的观察,英美法系的法庭审判,不啻一场故事比拼,控辩双方各抒己见,讲述着内容迥异的两个故事,结果就看谁的故事讲得更生动,更符合生活逻辑和人们的情感认知。
法律的故事属性易于理解,故事的法律属性却常被人忽略。故事的法律属性在中国古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古人的词典中,“故事”通常并不是对过去的人和事的泛指,而是特指先例、惯例、不成文的制度。看完以下几则材料,当信吾言不虚:
故事,天子未得鱼,侍臣虽先得鱼,不敢举竿。(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
本朝殿试,有官人不为第一,自沈文通始,迄今循之,以为故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
赵昌言参机务,旦(指王旦,时为虞部员外郎、同判吏部流内铨、知考课院,与赵昌言为翁婿)避嫌,引唐独孤郁、权德舆故事辞职。(脱脱《宋史》卷二八二)
对故事的重视和遵循无疑体现出一种法治精神,因而构成中国古代法治文化传统的重要方面,其影响力迄今不绝。而通向未来的中国法治要想接续文化根脉,焕发文化生命力,恐怕绕不过对故事的温寻和讲求。
在故事中发现法理不应该是一种奢望。因为即便是广义上的故事,其中也一定包含着创作者的是非观念和价值意图,凝聚着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公平、正义、人道和爱的理解。此种由故事所传达并塑造的意识形态姑且可名之为“故事正义”。“故事正义”既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制度正义和社会正义,又具有一定的理想成分,从而能够反作用于实然的正义体系。
文学影视作品大都是在讲述故事,易言之,在表达正义。那么,这种“故事正义”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它与现实正义的出入到底有多大?或者,这种法理追问可以置换为一个个更为平易而具体的问题——那些读者耳熟能详的经典文学影视作品中“埋伏”着多少好玩有趣的法治元素?在波澜起伏、激动人心的故事情节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法律文化谜题?
本书即致力于回答这些问题。从内容上看,本书的各篇章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联系,但大体上都遵循着法律与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因而可以划入同一类型。具体来说,就是以特定的文学或影视作品为抓手,探讨作品故事情节中所包含的与法律相关的实践问题或理论命题,在求得问题答案的过程中,帮助读者更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文化内涵,也更深入地理解传统法律文化。为使结构看上去更为齐整,笔者把全书划为四个单元,分别从四个方面探讨文学影视作品中的法律文化,描摹“故事正义”的可能面相:
单元一探讨中国古代与身份、婚姻、家庭有关的法律建制和法律实践,揭示传统婚姻家庭法制和实践的历史文化特征;
单元二探讨中国古代与政治、行政有关的法治安排和法律实践,揭示推动制度形成和实践展开的文化因子;
单元三针对中国古代司法审判制度和司法社会实践,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予以解答,以求管中窥豹,呈现传统司法文化的突出特点;
单元四聚焦古今中外司法领域或法律实践中的一般性法理问题,揭示法律(司法)正义的历史文化属性,呈现法理的迷人和深邃。
笔者真诚地期盼,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引领读者开启一段法律文化之旅。读者会在不知不觉间领略到法律文化的魅力所在,从而产生进一步了解和研习的兴趣和动力。至少,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不再觉得法律的学习和研究是枯燥无味的。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写作本书的目的都达成了。
在这套丛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的语言文字是轻松随性的,但态度是严谨认真的。面对很多人对中国古代法律抱有的猎奇心态和网络上真假参半的各类传言,我们也希望通过“趣味法律史”丛书,澄清部分对中国传统法的误解,让读者看到法律史的真实面貌。
——景风华(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书以法律史和法律文化为学术底色,探讨了文学影视作品中所包含的与法律相关的实践问题或理论命题,试图解开其中隐藏的法律文化谜题,呈现法理的迷人和深邃。
在《公主为什么不幸福?》一文中,作者以热议一时的电视剧《清平乐》为着眼点,讲述徽柔公主(以宋朝福康公主为原型)与夫家矛盾的前因后果,并试图挖掘其婚姻不幸背后的深层原因,认为除了公主本身的性格使然,更主要的原因是,公主所代表的皇权(君为臣纲)与夫家的夫权(夫为妻纲)之间的角逐斗争决定了公主悲剧的宿命。
《君主该不该使诈术?》一文通过权谋剧《鹤唳华亭》探讨了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宋江浔阳楼题诗被定谋反冤枉吗?》探讨了罪刑法定与原心定罪;《宋慈的父亲为何自杀?》探讨了古代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正义为何令人困惑?》探讨了自然正义与司法正义……
作者借助具象化的文学影视故事丰富了人们对法律问题的认知,加深对文学影视作品中文化背景的理解,兼具学术性和趣味性。
公主为什么不幸福?
电视剧《清平乐》的前身是米兰Lady的言情网文《孤城闭》。与《清平乐》的宏大叙事不同,《孤城闭》从个体的视角将故事的重心放在福康公主和内侍梁怀吉的凄美爱情上。故事取材于宋朝福康公主的真人真事,又做了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堪称以今释古之佳例。历史上的福康公主(剧中名徽柔)是宋仁宗赵祯的长女,是不折不扣的天潢贵胄、金枝玉叶,集万千宠爱在一身,可是她的婚姻生活却只能用“失败”来形容。本来,公主的婚后生活幸与不幸,均无关国政,无伤大雅,顶多作为一种皇家秘闻,成为街谈巷议的闲谑之资。然而,似乎是受到某种不可抗力的裹挟,福康公主的婚姻家庭纠纷竟一发不可收,以致超出礼、法的边界,引得庙堂喧腾,各方关注,不仅由家事上升为国事,而且留给后人无限感慨遐思。
嫁给表叔
据史籍记载,宋仁宗赵祯前后共生育十六个子女,可是只有四个女儿长到了成年,其他三个儿子、九个女儿均早夭(帝王家尚如此,可见当时国人寿命之短)。福康公主既是长女,又最得仁宗喜爱。按照《宋史·公主传》的说法,福康公主自幼聪慧乖巧,很懂得讨仁宗的喜欢。一次,仁宗生病,福康公主亲侍汤药,不离左右,而且赤足散发向天祷告,愿以己身代仁宗之病。仁宗非常感动,于是更加疼爱福康公主。
俗话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其实,这是平头百姓的想当然之词,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为什么?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齐大非偶。中国传统观念最重视婚姻的门当户对,可是放眼天下,又哪里能再找出第二个可以和皇家望衡对宇的家族?即便适当放宽标准,适合与皇家联姻的家族的范围也十分有限。超越阶级阶层的爱情不能说绝无可能,但现实生活中肯定是凤毛麟角,况且在中国古代礼制的社会背景下,婚姻尚未缔结,又何谈爱情呢?一方面,公主出阁即为下嫁(是以名“出降”),皇家自不愿过分纡尊降贵。另一方面,任凭你什么样的高官权贵之门,与皇家相比都相形见绌,娶公主自属高攀,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其二,得不偿失。娶公主自然有很多好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增耀门楣,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有很多不利之处。如,公主身份尊贵,娶进门后,夫为妻纲的家庭秩序不易理顺。再如,历朝为了避免外戚篡权干政,通过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限制外戚参政的权力,尚公主者自然在此列。如剧中徽柔对怀吉所说:“在国朝,任何男子娶了公主,便不可以做朝廷的大官,管朝廷的大事了,只能做个游手好闲的驸马都尉。”这确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之一。是以,在剧中,仁宗固然不愿意把女儿嫁给曹评(表面原因是曹评的风评不佳,真实原因是仁宗担心皇后的娘家势力坐大),曹评似乎对娶公主也充满了顾虑。曹评出身将门,文武双全,他有他的政治抱负,怎么会甘心做一个吃闲饭的驸马都尉呢?
为公主择婿的确成了仁宗的一块心病,正如剧中所演的那样。经过慎重的考虑,仁宗决定把福康公主嫁给国舅李用和的儿子李玮。对于指婚的经过,《宣和画谱》卷二〇提供了简要的线索:
(李玮)字公炤,其先本钱塘人,后以章懿皇太后外家,得缘戚里,因以进至京师。仁宗召见于便殿,问其年,曰十三。质其学,则占对雍容,因赐坐与食。玮下拜谢而上,举止益可观。于是仁宗奇之,顾左右引视中宫,继宣谕尚兖国公主。玮善作水墨画,时时寓兴则写,兴阑辄弃去,不欲人闻知,以是传于世者绝少,士大夫亦不知玮之能也。平生喜吟诗,才思敏妙,又能章草、飞白、散隶,皆为仁祖所知。
可见,仁宗对驸马的人选是经过了认真的考察的,而李玮的表现也十分令人满意,不仅应对得体,举止可观,而且富于才华,书、画皆佳,只是为人低调,不喜张扬,作品多随兴创作,作完就扔在一边,是以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宣和画谱》收录了李玮的《水墨蒹葭图》《湖石图》),名气也不大显。
当然,仁宗之所以决定与李氏结亲,不仅仅基于对李玮人才的认可,更主要的其实是出于“亲上加亲”的情感需求和利益考量。按辈分,李玮是福康公主的表叔,二人的亲属关系是很近的。按照当代中国婚姻法的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李玮和福康公主的关系刚刚超出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的范围,因而即便放到今天也不违法,不过还是难免乱伦的嫌疑,所以社会一般观念并不认可,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也很少见。奇怪的是,中国古代社会虽极为重视伦理,却推许此种“亲上加亲”的做法。至少,仁宗在为福康公主指婚李氏时,他应该是非常满意的。据仁宗朝大臣张方平的描述:
仁宗之仁,周于万物,而仁之所施,常自亲始,肆其眷待宗室,恩礼隆密,朝政之暇,佳辰令节,合族缀亲,宴于内朝,如家人礼。(《乐全集》卷三八)
仁宗得享“仁”的谥号,与其情感丰富、重视亲情伦理是分不开的。综观仁宗一生,无论对宗亲还是外戚,都是恩礼有加。由于未能尽孝于生母李太后于生前,仁宗一直耿耿于怀,是以对李家尤其照顾,不断给舅舅李用和加官晋爵,一直给他加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的头衔。至此,犹嫌未足,于是才有指婚李氏之事。对此种补偿心理,《清平乐》有充分的表现,此不赘述。
嘉祐二年(1057)八月,兖国公主(仁宗为了表达慈父之爱,在福康公主出嫁前特意进其为兖国公主,并破例举行了隆重的册封典礼)出降李玮。仁宗不惜花费数十万缗钱为公主建造府邸,同时,指令礼官仿照古礼专门为公主设计了隆重而典雅的皇家婚礼。和平常人家的爹爹一样,仁宗此番嫁女也是不遗余力了。
从仁宗为福康公主赐婚李氏一事不难看出,即便贵为公主,也难享婚姻的自由。身为皇帝的女儿,嫁给谁不由自己,而由君父说了算,要服从于君父的利益和意愿。仁宗钟爱福康公主,拒绝了辽国的和亲提议,却把她配给自己的表弟,觉得这是天作之合,殊不知已经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夜扣禁门
兖国公主为了皇家的利益下嫁李玮,可能一开始就是不情愿的。因为李玮虽然有一副艺术家的灵魂,但是躯壳并不匹配,甚至有些寒酸。史书上明白记载,李玮“貎陋性朴”。这是不是说李玮很丑?想来应该不会太丑,否则仁宗也不会舍得把女儿嫁给他。只能说李玮的相貌很一般,性格也拘谨,总之,与潇洒风流不沾边。所以,兖国公主非常不喜欢这个驸马。看来,公主和她的爹爹仁宗一样,是个标准的颜控。
好好色是人之常情,但又是很多婚姻不幸福的起因。对于皇帝爹爹赐给自己的这个驸马,兖国公主是半只眼也瞧不上。史书上记载:“公主常佣奴视之。”并且连带轻视驸马的家人。此时的李家,家主李用和已去世多年,李玮与兄长李璋分府别居,平日里自家过自家日子,倒是井水不犯河水,可是李玮的生母杨氏随同李玮、公主共同生活,婆媳关系十分不融洽,这使得公主和李玮本就不和谐的夫妻关系生出更多变数来。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在驸马与公主夫妻交恶的过程中,公主身边亲信没能正面引导和规劝,甚至还挑拨离间、推波助澜。兖国公主出降时,身边跟了一大帮随侍人员,包括公主的乳母韩氏和以梁全一、梁怀吉、张承照为首的一批内臣。史书上“韩氏复相离间”“为家监梁怀吉、张承照所间”一类的说法反映出这些人在公主的婚姻生活中发挥了很坏的作用,当然这也可能是曲笔,目的是通过卸责于下人,减轻公主的责任。但是不管怎么说,公主的夫妻、婆媳矛盾的集中爆发确实与梁怀吉等人有关。
嘉祐五年(1060)九月的某天晚上,秋凉初上,公主与家监梁怀吉于月下对酌。(驸马哪里去了?)这情景有没有让你联想到《清平乐》中徽柔与怀吉的两小无猜、心心相印?那画面一定是极美的。按照司马光的说法,“梁怀吉等给事公主阁内,公主爱之”(《孤城闭》的艺术灵感可能即来源于此)。这种爱未必是男女之爱,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基于长期陪伴而形成的类似于亲情的感情。不过,在婆婆杨氏眼中,那场面一定是非常刺眼的,可又惮于公主之尊,不敢发作,只能忍气吞声,在一边探头探脑地偷窥。公主对杨氏的偷窥行为非常恼怒,当场痛打了杨氏一顿,打完还不解气,连夜敲开皇城门,跑到皇帝爹爹那里去告状。
看到宝贝女儿受了委屈,仁宗也很生气。事后,李玮“惶恐自劾”,狠作自我检讨。于是,仁宗下旨,将驸马都尉、安州观察使李玮降为和州防御使,让他到外地任官。转过天来,仁宗冷静下来,免去了对李玮降官的处罚,只罚铜三十斤,仍然将其留在京师。
然而,风波并没有就此止息。兖国公主殴打婆母、夜闯禁门的新闻不胫而走,朝野间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言官们的弹章很快就递到了仁宗的御前,公主是皇帝的心头肉,不好直接弹劾,他们把炮火对准了皇城门的守卫和公主府的内臣。右正言王陶、知谏院唐介、殿中侍御史吕诲等人要求追究皇城、宫殿内外监门使臣守卫不严之责,仁宗没有搭理。言官们还指出,公主府的内臣数量过多,其中颇有不守规矩仪制者,对公主的失范,这些内臣难辞其咎。仁宗“不欲深究其罪”,只是下旨,缩减公主府内臣的人员编制,重新选拔一批老成持重的内臣到公主府任事,而之前的那批通通被换掉,梁怀吉被“分流”到西京洒扫班。此外,公主乳母韩氏也被查出来有监守自盗的行为,被削去了“昌黎郡君”的封号。
身边亲信被驱逐后,公主的精神状态一落千丈,一会儿要自尽,一会儿要纵火焚屋,显是受了极大的刺激。仁宗不忍心,于是将梁怀吉等人又召回公主府。谏官杨畋、司马光、龚鼎臣等人坚决反对仁宗的召回决定。司马光不客气地指出,“公主生于深宫,年齿幼稚,不更傅姆之严,未知失得之理”,所以,应当严格遴选公主身边的侍从,而梁怀吉等人恰是反面的样板,“此二人(当指梁怀吉、张承照)向在主第,罪恶山积,当伏重诛”。他还举太宗处罚兖王乳母和齐国大长公主(仁宗姑母,剧中的魏国大长公主)谦恭率礼的故事,建议“陛下教子,以太宗为法,公主事夫,以献穆(指齐国大长公主)为法”,仁宗不予理会。
令人担忧的是,公主对驸马李玮始终爱不起来,甚至可以说充满了厌恶。夜扣宫门事件之后,公主虽然又回到了公主府,但是动不动就要寻死觅活,夫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公主的生母苗贤妃(剧中的苗娘子)想结束公主这段不死不活的婚姻,于是与宫中好姐妹俞充仪(剧中的俞婕妤)商量,派遣内臣王务滋到驸马府任总管,实则是伺察驸马的过错,可是李玮行事谨慎,始终没让王务滋抓到把柄。王务滋没辙,向苗、俞二妃建议:“只要皇帝下一道圣旨,务滋拿一杯卮酒(指毒酒)就把这事儿了结了。”苗、俞请示仁宗,仁宗不置可否。过了几天,仁宗和曹皇后同坐,俞充仪又提出了这个建议,结果被曹皇后否决。
就这样折腾了一年多,至嘉祐七年(1062)二月,仁宗终于决定让公主和驸马正式分居,兖国公主搬入禁中,驸马都尉李玮知卫州,内臣梁怀吉勒归内侍省。李玮之兄李璋上书仁宗,请求解除李玮和公主的婚姻关系,仁宗有意批准。在此过程中,朝臣颇有异议。御史傅尧俞上疏说:“主恃爱薄其夫,陛下为逐玮而还隶臣,甚悖礼,为四方笑,后何以诲诸女乎?”司马光亦上书:“玮既蒙斥,公主亦不得无罪。”为了平息物议,仁宗于三月下诏,将公主的封号由兖国降为沂国,改李玮为建州观察使,免去他驸马都尉的头衔,依旧知卫州,还多次派人犒赏李氏,赐李玮金二百两,抚慰他说:“凡人富贵,亦不必为主婿也。”
公主之死
“强扭的瓜不甜”,在今天,这已是广为大众所认可的婚恋原则。可是,在传统社会,人们对这一朴素的原理似乎还没有充分的体认。以现代视角来看,福康公主和李玮的婚姻中,谁对谁错可以不论,既已不相安谐,离婚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一种解脱,未尝不是很好的选择。然而,在仁宗这个慈父的心中,爱女的婚姻失败始终是需要尽力弥补的遗憾。于是,在预感自己时日无多之际,仁宗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让兖国公主和李玮复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七载:
(嘉祐七年)十一月己巳,进封沂国公主为岐国公主,建州观察使、知卫州李玮改安州观察使,复为驸马都尉。
转过年来的三月,仁宗就驾崩了,而岐国公主则重新陷入婚姻的泥沼。此后的几年,婚姻的痛苦一如往常,而慈父不在,公主再没有了御前哭诉的机会,就这样在煎熬和苦闷中早早地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正月九日,楚国长公主(神宗即位后,封岐国公主为楚国大长公主)薨,享年三十三岁。据说,临终前公主的衣服、饮食、药物多有短缺,似乎受到了李玮的虐待(有网友认为李玮没有能力和胆量虐待公主,顶多是对公主不够关心而已),以致衣服上长了虱子,由于没有下人侍奉,自己动手取炭生火,还烫伤了脸。神宗痛惜姑母早亡和晚景的凄凉,以“奉主无状”为由将李玮贬为郴州团练使、陈州安置。不过,李玮后来遇赦还朝,一直活到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
作为世间最尊贵的女子,公主为何得不到想要的幸福,却要被困在婚姻的牢笼中苦苦挣扎?不少人受小说的影响,认为是砸缸的司马光“砸”了公主的幸福。对此,司马光是不会认账的,在司马光等士大夫看来,“不睦之咎皆由公主”。而在朝廷降封沂国公主的制书中,则将“闺门失欢”的原因归结为“保傅无状”。那么,这场人间悲剧到底谁司其咎?剧中,仁宗有感于姑母魏国大长公主遇人不淑,发誓一定要给女儿徽柔选一个疼她爱她的好丈夫,哪知事与愿违,竟似冥冥中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决定了公主婚姻悲剧的宿命。那么,这股看不见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造成福康公主婚姻不幸的诸多因素中,公主的性格缺陷是不可忽视的主观原因。古语有云:“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此乃物之常理,人情亦然。从史籍所述福康公主殴打婆母、夜扣禁门、以死邀君诸般表现来看,其性格中任性使气、鲁莽冲动、偏执狂躁的成分显而易见,甚至有精神障碍的迹象。当然,此种性格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后天的教育和环境决定的。司马光指责公主“纵恣胸臆,无所畏惮,数违君父之命,陵蔑夫家”,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公主自幼锦衣玉食,颐指气使惯了,很容易养成自私、狭隘的性格,不懂得隐忍和退让,更不懂得“夫为妻纲”的礼法社会中女子守柔的道理。
当然,把板子都打在福康公主身上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即便公主性格柔和,温良恭俭让,很大概率也是不会幸福的。太宗第七女齐国大长公主谦恭知礼、谨守妇道(剧中形象为魏国大长公主,被誉为国朝女子的典范),驸马李遵勖却与公主乳母通奸,公主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佛系心态,最终熬死驸马才得解脱。福康公主的妹妹永寿公主生性节俭自律,“于池台苑囿一无所增饬”,然而驸马曹诗风流放荡,“数以帷簿不谨,浼挠大主,致悒怏成疾”,公主生病了也得不到及时医治,二十四岁就含恨而终。英宗第二女宝安公主性格宽和,事婆母尽孝,中外称贤,驸马王诜却“不矜细行,至与妾奸主旁”,小妾甚至嚣张到当面辱骂公主,最终公主被活活气死,享年仅三十岁。所以,福康公主的性格缺陷并非她婚姻悲剧的根本原因。作为特殊的群体,公主婚姻的不幸福具有某种必然性,背后起作用的是制度和文化的力量。
“三纲五常”起自中国古人对宗法原则的理论概括,却被宣称为与天地同久的“道”。“三纲”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任何一条都是宗法社会特定领域的最高准则,是无可置疑的金规铁律。然而,在特殊情境下,三条原则却可能彼此冲突,出现孰主孰次、孰先孰后的问题。如儿子当了皇帝,老子尚健在,谁当拜谁?这就是君为臣纲和父为子纲在打架。打架的结果是君为臣纲占了上风,于是,刘家太公要为已登九五之尊的刘邦“拥彗(扫帚)却行”,以示臣子之恭。
而君为臣纲和夫为妻纲的参差抵牾则比较明显地体现在公主的婚姻中。公主是皇家血脉,代表了君权,所以,驸马娶公主被称为“尚主”“奉主”,反映出二者君与臣的关系。《明史·礼志九》记载了公主与驸马的婚仪:“驸马黎明于府门外月台四拜,云至三月后,则上堂、上门、上影壁,行礼如前。始视膳于公主前,公主饮食于上,驸马侍立于旁。”总之,驸马应当唯公主马首是瞻,唯公主意志是从。可是另一方面,驸马是丈夫,公主是妻子,二人又当遵循夫唱妇随的原则,公主应该雌伏柔顺,听命于驸马。君为臣纲和夫为妻纲就是两条无形的绳索,捆缚着公主和驸马,向两个相反的方向用力撕扯。富丽堂皇的公主府就是君权和夫权的角斗场,一日百战,势同水火。试问在此情境之下,夫妻关系又如何能够做到和谐融洽、相敬如宾?
当然,如果公主主动退让,不摆出一副主子的架子,对驸马做小伏低,倒是未尝不可以相安无事,齐国大长公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大长公主下嫁李遵勖,按照太宗、真宗定下的规矩,驸马“升行”,以祖为父,公主成了与公公婆婆平辈之人,不必对他们行卑对尊之礼。然而,公主却没管这些规矩,当驸马之父生辰之际,仍然坚持以子媳之礼拜贺,赢得当时上下一片好评。史书上没有明白记载福康公主出降李家后李玮是否升行,但在《清平乐》剧中,确是升行制度激化了婆媳间的矛盾,杨氏摆出家姑的姿态要教训徽柔,徽柔怒斥:“什么家姑?敢与我父母平起平坐?再教阿嫂一遍规矩。”杨氏则回怼:“什么糊涂的规矩,皇家的规矩是多,那能大过天理人伦?”想来,在那样一个时代,杨氏的观点才代表了主流的价值观。于是,到了神宗时,干脆废止了“升行”制度,貌似强大的君权在更为强固的夫权面前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由此可见,从根源上讲,正是皇权和夫权的斗争决定了公主悲剧的宿命。历朝历代那些高傲的公主们,自觉有皇权的加持,便可以挑战夫权,实在是高估了皇权的魔力,也低估了夫权的强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康公主的不幸婚姻故事不仅具有文学审美意义,更具有制度史和文化史的意义。
——选自《故事正义:文学影视中的法律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3月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