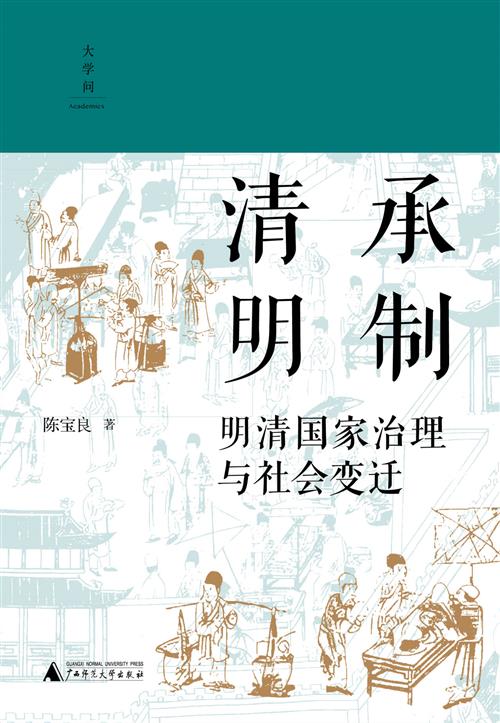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5-02-01
定 价:98.00
作 者:陈宝良 著
责 编:张洁,吴楠楠
图书分类: 中国史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历史/中国史
开本: 32
字数: 400 (千字)
页数: 4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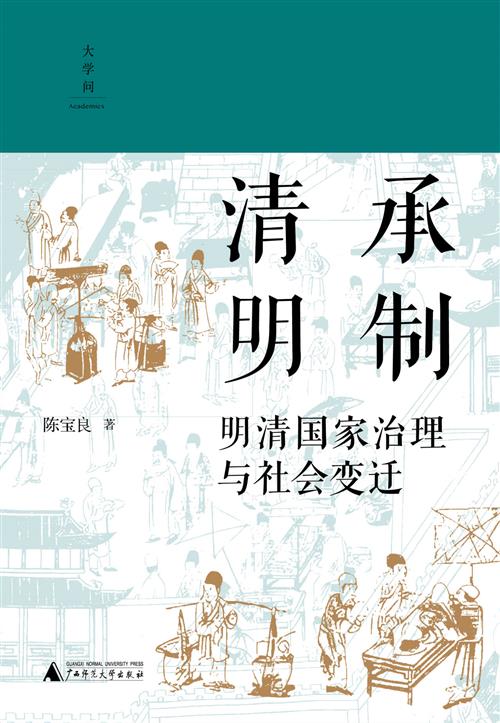
一部从社会史、文化史视角重新解读“清承明制”传统命题的创新之作,全景勾勒明清世俗化社会的全貌,深入考察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的内在继承性。作者着眼于地方治理的繁难、人事制度的琐碎、社会群体的复杂、生活秩序的变动,通过对幕府、镖局、会馆、塾师、侠客化僧人、恋世尼姑等社会组织和群体的细致梳理,多维呈现了明清世风世情的世俗化特征与继承关系。本书结合宏观与微观多重视角,充分挖掘以文证史的潜力,生动的文笔与深刻的认识交相辉映,不仅是一部极具创见的明清社会史新论,更是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通俗性的历史佳作。
陈宝良,1963年生,浙江绍兴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理事。著有《中国流氓史》《明代社会生活史》《狂欢时代:生活在明朝》等。《明代风俗》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入围中国图书评论协会“2017年度中国好书”。
“认真”新说(代自序)
上编 国家治理
第一章 博访利病:访察体制与地方治理
第二章 兴讹造言:谣传与民间信息传播
第三章 “无讼”抑或“好讼”:好讼社会的形成
第四章 阴曹地府:文学中的阴司诉讼
中编 制度溯源
第五章 佐治检吏:幕府人事制度
第六章 护卫重赀:标兵与镖局的起源
第七章 招徕乡人:会馆的起源及其功能演变
第八章 结万为姓:秘密社会与天地会的渊源
下编 社会群体
第九章 富不教书:塾师的生存状态及其形象
第十章 清客帮闲:无赖知识人的形象重构
第十一章 禅武僧侠:佛教僧人的侠客化
第十二章 花禅娼尼:尼姑的恋世情结及其世俗化
后记
“认真”新说(代自序)
何谓“认真”?照着字面直白地去理解,大概应指认得“真”字明白、真切。稍加引申,释其词义,则是说做事必须切实、不苟且。
说者易,行者难。此话大有道理,大抵可以证明“知易行难”的合理性。一个“真”字,并非人人认得清楚,若是认得明白,到头来未必有好果子吃。谓予不信,那么不妨引用一则名叫《认真》的寓言加以印证。这则寓言收录在陆灼所著的《艾子后语》中,故事记载:艾子有两个弟子,一个名通,另一个名执。艾子带着两人去郊游,口渴想讨点酒喝。主人正在读书,指着“真”字说,认得这个字便给三人酒喝。叫执的弟子不假思索,直接说是“真”字,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而那个叫通的弟子见势不妙,灵机一动,就说是“直八”两字,反而得以享用美酒。寓言的作者无疑是为了批评当时社会盛行一时的弊端风气,认真执着不如圆通随和能捡便宜。社会已是如此地是非善恶不辨,自然只有圆通的人方可以得到好处,而执着方正的人反而会吃亏。
“凡事何必认真”。这句民间俗语确乎可说耳熟能详,人人晓得,其风行乃至渗透于人心的程度,实在堪与中国人见面必称“吃了没有”相提并论。“凡事何必认真”的俗语,可以从元代找到证据,《元史·王克敬传》中就已有了“世俗喜言勿认真”的记载,大抵可以作为此句民间俗语的出典。到了清代,该语更是演变成“天下事无非是戏”“何必认真”一类的话头。这是一句乡言,中间还有一个故事出典。当时有一个乡村在演戏,老学究前来看戏,见到庙门上有对句云:“古寺无灯凭月照,山门不锁待云封。”就问僧人道:“只是有门而无山,怎么能称之为山门?”僧人随手一指戏台上说:“台上唱的是《醉打山门》,不但无山,而且无门,他也自管去打。”学究听后大怒:“你敢以我言为戏?”僧人急忙辩解道:“天下事无非是戏,老施主何必认真。”
老实做人,认真做事,必会吃亏。时日一久,上至官场,下及民间,无不养成了诸多病态之风。细加勾勒,大致有下面几种病状:
一曰“苟延”之病,说白了就是图虚名甚或行事苟且之病。说到图虚名,不由让人想起一则名为《猫号》的寓言,收于刘元卿的《贤奕编》中。寓言故事的梗概如下:有一位姓齐的宦官,家中养有一猫,自以为奇,向众人宣称是“虎猫”。其中一位门客道:“虎诚然威猛,不如龙之神灵莫测,请更名为‘龙猫’。”另一位门客则说:“龙固然神于虎,龙升天必须凭借浮云,云岂不是比龙更高尚?不如改名为‘云猫’。”又有一位门客说:“云霭蔽天,风倏散之,云显然不如风,还是更名‘风猫’为好。”又有门客说:“大风飙起之时,唯有土墙作为屏障,才可以遮蔽狂风,不如更名为‘墙猫’。”最后一位门客说:“土墙不管何等牢固,只要老鼠打了洞,墙就会坍圮,还是更名‘鼠猫’最好。”门客帮闲的献媚、凑趣伎俩,显然已是极尽能事。其丑态固可置而不论。说到底,猫的职责不过是捕鼠而已,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捕到老鼠,就是好猫。进而言之,猫如果失去了它捕鼠的本真,无论是取名“虎猫”“龙猫”,还是取名“云猫”“风猫”,即使名头何等响亮,也不过是一个虚名罢了。这则寓言以猫之起名为核心,犹如剥笋,层层向里,又如同逻辑学中的归谬法一般,逐次揭示出图虚名、搞浮夸者之滑稽可笑,进而告诫人们,要务求实际,力戒虚名。
至于行事苟且,实则做事缺乏担当精神。寓言譬喻,最为确当,也最能针砭时弊,那就再借用一次罢。明朝人江盈科所著《雪涛小说》中有一篇《任事》,包括两则故事。第一则故事记一位脚上生疮的人,他痛不可忍,对家人说:“你替我在墙壁上凿一个洞。”洞凿成后,他就将脚伸到洞中,深入邻家尺许。家人不解,就问:“这是什么意思?”他答道:“让它去邻家痛,再无关我事。”第二则故事记一位医生,自称擅长外科。有位裨将从阵上返回,身中流矢,矢深入膜内,就请这位医生治疗。医生持刀并剪,剪去矢管,跪而请谢。裨将责问:“箭镞深入膜内,必须快治。”医生答道:“此内科事,不关我事!”这两则寓言故事,各有侧重,前者是以邻为壑,后者是敷衍塞责。说到底,还是一种不敢任事、不愿担当的陋习。当事官员,见事不可为,一味因循苟安,以遗来者,也就如同委痛于邻家、推责于内科之举。
二曰“软熟”之病,借此博取“持重博大”的美名。儒家有“无欲则刚”之说,实在道出了为人处世的底蕴。人一旦有了欲望,就难免变得“软熟”了。很多官员,为了维持自己的官位乃至富贵,对时政的弊病就不闻不问,表面上是通过谦卑逊顺之态,维持自己的一种“体面”,并借此博取一种好的名声,实际上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富贵。这也怪不得他们,因为他们一官半职的得来实在不易。很多官员,起家并非一帆风顺,一路读书过来,过的都是淡薄的生活,而后才得以占据官位。不过,一旦位高权重,就不再淡薄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利益盈满的“膻路”,会有无数好处的诱惑。为了保持这条膻路一路畅通,保证自己安全退休,他们不得不变得小心翼翼,不再敢于直言相谏,甚至面对下属官员也会装出一副谦卑逊顺之态。如此做官,一如嚼甘蔗,既思据有官位之甘甜,又思获取官位之苦辛,富贵功名,愈是咀嚼,愈是有味。
闲来翻阅史书,看到宋朝人曾有愤激之言,道:“举朝皆须眉妇人。”当时并不以此为然,认为不免有些夸大其词。今日看来,反而有诚哉斯言之叹。有些人一方面悍然不顾,肆无忌惮,倒还像个男儿身;另一方面,则又委婉听从,人哭也哭,人笑也笑,人贪也贪,毕竟更像一个妇人。《易》云:君子以独立不惧。人能做到独立,自然不妨与妇人杂居。然世风毕竟容他不得,所以才有了后面的一句,即“遁世无闷”,借此以示自我独立。同是病态,若病在率直粗放、顾无别肠,还是容易医治。若是病在细软谦卑、顾多别肠,就不免病入膏肓,即使华佗、仲景再生,也很难下一针砭。
三曰“奔竞”之病,自守恬退之人已是寥若晨星。俗语有云: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名利之必争,其来已久,不必有吠雪之怪。让人感到震惊的是,昔之争名争利,大多在于昏夜,多少还有些羞耻之心;今之争名争利,则多发生在白昼,毫无避人之想。大文豪苏东坡在论及宋朝官场时,曾有一官而三人共之之叹,即居官者一人,已经去职者一人,而伺机想取而代之者又一人。人之争名争利,古今莫不皆然。虽说世上并不缺少恬淡无营的君子,但十人奔竞而一人恬退的世况,难免会让恬退者不能自立。其可怕的结果,就是官愈多,而事愈不治。究其原因,世风躁竞,难辞其咎。
奔竞之风演至极致,自然会出现抢官之风。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历史上确实曾经上演过如此的一幕。明代的京师官场就有“讲抢嚷”嘲讽之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时官员流行“讲”“抢”“嚷”三部曲:讲者,求情之谓。若是一官有缺,就各趋权势之门,讲论自己按年资或体例应得此官之故。抢者,争夺之谓。先去求情者笃定可补此缺,那么后来者或许不能得到此缺,于是无不争先趋走,争夺此缺。嚷者,流言诽谤之谓。一旦讲情、争夺不得,就不免流于喧嚷腾谤,广布流言,加以诽谤。
如此弊端士风,一旦形成,就会通过渐移暗转,慢慢使读书人的筋骨化为木石而不自觉,如同“中蛊”一般;即使心有所觉,但呼吸之地已为所制,心可得知,而声不能出,有若“中魇”一般。两者相合,终成一个末法世界。可见,官场病的病根,终究还是那些官员只是满足于“做官”,而不是“做人”,更不愿“做事”。就此而论,老实做人、认真做事,倒是称得上是治疗官场病的一剂良方。
如何认真做事?历史上同样不乏认真做事的人,大可成为今人学习的榜样。早在元代,王克敬就已明确宣称:临事不认真,终非尽忠之道。抛开传统读书人的忠君意识不言,从这句话还可以读出另外一层涵义,即临事不认真,终非尽职做事之道。王克敬之后,明代中期有一位朱英,曾将他的诗集命名为《认真子集》,显然也是有所意属,体现了那种为人、为官讲究认真的精神。继朱英之后,吕坤、鹿善继等人,对认真之说均有别开生面的解读。
明朝有一位官员,曾经批评他人道:“渠只把天下事认真做,安得不败?”言外之意,做事不必认真,否则必败无疑。这句话至少可以说明,明哲保身的苟延之风已经弥漫明代整个官场。闻听此说,吕坤大感惊讶。他认为,天下之事,即使认真去做,尚未必做得好,假若只在假借面目上做工夫,成甚道理?在他看来,天下事只要认真去做,还有什么可说?当今最大的病痛,正患凡事不肯认真去做。由此看来,天下之事,只怕认不真,这才导致人们依违观望,看人家的言为行止而定。凡人做事,先要看到事后的功业,又要体恤事前的议论,事成之后,众人自然噤口。即或万一事情不成,但只要自己所做的事,是当下应该做的,就不必去计较成败得失。
做事认真,至鹿善继而集其大成,这从他将自己的奏疏集取名《认真草》可以窥见一二。明末人孙承宗在论定鹿善继其人时,称其众推独任,众趋独辞,惟是一副真肝胆;立身只为“公家”,而不敢有“私”;为国求“真才”,做“真事”。大抵把握了鹿善继为人处世的真精神,洵为不刊之论。这可以拿鹿善继自己的说法加以印证。他以“真”“痴”二字当作自己做事的标帜:真者,是空而无私;痴者,则是顽而不解私。真是为了与赝有所区别,而认真者则又有别于赝者之笑真。鹿善继有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就是犯得一分难,便干得一分事;拼得一分官,便做得一分人。这就是说,为了干事,就必须知难而上;而为了做一个真正的人,甚至宁可放弃官爵。换言之,他做事的原则,就是“置办”一副真实心肠,先为国家,后为自己。
认真做事之人,自然会被视为愚钝甚或痴愚之人。自古以来,民间形象地称巧者为“乖觉”或“乖角”之人。“乖觉”一词,按照叶盛在《水东日记》的解释,就是“警悟有局干”。这或许尚属中性的说法。不过在后世的传衍中,所谓“乖”,已经相当于“黠”,而“黠”并非美德。凡是乖觉之人,必定与人背离。譬如乖觉之人与人相约一同谏君,劾奸死难,但随后稍计利害,违背原先的诺言,以苟全自己的性命,反称谏君者为“痴”。所谓乖觉之人的真面目,已是一览无余。
随之而来者,则是有人以愚钝自居,甚或倡导一种“愚愚”精神。明代名将戚继光自号“愚愚子”,可谓这方面的典范。这一别号的出典,基于戚继光将人分为三类:一是所谓“上智”之人,其人只是厚积金帛,广殖田宅,贪求功名,保得首领,与时迁移而已;二是“下愚”之人,其人只知竭尽心力,整治本职之事,一心尽自己的本分,为国忘家,而将利钝付之他人,或许因为时运不济,生前难以拜相封侯,但死后必能祀于文庙、武庙;三是“愚而又愚”之人,其人尽管面对谋不合、道不行的时势,还是愿意竭尽自己有限的精力,去忠于应尽的职守,甚至陷阱在前,斧钺不惧。言下之意,戚继光还是以“愚愚”自期。
若是追溯其思想的渊源,无论是老实做人,还是认真做事,事实上有两大精神源泉:一是来自《中庸》的“诚”;二是出自佛教的慈悲、献身精神。当然,所谓认真做事,其实就是一种大无畏的担当精神,也是英雄实心任事的精神。从古迄今,豪杰精神一脉相承,真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如伊尹放逐太甲,就是一心把商家天下挑在自己肩上,任劳任怨,何尝有些小的顾虑,一有顾虑,就任事不成;诸葛亮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奉为自己做事的信条,不去顾及成败利钝;范仲淹坦言,自己只管做应该做的事,至于能否成功则并不取决于自己,无暇考虑;韩琦认为人臣应该尽力事君,甚至死生以之,决不可因事先担忧事情不济,辍而不为;李纲更是直言,事君之道,只可考虑进退之节,不必计较其中的祸患;戚继光主张,“鞠躬尽瘁,夕死何憾”,追求的并非肉体的永生,而是精神的长存;鹿善继更是别具一副真肝胆,不分炎冷,不计险夷,甚至敢于辞夷就险,把举世莫胜的重任担在自己的肩上。
如此种种,都是不顾利害、不计个人得失、正好契合于儒学的真精神。在英雄不再且儒家真精神几已沦丧殆尽的当代社会,唯有老实做人、认真做事者,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豪杰,方可使儒学真精神得以理性地回归。为官如是,治学何尝不是如是。
——摘自陈宝良:《清承明制: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2月
陈宝良教授的《清承明制: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一书,是一部别开生面、另辟蹊径的学术探索性著作。全书以过往学界绝少涉及的社会政治生态、官场习气、世间百态的独特视野,深入考察明清时期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极大地丰富了明清历史研究的内涵与外延。陈宝良教授是研究明清时期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大家,此书更是富有创新探索性的最新成果,可以说在同领域的研究著作中,无出其右者,令人敬佩。
——厦门大学教授、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陈支平
明清社会史名家陈宝良教授的新著中,有关明清访察体制与地方治理的论述,很好诠释了明清国家治理的特色;对于明清幕府人事制度的溯源,有效证明了清承明制问题。新著所论“社会变迁”,包括社会治理方面的谣传与民间信息传播、“好讼”社会的形成,社会组织方面的标兵与镖局的起源、会馆的起源及其功能演变,社会群体方面的塾师、清客帮闲的形象问题,所论或为人所忽视,或出人意表,且不乏深刻。这是一部多有创见且很有可读性的明清社会史新论。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常建华
作者重视的明清之际的历史变化,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而持久的朝代过渡;清承明制的论说,虽属宏观的认知,但从生活细节与制度实践的层面重新予以考察,则又别具新意,举凡地方治理的繁难、人事制度的琐碎、社会群体的复杂、生活秩序的变动等,皆能钩稽大量史料,力求论从史出,立论允当。不仅如此,全书文笔生动,考述精详,条分缕析,既具极高的学术价值,也富现实需求的社会价值,是目前学术界有关明清国家社会治理最精彩的论著。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冯贤亮
对于治史者而言,“清承明制”这一跨朝代论述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学界共识。前贤多从政治史或国家层面着眼,强调清王朝统治中中原元素的主导地位和清代君主专制的进一步加强。与之不同,本书更多地关注社会层面,关注多种组织、群体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对访察体制、幕府人事制度、塾师的生存状态及其形象、僧人的侠客化、尼姑的恋世情结等进行专题梳理,既明确了这些个案在明清两代的具体演变情况,又揭示了两代世风世情的继承关系,为“清承明制”命题提供了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多维阐释。
另外,借助文学作品中的描述,我们得以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人,他们或是蒙冤受屈之人,或是清贫度日的书生,或是尚侠义的僧人……同处明清世情世风之下,不同的遭际似乎指向同一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大潮之下,社会景象日益多元的同时,社会风气也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世俗化转变。
阴司诉讼:重建法律公正的有力途径?
明初人瞿佑所作文言小说《剪灯新话》中《令狐生冥梦录》一则,记载了一位刚直之士令狐譔至阴司打官司的故事。
小说记道,令狐譔生平不信神灵,傲诞自得。凡是有人谈及鬼神变化、幽冥果报之事,他就大言加以驳斥。他有一位近邻乌老,家资巨富,尚贪求不止,而且“敢为不义,凶恶著闻”。一天,乌老病卒,死后三日再次苏醒。有人问他死而复生的原因,乌老则说:“吾殁之后,家人广为佛事,多焚楮币,冥官喜之,因是得还。”令狐譔听说之后,尤感不平,感叹道:“始吾谓世间贪官污吏受财曲法,富者纳贿而得全,贫者无赀而抵罪,岂意冥府乃更甚焉!”于是愤而作诗一首,道:“一陌金钱便返魂,公私随处可通门!鬼神有德开生路,日月无光照覆盆。贫者何缘蒙佛力?富家容易受天恩。早知善恶都无报,多积黄金遗子孙!”诗成之后的当天晚上,令狐譔在梦中被勾摄到阴司,后遭逼供。阴司据以为罪证者,即为令狐譔所撰诗作中“一陌金钱便返魂,公私随处可通门”一句。为此,令狐譔作了供辩。在辩状中,令狐譔本来相信,“地府深而十殿是列,立锉烧舂磨之狱,具轮回报应之科,使为善者劝而益勤,为恶者惩而知戒,可谓法之至密,道之至公”。换言之,地府之说的存在,理应改变“以强凌弱,恃富欺贫”的社会现实,使“上不孝于君亲,下不睦于宗党”,以及“贪财悖义,见利忘恩”之徒,在阴曹地府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事实并非如此,即地府“威令所行,既前瞻而后仰;聪明所及,反小察而大遗。贫者入狱而受殃,富者转而免罪。惟取伤弓之鸟,每漏吞舟之鱼”。地府号称公正,其赏罚之条,不宜如是。正因为此,令狐譔才大胆提出质疑。地府中的明法王览毕令狐譔的辩状,批道:“令狐譔持令颇正,难以罪加,秉志不回,非可威屈。今观所陈,实为有理,可特放还,以彰遗直。”仍下令复追乌老,置之于狱。这则故事大抵反映了下面一个事实,即地府中同样存在不公正。
尽管如此,明清时期的民间百姓还是相信,地府可以为他们的冤屈主持公道,所以才有大量阴司官司的事例出现。这种事例,同样在史料中可以得到印证。如明末的法律文书显示,原籍江西的医人萧德魁,住在广东已经多年,并与王遡琴为邻居。德魁家中有一使婢育英,因被遡琴挑逗而与之产生奸情。为此,萧德魁气愤不过,自认是“异乡孤踪,难与地方人角”,于是就选择了“不声之官而诉之神”,采用在城隍庙贴黄纸的方法,希望能得到神的公正待遇。这应该说是一种“情亦窘矣”的无奈之举,但也反映了民间百姓对神灵的崇奉。
清朝人李西桥在为明代无名氏所撰小说《包青天奇案》所作之序中,就包公判案进入公案小说的原因作了相当详细的分析。首先,他强调了听讼之难。他说:“明镜当空,物无不照,片言可折狱也。然理虽一致,事有万变,听讼者于情伪百出之际,而欲明察秋毫,难矣。”其次,正因为听讼或者说判案如此之难,所以才出现了包公这样的人物,甚至进入民间的传说或小说之中,以至千古之下,对包公其人闻风敬畏,遇到无头没影之案,即说“非包爷不能决”!进而言之,民间将包公说成是“阎罗主”,所以京城有“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之说。第三,清朝人明白地知道,所谓阴司,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之事。那么,为何民间将包公称为阎罗王?正是因为包公刚毅无私,所以民间才以“神明况之”。李西桥进一步提出:“夫人能如包公之公,则亦必能如包公之明;倘不存一毫正直之气节,左瞻右顾,私意在胸中,明安在哉!”可见,还是公则明的道理。
至于阴司诉讼,按照民间的传说,其审理诉讼的程序也有一个等级层次,一般是先向当地的“社公”控诉。若是社公无法解决,则必须上诉到东岳行宫。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为我们详细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小说卷16记载了下面这样一件因为经济纠纷而引发的诉讼案件。
案件的原告方叫陈祈,是一个狠心不守分之人。被告方是一位富民,叫毛烈,平日贪奸不义,一味欺心,设谋诈害。两人一向交好。两人之交恶乃至诉诸公堂主要源于经济纠纷。原来陈祈家较为富裕,尚有三个兄弟。他害怕将来财产四人平分,就起了贪心,打算多占家产。为此,他就与毛烈商量。毛烈于是替他出主意,让他将好的田产暂且出典给他,就可以避免将来被均分。为此,两人就立下了文书,并请人做中间人,将田立券典给毛烈。考虑到这些田产将来都要取赎,所以典钱只收三分之一。
陈祈在将家产分割以后,就拿出赎田的银价,前来向毛烈取赎。拿出赎银后,毛烈借故原券不在,再过几日交还给陈祈。陈祈要求毛烈给一份收据,但毛烈还是百般搪塞。因为两人平日交好,陈祈就有点托大,不再要求收据。
过了两日,毛烈不再承认有典田之事。为此,陈祈将毛烈告到知县衙门。因知县得了毛烈的好处,且陈祈又拿不出典田的原始证据,于是被判败诉,甚至还被说“图赖人”。陈祈在受了冤枉之后,没处“叫撞天屈”,心中气愤,只好宰了一头猪、一只鸡,买了一对鱼、一壶酒,将这些东西拿到社公祠中,跪在社神前,直诉自己冤屈,相信天理昭彰,神目如电,替自己伸冤,在三日内给毛烈一个报应。到了家里,晚上得一梦,梦见社神对他说:“日间所诉,我虽晓得明白,做不得主。你可到东岳行宫诉告,自然得理。”
次日,陈祈写了一张黄纸,捧了一对烛、一股香,径往东岳行宫。陈祈一步一拜,拜上殿去,将心中之事,是长是短,按照在社神前时一样表白了一遍。到了晚上,陈祈又到了东岳行宫,再次诉告。
本来世间的一件经济诉讼案件,于是也就变成了阴间诉讼。其结局则是毛烈因为犯了欺心之事,被索命而死,而陈祈也死去七昼夜,去阴司走了一遭后,回还人间。但陈祈因起先就已“欺心”,所以被罚“阳间受报”,得了心痛之病,不得不将原先欺瞒的家产再分给三个兄弟,最后此病随身,终不脱体,结果还是将家产消耗殆尽。
小说的编者不厌其烦地渲染这一则故事,其目的无非说明诈欺之财不是很好受用的。“阴世比阳世间公道,使不得奸诈,分毫不差池”。毛、陈两人的显报,就是最好的例证。
——摘自陈宝良:《清承明制: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2月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