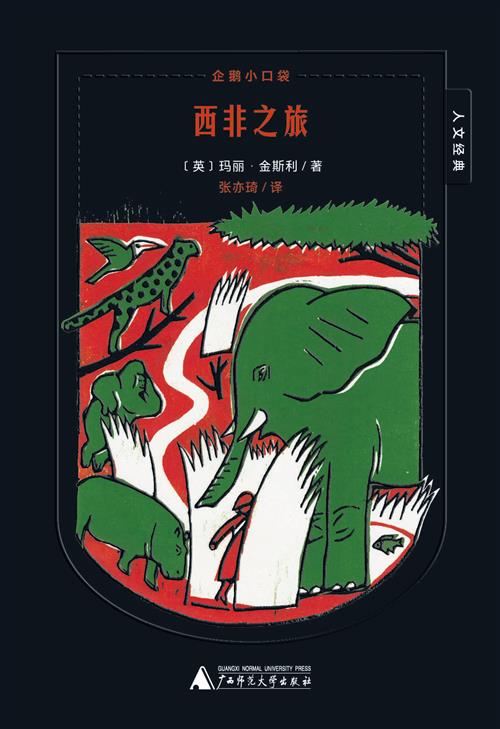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5-02-01
定 价:19.80
作 者:(英)玛丽·金斯利 著;张亦琦 译
责 编:孙才真
图书分类: 11-14岁
读者对象: 8-14岁
上架建议: 童书/11-14岁
开本: 64
字数: 40 (千字)
页数: 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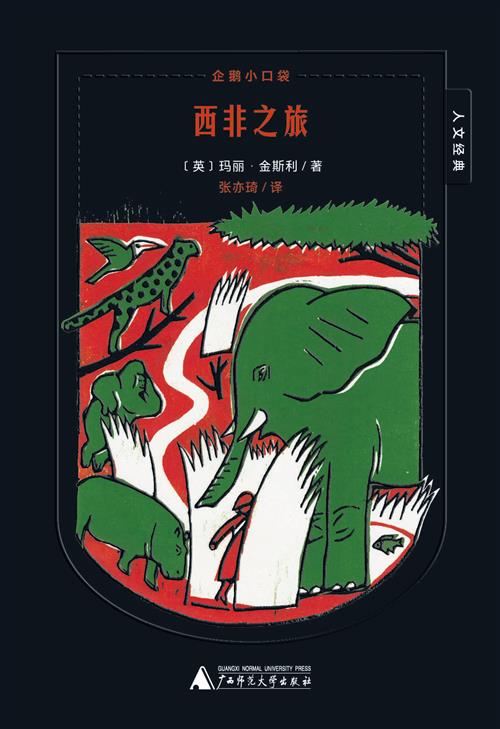
本书摘选自玛丽·金斯利《西非之旅》一书。19世纪的女探险家玛丽·金斯利来到非洲,独自穿越峡谷和沼泽,拜访当地包括食人族在内的部落。她还穿着一件繁复的维多利亚式服装,登上西非的喀麦隆山,成为第一位登上西非最高峰的女性。探险期间,玛丽收入微薄,没有其他资助,因此她沿途做些小生意,出售朗姆酒、衣料和金属鱼钩,换一些象牙和准备交给大英博物馆的鱼。在当地人的带领下,她体验了非洲的民风民俗,观察到了许多动物,包括鳄鱼、河马、猩猩、大象、蛇和非洲豹,记录了危险且不道德的猎象活动。
著者简介
玛丽·金斯利(1862~1900):英国探险家。著有《西非之旅》《西非研究》等。她的作品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英国的帝国主义以及种族论。
译者简介
张亦琦:中国翻译协会会员,长期从事英语、德语文学翻译工作。已出版译作《大地之上》等。
导读学者:
程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助理教授
《西非之旅》导读 5
河马的盛宴 15
五头大猩猩 64
猎象 92
与豹相争 100
译后记 109
《西非之旅》导读
程莹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助理教授)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小书是一本经典的非洲研究读物—玛丽·金斯利的《西 非之旅》(Travels in West Africa)的节选本。玛丽金斯利(Mary Kingsley,1862 ? 1900)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女性探险家, 这本书记述了她1893 年到 1895 年间先后两次前往西非旅行的见闻。通过生动而又不 失幽默的笔触,玛丽·金斯利为我们保存了 19 世纪末的非洲自然风貌和生活图景,在植物学、人类学、旅行书写和历史研究等方 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 世纪后半叶是西方殖民扩张的鼎盛时期,欧美强权国家对全世界的控制从 1867 年的 67% 增长至 1914 年的 85%。这 一时期英国在非洲的统治也进入“新帝国主 义”(New Imperialism)阶段,越来越多的 旅行者深入非洲大陆,这其中包括大名鼎鼎 的大卫·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理 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亨利·莫 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等人。 他们塑造的“探险家神话”成为当时十分流 行的一种书写体裁,这些书写进一步丰富了 西方世界有关非洲的自然地理知识,也成为帝国话语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些文本往 往采用种族中心主义的叙述视角,将欧洲人置于理性、启蒙的一方,将非洲置于野蛮、 落后的一方,认为非洲处于更为低级的发展阶段。在“帝国之眼”的视角下,英国人认 为他们对其殖民地的“臣民”负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从而为帝国的进一步扩张构建了 合法性。然而,也有一些声音开始反思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谴责殖民主义的掠夺本质。 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玛丽·金斯利踏上了她的非洲之旅。
玛丽·金斯利于 1862 年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书香门第,她的父亲和叔伯都是当 时有名的作家。虽然由于时代局限,身为女性的玛丽·金斯利从未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 育,但她自幼博览群书,很早就对探险记述和回忆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92 年,也就是玛丽·金斯利 30 岁这一年,她的父母不幸病逝。她随后决定前往西非旅行,为父亲生前未能完成的非洲书籍收集素材。1893 年 8 月,玛丽·金斯利抵达塞拉利昂,她的第一次西非之旅从这里开始,一直抵达今天 安哥拉的罗安达。同年 12 月,她安全返回英国并获得了出版社等相关机构的支持。一年之后,她再度前往非洲,在旅行途中一边收集动植物标本,一边计划写作和出版书籍。如这本小书所示,她那本“日晒雨淋的小记事本”里充满了激动人心的回忆。
科学考察是玛丽·金斯利西非旅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她发现和记录了一些之前不为 欧洲人所知的物种,并且成功登顶非洲西部沿海最高峰喀麦隆火山。除此以外,她对非 洲文化充满好奇,旅途中记录了与不少非洲部族进行贸易和交往的故事。学者杰拉德·卡恩斯(Gerry Kearns)认为玛丽·金斯利是一个人类学家,她书中的一些深度白描和分析清晰地展现了当地人特有的技能和特定的文化价值观。
在本书的记录中,她步入芳族小镇的住处之后,仔细地记录了挂在屋子里的精心制作的、能够赶走毒蛇的“护身符”;在《猎象》一节中,她又留心描写了狩猎过程中当地人的信仰仪式。
值得注意的是,玛丽·金斯利并非完全将这些本土人的信仰划归为低等的原始思维。在她的另外一本书《西非研究》(West African Studies, 1899)中,她曾坦言:“尽管我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但是我却对将拜物 教置于底端而基督教置于顶端的线性演进观保持怀疑。”
今天看来,她在这本书中的叙述仍然有着十分“他者化”甚至是种族主义的视角, 例如她使用“未开化的”(savage)一词形容当地人的发音方式,或以从猿到人的进化论视角对比黑皮肤的当地人与猩猩,凡此种种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都是难以接受的。但她行文中同时也体现出了一定的自省意识,在当时欧洲众多对于异域的旅行书写中,显得十分可贵。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叙述中存在的偏见、问题与矛盾,也应批判性地认识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回到特定的语境审视种族话语产生的复杂历史背景。
在玛丽·金斯利的写作和演讲中,她的许多观点已经开始引导大众反思殖民管理机制、殖民文化。比如,她曾经批评英格兰传教士对非洲当地宗教文化和社会习俗的粗暴干涉,以及英殖民政府在一些西非地区的税收政策。她的著作出版以后,人们时常将玛丽·金斯利的作品与在她同时代的旅行书写和文学作品(例如英国作家康拉德的作品)进行对比,认为她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打破人们对非洲的刻板印象。例如,在这本小书中,玛丽·金斯利曾写道:“当地人对各式各样的森林有七种不同的叫法,而我认为这个数字轻而易举就能拓展到九。”以及:“每个来到这一地区的旅行者都应该认真学习当地用来表达‘我不知道’的每一种说 法—我曾在这里打听过四座村庄跟两条河 流在本地语言中的名字,得到的答案却是以 不同的说法郑重地表达了‘我不知道’这个 意思。”这些描述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出, 非洲人民拥有丰富的语言表达,这片广袤的 大陆内部存在多种多样的差异,这里并不是一片文化荒漠抑或“黑暗之心”。
在《西非之旅》诞生的年代,也就是 19 世纪末的时候,科学、旅行和探险尚被看作是男人的事业。当时,除了一些传教士和政府官员的随行妻子,抵达过西部和中部非洲的女性旅行者少之又少。玛丽·金斯 利只身前往西非的旅途中,几乎没有白人同伴,她也因此时常被问起为何不与她的丈夫同行。虽然出于多种考量,玛丽·金斯利并不认为她自己是一位当时的媒体宣称的“新女性”(New Woman),但女性的身份或许 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她在旅行途中的观察与视角。比如,玛丽·金斯利曾考察一夫多妻制在非洲一些地域存在的原因。她认为,一夫多妻制在当时的部族语境下其实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这种制度可以极大地缓解个体女性所面临的社会与家庭压力。这种观察在后来一些非洲本土的女性主义者的研究论述中也得到了印证。由此可见,在许多层面,玛丽·金斯利都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先驱者。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旅行书写、女性作家或者 19 世纪西非历史和自然风貌感兴趣的读者,必将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她为我们保留下来的那些丰富、驳杂甚至矛盾的瞬间。
★面向青少年的口袋本西方人文经典读物,精选自全球知名出版商企鹅兰登的企鹅经典小黑书,从畅销80年的128种企鹅经典小黑书中精选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人文通识读物。
★19世纪欧洲女性探险家的非洲行记,维多利亚时代的旅行书写。
★邀请北京大学助理教授程莹撰写导读,为青少年读者阅读这套跨越时代之作提供必要的阅读指引。
★增添大量历史背景知识注释,帮助青少年读者理解历史情境,理解文本,获得深入的阅读体验。
★64开口袋本设计,篇幅适中,盈手可握,随身携带,随时阅读。
★知名画家黑眯创作封面版画,封面采用起凸工艺最大程度展现版画质感,提升图书的审美性。
★封底摘取书中金句,精炼展现本书的精神气质,青少年的座右铭之书:
《西非之旅》:上苍之道在这里尤为奇妙,拥有自相矛盾的双重目的,既在于拯救,又在于摧毁。
★导读学者的话
(玛丽·金斯利)行文中同时也体现出了一定的自省意识,在当时欧洲众多对于异域的旅行书写中,显得十分可贵。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叙述中存在的偏见、问题与矛盾,也应批判性地认识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回到特定的语境审视种族话语产生的复杂历史背景。……在许多层面,玛丽·金斯利都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先驱者。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旅行书写、女性作家或者19世纪西非历史和自然风貌感兴趣的读者,必将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她为我们保留下来的那些丰富、驳杂甚至矛盾的瞬间。
——程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助理教授,导读《西非之旅》)
无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