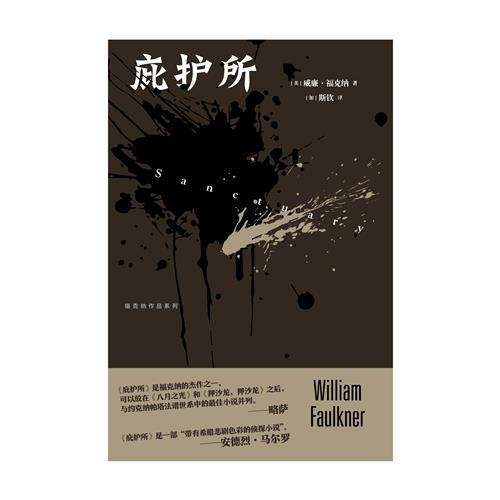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4-10-01
定 价:48.00
作 者:(美)威廉·福克纳 著 ;(加)斯钦 译
责 编:吴义红 ,孟繁强
图书分类: 名家作品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文学·小说
开本: 32
字数: 200 (千字)
页数: 2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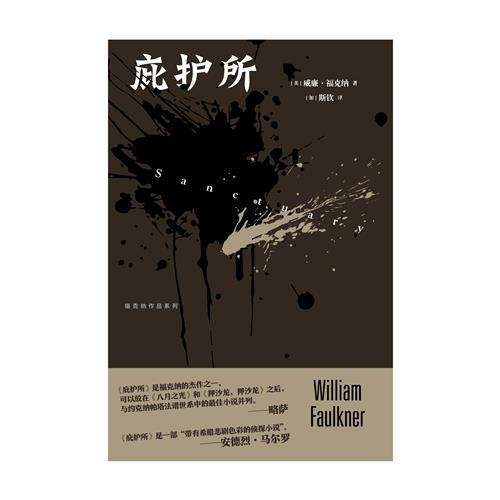
《庇护所》描绘了一幅被败坏了的南方社会的场景,堪称福克纳揭露和抨击美国南方丑恶现实的最有力的作品。小说情节黑暗狂暴,描写20世纪20年代美国禁酒期间,南方小镇有一帮以金鱼眼为首的私酒贩子。女大学生谭波尔被男友抛弃后混到这帮人中,惨遭强奸,后又被金鱼眼送进菲斯城的妓院。金鱼眼杀了人,嫁祸于戈德温。律师说服谭波尔出庭作证,但她已被金鱼眼的变态行为折磨得精神失常。戈德温还是被判死刑,被群众劫出私刑烧死,而出逃的金鱼眼也终因一桩他并未参与的谋杀案而被判死刑。
作者简介: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国文学史上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人物。1949年因“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福克纳以小说创作闻名于世,他为人熟知的诸多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讲述了发生在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故事,被称为“约克纳帕塔法谱系”。主要作品有《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圣殿》《押沙龙,押沙龙!》《去吧,摩西》等。“斯诺普斯三部曲”作为福克纳晚期作品,对“约克纳帕塔法谱系”的主题具有很重要的强化和升华作用。
译者简介:斯钦,先后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以及加拿大的乔治布朗学院(George Brown College)和圣力嘉学院(Seneca College)学习,旅居海外多年。2018年至今翻译出版了《野棕榈》《婚礼的成员》《谁见过那风》《小镇艳阳录》《闲适富人的田园历险记》《伤心咖啡馆之歌》《两种孤寂》等作品。
一 001
二 009
三 019
四 024
五 035
六 039
七 047
八 057
九 070
十 073
十一 076
十二 083
十三 087
十四 091
十五 093
十六 101
十七 112
十八 122
十九 144
二十 161
二十一 169
二十二 180
二十三 186
二十四 202
二十五 218
二十六 234
二十七 240
二十八 255
二十九 262
三十 267
三十一 272
无
《庇护所》是福克纳的杰作之一,可以放在《八月之光》和《押沙龙,押沙龙》之后,与约克纳帕塔法谱系中的最佳小说并列。
——略萨
《庇护所》是一部“带有希腊悲剧色彩的侦探小说”。
——安德烈·马尔罗
如果说《庇护所》从某几个方面说可以算是福克纳最最悲观的小说,它显然也是他最最精彩的作品之一。
、 ——克里斯·布鲁克斯
《庇护所》是一本“直截了当的书”,“有力地证明了福克纳是第一等重要的作家”。
——伦纳德·斯特朗
只有天才才能写出如此残忍、荒谬、几乎令人眩晕的故事,令读者不能自已地沉浸其中。这种技巧正是福克纳的迷人之处。涉猎广泛的读者能从这部作品身上看到希腊悲剧、哥特小说甚至侦探小说的影子。福克纳的说服力如此强大,以至于读者将他的虚构视为真正的生活,在此过程中,我们学会与内心深处的某些幽灵“和平共处”。
一
透过屏障似的灌木,一个长着一双金鱼眼睛的男人看着对面正在喝水的男人——喝水的男人身材削瘦,头上没戴帽子,下身穿一件法兰绒质地的灰色裤子,胳膊上搭着一件粗花呢外套——他蹲在泉眼边儿上,把水捧到嘴边一口一口地喝着。在他旁边,一条若隐若现的小路把大路和泉眼连起来。
泉眼位于一棵山毛榉树的根部,四周长满了藤条、荆棘、柏树和橡胶树,水流从树下流出来,把水底下的沙子冲成漩涡状或者波纹状。从被阳光照耀的树丛里传来三声鸟叫。
喝水的男人一直低着头,水里映出他的脸的模糊映像,很快又被搅散。喝完了他刚要起身,突然看见水里晃动着一个戴草帽的人的脸,忽隐忽现看不清楚。他抬起头朝对面看去:那是一个穿黑色西服的矮个子男人,眼睛鼓鼓的似金鱼,双手插在大衣外套的口袋里,大衣紧紧箍在身上,挽起的裤腿和腿上满是泥点,脚上的鞋也是。那人嘴里斜叼着一根香烟,脸色苍白得像是电灯下的一张脸,没有血色,让人感到诡异,虽然他站在阳光里,周围也很安静,但他头上的草帽和两手揣在大衣口袋里的姿势让人想到印在罐头盒上的暗藏心机的警察。
空气里又传来三声鸟叫,叫声是从那人身后传来的。这地方听到鸟叫本没什么出奇,但因为叫声过后,周围重新归于寂静,反倒衬托出那三声鸟叫似乎有什么深意,把这块地方和它周围隔绝开来。从公路那边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很快又消失了。
喝水的男人没有站起来,蹲着说:“我猜你口袋里有枪。”
长着金鱼眼睛的男人说:“你呢?口袋里装的什么?” 他说话的时候一直用像两团软塌塌的黑色橡胶的眼睛盯着喝水的男人。
喝水的男人一只大衣口袋里装着一个被揉扁的礼帽,另外一只口袋里装着一本书。他抬起一只手,往搭在胳膊上的大衣口袋摸去。“你说哪个口袋?”他问。
“别动!直接告诉我!”
男人不动了,说:“是书。”
“什么书?”
“书就是书!随便拿的一本,我喜欢看书。”
“你看书?”金鱼眼睛的男人说。
男人的手再一次僵在大衣外面。两个人隔着泉水盯着对方,一缕香烟从金鱼眼睛的男人嘴里滑出,从他的脸前飘过,他的一只眼眯缝着,那张脸像是一张被雕刻成左右脸庞挂着两种不同表情的面具。
金鱼眼睛的男人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块脏手帕,扔在自己的脚底下,然后慢慢蹲下坐在上面,他的眼睛始终盯着对面的男人。现在是5月,下午4点钟左右,两个人隔着泉水耗着,两个小时过去了,空气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传来一声鸟叫,好像时钟到点打鸣似的;至少两次,从公路那边传来汽车穿过的声音,每次汽车驶过后都会传来一声鸟叫。
“你知道刚才那是什么鸟叫吗?”蹲在水边的男人说,“不过我猜你只关心那些关在酒店大堂笼子里的鸟和花四块钱买来的放在盘子里已经煮熟的鸟。”金鱼眼睛的男人没有回答,他脸色乌青,没有血色,鹰钩鼻子,下巴几乎没有轮廓。这样的一张脸让人想到被人遗忘在里面烧得很旺的火炉边上的蜡像娃娃,说消失就消失,没人会记起。他胸前挂着一个蜘蛛网似的白金链子。喝水的男人说:“我叫霍拉斯·班鲍,是个律师,我在杰弗生镇长大,现在住在金斯顿,你可以去杰弗生镇打听一下,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不喜欢害人,如果你是酿私酒的 ,那不关我的事,我更不关心你靠酿私酒挣多少钱。我只是路过这里,口渴,喝点水,喝完水继续走我的路,去杰弗生镇。”
金鱼眼看着霍拉斯,不说话。那两只金鱼眼睛让人想到被人用拇指摁了一下的橡胶,形状虽然很快复原,但指纹还是留在了上面。
“我必须天黑前到达杰弗生镇!你不能把我扣在这儿,不让我走。”霍拉斯说。
金鱼眼抬嘴把叼着的香烟吐进水里,还是不说话。
“你不能这样做,难道你非得逼着我和你打一架才放我走?”霍拉斯说。
金鱼眼瞪起眼睛:“你想跑?”
“不想!”
金鱼眼把眼睛从霍拉斯身上移开,说:“很好,那就别跑。”
鸟又叫了几声,霍拉斯在脑子里想着鸟的名字。从公路那里又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太阳越来越往下掉,四周的光线越来越黯淡,金鱼眼从裤兜里掏出一块廉价怀表,看了一眼,然后重新把那块比硬币大不了多少的怀表放进口袋里。
天黑时分,金鱼眼和霍拉斯离开了泉眼。两个人沿着从泉眼附近延伸出来的一条小路一直往前,最后来到一条沙子路上,刚上沙子路不久,就看见前面横着一棵大树,似乎是不久前被人故意砍倒放在路上,他们跨过树继续往前走,这条沙子路的路面只有汽车轮胎的印记,没有任何拉车的牲口的蹄印。金鱼眼一直走在霍拉斯前面,从后面看,紧巴巴的衣服和支棱着的帽子让他看上去像是一个现代派设计师设计的灯座。
走了一段距离后,沙土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盘山路。天马上就要黑了,走在前面的金鱼眼扭头对霍拉斯说:“跟上!”
霍拉斯说:“刚才我们翻山过来多好!”
“翻山?那么些树!你试试!”金鱼眼看着脚下他们刚走出来的那片树林说。夜色中只有他头上的帽子是白的,闪着幽暗的邪恶的微光。往下看去,脚下一片树林,黑黢黢的像一圈儿墨黑的湖水。
天越来越黑。金鱼眼不再走在前面,而是挨着霍拉斯,一边走一边看着四下,很警惕的样子,他的帽子一直在霍拉斯眼睛斜下方晃来晃去。
一只黑色的影子突然从空中俯冲下来,唰地从他们眼前掠过后往斜上方飞去,金鱼眼一惊,身体往后一退,手一把抓住霍拉斯的衣服。“一只猫头鹰也把你吓成这样?!”霍拉斯说,“这里的人把卡罗来纳鹪鹩叫作鱼鸟,对了,鱼鸟,刚才在泉水边我怎么想不起来呢?!”金鱼眼还是紧紧抓住他不放,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去赶鸟,让人想到猫受惊后的举动。“这人有点邪乎,身上有种黑色的味道。”霍拉斯想,“像是包法利夫人临死前嘴角流出的黑血,当人们抬起她的脑袋时,那黑色的血流到她的面纱上……”
两个人继续往前走,很快,他们的前方出现了一座四四方方的大屋子,矗立在低垂的天空底下。
那是一座建在坡上的荒屋,屋子有些年头了,屋子下方是一片由雪松组成的树林。屋子在当地很出名,被叫作老法国人宅子。屋子建于内战之前,位于一座曾经是原始丛林,后来被开发成棉田、花园和草坪的种植园的中心。五十个年头过去了,如今这座屋子被拆得七零八碎,拆下来的东西大部分被人拿去当柴火烧了。传说内战时格兰特将军 攻打维克斯堡经过这里,屋子的主人在老屋附近埋了金子,所以常常有一些住在附近的人揣着发财梦偷偷跑来,想神不知鬼不觉挖出点金子。
他们走到老屋跟前:阳台角落里坐着三个男人,从屋子走廊(走廊前后相通,是开放式的)里泻出来一点微弱的灯光。金鱼眼对着那三个人手往身后一指:“来了个教授!”说完上台阶径直往屋子里走去。他沿着那条前后打通的过道儿 走到最里头靠边儿的房间门口站下,房间里亮着灯,一个穿棉布花裙的女人正在炉火旁忙着,她穿了一双男人穿的短靴,鞋子很旧,没有鞋带,鞋一看就不跟脚,一走动就啪嗒啪嗒地响。听到门口有动静,她扭头看了金鱼眼一眼,然后扭过头继续照看炉子上嗞嗞作响的烤肉。
金鱼眼没有进去,站在门口看着女人的背影,斜扣在脑袋上的帽子几乎遮住了他半边脸。他把手伸进口袋,从烟盒里摸出一根烟,揉揉后放进嘴里,又掏出火柴在大拇指甲盖上擦着,点着烟后对女人说:“我给你领了个人。”
女人翻着炉子上嗞嗞作响的肉,头也不抬地说:“别和我说这些!我不伺候生人!”
“他是个教授!”金鱼眼说。
女人转过身来,手里举着翻肉的夹子说:“是个什么?”在炉子后面光线阴暗的角落里放着一只木头箱子。
“教授!口袋里带着书的教授!”金鱼眼说。
“教授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不知道,我没问,兴许跑到这里来看书。”
“只有他一个人?”
“我在泉眼那儿看见他的。”
“他来找我们买酒?!”
“不知道!我没问。”看到女人不解地看着自己,金鱼眼说,“我会给他找辆卡车把他送到杰弗生镇去。他说他要去杰弗生镇。”
“你告诉我这些干吗?”女人说。
“因为你是这里的厨子,我想让你把他的饭也做上。”
“把他的饭也做上?!”女人背转身,对着炉子说:“我现在还能干什么?每天待在这里,给一帮流氓无赖做饭吃!”
金鱼眼还是站在门口,两手插在兜里,嘴里叼着烟看着女人的背影说:“如果你不想在这儿做饭的话,你可以离开,我带你去孟菲斯,这样你就可以出去卖了。”女人没有理他,金鱼眼又说:“我看你在这儿长胖了,乡下生活让人变懒,我替你保密,不告诉曼纽尔街上的人。”
女人手里抓着翻肉的夹子猛地转过身骂道:“王八蛋!”
“骂得好!我不会和街上的人说鲁比·拉马尔 跑到乡下,穿着李·古德温 的鞋子,给他砍柴烧火做饭。不,我只会告诉他们李·古德温是个有钱的主儿。”
“王八蛋!混账王八蛋!”女人骂道。
“骂得好。”金鱼眼说。这时从阳台传来一阵噌噌的脚步声,金鱼眼扭头看去,一个穿工装裤的小个子男人朝厨房走来,那噌噌的声音是他的两只光脚摩擦地面发出的,他的头发又脏又乱,被太阳晒得焦黄,脸上的胡子短而软,颜色像是弄脏的金子的颜色,两只浅色的眼睛像是和人生气似的瞪着。
那人一进来就对女人说:“他又来找你的事儿了?”
女人没有理他,反问道:“你进来干什么?”进来的人没搭腔,径直往最里面走去,经过金鱼眼时似笑非笑地瞟了一眼,好像他是来听金鱼眼讲笑话,而他自己随时可以哈哈大笑似的。他走起路来步子很沉,像一头步履迟缓的狗熊,脸上始终带着一股似有若无的兴奋劲儿 。当着金鱼眼和女人的面,他从厨房地板上取下一块早已松动的木板,从里面取出一个一加仑的酒瓶,金鱼眼双手拇指钩在马甲口袋里不友好地看着进来的人,嘴里虽然叼着香烟,但不抽(他的嘴里一直叼着那根烟,好像从来没取下来过)。拿到酒后男人转身向门口走去,经过金鱼眼时他又瞟了他一眼,脸上的表情既警觉又好像随时可以乐呵一下。很快,从阳台传来下台阶的脚步声。
金鱼眼说:“对了,我不会告诉曼纽尔街上的人,说鲁比·拉马尔现在给一帮流氓无赖做饭吃。”
“流氓!无赖!”女人说。
二
女人手里托着一盘子肉走进房间。房间里摆着一张两条桌腿的简易餐桌,餐桌桌面由三块木板拼凑而成。桌子旁边坐着金鱼眼、霍拉斯还有刚才去厨房里拿酒的男人。女人把手里的托盘放在桌子上,油灯的光映出一张还算年轻但耷拉着的脸,女人把肉放在桌子上后退到一边,扫了一眼桌子,好像在看还缺什么,随后走到屋子不远的角落里,从一个敞开盖的箱子里拿出一只盘子和一对刀叉,然后走回到桌子旁,把盘子刀叉放在霍拉斯面前,女人的一举一动虽然不慌不忙,但并不轻柔,袖子不时在霍拉斯肩头拂来拂去,霍拉斯抬头看着女人,女人自始至终没有看他。
刀叉摆好后,一个黑人壮年男子扶着一个长胡子的老头儿走进来,在霍拉斯对面坐下。霍拉斯已经知道这人是这里的主人,叫李·古德温。 古德温长了一张饱经风霜的脸,额头两侧的头发已经有些灰白,人比较瘦,下巴上的黑色胡须刚刚遮住皮肤,衣服上沾满了泥点子。他手里扶着的老头儿佝偻着身子,头已经完全秃了,松弛的微微泛红的脸上,一双白内障眼睛像是两块浓痰。老头儿胡子全白了,嘴角四周的胡子沾染了一些脏东西,从始至终老头儿都很安静,脸上挂着小心翼翼讨人怜悯的神色,显然,这是一个生活中已经没有多少欢乐的又瞎又聋的老头儿。老头儿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脏兮兮的手帕,把嘴里的已经被咀嚼得失去了颜色的烟草吐在手帕里,然后重新叠好手帕,放进口袋里。女人把盛着食物的盘子放在老头儿面前,老头儿低下头,花白胡子颤抖着,一只手颤巍巍地伸到盘子上小心翼翼地摸索着,摸到一块肉后他把它放到嘴里,咂着肉汁,女人看见了,打了一下老头儿的手,老头儿把肉放回到盘子里,安静地等着女人给他把盘子里的肉、面包等切成小块,然后又往上面浇了一勺高粱糖汁后慢慢吃了起来。其他人开始大口大口地吃着盘子里的食物,谁也不说话,霍拉斯也把注意力放在自己面前的食物上……老头儿吃完后,古德温问他要不要离开,老头儿点了点头。古德温站起来,搀着老头儿出了房间。
吃完饭后男人们去阳台上聊天。屋子里只留下女人一个人,她收拾好桌子上的碗盘,走到厨房炉灶后面的一个木头箱子前看了一眼,然后坐到桌子旁开始吃东西,吃完后她抽了根烟,抽完烟后清洗剩下的盘子刀叉,再把洗好的盘子刀叉放进柜子里……收拾停当后她沿着过道儿走到门口,站在靠门里的一侧,听着阳台上的动静。从阳台上传来金鱼眼带来的陌生人的说话声。女人心里嘀咕道:“这个傻子,他来这儿干啥……”那声音很容易分辨,叽里咕噜没完没了。女人站在门口里侧想:“他为什么还不走呢?难道他没有女人等着他回家吗?”
“从我房间的窗户里可以看到院子里的葡萄架子,葡萄架子底下有张吊床,冬天的时候,葡萄叶子都掉光了,只剩下吊床孤零零地挂在那里。知道为什么人们用‘她’称呼大自然吗?因为大自然的季节更替就和女人的身体一样。葡萄树一到春天就变得生机勃勃,叶子多得遮住了整个吊床,但绿色里隐藏着躁动不安,到了5月,葡萄叶子把吊床遮得严严实实,从散发着蜡状光泽的花骨朵上开出碎碎密密的小花来。小贝的声音就像黄昏中的野葡萄在低语,我看见她和一个年轻人躲在葡萄树下,我走过去,听见她对那个年轻人说:‘这是霍拉斯。’然后就不说话了,甚至连那个年轻人的名字都没有提 ,比如说:‘霍拉斯,这是路易斯或者保罗或者什么的。’而仅仅说了句‘这是霍拉斯’就完事儿了。她穿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两个人看上去有点拘谨,似乎等不及要走。
“所以今天早晨,不对,应该是四天以前! 因为今天已经星期二 了,她从学校回来那天是星期四,我和她重新提起那个年轻人,我对她说:‘孩子,你说你是在火车上认识的他 ,那这么说他是在铁路工作了。可是他放下工作和你跑到咱们家里来是违法的呀!这和扒掉电线杆上的绝缘线一样,是在做违法的事。’
“她说:‘他和你一样,也是读书人,他在图兰大学念书。’
“我说:‘孩子,可是你们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啊!’
“她说:‘不是火车,是在比火车还不怎么样的地方碰到的!’
“我说:‘我知道。我也去过那种不怎么样的地方。如果是在那种地方认识的人,你怎么可以把他带回家来呢?你们俩只是路人,碰见后你继续走你的路,怎么能和这样的人搅在一起呢 ?’
“贝尔 那天去镇子上了,所以吃晚饭的时候只有我和小贝,我又和她提到了这件事。
“她说:‘你管我这些事情做啥 ?你又不是我父亲。你是——你是——’
“我说:‘是什么?’
“她说:‘你去告诉妈妈吧,告诉她,你就会告状,那去告诉她好了!’
“我说:‘可是孩子,这个人是你刚刚在火车上认识的,你并不了解他,万一他带你去酒店,然后在酒店里把你……噢,如果他那么做,我会杀了他。我接受不了自己的孩子在火车上刚认识一个人就把他带回家里!你让他走!’
“‘您可真会想象,说得像真事儿似的,火车上认识的人就一定是坏人吗?一天到晚就知道管闲事?!’”
女人站在门口听着,心里说:“这人是疯子!” 夜色里继续传来霍拉斯嘟嘟囔囔的说话声。
“……然后她说:‘我不应该那么说你,霍拉斯!’她抱住我给我道歉。我闻到了她身上的香味,她像刚刚被掐下来的花朵,无力地倒在我怀里,脸上都是泪水,可是她不知道她的身后有一面镜子,我的身后也有一面镜子,我从对面的镜子里能够看到她的脸,我看到了她脸上的表情,一种很假的表情。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说人类说到自然时用的是‘她’这个字眼,说到‘生长’却多用‘他’这个字眼,原因就在这里:女性好比葡萄,而男性好比镜子。”
“这人是疯子。”女人站在门口靠里的地方,一边听一边心里嘀咕。
“……我不知道是因为春天到了的缘故,还是因为我是一个43岁的男人,所以才这么郁闷。也许到山坡上躺一会儿烦恼可能就没了——人只有躺在大地上才能放松,平坦而丰饶的大地,刮阵风都能生钱的大地,就好像树上的叶子都可以拿到银行换现钱一样!这片三角洲,整整5000平方英里的土地,被密西西比河淹过后,一马平川,最高的地方也不过是过去印第安人为了发号施令垒起来的几个土堆。
“所以我离开家只是想找个能站在上面发号施令的土堆,而不是因为小贝。你们知道我离开家时带了什么吗?”
“这人是傻子。”女人心里嘀咕道,“古德温不应该留他吃饭。”
“……瞧这个,这手绢是我特意去贝尔房间拿的,上面还沾着她的胭脂。她打扮的时候用它擦掉多余的脂粉,她通常把它放在壁炉台子上的镜子后面。离开时我找到这条手绢,把它塞进行李箱里,然后拿上帽子离开了家。我先搭了一辆卡车,上车后就发现自己一分钱都没带。一路上没有碰到银行,我又不想下车回去带上钱出来,所以这几天我基本上一直是步行,碰到车就央求人家搭我一程,第一天晚上我是在锯木厂的木头堆里睡的,第二天晚上在一个黑人的家里凑合了一晚上,我还在铁路上的火车车厢里睡了一个晚上,我就想找到一个能让我自己说了算的地方待着,仅此而已。如果你娶的是一个姑娘,你和她结婚,然后过日子,可是如果你娶的是一个曾经当过别人老婆的女人 ,说明你对人生通常已经比别人晚了10年,那些早你结婚的人10年前就已经开始过日子。我现在只想找座山坡,在上面躺一会儿……”
“傻子,可怜的傻子!”女人嘀咕出声来。
过了一会儿,从阳台上传来金鱼眼的声音:“喝好了就走!我们得去装货!”等金鱼眼带着那三个人走远后,陌生人踉踉跄跄地站起来,穿过阳台,向门口走来,女人没有走开,身体靠在墙上等着那人走到自己跟前:一个身材削瘦的男人,头发稀疏且不整齐,走起路来带着醉态。女人心说:“他们肯定灌他酒了。”
女人倚着墙站着。霍拉斯说:“你喜欢这儿?为什么要住在这儿呢?你还年轻,你可以回城里住,好好地过你的日子。”
女人靠在墙上,两只胳膊抱在胸前说:“我刚才一直在听,你可真是个可怜人!胆子小,人也傻。”
“嗯,我缺乏勇气,我没有一点勇气,我有男人那东西,可就是……”霍拉斯抬起手,用手背轻轻蹭着女人的面颊,“你还年轻。”女人没有动,霍拉斯的手指划过女人的脸颊,好像在探寻女人的骨头的形状和肌肉的纹理,他喃喃地说:“你的人生还长着呢……你今年多大?不到30?”声音很小,像是在咬耳朵。
“你为什么要离开你老婆?”女人没有躲,胳膊抱在胸前说。
“因为她吃虾。上个星期五我去车站帮她拿虾,虾很重,走在路上,我来回换着手,然后——”
“你每天都要去拿虾吗?”
“不是,只是星期五。但是我这样做已经10年了,从我们结婚起我就每个星期五去车站提虾,然后拿到家里,这个活儿我一做就是10年,可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虾散发出的味道,还有,我可以忍受箱子的沉,但是我忍受不了从箱子里滴滴答答地流出的水,走一路淌一路,我感觉自己好像看着这一路的足迹,从家里出来一直走到车站,然后在铁道旁接过从火车上卸下来的装虾的箱子,再往家走,走上一百步左右就得换换手,我就这样看着自己,脑子里想,也许走在路上我就躺倒了呢?身上散发着虾臭味躺在密西西比州的一条小路上。”
女人“哦”了一声掉过头往屋里走去,她的胳膊一直抱在胸前,霍拉斯跟上去,两个人走进厨房。“你能接受我的处境吗?”进入厨房后女人说,然后她直接走到炉子后面,从里面拉出来一个箱子,两手抱在胸前看着霍拉斯说:“怕老鼠咬,我把他放在这个箱子里。”
“什么?”霍拉斯说,“里面是什么?”霍拉斯说着走过去,看到里面躺着一个婴儿,那婴儿睡着了,看上去也就几个月大,看那孩子的脸色似乎生着病。
“哦,你的儿子?”霍拉斯看着孩子说,女人没说话,看着孩子。从后阳台传来一阵脚步声,女人紧张地用膝盖把箱子顶回到角落里,很快,古德温走了进来,一进来就对霍拉斯说:“安排好了,一会儿汤米会带你去卡车停的地方,然后带你搭车回杰弗生镇。”
等古德温走后,霍拉斯看着女人说:“谢谢你做饭给我吃,也许……”女人的脸色舒缓了许多,但手还是裹在衣襟里,看着霍拉斯。
“也许我可以给你买点什么,让人从杰弗生镇捎过来……”
女人把手从衣襟里抽出来,似乎要给霍拉斯看什么,但很快又缩回去,藏到衣襟后面,说:“我的手……老是泡在洗碗水里……也许你可以给我买根修指甲棍捎过来。”
汤米和霍拉斯从老屋里出来,两个人一前一后沿着那条鲜有人走的小路往山下走去。霍拉斯回头看了一眼他们刚刚出来的那座老屋,它矗立在山坡上,脚下是一大片雪松林,空旷的天空衬托出屋子的年代久远和荒凉。
走到半道儿霍拉斯说:“我们就是在这儿看见那只猫头鹰的。”
“那鸟是不是把他吓得不轻?”走在前面的汤米调侃似的说。
“是的。”
“那家伙是我见过的胆子最小的白人,这个我敢和你打赌,我要撒谎我就是狗!”
“谁的狗?”
“我的!而且是一条老狗,即使想咬人也力不从心。”汤米笑着说。
他们从下坡路来到平地上,霍拉斯穿着鞋的双脚陷进沙子里,发出沙沙的声音。汤米光着脚走在前面,每走一步都有沙子从他的脚趾缝漏下来。他走起路像骡子,拖着脚,但很轻松。
路前方出现一道阴影,霍拉斯走到跟前看清就是来时那棵横在路上的大树,树干上的青绿色树叶还没有掉落。汤米翻过树干,问霍拉斯:“你行吗?”
“没问题。”霍拉斯小心翼翼地翻过树干。
汤米继续走在前面,一边走一边说:“把这棵树撂倒拦在这儿是金鱼眼的主意。他说这么做可以防止外人进来,可是这么做除了让我们几个去卡车那里多走一英里的路外啥用都没有!我和古德温说,这附近的人4年了一直都在他这里买私酒,从来没有人告发过他。不过金鱼眼撂倒这棵树的时候,古德温没有阻止他。金鱼眼那家伙连自己的影子都怕,他要不是那样的人我就是小狗!”
“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也会怕自己的影子。”
汤米压低声音笑了起来。夜色里那条沙子路面越来越黑。霍拉斯觉得那条去泉眼的路好像就在附近,他开始注意四周,看有没有一条小路分出去。
“运酒的卡车谁开?孟菲斯来的人开?”
“嗯,卡车是金鱼眼的。”
“你们为什么要和金鱼眼那伙人打交道呢?他们是孟菲斯人,出现在这里不是很容易引起警察注意?”
“还不是因为和他们打交道能赚到钱!”汤米说,“咱们这里的人都是买散酒,仨瓜俩枣挣不了几个钱,古德温卖给他们酒纯粹是为了看在乡里乡亲的面子上,但他和金鱼眼这样的家伙打交道挣的是大钱!而且酿好一批酒后能马上脱手,来钱也快。”
“哦,换了是我,宁愿饿死也不和金鱼眼那样的人做生意。”
汤米撇撇嘴说:“他也没什么大毛病,除了有点疑神疑鬼。不过,看他那样要是有一天不惹点大事出来,我就不是人。”
“我看也是。”霍拉斯说。
两个人的影子和路边灌木丛的影子融合在了一起,前方出现了一辆卡车,卡车停在路边,沙子路到这儿就没了,往前是一段黏土路,这条路通向公路。卡车后面站着两个抽烟的男人,看到他们来,其中一个人说 :“你们可真够磨蹭的!不等你们的话我们现在至少都走到一半了,说不定已经快到镇子了!我家里有女人等着呢!”
“可不是嘛,等着是等着,只是给你个后背看!”他的同伴说。第一个男人回骂了一句。
“我们没有耽误时间。你们怎么还抽上烟了?干脆点个灯笼得了!一旦警察带着我们找你们,多容易发现你们两个。” 汤米说。
“哼!换了你是不是得坐到树上躲着?!”第一个男人说,汤米压低声音笑了。那两个人掐灭香烟,上了卡车。霍拉斯转过身,向汤米伸出手说:“再见了,很高兴认识了你,请问大名——”
“叫我汤米就行。”汤米脸上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他伸出手,狠狠地似乎很正式地握了一下霍拉斯的手,然后抽出手。
“上车吧,伙计!”驾驶室里人吆喝霍拉斯上车,霍拉斯往车里坐的时候,看见卡车后排座位上放着一把长枪。车沿着崎岖不平的石子路向孟菲斯和杰弗生的方向开去……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