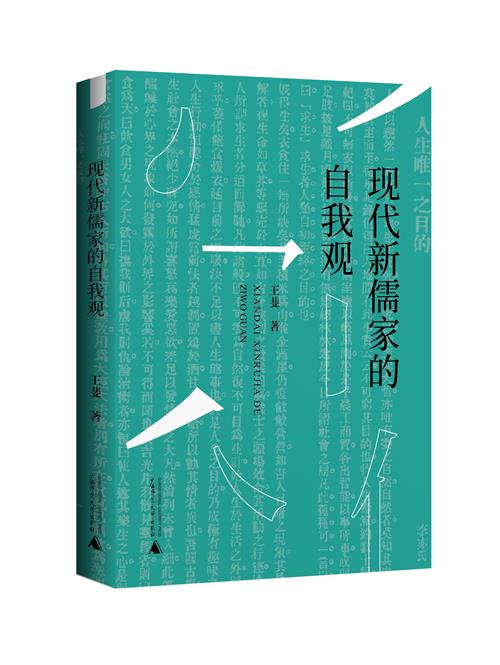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4-06-01
定 价:69.00
作 者:王斐 著
责 编:郭春艳,王晓彤
图书分类: 哲学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哲学/宗教/哲学
开本: 32
字数: 230 (千字)
页数: 3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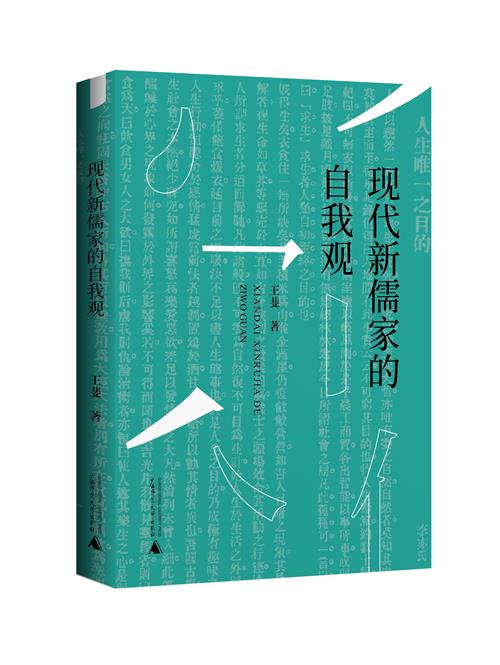
本书稿围绕“自我观”这一话题,探讨了中国近代自我观的转型过程以及现代新儒家的兴起过程。全书由“绪论、中国传统自我观的现代转型、梁漱溟的自我观、张君劢的自我观、熊十力的自我观、结论”等六个部分构成。首先结合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探讨自我问题的相关文献,梳理了中国近代自我观的发展演变过程,理性指出近代个人观、自我观研究中存在的优势和不足;然后结合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梁漱溟、张君劢和熊十力针对“自我观”问题的相关论述,梳理了新儒家的兴起历程,并试图重新发掘其思想史价值。
王斐,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共党史。编著《思政课:抗战史观这样讲》(广西师大出版社,2022年7月)等。
绪论
第一章 中国传统自我观的现代转型
一、传统中国的自我观
二、二十世纪初传统自我观的裂变
三、新文化运动时期感官功利主义个体自我观的形成
四、感官功利主义个体自我观带来的道德困境与时人之对策
第二章 梁漱溟自我观之研究
一、梁漱溟早年思想历程
二、东西文化论争中的自我观重建
三、印度、中国文化的重释与功利主义自我观批判
第三章 “科玄论战”再审视与张君劢自我观之研究
一、“科玄论战”:一段学术史回顾
二、“科学”的三重面向:权势话语、知识论和世界图景
三、科学派人生观之典型:吴稚晖的“科学的人生观”
四、别“自我”与“非我”——张君劢对还原论的抵制
第四章 熊十力自我观之研究
一、“矛盾”的哲学家熊十力
二、熊十力的“证人之学”——理解《新唯识论》的一个视角
三、道德化世界图景与超越性自我观的重建
结论
一、自我观重建与现代新儒家的崛起
二、新儒家对抗虚无主义的两条道路
参考文献
无
1.自我观是什么,为什么要结合近代中国的历史背景讨论自我观?
“个人”的出现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事件,是人们对自我看法的集中体现,在传统中国,个人依附于家族与群体,在践行超越性价值的过程中获得存在价值与生命意义来源,也使自我获得内在深度,而在近代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旧时的伦常秩序与社会结构发生解体,人对自我的看法也发生了巨变,自我意识觉醒、个人主义张扬,对自我观问题的考察会给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提供较为新颖的视角。
2.新儒家派的学者如何看待传统思想与现代?如何重新判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在社会巨变,传统观念被冲击,人们以批判宗族社会、家庭伦理为手段来张扬个性、突出个体自我地位时,新儒家学者坚持在发掘传统中重建自我观,从中国传统“自我”的精神资源中汲取营养,在新环境下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对自我的看法进行梳理,并解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本书中,三位学者就个人与集体、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中尝试通过重构“自我”的方式,回应时代危机。
共5篇书摘,分别为《“科玄论战”与作为权势话语的“科学”》《张君劢与“科玄论战”的发端》《熊十力对“自然”与“自我”的理解》《梁漱溟与新文化派对东西文化理解之异同》《梁漱溟的精神危机》。
近代科学改变了世界,使人类社会快速发展起来,人们承认和敬畏它改造世界的力量,又为它给传统思想和伦理带来的冲击感到恐惧。而在知识分子的论战中,科学逐渐成了一种有利的证明工具,作为权势话语被他们使用。
——编者按
“科玄论战”与作为权势话语的“科学”
“科玄论战”结束后,汪孟邹将散见于各报纸杂志中的论战文字搜集整理成为一书,名之曰《科学与人生观》,并邀陈独秀和胡适为该书各做一篇序言。胡适在序言中写道: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
懂科学、了解科学改造世界力量的人,自然会对其有一种崇敬的态度,而不懂科学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可见“科学”在当时已经具有怎样的权势。胡适在这段文字后接着写道:“直到民国八九年间梁任公先生发表他的《欧游心影录》,‘科学’方才在中国文字里正式受了‘破产’的宣告。”梁启超虽然在此书中反思了“科学”在现代欧洲所造成的种种弊病,甚至认为“一战”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盲目崇拜科学所带来的恶果,但始终没有喊出“科学破产”,所谓“科学破产论”,他借着“欧洲人”的嘴才敢说出来:“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为了避嫌,还加上两行自注:“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因《欧游心影录》而被视为玄学派“始作俑者”的梁启超对待科学,也只是不承认其万能罢了,可见科学权势之盛。至于科学“能”在何处,“不能”在哪里,他在后来论战时的《人生观与科学》一文中写道:“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
不懂科学的人也敬畏科学,同时更懂得利用科学的权势作为修辞策略去论证自己的观点,或以“不科学”打压他人。1918年姚明辉在《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学会杂志》上发表《三从义》和《妇顺说》,企图利用数理逻辑的“科学”方法来证明“三从四德”的道德观。“一,阳数,男也;二,阴数,女也。然无一,焉有二?是二者从一而生。废一则无二矣,此从父之出于数也。”这是在用数字关系来论证“幼从父兄”。“又如一与二相加,则犹男女之相合也,然而不成阴数,是一统二,非二统一,此从夫之出于数也。”这是在用数字关系论证“嫁从夫”。姚氏这种以论证传统伦理道德合理性为目的的“科学”,自然不被新文化派承认,钱玄同评论道:“姚先生这种高深莫测的数学,当然是没有别人懂得的,我们可以不必顾问。只是他所说的‘凡言夫妇平权者,岂礼也欤’一句话,倒是一点不错。不过这个什么‘礼’,已经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给中国‘人’陈列到博物馆里去了。”然而仅仅不过数年时间,曾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高举“科学”大旗的新文化派代表胡适,便被更年轻更激进的左派青年批判为“不科学”了:“实验主义,从哲学的观点上看来,是一种变相的中世纪式的‘烦琐哲学’”,其“表面上带着民主主义和似是而非的激进的科学的面具,然而实际上却是十分保守的、专断的、反动的、违反科学精神的”。这种作为权势话语和修辞策略的“科学”实际上已经同具体的内容相分离,成为一种增强自我说服力与合法性的工具,以及一种“象征符号”,非常接近于郭颖颐所定义的“唯科学主义”:“这样,唯科学主义可被看作是一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一种倾向。”
——选自王斐《现代新儒家的自我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
社会和政治危机伴随着原有文化根基失落时,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的“科学派”和“玄学派”展开了论战。这场论战由张君劢的“人生观”演讲开始,对什么是科学,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分界线在哪里,如何看待科学和自我等问题展开了大讨论。
——编者按
张君劢与“科玄论战”的发端
自1923年3月,张君劢于清华大学发表“人生观”演讲,丁文江于同年4月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予以批驳,张君劢遂撰成答辩文《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以来,“科玄论战”算是正式展开。不久,梁启超发布《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颁布了两条“论战公法”,开始自觉地规范引导论战走向:“第一:我希望问题集中一点,而且针锋相对,剪除枝叶。倘若因一问题引起别问题,宁可别为专篇,更端讨论。第二:我希望措词庄重恳挚,万不可有嘲笑或谩骂语。倘若一方面偶然不检,也希望他方面别要效尤。”随着胡适、任鸿隽、林宰平等愈来愈多的人加入论战,这场论战的规模也逐渐扩大并逐渐呈现出以下三大特点:
其一,因科玄两派皆从知识论角度理解“科学”,因此双方对于科学的定义并无太大分歧,争论焦点始终集中于科学方法的范围之上。胡适相信作为科学知识重要构成的“因果律”与“矛盾律”可以支配人生观:“张君劢翻了二七一十四天的觔[筋]斗,原来始终不曾脱离逻辑先生的一件小小法宝——矛盾律——的笼罩之下!”任鸿隽承认科学有其界限,笼统的思想、未经分析的事实非科学所能支配,但科学的任务就在分析及弄清这些思想与事实,因而“人生观若就是一个笼统的观念,自然不在科学范围以内。若分析起来,有一大部分或全部分,都可以用科学方法去变更或解决”。孙伏园认为科学可以影响但不能支配人生观:“再说,人生观受科学影响与受科学支配并不是一件事。如果人生观是思想方面的东西,那么我替他要求绝对的自由。如果凡属思想都要受科学的支配,那么许多文学美术上极有价值的空想,都要宣告死刑了。如果各个人的人生观都要统一起来,那么思想没有自由发展的余地,人生只是呆板的干燥的单调的动物生活罢了。”梁启超以“中立者”身份颁布“战时国际公法”后不久,耐不住技痒,以一篇《人生观与科学》加入论战,并站在张君劢一边,反对科学万能,“我把我极粗浅极凡庸的意见总括起来,就是: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梁启超认为人的“情感”方面可以超越科学,实质上代表了很多“玄学派”人士的看法。他们通常承认科学对于“死”的物质世界有决定作用,但难以想象机械化的科学会支配人类活泼泼的瞬息万变的“情感”世界。张君劢不承认心理学有“确实科学”之地位,便基于同样理由。科学派意识到对手将“情感”与研究人类情感的“心理学”作为抵抗“科学万能”的堡垒,就将进攻火力大多集中于此堡垒上,因而论战呈现出第二大特点——关于“情感”或“心理学”能否为科学方法所支配成为论战焦点中的焦点。
——选自王斐《现代新儒家的自我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
在科学知识的冲击传统伦理的背景下,熊十力一度怀疑世界存在的意义与自己生命的价值,但对经验世界的虚幻性体悟,促使熊十力去寻求其背后的真实存在。
——编者按
熊十力对“自然”和“自我”的理解
熊十力意识到,天演说的盛行,使得从“人格化神”或“泛神”角度理解“天”的思想日益缺乏说服力,“晚近天演说张,形气之秘机愈泄,斯以自然言天者贵矣”,具有“虚无真理”内涵的“天”最终转化为物质化的“自然”;然而,比之于物质化的“天演说”,熊十力更赞成“唯心”的佛学对“天”之理解:一方面,佛学对“天”或世界本质的理解更接近于自己对物质世界虚无幻化本质的生命体验;另一方面,他认识到丧失了道德性的物质化“天”“世界”无法赋予生活于中的“人”以德性内涵,使得人日益从功利主义角度理解“自我”,物化世界与功利化的自我具有内在关联,而二者共同促使现今成为“残酷竞争之世”:
挽世唯物之说胜,功利之习炽,又值东西学说,汇流交错,互相冲突,人心靡所依止,妄动以赴竞争之壑。争必有所托,故仁义托于五伯,文明人道托于今日竞争残酷之群雄,孰与正其是非哉?
熊十力对于“科学”有着非常复杂的情感,毫无疑问,无论是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还是因对科学的物质化世界图景所带来的功利主义盛行之憎恶,他都不喜欢也不认同科学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但是,他又无法否认科学所带来的巨大的技术变革及其对现实世界的功用,因而,最理想状态是“科学”与“佛学”互相调和,祛除科学的“物质化”特点。这可以解释他读到梁漱溟对鲁滂学说的佛学化解释之喜悦,他专门摘抄了部分内容,并加上自己的理解,撰成《记梁君说鲁滂博士之学说》:
顷见梁漱溟引法博士鲁滂之说,比合佛旨,融相入性,科学家执心外有物,庶开其蔽尔。按鲁君说:“以太涡动,形成原子,非物质之以太,能变成岩石钢铁。力与物质,同一物而异其形式。质力非不灭者,质力之相续灭,则归于万物第一体不可思议之以太。”此其大旨也。梁君说其义曰:“所谓第一本体不可思议之以太者,略当佛之如来藏或阿赖耶。《起信论》云‘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者也。’鲁君所获虽精,不能如佛穷了。”
遗憾的是《记梁君说鲁滂博士之学说》中的“科学”是经过了梁漱溟佛学思想改造过的“科学”,以物质主义与还原论为其核心,而物质主义将熊十力否定物质世界的“生命体验”变为了“玄想”,还原论则将他眼中具有道德性与超越性的自我还原为功利主义的感官性动物。熊十力虽然没有参与“科玄论战”,但对论战中科学派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和吴稚晖嬉笑怒骂的“漆黑一团的宇宙观”有着深刻印象:对于科学派宣传科学的文字中所带有的“杀伐之音”,熊十力与林宰平有着同样的感受。熊十力认为科学可以探究到物理世界的真实,但无法得到本体世界的真实,后者必须求诸“证会”或“体认”:熊十力深信得自自我生命体验的“真理”,比科学研究物质世界所得的真理更加真实,属于“本体世界”的真实。这个观点说来简单,论证起来并不容易,若要普通读者获得自己证悟而来的“本体世界的真实”,关键之处在于证明这个现实的物质世界并不如我们日常生活中感受的那般“真实”,换言之,解构掉这个物质化的世界乃是达至“证悟”终点的必经之途。
——选自王斐《现代新儒家的自我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
在东西文化论争的背景下,梁漱溟将西方文化下产生的制度与东方文化下人的态度之间的矛盾视为中国问题之症结所在。他与宣传西方思想,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文化派学者产生了交集和冲突。
——编者按
梁漱溟与新文化派对东西文化理解之异同
1917年梁漱溟来到北大。初至北大时,他延续了出世那些年间对于印度哲学和佛学的兴趣,给学生讲授印度哲学和佛教唯识学,并于1919年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于1920年出版了《唯识述义》。然而不久之后,梁漱溟便意识到这些抽象而古老的印度哲学、佛教唯识学与自己所关心、思考的中国问题相隔太远,而现实的政治环境与思想氛围促使他将注意力由这些遥远的古学转移到现实的中国问题上来。
多年后他这样回忆初到北大当老师的一段日子:1917年的北大文学院群贤毕至,陈仲甫担任文科学长,以他为代表汇集了一大批内心崇拜并大力宣传西方思想,同时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文化派”学者,其中包括陶孟和、胡适、李守常和高一涵。梁漱溟和这批新文化派朝夕相处,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当时北大也并非全是宣传西方文化的学者,同样有一批讲授中国传统学问的教员。但是这批教员面对新文化派对传统文化的严厉批判,却丝毫没有不适之感。两派人彼此也不沟通,仿佛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的人。梁漱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遭到批判这一问题,觉得有很严重的压迫感,一直在寻找一条解决问题的道路。
梁漱溟的这段回忆有两点值得注意之处:其一,当时梁漱溟在北大几乎身处新文化派人士的包围之中,面对他们对东方文化的批判,自己感到非常不自在;其二,北大另有一批教授中国哲学的学者却将新文化派对东方文化的批判视若无事。从这两点事实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即梁漱溟对东方文化怀有深厚的情感,是一个与主张西化的新文化派相对立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但这个结论不能说完全错误,至少很不准确,它忽视了梁漱溟与新文化派身处同一个问题语境中,因而分享着很多共同的问题预设,例如将东西文化问题视为解决当时中国政治社会危机的关键性问题,因而陈独秀们才会对东方文化发起如此猛烈的攻击,梁漱溟对于东方文化受到批判才会感觉“压迫之严重”,相较而言,反是那些“讲程朱老庄之学者”将中国文化视为不切己身的纯粹学术问题,同新文化派和梁漱溟二者的差距更大。从后面的分析将可以看出,梁漱溟与新文化派的共同之处不仅在于问题预设,在某些问题的结论上也有相似之处,他们二者的区别绝非表面上对东方文化的态度或激进与保守的差异,而是对同一问题有着不同层次分析的差异。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卷开始改名为《新青年》,学界普遍将《青年杂志》的创刊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1916年,陈独秀于《青年杂志》发表文章《吾人最后之觉悟》,该文认为数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皆因为中西两种文化相接触冲突所致,另一方面两种文化之冲突也使国人日益觉悟。文章将这一冲突与觉悟的过程分为了七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明朝中期,西学和西方器物初入中国,了解情况的人极少,真正信服西学的只有徐光启一人;第二阶段在清朝中期,西方的火器、历法被清廷接受,此时期还发生了中西历法之争,陈独秀认为这是新旧之争的开端;第三阶段在清朝中叶(原文即为“清之中世”)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西方的武器战力之强令中国相形见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始提倡西方的制械练兵之术,开展洋务运动;第四阶段在清末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战败,陷入严重民族危机,稍有知识的人皆认识到西学之价值,康、梁等人提倡变法遭到守旧势力阻挠而失败,但随后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使得守旧势力彻底失去影响力,西学之影响也由政治制度扩展到政治根本问题;第五阶段在民国初年,这一时期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探讨政治的根本问题,而辛亥革命则将民主共和制在中国变为现实;第六阶段为现阶段(即1916年),现阶段中国已经是共和政体,但广大人民却仍然受到专制政治之压迫,因而此阶段需要巩固共和立宪政治;第六阶段能否成功则取决于最后阶段吾人能否有最后之觉悟,这一阶段是新旧思潮之大激战时期,最后的觉悟则是文化方面的伦理之觉悟,“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这篇文章描述了西方文化对于中国人自历法与器物至政治制度再至学术思想一步步深入的影响,并明确揭示出现阶段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在于是否能从学术文化根本层面学习西方,是否能获得伦理上之最后的觉悟。有研究者将该文视为“新文化运动之纲领”,纲领之说固然尚值商榷,但此文确可代表陈独秀等新文化派人士对于当时中国问题的理解与反应。新文化派将探讨重点集中于中西文化对比,批判传统文化、伦理,输入西方学理与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实践了《吾人最后之觉悟》对于“现阶段最后之觉悟”的呼吁。
——选自王斐《现代新儒家的自我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
梁漱溟对于生活非常认真。受饱读诗书的父亲影响,他什么事都讲究功利和实用,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社会变得更好,但面对丑恶的现实他无能为力,陷入了失望,同时他对事物的思考也陷入了困境:“快乐”与“痛苦”到底是什么?
——编者按
梁漱溟的精神危机
梁漱溟一生中曾多次强调,自己对人生持一种非常严肃的态度,遇事不愿随波逐流,总想提出自己的想法、思考,并希望在这些思考中寻出一条定则,来解释事物,评估价值,规范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十四五岁时,他曾一度信服于功利主义思想,后经同学启发,开始质疑这一思想,随着年龄增长,思想进一步成熟,梁漱溟开始反思构成功利主义的两大基本元素“快乐”与“痛苦”到底是什么。
梁漱溟少年时家里曾雇有女工负责家务活,他发现这些时刻忙碌于洗衣做饭等杂事的女工看上去一点也不觉得苦与累,相反经常是满脸笑容。那时他自己作为富裕人家的小儿子,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生活简直可以说像泡在蜜罐子中一般,找不到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心中反而充满苦闷。身边这种鲜明的反差对比,促使梁漱溟开始思索苦与乐的缘由。经过反思,他认识到其缘由并不在于外在环境,而在于一个人的主观内心,根源则在于人的欲望,欲望满足就会感到“乐”,反之则“苦”,然而人生在世,欲望是没有穷尽的,欲望也是无法全部得到满足的。
这样一来,人生在梁漱溟眼中便成了一条欲望不断翻滚的河流,所谓“乐”只是河流上短暂翻滚的浪花,最终汇入的却是一片无边的“苦”海。这是一幅十分悲观的人生图景,更可怕的还不在于人生之“苦”,而在于这个“苦”是毫无目的性、看不到希望之“苦”。如果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相信自己今世所受的折磨是为了能在彼岸或来世获得幸福得到拯救;如果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相信自己此生所冒的艰险是为了未来人类更美好的生活;如果是一个传统士人,他相信自己的“劳筋骨”“饿体肤”是成为一个大丈夫、一个君子的必要过程,那么“苦”也许还不是无法忍受的,相反可能成为历练人格、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宗教信徒、革命者和传统士人,他们对于自我的理解同一个更高的超越性价值联系在一起,自我所遭受的各种苦难一旦被解释成价值实现的必要阶段,就被转化成自我磨炼的过程,反而获得一种自我实现、人生充实之感。年轻的梁漱溟却将自我理解成纯粹的欲望载体,这样一来,人生之“苦”只是揭示了人生的毫无意义、自我存在的价值虚无性,而这一点正是他在《究元决疑论》中所谓的“大秘密”“大怪异”:
此世间者多忧、多恼、多病、多苦,而我所信唯法得解,则我面值于人而欲贡其诚款,唯有说法。又此世间有种忧恼病苦最大最烈,不以乏少财宝事物而致,亦非其所得解。此义云何?此世间是大秘密,是大怪异,我人遭处其间,恐怖犹疑不得安稳而住。以是故,有圣智者究宣其义,而示理法,或少或多,或似或非,我人怀次若有所主,得暂安稳。积渐此少多似非暴露省察,又滋疑怖;待更智人而示理法,如是常有嬗变。少慧之氓,蒙昧趋生,不识不知。有等聪慧之伦,善能疑议思量,于尔世理法轻蔑不取。于尔所时,旧执既失,胜义未获;忧惶烦恼,不得自拔。或生邪思邪见;或纵浪淫乐(远生《想影录》所谓苟为旦夕无聊之乐);或成狂易;或取自经(《想影录》所谓精神病之增多缘此,自杀者亦多)。如此者非财宝事物之所得解,唯法得解。此忧恼狂易,论者身所经历(辛亥之冬壬子之冬两度几取自杀)。
由于对人生意义、自我存在价值这些“大秘密”“大怪异”存在不解与迷惑,人的精神非常容易陷入“犹疑不得安稳”的状态,一些智者对这些问题答案的宣讲,常常能说服大多数人,使其获得安稳,但对于少数聪慧之士,这种安稳常常是短暂的,他们通过自己的反思发现原有“答案”的漏洞,便“于尔世理法轻蔑不取”,遂再次陷入意义危机,“忧惶烦恼,不得自拔”,甚至选择自杀,以作了断。这段文字几乎就是其作者本人对精神危机产生与发展过程的详细自述。由此可见,青年梁漱溟找不到一个可以赋予自我存在意义的价值中心,而对生活严肃认真的他又急需这样一个中心来阐明人生的价值,并以此作为生活的规范。这种内在矛盾是其精神危机的重要诱因,而精神危机又放大了外界环境的刺激,遂使他陷入极为苦闷的状态,以致两次尝试自杀。这些痛苦经历最终促使他转向佛学,以寻求消除精神危机的良方。
——选自王斐《现代新儒家的自我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