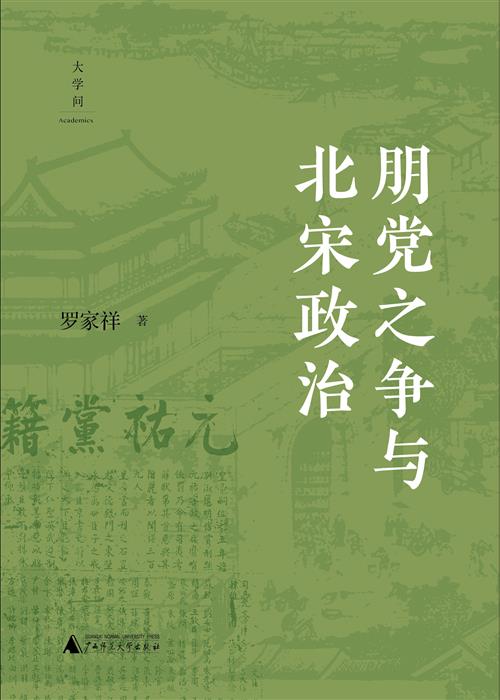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4-08-01
定 价:89.00
作 者:罗家祥 著
责 编:张洁,吴楠楠
图书分类: 中国史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历史/中国史
开本: 32
字数: 332 (千字)
页数: 4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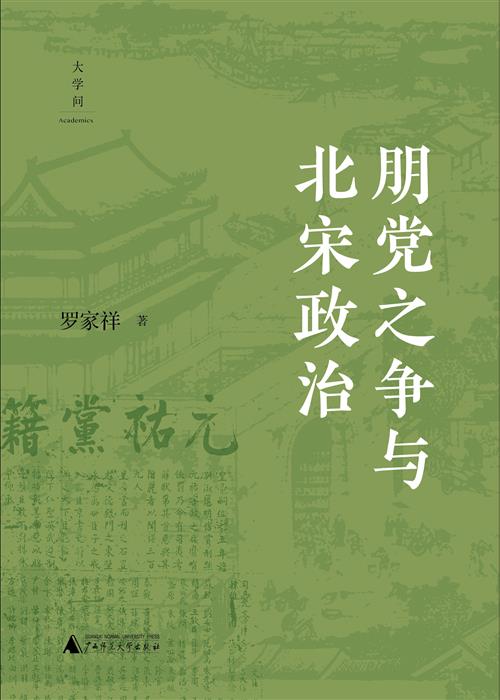
本书是一部北宋党争研究的经典之作。书中以王安石变法为关键节点,立足于神宗熙宁以来的新旧党争,将党争的范围上延至庆历党论,下延至南宋初年的靖康党论,关注新旧党各自的政治侧重、人事变动以及对政局的即时因应,细致分析了北宋中晚期政治人物、集团的作为和政治局势的反复对王朝统治根基的动摇,从实质性层面解释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和士大夫政治的异化,揭示了士大夫政治何以走向僵局的某种必然性。
书中史料扎实,考证严谨,作者文笔颇具感染力,将士大夫宦海沉浮的扣人心弦之处展现得淋漓尽致,具有较强的叙事感和可读性,可作为把握北宋党争的基础性读物。
罗家祥,湖北天门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93—199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入选2005—2006年度中美富布莱特学者,并应邀赴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研究领域侧重于宋代政治史和学术文化史。代表作有《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宋代政治与学术论稿》等,并主编有《华中国学》1—15辑。
北宋官僚士大夫的朋党理论(代绪论)
第一章 北宋政治的发展演变与北宋党争的产生
第二章 熙宁、元丰时期的党争问题
第三章 元祐新、旧党之争
第四章 元祐时期的洛、蜀、朔党争
第五章 从哲宗“绍述”到“建中靖国”
——新、旧党争的发展演变
第六章 “崇宁党禁”与北宋晚期政局
第七章 靖康党论与党争的流播
征引文献目录
附录
不朽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
——纪念先师邓广铭教授诞辰115周年
深切缅怀先师王瑞明教授
后记
为何恰恰在北宋王朝统治时期,“君子有党”的观点被一些官僚士大夫从正面加以肯定,并予以系统深入的阐述?出现这种情况的动因又何在?下拟对这些问题作些分析。
首先,宋以前、尤其是汉唐时期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客观存在的朋党、党同伐异是北宋部分官僚士大夫借以获得这种认识的重要原因。在王禹偁、欧阳修、司马光、秦观等人的朋党论中,均远引上古尧舜时代的所谓“八元、八凯”“四凶族”作为其立论的依据,“八元、八凯”“四凶族”是否果有其事姑且不论,至少检索先秦时代的文字记载,我们难以找到将其划分为“君子”“小人”之党的说法, 应该说,宋人的主要依据来自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确立后的汉唐时代。东汉“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在宦官擅权的黑暗统治下,以部分朝野士大夫和太学生为主干形成一个奉“道”而行的集合体,与宦官抗衡,用当时的政治标准和道德伦理标准去衡量,即是“君子”与“小人”的对立,这应该是诱发宋人提出”君子有党”论的重要史实。
但是,仅有东汉的“党锢之祸”,还不足以使宋人得出“君子”“小人”分朋结党,自古有之的结论,是否各个王朝一直存在着“君子”和“小人”形成的两种势力,还需要历史作进一步的证实。李唐王朝是继两汉之后第二个享国长久的朝代,其后期大规模的朋党之争即起到了这种作用。较之东汉的“党锢之祸”而言,唐代党争表现得尤为复杂。故王禹偁因读唐史而作《朋党论》,司马光以黄介夫《坏唐论》五篇言犹未尽而述朋党观,均是鉴于唐代史实而发的;欧阳修纵论尧时八元、八凯为一朋,舜时皋、夔、稷、契凡22人为一朋,周武王时3000人为一朋,东汉时天下名士尽为朋党,唐末朝廷名士尽为朋党,并用唐末将党人投诸黄河而唐以亡一事与东汉末党锢事互相印证,才使得“君子有党”的观点最终产生。这一点,通过刘安世《论朋党之弊》一文看得更清楚,他说:“臣尝于史册之间,考前世已然之事,盖有真朋党而不能去,亦有非朋党而不能辨者”,则仅以汉、唐党祸作为论据。
其次,“君子有党”论作为一种对社会政治现象进行抽象概括的理论形态,也有其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其核心是对“君子”与“小人”的认识与甄别。先秦时代,“君子”一词是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而“小人”(或“野人”)在一般情况下则是被统治者的通称。相对来说,“君子”所包含的内涵更为丰富,除“大夫士”“士已上”者、“在位者”之外,还指“薰然慈仁”者、“有道德”者、“国中之盛德者”以及硕学之士。“君子”与“小人”的划分涉及政治才能、道德修养与学问造诣等诸方面,但最主要的划分标准,似乎还是社会政治地位,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身份。
“学在官府”的制度洞开、文化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后,“君子”和“小人”已不可能完全依照既往的界定方法,因为“小人”中也可能有人“学而优则仕”、跻身统治阶级的行列,尤其是在科举制度确立之后的唐宋时代,此种事例更是屡见不鲜。然而不管怎样,传统的“君子”“小人”观仍一直延续下来。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统治阶级中具体成员的地位升降,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变化,“君子”和“小人”的概念中一方面保存了原义,另一方面也日渐成为一对专门的泛道德化的政治术语,用以甄别统治集团内部的成员。在有案可稽的众多宋代史籍、宋人文集、笔记中,这样的情形比比皆是,而“君子有党”论者笔下的“君子”“小人”更是如此。
尽管“君子”、“小人”的内涵有了若干变化,但儒家经典《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说教仍是鉴别“君子”“小人”的重要标志。“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小人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这种看法几乎成为北宋所有官僚士大夫公认的至理。
在司马光那里,“君子”与“小人”的定义略有差异,他在《资治通鉴》卷1威烈王二十三年中追述智伯之亡的过程后论曰:
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进而,他将“才”“德”作为品评人物的尺度,将人分为四种类型:“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表面上看,“义”“利”与“才”“德”不能完全等同,但实质上却毫无相左之处。且看司马光的另一段文字。他在《与王介甫书》中引樊迟请学稼,孔子鄙之为“小人”比附王安石变法时有云:
使彼诚君子邪,则固不能言利;彼诚小人邪,则固民是尽,以饫上之欲,又可从
乎?
基于以上对君子和小人的认识和界定,司马光进一步指出:“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又司马光的积极追随者刘挚在王安石变法之际也上疏说:“君子小人之分,在义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义。”显然,“义”“利”与“才”“德”只是相为表里的关系,欧阳修与司马光对“君子”、“小人”作出的定义并无本质的区别。因而,归根到底,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君子”“小人”只能以“义”“利”作为辨识的标志。
将“义”与“利”,“才”与“德”截然对立起来,这种价值观又如何呢?无数的历史事实表明,这种荒谬的理论是无法实施于任何社会政治实践中的。这种观念固然体现了官僚士大夫们对一种思想人格的追求和对一种完美形象的自我塑造,从理论上讲,不无积极意义。然而,在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政治环境中,它只是一种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虚幻的价值观念。作为政治理想,它违背了人类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作为人格修养的一种追求,亦有悖于人的自然本性,必然会导致道德上的虚伪作态和政治上的苟且无为。何况,人们在解释“义”与“利”,“才”与“德”时,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换言之,人们在解释这些范畴时,常常带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而一旦将这种理论应用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中、给具体对象贴上异常极端的道德判断标签时,势必会导致政治上的巨大动荡和相互间的残酷倾轧,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尤其是宋哲宗元祐年间的政治发展对此展现得异常清楚。
第三,“君子有党”论的出现也与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王禹偁著《朋党论》之确切年代不详,只能大致断定其出现于宋太宗淳化二年(991)之前。根据宋初的情况看,王禹偁不一定仅在就史论史,太祖太宗时期赵普与卢多逊之间的明争暗斗,很可能是驱使其撰写此论的因素之一。
如果说王禹偁“君子”“小人”各自有党的提出与宋代政治的关系尚不太明确,那么,欧阳修等人对“君子”有党的详尽阐述则显系北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需要使然。仁宗庆历以前,以“朋党”之名加诸他人的情形就已出现。景祐三年(1036)五月,范仲淹因言事忤宰相吕夷简,又作四论讥切时政,吕夷简即“以仲淹语辨于帝(仁宗)前,且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于是,仁宗惑于“朋党”之说将范仲淹贬知饶州。随之,又同意侍御史韩渎的请求:“以仲淹朋党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庆历元年(1041)五月,龙图阁直学士、权三司使叶清臣,权知开封府、天章阁待制吴遵路与宋庠、郑戬皆同年进士,“四人并据要地,锐于作事,宰相以为朋党,请俱出之”。
这一连串的政治斗争表明,最高统治者十分忌讳的“朋党”之名,在当时已经成为保守势力排斥革新势力的有效工具。这种情况正如包拯所云:“臣伏闻近岁以来,多有指名臣下为朋党者,其中奋不顾身、孜孜于国、奖善嫉恶、激浊扬清之人,尤被奸巧诬罔,例见排斥。故进一贤士,必曰朋党相助,退一庸才,亦曰朋党相嫉,遂使正人结舌,忠直息心,不敢公言是非,明示劝戒,此最为国之大患也。”随着宋王朝腐败程度不断加深,随着在政治上试图有所作为的改革势力出现在政治舞台,从理论上系统地解释“朋党”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早在宝元元年(1038),参知政事李若谷在仁宗诏戒朝臣朋党、范仲淹徙润州后,就曾指出:“君子小人,各有其类,今一目以朋党,恐正人无以自立矣。”其意已十分明显。
以改革吏治为中心的“庆历新政”,为”君子有党”论的最终问世提供了重要契机。吕夷简罢相后,面对积弊丛生的局面,仁宗“方锐意太平”,遂于庆历三年(1043)八月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试图革故鼎新,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而在“新政”中利益受到伤害的保守势力,则故伎重演,再次运用“朋党”这一行之有效的武器,煽起甚嚣尘上的“朋党”之说。果然,仁宗再次为之所惑,只是范仲淹等人历年表现出来的耿耿忠心才使仁宗未能骤以景祐之道治之。于是,范、欧等人的朋党观便应运而生。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8庆历四年四月戊戌条载:
上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 ”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这则材料即十分清楚地反映出”君子有党”论出现的政治环境。“君子”有党之提出,旨在从正面驳斥保守势力的“朋党”之说,释仁宗之惑,换得其对“庆历新政”的坚决支持。如果没有利益受到伤害的保守势力以“朋党”之名对范仲淹为首的改革势力进行尖锐激烈的攻击,范、欧二人是否会一反宋以前的朋党理论,在庆历时期理直气壮地提出“君子有党”,而且只有“君子”才可能结成真正的朋党,“小人”之间则只能有伪朋,并对其详加阐述,这殊难臆测。
苏轼、秦观等人之所以对“君子有党”之说反复论证,亦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所致。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政治形势有了很大的改变,但熙丰变法时期,始终存在着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激烈斗争;哲宗即位后,在宣仁高太后的全力支持下,司马光等人主持了全面颠覆“新法”的所谓“元祐更化”,对新党大加挞伐;嗣后,洛、朔、蜀三党互相倾轧,频起争端,苏轼、秦观置身于党争的漩涡中,循着范、欧等人的思路对朋党问题再加探讨,这也就毫不足怪了。
在宋朝政治史研究中,本书多有创见,如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提出“君子有党”论;北宋朋党之争的恶化源于“元祐更化”,并导致了北宋政治发展的严重后果;将宋徽宗、蔡京借推行新法之名而行祸国殃民之实的党禁,不称之为党争而称之为党祸等,均发前人所未发,甚有见地。本书对深入认识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至今对于我们也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张希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宋代士大夫的党争影响宋代政治深远,尤以北宋为烈,有谓北宋党争既导致改革失败,更致北宋的灭亡。过去学者研究宋代党争,多偏重于神宗至哲宗朝的熙丰元祐的新旧党争,或探索肇端于吕范相争至庆历变法之仁宗朝党争,笔者早年也写过《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一本小书。唯全面研究北宋士大夫党争,并深入剖析其对北宋政治的影响的,就非罗教授这本可称经典之作莫属。
——何冠环(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客席教授)
政治史是理解人类社会的核心视角,对传统王朝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其间关键问题常常通过不同派别相互间的党争表现出来。自从科举士大夫成为北宋官僚阶层主体,党争也开始呈现新的形态。然而各种政治关系之复杂隐秘,非穷极海量历史资料,深掘其底层信息而不可知。又其影响所至,若非旁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无以窥其全貌。此党争史研究之不易,罗家祥教授《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一书之所以系学术史上最重要著作之一,乃因其为关心我国传统政治史者不可不读之故也。
——包伟民(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教授)
陈寅恪先生曾有一著名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作为宋代文化或者宋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士大夫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熠熠闪光,这也与士大夫政治密不可分。只是,士大夫文化与士大夫政治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为什么“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文化模式会走向异化?新旧党争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王安石变法对北宋统治究竟有何影响?这些是研治宋史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书立足于神宗熙宁以来的新旧党争,将党争的范围上延至庆历党论,下延至南宋初年的靖康党论,关注新旧党各自的政治侧重、人事变动以及对政局的即时因应,细致分析了北宋中晚期政治人物、集团的作为和政治局势的反复对王朝统治根基的动摇,从实质性层面解释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和士大夫政治的异化。
对于有意了解这一时期历史的读者而言,本书以扎实的史料、严谨的考证为基础,侧重于事实层面的分析,故在可信的基础上具有较强的叙事感和可读性,可作为把握北宋党争的基础性读物。
宋哲宗绍圣年间,曾布以大公至正的多面形象,在与新党章惇、蔡卞、吕惠卿以及旧党诸人的政治斗争中游刃有余,在皇权面前,则竭力将自身塑造忠贞不二之臣、孤立不党之士,在适度保持政治张力的基础上达成自身的政治目的。
——编者按
多面曾布——党争“不倒翁”的“政治哲学”
绍圣初,无论是从言论还是从行动来看,曾布的政治态度均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给旧党以坚决打击,并努力绍述神宗政事。但没过多久,曾布的政治活动与政治态度却表现得极为矛盾和乖戾。一方面,他力主打击元祐党人,绍述神宗政事,旧党诸人遭黜责后,他认为:“蔡确五年不移,惠卿十年止得移居住处,吴居厚十年不与知州军,此皆元祐中所起例,自可依此。”以此鼓动宋哲宗严厉惩处元祐党人。《宋史》卷319《刘奉世传》:
绍圣元年,……(刘奉世)过都入觐,欲述朋党倾邪之状。帝将听其来,曾布曰:“元祐变先朝法,无一当者,奉世有力焉,最为漏网,恐不足见。”
此记载也足可看出曾布对旧党严密防范的政治态度。又绍圣四年五月文彦博去世时,曾布对哲宗云“老而不死,终被谪命乃即世”“臣常以为背负先帝,莫如此人”,此语也不可谓不刻薄。《长编纪事本末》卷101《逐元祐党人上》:
(绍圣二年)十二月乙酉,曾布言:“文彦博、刘挚、王存、王岩叟辈,皆诋訾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网者。”惇曰:“三省已得旨编类元祐以来臣僚章疏及申请文字,密院亦合编类。”上以为然。
曾布的意思,即是将漏网者清查出来,予以治罪。是时,曾布为同知枢密院事,三省与枢密院一并编类元祐臣僚章疏之议,布实为始作俑者之一。绍圣三年四月中,曾布对宋哲宗云:“司马光之徒,内怀怨望,每事志于必改,先帝以纯臣之礼待之,而用心如此,其为背负先帝,情最可诛。”以上都足以证明,曾布对旧党打击毫不手软。
但在另一方面,曾布又往往貌似大公至正,发出与章惇等人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论调。上引材料说明,绍圣时期的编类元祐臣僚章疏,曾布实为主要策划者之一,但在另外的场合,他又说“施行元祐之人,殊无伦理”,“方今编排章疏,中外人情不安,恐难施行”,表示出与前述完全不同的态度。绍圣四年五月,曾布又以“爱惜人材”为由,要将旧党分子孙觉、李常荐入朝廷。吕大防、刘挚南贬,曾布还曾提出要“稍徙近地”,以“感召和气”。绍圣四年十月,建议将陈瓘用为台谏或侍从官。降至元符之末,曾布则干脆直接建议哲宗引用元祐党人。
与之同时,在一些场合、尤其是与宋哲宗单独交谈时,又屡屡对章惇、蔡卞、蔡京以及新党中其他人表示不满乃至直接进行抨击。绍圣四年九月,曾布独对事,称“臣度章惇、蔡卞,必不能为陛下更修政事,进退人材”。稍后又说“与章惇、蔡卞议论不同之人,便指为异论”,攻击章、 蔡二人动辄以朋附元祐党人之名排斥异己。又据《长编》卷498元符二年五月癸酉条:
布曰:“陛下睿明天纵,士类之福。若以一言之差,便废一人,则何可胜废?章惇实有此议论,如与司马光争免役事,为天下所称,然其言亦未尝以免役为是,但云当徐议改更,不当暴废尔!”
上云:“方泽诚可罪,只是惇门下人,故主张他。”
布曰:“泽本惠卿亲党,然惇于惠卿亲党过于己亲党,无不主张者。”
上曰:“何故?”
布曰:“此陛下所素知,惠卿作执政时,惇乃门下士……”
以上的事实表明,随着元祐旧党被贬逐殆尽,曾布与章惇、蔡卞、吕惠卿等人之间也逐渐产生了严重的分裂。在与哲宗的对话中,曾布则隐伏着深刻的言外之意。元符二年二月,曾布还对哲宗云:“章惇、蔡卞施行元祐人,众论皆以为过当,然此岂为诋訾先朝,大抵多报私怨耳!”这里,曾布则完全将自己置于新党之外,俨然以中立不党之面目对章惇、蔡卞进行指责。
曾布的这些矛盾表现,招来了后世的不同评价。如缪荃孙认为“其论至公”,“较之惇、卞之徒,究属天良未昧”,给予一定程度的好评;而另则有人认为“绍圣初,元祐党祸起,布知公论所在,故对上之语,多持两端”,意在说明其恶不减章、蔡,只是善于文饰,城府更深。如何正确地评价曾布,不仅涉及到曾布个人的功过是非,而且还涉及一系列事件的性质判断。
笔者认为,在曾布的政治活动中,始终贯穿着其一套独创的官场哲学,即在君臣之间、同僚之间,始终适度地保持一定的政治张力,并不断地随政治环境的变化加以调整,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兼而达到个人政治上的目的。他的所有矛盾表现,都是由此而产生的。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中,曾布之弟曾肇曾给时为宰相的曾布修书一封,信中首先肯定了“兄与惇、卞异趋,众所周知”的事实,要求他引用善人( 按指元祐党人),扶助正道,并指出如若不然,“曾氏之祸”将不可逃。曾布在复信中谈了对当时局势的看法,并告知自己何以能在政局迭变、朋党相倾的复杂形势中成为不倒翁的奥秘:
自熙宁立朝,以至今日,时事屡变,惟其不雷同熙宁、元丰之人,故免元祐之祸;惟其不附会元祐,故免绍圣之中伤,坐视两党之人反复受祸,而独泰然自若,真自处亦必粗有义理,以至处今风波之中,毅然自立……元祐及惇、卞之党,亦何能加祸于我哉!恐未至贻家族之祸,为祖宗之辱,而累及亲友也。
曾布这一篇不可多得的道白,为我们通过现象了解曾布其人,了解当时的仕风,不啻提供了一把钥匙。曾布所说的处乱世而不败的“义理”,即是那一套官场哲学、为官之道。由于遵循了这一套“义理”和官场哲学,因此,曾布力主打击元祐党人,却又在打击的程度和方式上提出不同意见;力主绍述神宗政事,却又保留因时“损益”的观点;无数次在哲宗面前巧言诋毁章惇等人,离间章惇与哲宗之间的关系,却又时或对章惇有一两句公道之语。曾布力主“绍述”和打击旧党,是为了迎合哲宗,得到重用;而在其间所发的异论,则是为日后的“毅然而立”作准备。我们固然不能抹煞曾布的某些“公允”言行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必须看到,曾布这些行为的根本目的,只不过是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无所党同、无所依附的中正不倚之士,“坐视两党之人反复受祸,而独泰然自若”而已!
“中正不倚”只是相对于新、旧两党而言,而对于皇权,曾布却是挖空心思委身于斯、竭力效忠的。曾布深知君臣相处之三味,故而处心积虑要使哲宗相信他是忠贞不贰之臣,孤立不党之士,试看曾布与哲宗的如下一段对话:
上曰:“大臣所见,岂可不言? 言之何害?”
布曰:“臣每蒙陛下开纳如此,益不敢循默,然愿陛下更赐采纳。臣自初秉政,即尝奏陈以谓先帝听用王安石,近世罕比,然当时大臣,异论者不一,终不斥逐者,盖恐上下之人与安石为一,则人主于民事有所不得闻矣,此何可忽也。”
上曰:“冯京辈皆是。”
布曰:“非独京辈,先帝曾谕臣:王珪虽不言,亦未必不腹诽也。今三省无一人敢与惇、卞异论者。”
在以上对话中,他反复告诫哲宗“以先帝御安石之术为意”。向哲宗进此君人南面之术,无疑是曾布委身于哲宗的最佳方式,此种方式可谓一举三得:可获得哲宗的充分依赖;可以客观上收到离间哲宗与惇、卞关系之效;可为自己仕途的进一步通显打下基础。曾布的这种用意极为明显。
曾布既然想要扮演这样一个角色,那么他也就必然在新党内部寻找矛盾,偶尔制造矛盾而与其他新党官员处于若即若离,甚至敌对状态。至哲宗去世,曾布与章惇之间的矛盾终于发展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据曾布自己的记载,向太后垂帘之后,他曾与向太后论及章惇数事,认为:“今日事不成,惇与(梁)从政皆怀家族之忧,惇为首相从政握亲兵,内怀反侧,但无能为尔!”曾布此语的用意异常卑劣。“今日事不成”,系指章惇曾反对立端王赵佶为帝而未成功;“内怀反侧”,即是认为章惇有不臣之心。曾布能以此中伤、谄诬章惇,可以看出,二人之间的冲突已是异常尖锐、激烈。曾布与蔡京、蔡卞之间的关系,也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所以向太后垂帘之后,他一再要求将蔡京、蔡卞逐出朝廷。
——选自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