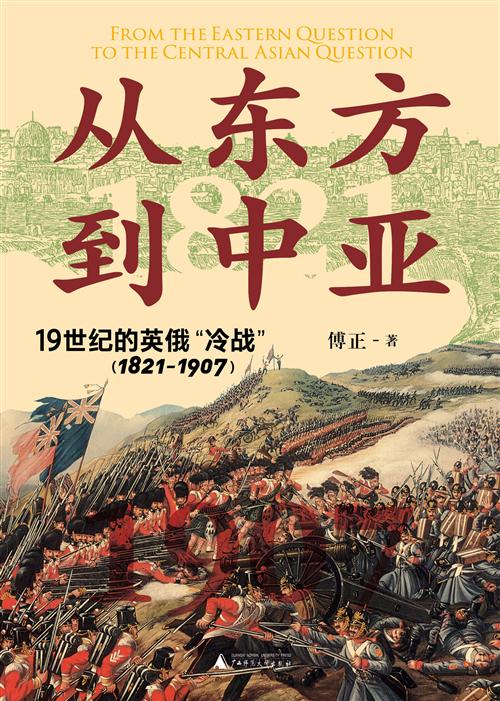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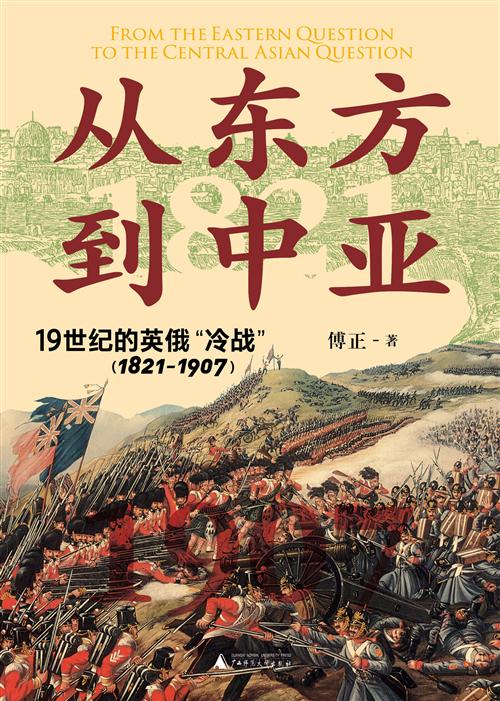
从19世纪前期到20世纪初,海洋霸主英国与陆上强国俄国进行了一场长达近百年的较量,即“维多利亚时代的冷战”,也被叫作“大博弈”。本书以“大博弈”中的两个焦点——东方问题和中亚问题为脉络,梳理了英俄双方在“大博弈”中的军事与外交行为,生动描绘了这场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力量角逐,并聚焦这一时期的地缘政治,阐释其中的权力逻辑,讨论了19世纪的地缘政治思想。本书将晚清中国置于全球视角之下,为我们认识中国与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横向比较历史视野,也为我们今天理解中国现代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意义,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视角。
傅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著有《古今之变: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等。
导论
一、东西帝国,两大“病夫”
二、“维多利亚时代的冷战”
三、理论框架与前人研究
上半场
第一章东方问题与中亚问题的起源
(1798—1829)
第一节东方问题和波斯问题的开端
(1798—1813)
第二节 19世纪英俄对抗的起源(1821—1829)
第二章 英俄冷战的正式展开(1829—1842)
第一节 英国中亚政策的出台(1829—1842)
第二节 “大博弈”中场休息与英国确立海峡政策(1839—1842)
对历史的反思
下半场
第三章 两次革命之间的东方问题与中亚问题(1853—1874)
第一节 克里米亚战争与英国在亚洲的麻烦(1853—1860)
第二节 俄国在中亚的全面扩张
(1861—1868)
第四章 英国东方政策与中亚政策的转变(1874—1880)
第一节 迪斯累利的东方政策(1874—1878)
第二节 英国中亚政策的演变(1863—1880)
第三节 英国对清政府军事、外交的渗透(1874—1878)
第五章 新的战争危机(1879—1889)
第一节 征服土库曼与平狄危机(1879—1885)
第二节 新外交政策与“新地理学”
(1886—1889)
第六章 英国的外交转型与俄国的远东扩张(1889—1904)
第一节 《地中海协定》的终结(1889—1897)
第二节 俄国的远东扩张与英日同盟的建立(1897—1902)
对历史的反思
落幕
第七章英俄和解与从未终结的冷战
(1904—1907)
第一节 英俄和解与分割亚洲势力范围
(1904—1907)
第二节 未曾终结的冷战
简短的结论
附论:马克思、恩格斯论“东方问题”与中国革命
参考文献
后记
导 论
一、东西帝国,两大“病夫”
在英俄冷战行将中止的岁月里,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突然宣称,早在1898年6月“百日维新”伊始,他就给光绪帝上呈了《突厥守旧削弱记》,希望皇上能够以土耳其为鉴,自强图存,否则瓜分豆剖,势所难免。康有为说道,昔日奥斯曼帝国兵强马壮,所向披靡,几乎要灭掉整个欧洲,“当明之中叶,其苏丹索立曼(今译为“苏莱曼”)拥马队兵百万,以压全欧,玉节金幢,铁马鸣镝,鞭棰所指,指日灭欧”。西方基督教文明得能苟延残喘,纯粹是机运所致,“幸霖雨泥泞,疫病大起,仅乃得解,否则诸欧咸为吞并矣”。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庞大帝国却冥顽不化,自甘堕落。短短百年之间,攻守易位,曾经弱小之欧洲由变法而强,曾经强大之土耳其因守旧而弱。康有为接着说道:
及夫欧势内膨,兵力外挺,眈眈逐逐,惟此地兼三海三洲之神皋腴壤,始因种争教争,借扶其民,于是埃及、希腊自立,罗马尼亚、塞维(按,塞尔维亚)继之。及布加利牙(按,保加利亚)教案之起,俄人借口仗义兴师,于是可萨克(按,哥萨克)数十万兵,立马巴达坎岳(按,巴尔干山脉)之巅,以俯瞰君士但丁那部(按,君士坦丁堡)矣。
以土耳其当日之强大,尚且如此,何况大清乎?
需要指出,康有为《我史》中所说他戊戌时期进呈的书籍中,未有《突厥守旧削弱记》条目,清宫档册中亦不见相关记录,或许此《突厥守旧削弱记》世无其书,系康氏编造而来。但无论如何,他对于土耳其的评说就反映了彼时维新志士的普遍看法。
清代中国人对于土耳其的介绍初见于乾隆平定回疆之后,至道咸年间边疆史地学兴起,亦散见于学者著述。然有识之士真正开始关注土耳其,要等到甲午战争以后。例如1898年2月11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文章,开头就称:“西欧人恒言曰:‘东方有病夫之国二,中国与土耳其是也。’”此话一下子就拉近了中国与那遥远西亚帝国之间的距离。
土耳其之为“病夫”,其故有二:“一曰内治不修,纲纪废弛,官吏贪黩,鱼肉其民,因循成法,莫肯少更,束缚驰骤,激成民变。二曰外交不慎,妄自尊大,不守公法,屡起教案,授人口实,取怨各国,合而谋之。”这更让人感到梁氏不是在说土耳其,而是借土之名暗讽中国。按照他的说法,“西方论者,以为若在十年前,则土其必亡矣,今者欧洲诸雄,方并心注力于中国,无暇以余力及区区之土,而土遂获全焉。呜呼!与土同病者,其危可知矣”。言下之意,要不是中国分担了西方列强的注意力,土耳其早就被瓜分殆尽了。“呜呼!其与今日中国之情实何相类也!”
谭嗣同更是别出心裁,主张中国、土耳其这对远东、近东“病夫”,应该合力自保,修筑一条“东起朝鲜,贯中国、阿富汗、波斯、东土耳其,梁君士但丁峡,达西土耳其”的大铁路,将此“同在北纬三十度至四十度之间”的大大小小各个“病夫”“穿为一贯”。“诸病夫戢戢相依,托余生于铁路,不致为大力者负之而走,其病亦自向苏,而各国所获铁路之利,抑孔厚矣。”不论此等主张如何天马行空,另类出奇,中国与土耳其同为“病夫”,同病相怜,却是当时人的一般感受。
值得一提,康有为故意将“土耳其”翻译成“突厥”,实是要让大清与之建立血缘关系:“突厥出自匈奴,盖殷人淳维之后,而吾同种也。”至1908年7月,他撰写《突厥游记》时,开篇就痛骂土耳其青年党人别的不学,偏偏学习法国大革命那一套“人人平等自由”之说,正所谓“乱国之人,不学治术,徒愤激于旧弊而妄行革变,未有不危亡其国者也”。准此,不仅土耳其的国运与大清的国运紧密相连,土耳其的人种与大清的人种同出一源,就连土耳其的革命党与大清的革命党都殊无二致。
与这种立场针锋相对,在清季革命派看来,土耳其帝国境内的历次民族独立运动,才是真正值得效法的对象。章太炎在《哀焚书》中称:
今夫血气心知之类,惟人能合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列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俄罗斯灭波兰而易其言语。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支那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
“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岂不等同于清军入关剃发易服?中国与土耳其的关系有了另一种说法,仿佛中国不像土耳其帝国,而像土耳其治下的巴尔干民族。由此,土耳其非但不值得相怜相结,反倒应该被一并尽力攘除。
上述说法各不相同,要皆一也,即大清与奥斯曼帝国本来各处亚洲之东西两端,风马牛不相及,此时却同处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枪炮之下。说得更确切一些,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欧洲部分相接壤,又跟英国本土相去不远;大清与俄国的亚洲部分相接壤,又跟英属印度相去不远。奥斯曼帝国毗邻俄国的部分涉及欧洲近代史上著名的“东方问题”(the Eastern Question),而大清毗邻俄国的部分涉及英俄外交史上著名的“中亚问题”(the Central Asian Question)。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这两个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性帝国,通过“东方问题”和“中亚问题”把中国与土耳其的命运拴到了一起。
二、“维多利亚时代的冷战”
米歇尔·埃德沃兹(Michael Edwardes)曾把19世纪的英俄对抗(Anglo Russia Rivalry)称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冷战”(a Victorian Cold War),它起源于19世纪前期,结束于20世纪初期,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
这场冷战的范围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半岛,从小亚细亚到东北亚,几乎涵盖了大半个地球。除了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这两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近代帝国之间并没有爆发直接战争,但直接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挂在它们头上,用一位俄国大臣的话说,双方是在进行一场“影子比武”(Tournament of Shadows)。
其中,英俄冷战的一个重要战场在中亚。关于两国在中亚地区的较量,埃德沃兹在其专著《玩转大博弈》(Playing the Great Game)的开篇,就这样说道:
19世纪的帝国历史学家约翰·威廉·凯伊(John William Kaye)在亚瑟·康诺利(Arthur Conolly)的论文中,发现了这一表述。康诺利是“大博弈”最热心的玩家之一,他于1842年在布哈拉被杀害。在所有以体育比赛作为隐喻的政治中,“大博弈”占据了恰如其分的位置——“玩起来,玩起来,玩转大博弈”“博弈本身比参与博弈的玩家更加伟大”——不列颠人喜欢用这样的隐喻来掩盖他们的商业帝国的残酷现实。“大博弈”囊括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公共戏剧和私人悲剧,囊括了废墟中代价高昂的政策、不必要的战争、散布在荒野中的游魂。它是一个经过无情编辑的剧本,非常符合维多利亚时代“帝国的浪漫”(the romance of empire)。
英国军官亚瑟·康诺利为这场明争暗斗创造了一个具有冒险主义色彩的浪漫名词——“大博弈”。从此以后,“大博弈”逐渐成了英俄中亚冷战的代名词。
“大博弈”之所以重要,往往不在于双方在中亚地区的对抗有多么激烈,而在于中亚地区是一个地理上的中枢,一头连着奥斯曼土耳其的东部省份,另一头连着中国的新疆和西藏,不仅位于英俄两大帝国之间,而且同样位于奥斯曼帝国和大清之间。“中亚问题”的一边是“东方问题”,另一边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边疆危机。因此,它不仅是英俄冷战的战场,更是大清与土耳其帝国命运的缩影。
1907年,英俄冷战结束。四十年后,美国杜鲁门政府跟着当年英国的脚步,再一次挑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当今美国冷战史研究权威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便指出:
英国人比他们的盟友美国人更早得出与苏联合作将不再可能的结论;在整个1946年和1947年初他们无疑欢迎,有时还试图补充杜鲁门政府日益释放出的认可这一观点的更多迹象。……的确,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伦敦的态度是,美国人做得还不够:……
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的美苏冷战实乃19世纪英俄冷战的升级版。我们都会承认,不理解美苏冷战的背景就不足以谈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但英俄冷战之于晚清中国的巨大影响,是否得到了我们应有的重视呢?
又,“东方问题”和“中亚问题”之间的关联具体是怎样的?“中亚问题”又如何转化为中国近代的边疆危机?边疆危机又对中国近代的政治改革造成了什么影响?这些影响是如何促使中国由一个传统帝制国家转向现代民族国家的?
对于上述问题,需要做全局性的思考。解答这些宏大的问题,则意味着必须把中国近代史放到国际关系史中去理解。徐国琦教授曾呼吁:“要理解‘一战’对中国的意义,学者必须打破藩篱,对内政外交以及社会与国际关系都要涉猎,否则即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误。”不只对于北洋史应当如此,对于晚清史也应当如此。不理解边疆危机则不足以理解晚清中国的政治改革,不理解19世纪英俄冷战则不足以理解中国近代的边疆危机。
本书正拟在这个方面做出尝试。其着力之处不在于对具体事件的辨析考证,而在于尝试提出理解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宏观框架,把内政史与边疆史联系起来,把中国史置于世界史之中。
三、理论框架与前人研究
1995年春,美籍土耳其裔学者德里克(Arif Dirlik)在香港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的论文。文中借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的术语指出,中国的史学界正在面临一场“范式危机”,过去的革命史范式正在遭到抛弃,现代化范式取而代之。
德里克的话引起了罗荣渠教授的关注。作为现代化研究的得力干将,罗教授在1997年出版的遗著《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回应了德里克的说法:“现在还谈不上这个新范式已经取代了传统范式,只能说是出现了两种范式并存的局面,目前主导范式仍然是革命史范式。”罗荣渠这样说显然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端,减少推进现代化研究的阻力。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批评反而给德里克打了广告。一石激起千层浪,两个范式对立的说法,迅速成为学术界的时髦,甚至“现代化范式”或“去革命化”一度成为学者“有思想”的标志。
所谓“现代化范式”“现代化史观”对学术研究的推进诚不可非,但久而久之,这让人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大抵我们在讨论近代某人的政治思想时,往往先将他的观点分类罗列,再以今天人的思维标准逐条裁断之——凡是接近于今人的便取而褒扬,凡是有违于今人的便弃而贬斥。
例如我们谈到李鸿章、郭嵩焘时,便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他们已经具备了“平等交往”“遵守条约”等现代外交意识,因此对他们无限拔高,捧之上天。此举反而忽略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忽略了只有在政治关系中才能准确认识政治人物,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按照今天人的标准,李鸿章、郭嵩焘们的外交主张时而无比精明,时而幼稚可笑?
于是乎我们又会简单地得出结论:李鸿章等人是现代化的先驱,但他们受到的封建糟粕束缚还很重,现代化程度还不够。这样千篇一律的评判不可能如实反映纷繁复杂的历史实相。事实上,“精明的李鸿章”“现代的郭嵩焘”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人暗中教导的结果,当失去了英国人的教导或中英利益不一致时,“精明的李鸿章”就突然变得鲁钝不堪,“现代的郭嵩焘”就迅速对现代几无所知了。
人物研究如此,国家研究亦复如是。我们常常用“工业化指标”“民主化程度”等抽象的标准去衡量一个国家、一项政策有多少现代性,而恰恰忽略了对国家政策的评判同样需要将其置于国际关系当中。约翰·伯顿(John W. Burton)在他的政治学名著《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中曾提及:
越南战争和伊朗事件的震撼,美国在控制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上以及在控制中美洲和其他地区富于压迫性的权贵的行为上所表现的无能,都使得这种观点更具说服力。权力是有限的,当有其自身的利益要追求时,当大国又很重视与这些小国的关系时,大国就成了软弱无力的巨人。
类似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所谓“现代的国家”“强大的民族”常常在特定的国际关系中反而被“落后的国家”“弱小的民族”牵着鼻子走,甚至不自觉地成为弱小民族国家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可见强弱程度、现代与否并不依赖于抽象的标准,它往往取决于具体的国际关系。
不只如此,国家毕竟不同于个人,它的内部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取向的利益集团组成的。国内各个集团的博弈斗争完全可能反过来制约国家实力的运用,甚至引发国际冲突。伯顿接着指出:
这种被忽略的东西就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最初的那种传统设想是虚妄的。它认为国际关系可以作为一门孤立的学科加以研究,国内政治则属于国内司法问题。
我们常常能在历史中看到,一项看似现代化的改革很可能招致无休止的纷争,甚至引发国际冲突,一项看似保守落后的举措反而行之有效,并带来周边国际环境的稳定。国家政策不只需要考虑国与国的关系,也要考虑国内与国际的关系。
总之,上述理论提醒我们,在研究政治事件时应该摒弃那些抽象教条的标准,而把它置于国内、国际等多个层面加以比对分析。事实上,伯顿的观点在历史学研究中早就被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近代奥斯曼帝国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本。
(一)东方问题的相关研究
例如马里奥特(J. A. R. Marriott)在1917年出版的《东方问题:欧洲外交史研究》,“是第一部整体研究东方问题的主要专著。直到现在,它仍然是综合和理论方面唯一详尽的著述”。该书把“东方问题”划分为三个层次:巴尔干半岛的各个民族是相关纷争的当事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沙皇俄国是相关纷争的外部参与者,英、法、德等其他欧洲列强则是相关纷争的积极介入者。“东方问题”既不只是巴尔干民族的问题,也不只是土耳其和俄罗斯、奥地利的问题,更不只是其他欧洲列强的问题。巴尔干民族矛盾既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政,又是欧洲国际冲突或大国协调的目标。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改革很可能挑起巴尔干民族的纷争,巴尔干民族的纷争又会引发欧洲列强的介入,欧洲列强的介入又反过来刺激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改革。“东方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它能够把这些截然不同的层次勾连到一起,从中折射出欧洲政治最复杂的一面。
马里奥特由此概括了“东方问题”的六个核心议题:一、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二、巴尔干半岛的分离主义;三、土耳其海峡;四、俄国对地中海的渴望;五、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对于东南欧的兴趣;六、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这六个议题详尽地展示了“东方问题”的不同面向。正如西方学者所言,该书分析角度的层次性与核心问题的明晰性,使得它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通史性著述,今天对该主题进行通史性研究的基础。……因为马里奥特的丰富著述为后来大多数对东方问题的解释,建立了模型”。
在此基础之上,“安德森(M. S. Anderson)的后续研究《东方问题(1774—1923):国际关系研究》(1966),更新了马里奥特全面综合学院研究者的方法。”但马里奥特和安德森仍然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即他们受到许多现实条件的限制,对于“东方问题”的研究主要依赖英文材料,使用的俄文材料少之又少,更不用说巴尔干各民族的资料了。“尽管马里奥特和安德森都融入了一些本土和俄国的声音,但他们都主要是从英国外交和政治的角度来分析东方问题的。他们的作品很少涉及那些生活在俄罗斯—奥斯曼边疆广阔空间中的人们的经历,从巴尔干到高加索,在这里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案最令人印象深刻。”
简言之,马里奥特、安德森等人的研究属于传统西方外交史的范畴,既不属于俄罗斯东南欧问题研究,也不属于巴尔干、外高加索的地区研究。后两者恰恰是当今西方学界对于“东方问题”的研究重点。例如约翰·戴利(John Daly)就在他的著作《俄罗斯海上力量和“东方问题”》中特别选取从1827年第八次俄土战争前夜到1841年《伦敦海峡公约》签订这个时间段,考察俄国海军政策对于东方问题的影响。
按照戴利的思路,1828年的第八次俄土战争起源于1821年的希腊民族独立战争,正是巴尔干半岛的民族独立运动刺激了俄国海军扩张的野心,这种野心又转化为俄土两国的战争,最终各方通过欧洲大国协调机制确定了土耳其海峡的封闭原则。这个原则又为后来的克里米亚战争埋下了伏笔。可以说,戴利延续了马里奥特多层次的优点,并以某个特定时间段的俄国海军建设为切入点,部分地补足了马里奥特等人俄国方面材料不足的缺陷。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东方问题”研究,都必然会以英俄对抗为背景,并涉及“中亚问题”。对于绝大多数研究来说,“东方问题”和“中亚问题”是通过英俄对抗联系起来的,但它们本来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然而唐纳德·布洛克汉姆(Donald Bloxham)研究的对象,既是“东方问题”,又是“中亚问题”。
奥斯曼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教逊尼派帝国,其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却信奉基督教。这个民族既心向欧洲,又具有浓厚的中亚特点。换句话说,沙俄帝国既通过亚美尼亚人挑起奥斯曼的内部纷争,又通过亚美尼亚人渗透中亚。布洛克汉姆关注的是,土耳其人在历史上曾对亚美尼亚人有过多次大规模的屠杀,这种屠杀行为又成为欧洲国际关系的议题。一方面,英俄两国从道义和宗教情感上都同情惨遭杀戮的亚美尼亚人;另一方面,它们在“东方问题”和“中亚问题”上的现实斗争又限制了这种同情。这本题为《种族灭绝的大博弈: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毁灭》的著作,既是对奥斯曼帝国境内民族的民族史研究,又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欧洲国际关系史的重要视角。
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汗牛充栋,数不胜数。相比较之下,国内对于“东方问题”的研究则显得颇为稀少,主要方向也集中在马里奥特等人关注的西方外交史层面上。相较于马里奥特的通史性研究,国内的讨论主要围绕着某些具体事件展开,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东方问题”的起源;二、19世纪英国、俄国、德国围绕“东方问题”的外交史。除此之外,亦有少数学者探讨过“东方问题”在20世纪的延伸和结局。尽管如此,这些为数不多的讨论仍然为本书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不过,有别于国内的既有成果,本书恰恰要回到马里奥特“综合研究和理论分析”的道路上去,但重点考察的不是欧洲国际关系史,而是欧洲国际冲突和大国协调如何通过“东方问题”作用到“中亚问题”,进而影响中国边疆。可以说,本书需要综合和提升的地方不是欧洲内部的列强关系,而是欧洲边缘与亚洲腹地的关系。显然,这种关系是通过英俄冷战建立起来的。
(二)中亚“大博弈”的相关研究
不同于“东方问题”,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一开始并不是以国家面貌进行的。“中亚问题”首先是探险家和基层军官的事情,直到克里米亚战争以后,整体性的国家意志才直接介入进来。因此学术界对于英俄中亚对抗的研究也具有两种不同的路径,要么侧重探险家和基层军官,要么侧重国家意志。这两种研究对于“中亚问题”的起点也有不同的看法。
英国军官亚瑟·康诺利中尉曾在1829年秋天第八次俄土战争结束的时候,从莫斯科出发,沿途秘密考察了高加索地区、波斯、阿富汗,历尽艰辛,于次年底返回印度。英美学者关于“大博弈”的讨论,多以这次考察作为起点。他们或是往上溯源至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俄关系,或是干脆不往上追溯。例如2015年翻译成中文出版的霍普柯克(Peter Hopkirk)《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一书,就以康诺利为起点,再将背景溯及拿破仑战争时期。
然而康诺利考察之时,英俄两国还是名义上的盟友,这次考察虽然目的是了解俄国的军事动向,但还不能被称为英俄对抗。俄国人首次就英国人渗透中亚表示不满,要等到1834年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秘密出访阿富汗和布哈拉汗国,也正是这次出访对后来英印政府的中亚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故万伯里(Arminius Vambery)认定伯恩斯的访问,才是英俄中亚对抗的起点。
无论是康诺利还是伯恩斯,其研究都是以参与“大博弈”的探险家作为研究英俄中亚竞争的考察对象的。与这个视角不同,谢尔盖耶夫(Evgeny Sergeev)则把英俄“大博弈”的起点定在了1856年,即克里米亚战争结束的那一年。他的理由也很明确:自1856年起,俄国正式开启了兼并中亚的进程,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对抗因此迅速上升到中央决策层面。
相较于上述两种不同的看法,埃德沃兹的观点较为折中,他把“大博弈”(the Great Game,亦即“大比赛”)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从1829年康诺利的调查正式开始,结束于1842年英国第一次入侵阿富汗战争失败;1842—1856年为“中场休息”;下半场从1856年开始,全场结束于1907年《英俄协约》签订。本书也基本采纳了埃德沃兹的划分。
马里奥特曾说:“欧洲面临着一个‘东方问题’,从本质上说,这个难题未曾变过。它是产生于东南欧大陆上的,东、西双方文明围绕习俗、观念和前见的冲突。”“中亚问题”同样具有这些冲突,这些冲突可以表现为中亚汗国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表现为清朝与中亚汗国之间的矛盾。它们的存在又以英俄对抗为背景,或以清王朝内地行省和边疆藩部不同治理模式间的矛盾为背景。因此我们可以像马里奥特研究“东方问题”那样,把“中亚问题”划分为三个层次:浩罕、布哈拉、希瓦等汗国和波斯、阿富汗为当事人,清朝和沙俄帝国为外部参与者,大英帝国则为积极介入者。
并且我们还要考虑到,“中亚问题”在某些方面可能比“东方问题”更加复杂,因为这三个层次的相关者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例如清朝在18世纪后期还是“中亚问题”最重要的外部参与者,但在19世纪后半叶一度沦为看客。与之相反,沙俄帝国在19世纪前期还是积极介入者,在克里米亚战争后却成了直接参与者。这种变化正是“中亚问题”值得特别玩味的地方。
上述三个层次的相互作用和位置变化产生了四个核心议题:一、波斯势力范围;二、赫拉特之争;三、俄国吞并中亚与阿富汗北部边界划分;四、印度防务与亚洲同盟体系。它们共同构成了“大博弈”的主轴。
选自傅正《从东方到中亚——19世纪的英俄“冷战”(1821—190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8月
本书从19世纪帝国中亚“大博弈”的视角出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回望中国的全球视角。本书讲述了19—20世纪大变局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也为我们认识中国与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横向比较历史视野。我们注意到,在帝国主义全球扩张背景下与中国具有相同遭遇的土耳其、埃及等帝国,最终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本书为我们今天理解中国现代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意义,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视角。
——殷之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本书是一部具有强烈内外关系自觉的历史著作。傅正博士考察了从欧洲的“东方问题”到英俄百年“大博弈”的历史进程,展开探讨了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中的“海洋—陆地”命题得以发生的历史语境,描述和分析了作为20世纪开端的“亚洲革命”所致力于颠覆的支配结构。作为一个生动的寓言,本书更有助于读者理解中国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思考当代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的自我定位与未来走向。
——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
不理解美苏冷战之于社会主义中国的重大影响,就不足以谈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同样,不理解英俄两大强权在近东与中亚持续近百年的“大博弈”对于彼时帝制中国的强力辐射,我们也很难真正洞悉晚近中国为有效因应边疆危机而最终促就的倒逼民族国家建构的历程。这绝非一本旧题重炒、落于窠臼之作,而是立基于鲜明的问题意识,执持更为宏观的国际政治视角,重新阐释那段历史,并可给读者带来莫大智识冲击的一部力作:聚焦世界进入中国,使中国难以避免地进入世界的那个时代,只有将区域关系史与边疆政治史、中国史与世界史直接勾连,才能更为精准客观地呈现历史的全貌,进而更好地为当下中国大战略的勾画与铺排提供镜鉴。
————魏磊杰(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编辑推荐1
世界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冷战,当然要数20世纪后半期的美苏冷战。而在《从东方到中亚——19世纪的英俄“冷战”(1821—1907)》一书中,20世纪的美苏冷战被称为“19世纪英俄冷战的升级版”。英俄冷战的底色是对中亚地区的争夺,英国以英属印度为基准,俄国则从本土出发,力图将自己的势力渗透到中亚各国中。在19世纪,英国无疑是最强大的海权国,它的海上霸权直到19世纪末才遭受挑战;俄国的主要力量则在陆地上,尤其是在1856年结束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开始大规模兴建铁路,将势力延伸到亚洲各地。这引出了地缘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海洋—陆地命题。在这场冷战后期,海权论、陆权论先后出现,地理学家、政治学家们为此争论不休。但若置海陆之争于英俄冷战之中,结果则显而易见:英俄冷战的主要阵地不在海上,而在陆地,俄国占尽优势,步步进逼,英国则不得不取守势,始终处于防御状态。
然而,作者的关注不止于此。曾有人画过一幅波斯版的时局图:弱小的波斯猫被巨大的英国狮与俄国熊按在爪下。这生动地描绘了19世纪中亚国家受控于两大强国,乃至被来回撕扯的处境,联想至著名的清末《时局图》,能不令人心有戚戚焉?作者通过清朝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中亚国家的横向比较,将看似遥远陌生的英俄冷战与我们熟悉的近代史联系起来,让我们对晚清面临的国际局势有了更深的了解;作者更将晚清时期的“海防”“塞防”等朝堂纷争置于英俄冷战的大背景之下,考察列强势力对清朝的渗透与影响。书中殷切的现实关怀,对“历史学有何意义”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
◎编辑推荐2
世界史的一大阅读障碍来自其庞杂的知识体系,但《从东方到中亚——19世纪的英俄“冷战”(1821—1907)》却以清晰的脉络展现了这一时期的复杂局势。英俄冷战涉及众多国家,除了对抗双方,有在东方问题、中亚问题中处于焦点的奥斯曼土耳其、中亚三汗国、伊朗、阿富汗等,也有受到波及的晚清中国、英属印度等,更有因利益相关而积极介入的西欧列强。作者却能将这段历史细细梳理,娓娓道来,用颇具故事性的语言勾勒出一幅幅英俄交锋的生动画面,使人读来毫无晦涩之感。
“海防论”与“塞防论”之争早已为国人所熟知,然而,当我们将其放在英俄“大博弈”的背景下,就会发现其中处处是英国人的身影。英国通过赫德等在清政府任职的官员,以及《申报》等拥有巨大舆论影响力的媒体,为左宗棠收复新疆制造了重重阻力。
——编者按
“海防”与“塞防”之争:英国的渗透与操纵
一、“海防论”的由来
1871年,琉球国宫古岛岛民向日本萨摩藩上缴年贡的船队在返回途中遭遇台风,漂流至中国台湾东南部。船上69人当中,3人溺死,54人被台湾当地居民杀害,仅12人生还回国。等到1874年,日本政府突然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宣称琉球是日本属国,一则试图借机吞并琉球,再则以此为借口出兵中国台湾。
当年5月10日,日军登陆台湾屏东县射寮村,很快与台湾当地居民接战。这是日本政府自明治维新以来第一次发动对外战争,也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第一次重要的外交事件。清廷得闻奏报,一面命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配合恭亲王奕领导的总理衙门出面交涉,一面命令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督率福建水师赴台监视日军,又命福建巡抚王凯泰、福建陆路提督唐定奎率兵25000人备战待命。中日战争一触即发。
当年6月,清政府要求总理衙门出面交涉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那里,他在12日给好友,即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的去信中就说道:“日本人武力占领了台湾。中国已告诉日本,台湾是中国的,所以日本人现在要末(么)撤兵要末(么)开战,二者必居其一。”到了10月9日,清政府派遣福建巡抚王凯泰率兵赴台的消息传到英国国内,甚至有英国媒体报道:“中国已对日宣战。”当天赫德就在给金登干的电报中预言:“日本公使两星期后离北京,战争几乎确定无疑,如中国能抵抗最初的进攻,则可最后获胜,日本的成功取决于第一次打击。”
英国人显然不希望看到中日开战,让俄国坐收渔利。在这危急关头,驻华公使威妥玛奉命协调中日争端。在谈判过程中,日方不仅无理取闹,还利用清政府昧于西方国际法和外交规则的弱点,大做文章。据赫德的描述,9月30日,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在总理衙门辩论时理屈词穷,就大肆抨击西方的国际法学著作,例如瓦泰尔(Emeric de Vattel)的《国际法》和马滕斯(Klarl von Martens)的《外交手册》,意图回避国际外交惯例。但总理衙门对于这些惯例颇为生疏,只能回答:“十分感谢。但不管怎么说,台湾仍然是我们的!!”对此,赫德评论道:“日本人想使我们陷入一场国际法论点的争吵之中;而由于他们有一位法国法学家、一个李仙得和一座大图书馆,所以他们引用恰当段落的能力较强。我们避免讨论,只说:‘好吧;但台湾是我们的。’这就是今天的确切形势。”
但现实情况是,日本人之所以愿意坐下来跟清政府咬文嚼字,玩弄国际法条文,是因为他们的军队陷于台湾的山川沟壑之中,进退维谷,已不可能实现吞并台湾的野心。因此,1874年11月初,中日双方最终接受英国的调解。中国无端赔款50万两白银,还变相承认了日本对于琉球的宗主权,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威妥玛正是利用了这个机会,于中日签订协议之时,命令汉文秘书梅辉立(William Frederrick Mayers)前往天津面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公然要求清政府把伊犁割让给沙俄,把天山南路割让给阿古柏,承认天山为英俄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不得不说,他选择这个时机向李鸿章提出放弃新疆的要求,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不到一个月之后,即1874年12月10日,李鸿章上呈《筹议海防折》,挑起了“海防”与“塞防”之争,正是对威妥玛要求的最好呼应。1990年代后期,所谓“现代化史观”甚嚣尘上,许多学者抱着“不过正则不足以矫枉”的态度,肆意吹捧李鸿章,不仅将他举为中国近现代海军建设的奠基人,更称他为中国近代第一流的外交家。然而,李鸿章真的懂什么是近代外交吗?所谓近代海军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维护中国主权的目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保障李合肥个人的政治地位而建立的?王绳祖先生在1980年代初就曾敏锐地指出,所谓“弃塞防保海防”的实质,是李鸿章“阴谋扩大淮军系军阀的势力,与湘军系对抗”。十几年过去后,许多学者对于该问题的理解反而大大倒退了。
二、对于国防政策的舆论操纵
英帝国主义干预清政府外交国防事务,无非经由两个渠道:其一,通过操纵舆论,使“民情”倒向自己一方,给清廷决策者造成压力,甚至控制清朝大员的思想意志;其二,唆使在华有权有势的英国人出任清政府的决策顾问,为其制定政策方针。简言之,一则依靠新闻媒体,再则依靠英籍客卿。
仅就前者而言,正如恽文捷所说:“19世纪70年代上海和香港等口岸发行的中英文西式报纸是中国政界和知识界获取国际时事信息的重要渠道。”重要者,如英文《字林西报》《北华捷报》等自不必说,英国商人美查(Ernest Major)于1872年创立的中文报刊《申报》,尤以“英国投资人雄厚的财力、广泛的社会关系以及多样的信息来源,在江南地区拥有巨大影响力”。
从1874年11月威妥玛正式要求清政府承认阿古柏政权开始,《申报》就突然发表大量关于西北边事的文章,比如《论告贷》(1874年11月30日第1版)、《译论中国告贷事》(1875年1月23日第1版)、《译字林新报论中华新行告贷一事》(1875年3月15日第1版)、《论新报言土耳其国事》(1875年8月9日第1版)、《续述土国负债》(1875年12月14日第1—2版)、《论借饷征回事》(1876年3月3日第1版),等等。这些评论当然不会直接说阿古柏如何如何仁慈,新疆群众如何如何安居乐业。它们无一例外地抓住了清政府收复新疆最大的障碍,即军费问题。
左宗棠为了筹集远赴新疆的粮饷,曾通过胡光墉等人向上海的外国银行借款,以解燃眉之急。此时《申报》就大做文章,宣称英国等西方强国靠向外放贷发家致富,清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后患无穷。这些文章甚至拿出土耳其的例子,宣称土耳其因告贷而不堪重负,饱受西方列强凌辱。试思,中国国力相比奥斯曼帝国如何?倘举债西征,其后果较之土耳其又如何?
这些言论看似客观公正、科学合理,但其议题设定已经决定了它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西征耗费财力,不如放弃新疆;一旦清朝陷入债务陷阱,届时国家分裂、民族受辱,危害远较失去新疆为大。讽刺的是,二十几年后,当各国银行团争先恐后向清政府大举放贷时,《申报》又转而鼓吹“借款强国论”了。究其实质,正如刘增合教授所言,“光绪二年前半年,是左宗棠运筹举借外款的关键岁月。这期间,《申报》为阻止西征借款而转载和撰写的社论呈现一边倒的倾向,……其间甚至编造和传播谣言,该报通过转载外电消息,散布朝廷举借外债数额高达2000万两,担忧平定新疆叛乱之役将会拖垮中国财政,……通过营造阻借舆论,冀能最大限度影响清廷的决断”。
彼时中国新闻媒体行业尚且一片空白,这给了英国殖民势力自由发挥的广阔空间,《申报》之类的英资报刊几乎控制了中国人了解外部信息的一切渠道。其力量之大,甚至左右了各部重臣和封疆大吏对于形势的判断。例如刘增合教授就曾仔细对比过《申报》社论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山西巡抚鲍源深、刑部尚书崇实等高官的“弃疆”奏疏:
基本可以证实,崇实、李鸿章、鲍源深三位参与决策的督抚和部臣,在奏疏信息来源、观点模仿和逻辑借鉴方面,《申报》社论(包括该报关于西北战况的负面报道)明显具有向导性和启发性,李鸿章奏疏中干脆称,自己是屡屡参考“外国新闻纸”和“西路探报”,这显然包括为《申报》提供社论、战况消息的《字林西报》《晋源西报》等英文报纸,由此推知,中文报纸《申报》起到了展转中介的作用,它将英方背景的各类英文媒体与清廷大员的决策行为、决策方向联结起来,旨在影响朝政决策走势。
除去借款一事以外,《申报》等英资报刊也十分善于在战况上大做文章,如遇西征清军行动稍有迟缓,便不惜造谣生事,宣称清军无力收复南疆,不如就此罢兵。李鸿章自不必多言,沈葆桢、丁日昌等人也多依据《申报》社论,要求清廷放弃新疆。
左宗棠就对英国人操纵中国舆论以阻挠西北战事苦恼不已,“尤对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等东部大员动辄搜罗报纸言论,据以入告内廷的行为,十分愤慨”。他曾多次在书信中抱怨英人居心不良,“东部诸侯”误听误信。例如他在1875年给前任浙江巡抚杨昌浚的一封信中说道:
洋事坏于主持大计者自诩洞悉夷情,揣其由来,或误于新闻纸耳。此等谬悠之谈,原可闭目不理,无如俗士惟怪欲闻,辄先入为主。公谓忌之者多,不知忌之者尚托空言,此则以无为有,足惑视听。江浙无赖士人优为之,处士横议,托于海上奇谈,都人士遂视为枕中秘矣。所系在颠倒是非,辩言乱政,不仅江浙一时之害。
杨氏为官浙江时,曾鼎力襄助左宗棠平定西北,不想此时《申报》竟然利用杨乃武一案多方炒作,促使清廷将其革职。这也让左帅见识到了西方媒体如何制造热点,以达成其目的。
又如,左宗棠此时也提醒两江总督沈葆桢千万留神报刊舆论:
吴越人善箸述,其无赖者受英人数百元即编新闻纸,报之海上奇谈,间及时政。近称洞悉洋务者,大率取材于此,不觉其诈耳。
他在给台湾兵备道吴大廷的信中,索性直接点名批评李鸿章鼓吹的弃疆之论全部来自《申报》造谣:
《申报》乃称回部归土耳其,土耳其已与俄、英通款贸易,中国不宜复问!合肥据以入告,并谓得之亦不能守,此何说也?《申报》又云,弟与金和甫军进喀什噶尔,数战未能取胜。金军现在古城、济木萨,其地是准部非回部;弟在兰州,因办粮运、待协款,别部屯田哈密,前行尚屯关内,何曾越吐鲁番、辟展、乌什诸城以规喀什噶尔乎?此等风谣从何而起?岂庸妄者流授之意也。
按照事前战略规划,金顺率军经古牧地、乌鲁木齐,进取玛纳斯,主要负责北疆,根本不曾前往喀什噶尔,《申报》居然造谣其在喀什噶尔连吃败仗,可说完全不顾事实。偏偏李鸿章居然对这等小报造谣深信不疑,“据以入告”,诚令人担忧。
这些论述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英国人如何善于利用现代媒体技术,操纵一国政治。但像左帅这样了解现代舆论奥秘的清廷大员,又有几人呢?
利用“筹款问题”大做文章的当然不只《申报》主笔,更有堂堂英国驻华公使。或者可以说,《申报》舆论只是在配合威妥玛的行动。当初李鸿章甫一挑起“塞防”与“海防”之争,就受到了威妥玛的关注。他设法获取了相关讨论的全部奏折,对其仔细加以研判。精明的英国公使很快发现,影响左宗棠西征的最大障碍就是“财政困难”。他将这些奏折的副本以“1876年1月12日第10号发文”之名寄往伦敦。自此以后,利用借款打压左宗棠西征,就从报刊舆论上升为外交政策。
在威妥玛的精心安排下,福赛斯于1876年4月8日在天津与李鸿章会晤。在李福之会两天前,威妥玛曾写过一封长信给福赛斯,暗授机宜。威妥玛在信中指出,“左宗棠西征最致命的难题是缺乏军费”,根据他的估算,西征新疆每年需要开支军饷500万英镑,“还必须在俄国交付战争物资3个月内向其支付硬通货”,而各省协饷所得共计“约900万英镑”。折算下来,左宗棠还需要自行筹集300万英镑的款项,其中半数可以通过关税获得,另一半就不得不向列强借款了。威妥玛建议福赛斯从此点入手,说服李鸿章放弃新疆;如有可能,再说服李鸿章上奏朝廷,建议与阿古柏结盟,共同抵御俄国。
然而,这项问题事关重大,李鸿章不敢轻易答应福赛斯。于是威妥玛决定进一步就借款问题施加压力。1876年3月10日,英国领事馆就上海洋行借款一事照会总理衙门,声称在“马嘉理事件”解决之前,领事馆会阻挠英国商民向中国提供借款。“这些照会,是威妥玛为解决马嘉理事件而掀起的外交讹诈和战争叫嚣的一部分,在实际利益上,也符合英方对新疆的一贯政策。”
从后续的历史看,威妥玛的策略显然发挥了作用,不特李鸿章顺从其意,上奏朝廷要求接受阿古柏成为清朝的属国,即令原先支持左宗棠的沈葆桢,也转而反对收复新疆。左宗棠曾愤怒地给其同乡帮办刘典写信:
昨接雪岩信,说威妥玛前此阻借,系由吴人怂恿。俗云家鬼弄家神也。沈幼丹前奏,或亦由若辈撺掇而成耶?不然何今是昨非乃至于此!
沪局新闻纸公然把持国政,颠倒是非,举世靡靡,莫悟其奸。而当事者不但不加诃禁,又从而信之,甚且举以入告,成何事体,可为浩叹!
寥寥数语,十分清楚地说明了《申报》是如何与威妥玛等英国外交官暗自勾结,干预中国内政的。
选自傅正《从东方到中亚——19世纪的英俄“冷战”(1821—190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8月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