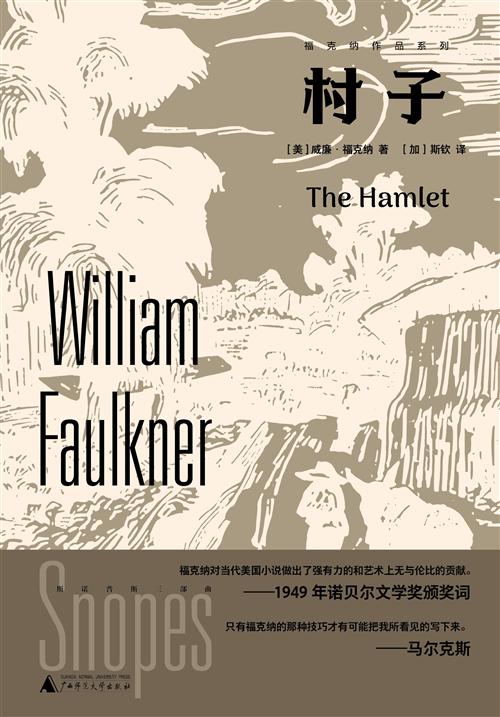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4-08-01
定 价:58.00
作 者:(美)威廉·福克纳 著 (加) 斯钦 译
责 编:吴义红
图书分类: 名家作品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文学/小说
开本: 32
字数: 290 (千字)
页数: 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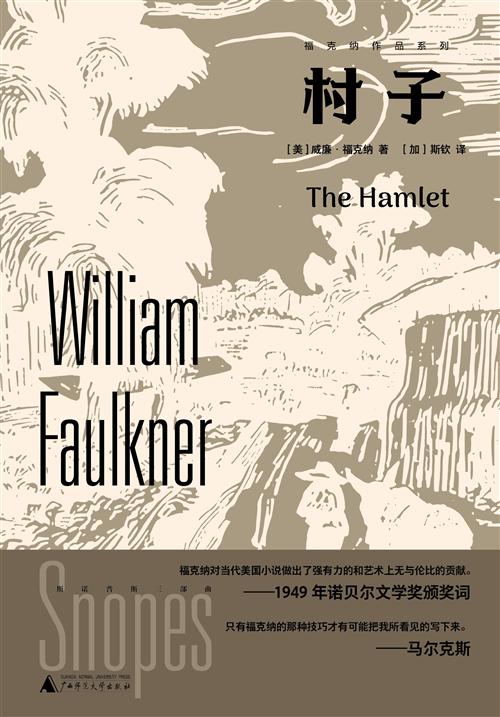
《村子》是福克纳“斯诺普斯三部曲”之首部作品,是福克纳后期的重要小说作品之一。小说以法国人湾乡村为背景,讲述了北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代表人物弗莱姆·斯诺普斯如何利用一系列狡诈和欺骗的手段逐渐从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方面征服了代表南方文化的村子法国人湾。小说在结尾处入木三分地描述了弗莱姆怎样把捕来的一群野马假冒驯马卖给当地居民,又把一块荒地伪装成有宝之地,高价卖给村子中的村民,然后离开村子进军杰弗生镇。作品风格简洁明了、干脆利落,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作者: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国文学史上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人物。1949年因“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福克纳以小说创作闻名于世,他为人熟知的诸多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讲述了发生在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故事,被称为“约克纳帕塔法谱系”。主要作品有《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圣殿》《押沙龙,押沙龙!》《去吧,摩西》等。“斯诺普斯三部曲”作为福克纳晚期作品,对“约克纳帕塔法谱系”的主题具有很重要的强化和升华作用。
译者:
斯钦,先后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以及加拿大的乔治布朗学院(George Brown College)和圣力嘉学院(Seneca College)学习,旅居海外多年。2018年至今翻译出版了《野棕榈》《婚礼的成员》《谁见过那风》《小镇艳阳录》《闲适富人的田园历险记》《伤心咖啡馆之歌》《两种孤寂》等作品。
目录
第一部分 弗莱姆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38
第三章 075
第二部分 尤拉
第一章 139
第二章 186
第三部分 漫长的夏天
第一章 229
第二章 293
第四部分 村民
第一章 377
第二章 466
无
福克纳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
——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只有福克纳的那种技巧才有可能把我所看见的写下来。
——马尔克斯
福克纳并不试图去解释他的人物,他只是描述他们的感觉,记录他们的行为。他们做出的那些事情是超乎常规的,但福克纳对于人物的刻画是如此真实而细腻,以至于你几乎不能想象他们不去做那样的事情。
——博尔赫斯
福克纳在技巧上取得的成就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自己的国家,去描写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
——略萨
《村子》以法国人湾乡村为背景,讲述了弗莱姆·斯诺普斯利用一系列手段逐渐征服了代表南方文化的村子法国人湾的故事,较为传统的叙事手法交织着作者独特的对意象、想象、象征等方面的艺术表现,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第一章
当弗莱姆·斯诺普斯第一次来到瓦尔纳的店里当店员时,尤拉·瓦尔纳还不到十三岁。瓦尔纳有十六个孩子,尤拉是老幺,是家里的宝贝。她十岁时身高就已经超过她母亲,不满十三岁已经出落得像个女人,胸脯圆润,一点都不像青春期女孩儿或者少女那种小巧坚挺的胸脯。她的模样很容易让人想到酒神时代的象征物——阳光下流淌的蜂蜜,丰收的葡萄在山羊蹄子的践踏下汁液四溅的场面。这女孩儿似乎是一个生活在真空玻璃瓶里等着慢慢长大的女孩儿,天生带一种只有雌性哺乳动物身上才有的与世无争的懒散劲儿。
这一点她和瓦尔纳很像,虽然懒散在瓦尔纳身上体现为一种优哉游哉打发日子的姿态,但在尤拉身上,懒散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不爱动弹的特点。还在婴儿时期她就很少活动,即便活动,范围也仅限于从桌子到床,从床到桌子这么一小块地方。她很晚才学会走路,有了摇篮车后下地玩耍的次数就更少了。那辆摇篮车是方圆百里第一辆也是唯一一辆摇篮车,既笨又沉,几乎和一辆狗拉车一样大。尤拉躺在摇篮车里被人推来推去,她一天到晚躺在这辆车里,一直长到伸直两条腿车子已经盛不下了,必须由一个大人很吃力地从车里把她抱出来时,父母才强制性地戒掉了她对这辆车的依赖。不能坐婴儿车后她开始依赖椅子,一天到晚坐在上面。也许这姑娘从小就已经明白自己哪儿都不想去,人生的每一阶段毫无新意,每个地方也和其他地方毫无二致,所以养成了走到哪儿都要人抱的习惯。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她五六岁。那时候她母亲不愿意把女儿一个人留在家里,走到哪儿都要带着,于是她跟着母亲去了很多地方,说得更确切点,她其实是被家里的黑人奴仆背着去了许多地方。母亲,她,和那个背她的黑人仆人的身影常常以这样一幅画面出现在大路上——瓦尔纳老婆身披披肩,穿一件星期天做礼拜穿的衣服走在最前面,她的身后是背着尤拉的黑人仆人,因为身上背着一个人,黑人仆人走得有点艰难,而他背上背着的那个长胳膊长腿、腿脚当啷着悬在空中的姑娘就像一个被劫持的萨宾妇女 。
家人给尤拉买了很多玩偶娃娃。她把它们放在自己座椅旁边的椅子上,很少搬来搬去。玩偶们大同小异,看模样几乎没什么差别。瓦尔纳让铁匠仿照尤拉一到三岁时坐的那辆摇篮车的样子另外给她打了一辆小型摇篮车,专门让女儿放玩偶娃娃。新的摇篮车做工粗糙且看着一点都不轻巧,但对住在法国人湾的村民来说这是很了不得的事,因为以前他们可没听说过(更没见过)谁家会专门请人给孩子打一辆专门放玩偶娃娃的摇篮车!尤拉把娃娃全部放在那辆小型摇篮车里,自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守着,但她很少摆弄那些娃娃。一开始家里人以为她之所以对那些娃娃冷漠可能是因为智力发育迟缓,要不就是她还小,还没朝着女人的方向成长,可是不久他们就发现真正的原因是这孩子根本不愿意动弹一下。
从一岁到八岁这段时间她几乎是在椅子上度过的,只有吃饭或者全家大扫除这样的事情才会让她从椅子上下来展展筋骨。在瓦尔纳太太的要求下,瓦尔纳让铁匠给女儿打制了几件迷你版的家庭用具——几把小扫帚和墩布,一台小铁炉——希望女儿可以用这些东西学习一下持家的本事,顺便多走走路。可是当他们把这些小东西放在她眼前时才意识到,这就像是给一个老酒鬼端来一杯冷茶,毫无作用。她很少找人玩,也没有形影不离的女伴,她似乎也不需要她们,在其他女孩儿身上常见的,为了团结起来对付和她们差不多大小的男孩儿或者大人而彼此之间形成的短暂亲密关系,在她身上从来都看不到。她只是懒懒地待着,样子让人想到待在母亲子宫里的胎儿。也许她出生时心智和肉体便彻底撇清关系,或者这两样东西根本不情愿结合在一起,所以选择了独自来到这个世界,而不是以相互陪伴来到世间并一同成长的方式;要不就是她的心智和肉体来到世间时已经发育得不对等,一方大一方小,大的把小的裹在里面。“没准儿这孩子长大了反而淘气得像个男孩子似的!”瓦尔纳这样说。
“长多大?”尤拉的哥哥乔迪说——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像是在冒火,很短,一闪而过。他就是这样,很容易被激怒。“像她这样长,哪个男人等她?等五十年吗?人不是橡树,可以等五十年,要我说没等到她缠上橡树,它已经烂了!被人当成柴火烧了!”
当尤拉长到八岁时,哥哥乔迪认为她该去上学,瓦尔纳夫妇也有这个打算,但什么时候送女儿上学,夫妇俩迟迟未定。瓦尔纳是村民推选出来的学校信托人(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瓦尔纳才不反对送女儿上学),是学校里说一不二的人物,甚至可以决定法国人湾学校的存亡。在那些已经当了爹妈的村民看来,这间学校早晚都会成为瓦尔纳家的产业,既然这样,他们觉得瓦尔纳把女儿送到学校上学是早晚的事,再不济也会让他女儿在学校里待上一阵子。瓦尔纳人精一个,收租子算利息时一毫一厘都不会让,他怎么会错过利用自己在学校的地位让女儿上学的机会?瓦尔纳老婆对女儿上学这事儿倒是不怎么上心,作为这一地区最会持家的主妇之一,她孜孜不倦地打理着这个家,收纳熨好的床单被罩,整理货架和储存土豆的地窖,在熏肉房里悬挂鲜肉条,其他人很难从繁重的家务活中感到愉悦,但她却乐此不疲。虽然嫁给瓦尔纳的时候她多少识几个字,但还达不到能够阅读整本书的水平,因为底子薄,所以四十年过去,她没有养成一丁点读书习惯,她更愿意从活人嘴里听到对事件、传闻和消息的描述,然后自己添加点议论或者从道德方面评判一下。在这个女人看来,女人识字纯属多余,光凭看书做不出一手食材搭配得当的菜肴,佳肴美食是从实践里来的,是通过搅动勺子以及品尝勺子里食物的咸淡磨出来的。一个认为自己只有去学校学习后才能算清楚家庭开支账目的女人,永远都不是一名合格的家庭主妇。
尤拉八岁的那年夏天,他的哥哥乔迪突然对念书这事儿重视起来,他强烈要求自己的妹妹去上学,但是三个月以后他后悔了,而且后悔得很厉害。他不是后悔说服爸妈让妹妹上学,而是后悔坚持让妹妹上学导致他付出了代价。这代价太大了,大到他一辈子都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尤拉从一开始就抗拒上学。不是因为上学就得和其他人待在一间屋子里而不想去,实际上她并不抗拒学习,这可以从她总共上了五年的学得到证明,不过,如果把她学到的知识折算成小时,再把小时折算成年月日的话,她从学校里学到的那点知识充其量可以折算成天数,而不是年月数。她抗拒上学是因为不愿走路,从瓦尔纳家到学校只有不到半英里远的路程,就这么一点路程,她也不愿意走着去。很多孩子住得比她远多了——他们的家离学校的距离是瓦尔纳家距离学校的三到五倍——但人家照样风雨无阻每天走着去学校,可尤拉不,她的理由很简单:不愿意走路。但她不吵不嚷,更不拳打脚踢又哭又闹地反抗家人的安排,而是不声不响地坐在家里的椅子上,脸上的神情像一匹倔头倔脑的小母马!而小母马的主人因为考虑到虽然现在这匹马因为年龄小还不值钱,但保不齐明年身价就一飞冲天,也不敢随便就用鞭子抽它。看见女儿这样,瓦尔纳大手一挥,劝自己老婆说:“那就让她待在家里!虽然在家她也懒得动动手指头,但看着别人干活儿也不是不能学到持家本事。反正我们也不指望她能为这个家做什么,只要她能平平安安地长大,找一个好心眼有本事的男人,跟着对方过日子就行!只要那人知道谋事儿,不给咱们和这个家惹麻烦就行,这比啥都强!如果女儿能找个有钱人就更好了!万一哪天乔迪吃不上饭了,沦落到去福利院生活的地步,还能指着他们拉他一把!她若是真找到一个有本事的男人,我和你就把房子、商店和家当交给他们管理,然后咱们两个放放心心地出去看世面去!最起码也得去一趟圣路易斯,到世界贸易大会参观一趟!如果喜欢的话,我们就买个帐篷,多住几天!”
乔迪还是坚持让妹妹上学,尤拉还是负隅顽抗, 理由是她不愿意走路。她坐在家里的椅子上,不哭不闹,像一个柔弱的小女人,在她面无表情的脑袋上方,是她又吼又叫、吵得不可开交的母亲和哥哥。最后母亲决定让家里的黑人仆人(小时候总是他背着尤拉跟着瓦尔纳太太走乡串亲,只是这一次不是背,而是用马车接送)接送女儿上学。于是每天一大早,黑人仆人赶着马车走半英里的路把尤拉送到学校,然后等在学校外面一直到下午三点学校放学把尤拉接回家里。两个星期后这个办法被喊停,原因是瓦尔纳老婆认为这种做法好比把二十加仑的水生生烧成一碗汤,浪费巨大。她对儿子下了一道命令,说如果他非得坚持妹妹上学的话就得自己承担起这个责任,并提醒他说既然他每天都要骑着马往返于家和杂货店之间,完全可以捎妹妹一程,先把她送到学校然后再返回杂货店工作。母亲的提议自然引发了乔迪的抗议,他对着母亲又吼又叫,声言自己不同意这么做。一旁的尤拉还是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但是之后的每个早晨,村民们看见尤拉手里拿着家里人给她买的油布书包坐在阳台上,等哥哥乔迪骑马接她上学。乔迪来到阳台边儿上,大声喊妹妹过来,尤拉站起身,走到阳台边缘,骑到马上。从此以后,接送妹妹上学的任务就落到了哥哥乔迪的肩上——他每天早晨把尤拉送到学校,然后回来做自己的事情,到了中午再去趟学校接她回家,吃完午饭后再把她送到学校去,之后他便等在学校门口,一直到下午放学再把妹妹接回来。一个月后,乔迪决定不干了,他告诉妹妹自己只负责从店里骑马送她回家,她得自己走从学校到商店那两百码的路程。他以为尤拉会反抗,但出乎意料的是,尤拉很爽快地答应了。可是乔迪的这个方案只施行了两天就作废了。第三天下午,尤拉一条腿着地被乔迪夹在胳膊底下拖回了家,刚进家门乔迪就冲到正在客厅里干活儿的母亲面前吼道:“难怪她答应得那么痛快!难怪她同意自己从学校走到店里!”他的声音因为生气抖得很厉害,“要是你每隔一百码安排一个男人在大路上站着,她肯定能同意自己一个人走回家里!她就是只母狗!只要经过男人身边,她就不安分了!离着十英尺远你就能闻到她身上那股骚味儿!”
“你少胡说八道!”瓦尔纳太太说,“少拿这种事烦我!是你非要她上学的!我养了八个女儿,个个都是正经姑娘!话说回来,一个二十七岁的单身汉比姑娘的妈还了解她的女儿,这话我也不是不明白!所以,如果你想让你妹妹退学的话,任何时候都可以,我和你爸不会反对。让你带的肉桂带回来了吗?”
“我忘了。”
“记着今晚带回来,我急着用。”
从那天起尤拉不再自己走着去哥哥店里,乔迪重新肩负起从学校接她回家的义务,两个人一周五天、每天四次骑着马在学校和家之间往返。一晃五年过去了,这样的场景似乎已经成了村子里必不可少的一道风景——乔迪怒气冲冲地坐在枣红马上,尤拉坐在哥哥身后,不管她的真实年龄是九岁、十岁还是十一岁,模样看上去都要比同岁的女孩儿大好多——从腿到胸到屁股都是大的,那具明显带着雌性哺乳动物特征的肉乎乎的身体和她身上背着的那个颜色花哨的小学生书包不仅不搭,还滑稽,让人觉得这样的孩子到学校接受教育简直是莫大的讽刺!她坐在哥哥身后,模样行为都像个吃奶的婴儿,让人不由得想到这具肉乎乎的身体似乎有两个生命,一个生命给她的屁股、大腿和乳房提供血液和营养,另一个生命蜗居在前一具生命里,前者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而它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避免麻烦,活得更舒适些。它对另一个生命的任何活动都不参与,这就好比一个人待在一所不属于自己的房间里,房子是别人设计好的,家具也是别人买好摆在里面的,就连房租也是别人付了的,而她只负责住在里面就行。接送妹妹上学的第一天早晨,乔迪本来想快马加鞭,赶紧交差了事,但是一种异样的感觉让他不得不坐直身体以躲避身后那具肉乎乎的身体。一路上他感觉自己不是在做穿过村子的直线运动,而是像太阳那样,在做一个浑圆的弧线运动。他只好让马的速度慢下来,坐在乔迪身后的尤拉一只手抓着哥哥裤子两条背带交叉的地方,另一只手紧紧抓着自己的油布书包。每次兄妹俩经过瓦尔纳家的商店都会看见商店门口聚集一堆人,经过小约翰酒店时也会看见酒店阳台上蹲着或坐着不少旅行推销员或者马贩子——有一天乔迪突然明白为什么他们当中有的人是从距离村子二十英里远的杰弗生镇来的——兄妹俩一般都会比其他孩子到学校晚,他们大部分人的家距离学校少说也有四五英里远。这些孩子穿着朴素,身上的工装服是粗布做的,脚上的鞋子一看就是大人穿剩下来的(这已经很好了,平时他们都没有鞋穿)。尤拉自己从马上跳下来,往教室走去,坐在马上的乔迪气呼呼地看着妹妹像个成熟女人似的扭着屁股的背影,心里不由得涌起一股冲动:他想冲进教室把老师(只因为他是男人)叫出来,警告他离自己妹妹远点。但是他又生气自己不能那么做,虽然他知道肯定早晚有那么一天,但至少现在不能那么做!打那以后乔迪每天十二点钟把妹妹接回去,一点钟送到学校,然后等到三点钟再把妹妹接回去。有一次走到离学校一百码远的一棵横亘在路上的大树(家里的黑人有一天晚上骑着马出去时差点被这棵树绊倒,因为树被旁边的树丛挡住了,当时他手里提着灯笼都没看见这棵树)边时,尤拉没坐好,摔了下去,当她站在那棵树上想爬上马时却遭到了乔迪的呵斥:“该死的!怎么就爬不上来?!这马又不是有二十英尺高!”
有一天他甚至头脑里冒出一个念头:她不应该跨着两条腿骑在马上。因为某一天他无意中往两边看时突然看到了妹妹那暴露在衣服和袜子之间的两条长腿,它们悬在半空中,丰满、浑圆,宛如天文台圆顶。其实他生气的不是她暴露身体的行为,而是她那种无所谓的似乎对自己袒露双腿的事一无所知的态度。他知道她并不是故意的,她只是不在意,如果她知道自己裸露的双腿会带给他人什么感觉的话,多少也会不嫌费事地遮掩一下。他知道对她来说,坐在一颠一颠行走的马上和坐在家里的椅子上没什么区别,和坐在学校的椅子上也没什么区别。这让他有时恨恨地想:她的屁股是如何承受那具一天比一天重的上半身的?在他看来,她不用说话,仅仅是走几步就已经能够吸引旁人去注意那具珠圆玉润的身体,他们看到她的模样,就认为她的心肯定也是五彩斑斓的。可是她从来都是安静地坐在乔迪身后,很少说话,但也不是哭丧着脸,那模样像在沉思,而且她思考的事情肯定和肉体无关。她周身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质,这种气质就连衣服也遮不住,而她作为衣服的主人从来都像是看不见别人投射过来的目光一样。
尤拉从八岁开始上学,一直上到十四岁那年圣诞节过后。她已经顺利完成了十四岁那年的学业,如果不是第二年一月的时候,学校突然关门,很可能她还会再继续待在学校上一两年学。学校关门是因为老师跑了,而且是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那老师一直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间租来的房子里,他在那间常年不生火的屋子里已经住了六年,走的时候不仅没领最后一个学期的薪水,就连他自己仅有的几件私人物品也没拿,更没有给任何人交代就离开了法国人湾学校。
老师叫拉巴夫,原本住在离法国人湾很近的一座县城里,有一次瓦尔纳去那个县办事儿时发现了他,于是请过来当了法国人湾学校的老师。当时法国人湾的学校已经有一个教师,此人虽是老师,但喜欢酗酒,常常喝得酩酊大醉来上课,而且这种习惯有愈演愈烈之势。女孩子们不尊敬他,是因为她们认为这老师无论是在教书理念,还是知识水平方面都不合格;男孩子们不尊敬他,是因为他们认为这老师的心思不是放在传授知识上,而是放在如何让学生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上——总之孩子们不仅不听他的话,还动不动拿他取笑,上课时课堂热闹得像古代罗马的乡下人欢庆节日,老师在孩子们的眼里宛如一头肮脏的掉了牙齿日趋无用的老熊。
因为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所以每个人,包括那位教师自己都明白下个学期他就不能在法国人湾的学校工作了。可没一个人关心如果没有老师,孩子们下一个学期就没法上课,学校就得关门这个问题。其实这所学校法国人湾的每一户人家都有份儿,他们出钱出力,包括老师的薪水也是每家每户出的,但是只有在家里的活儿不需要孩子们的时候,这里的人家才会把孩子送到学校读书。因为这个原因,学校每年只是在秋收过后到新一轮播种之前,也就是每年的十月中旬到第二年三月这段时间开门,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开学时间的不紧迫),找新老师的事儿一直搁置着,直到那年夏天,瓦尔纳去隔壁县城处理生意上的事儿时才敲定了新老师。那天办完事后天已经晚了,在招待他的人的邀约下,瓦尔纳答应住一晚再走。落脚的屋子坐落在一面光秃秃的山坡上,屋子里几乎没什么摆设,就连地板也是没有上漆打磨的糙木做的。屋子里没有生火,冰冷的壁炉旁边坐着一位嘴角叼着脏兮兮烟袋锅的上年纪的妇人,妇人的脚上穿了一双特别大的鞋,看鞋子应该是哪个男人的。当时瓦尔纳并没觉得有多么奇怪,直到转身看见一个十岁左右,身上穿一件虽然破旧但洗得干干净净的条纹棉布衣服的女孩儿脚上也穿了一双和那老妇人脚上一样的鞋子——如果非得要找出两双鞋的不同的话,只能说穿在女孩儿脚上的那双鞋比老妇人脚上的那双鞋看着还要大些——才觉得眼前这一幕有点奇怪。第二天早晨临出门时,瓦尔纳又看到了一双鞋子,鞋子摆在地板上,和老妇人脚上以及女孩儿脚上的鞋子一模一样!这三双鞋子和他以前看到的所有鞋子都不一样,不仅以前没见过,他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世界上还有这种样式的鞋子!他询问主人鞋子的来历,主人说那是双橄榄球鞋。
“什么?”瓦尔纳说,“橄榄球?”
“是的,橄榄球是一种比赛,只有大学里有。”主人和瓦尔纳解释,鞋子是他儿子小拉巴夫寄回来的,自打去年起,他的儿子开始在大学学习,现在已经完成了夏季一个学期的课程以及紧挨着的秋季课程的一半。作为一家之主的老拉巴夫对儿子想当老师的想法并不支持,在他看来,一家人靠经营农场生活,因为没有负债,日子过得并不差,另外这间农场早晚会归到儿子名下,所以儿子的这个决定没什么意义。但是小拉巴夫还是坚持要去大学学习。他去锯木厂打零工,是为了攒钱去大学开设的培养老师的夏季班学习。去年他去夏季班学习前和家里说好课程一结束就赶回来,帮家里收割庄稼,但是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儿子并没有回来,他来信说自己找到了另一份挣钱的活儿——“实际上那份工作比种地累!”老拉巴夫补充说,“可是孩子已经二十一岁了,他想干什么,我也拦不住。”——事情是这样的,小拉巴夫去年参加了大学里八个星期的夏季学期课程,他和家人说好八月课程结束后就回家,可是到了九月还没有回来。当时他们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他们除了担心他的安全之外还有点生气,觉得他不应该不回来,他回来还能帮着家里干点农活儿——比如采摘棉花、轧棉花、把玉米收回谷仓等等。九月中旬的时候他们收到了他的信,信里说他要在大学里多待一段时间,大概要过了秋季才能回到家里,还说他找到一份工作,所以没办法回来帮家里收割庄稼。信里并没有说那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老拉巴夫觉着儿子也许是在另外一间锯木厂找到了活儿干——他可没想到儿子这次是在学校找到的工作。到了十月,他们收到了小拉巴夫的另一封信,随信而来的还有一个包裹,包裹里包着两双后跟加了防滑条的鞋,看着和他们平时穿的鞋特别不一样。十一月初的时候他们又收到了一双相同式样的鞋。到了感恩节,他们又收到了小拉巴夫寄来的两双鞋。这样,前后总共收到了五双鞋,但家里住着七口人,所以这些鞋子其实是公共的,谁用谁穿,并不专属于谁,就像家里的雨伞,谁都可以用!哪双鞋空着,需要的人就拿来穿上,老拉巴夫这样解释。但五双鞋里只有四双是这样用的,剩下的一双鞋专门拿出来给了家里的老祖奶奶(她是老拉巴夫的祖母)。收到曾曾孙子寄来的第一双鞋后,老祖奶奶就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专属鞋,她从来不让别人穿这双鞋,而是自己穿着它坐在摇椅里,惬意地听着脚上那双上了防滑条后跟的鞋子踩在地板上发出的吱扭扭的声音。剩下的四双鞋大部分时间给孩子们穿,他们穿着它上学,到了家就脱掉鞋子给家里需要外出的人穿。一月的时候,小拉巴夫回来了,他给家人解释,说自己参加了大学里的球队,秋天那阵儿他一直在参加比赛,说球队的人要求他每年的秋季学期都得待在大学里参加训练或者比赛。他详细给他们描述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比赛,并告诉他们他寄给家里的那五双鞋都是学校发给他的。
“什么学校一下子发给学生六双鞋?”瓦尔纳问主人。
老拉巴夫说他也不知道。“也许碰巧去年他们手里有很多这样的鞋。”他说大学还给儿子发了一件深蓝色的毛衣,前胸上绣着一个大大的红色M,穿在身上很暖和。和上次一样,孩子们的老奶奶收了这件对于她来说尺寸显大的衣服,但是她只有星期天才穿它,把它当作她的教堂专属服,无论冬夏,只要去教堂就穿着它。一家人坐在马车上,老奶奶坐在老拉巴夫旁边的座位上,天气好的时候,太阳底下,那个鲜红色的M仿佛一枚红色的胸章,证明佩戴它的主人是一位不屈不挠、勇气可嘉的女人;天气不好的时候,它还是雷打不动地出现在嘴里叼着烟袋的老奶奶那佝偻干瘦的胸前,彰显出主人身上具有的一种临危不惧的气质。
“这么说那孩子现在还在大学里待着?”瓦尔纳说,“在打橄榄球?”
没有,老拉巴夫解释道,儿子想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仅为培养小学老师而设立的夏季班现在已经无法满足他对实现理想的渴望,所以今年夏天他没有去大学上课,而是在锯木厂找了份活儿,目的是多攒点钱,等到秋季开学时正式去大学学习一年的课程。有了钱,即使将来不打橄榄球他也可以继续待在大学里学习。
“他不是说他想当老师吗?”瓦尔纳说。
“那不是他的理想。”老拉巴夫说,“从夏季班毕业只能当小学老师,我说了您别笑话,他真正的理想是当州长。”
“不简单!”瓦尔纳说。
“我就知道您会笑话他的。”
“哪有的事儿?”瓦尔纳说,“谁敢笑话未来的州长?这样吧,你见到他时,告诉他如果他愿意把当州长的事情往后推个一年两年,利用这一两年的时间当个老师,他可以来法国人湾找我。”
和老拉巴夫的交谈是在七月,也许瓦尔纳根本就没指望小拉巴夫会来找自己要这份工作,但他再没有找人来填补老师的空缺也是真的。事情就这么一直耽搁着,但是村人们并不担心,因为他们觉得瓦尔纳不可能不管这件事!首先他是学校信托人,这件事他一定得管,另外他家不是还有一个闺女吗?那闺女也到了上学的年纪不是?!九月初的一个下午,就在瓦尔纳脱了鞋,躺在自家院子里那挂在两棵树之间的小吊床上优哉游哉地休息时,从外面进来一个人。虽然那是个陌生人,但瓦尔纳第一眼看到他时就已经猜到了对方的身份——这是个年轻人,身材虽不魁梧,但还算结实,一头硬硬的黑发宛如马鬃,高高的看起来像是印第安人的颧骨,一双不算漂亮的浅蓝色眼睛,鼻子较长,下勾的鼻尖让他的脸多了点盛气凌人的气质,薄薄的嘴唇表明这是个轻易不肯开口,不好接近的人。总之,这像一张法律人的脸,坚定不移,说出的每句话都是律法,是那种需要时可以不惜牺牲生命去捍卫原则的人。如果时光退回一千年以前,他应该是一个宁愿待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思考度过余生,也不愿搅和在人群中浑浑噩噩度过一生的人,而他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只是因为他无法按捺与生俱来的来自内心的渴望,和挽救人类或者不想看到人类遭受痛苦没有半点关系。
“我来是通知您一声,我今年没法来您这里教书。”年轻人说,“抽不开时间,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已经挣够了在大学里学习一年的钱。”
瓦尔纳没有起身,躺在吊床上说:“一年?那第二年呢?”
“我和锯木厂说好了,明年夏天我还去他们那里工作。即便去不了那儿,我也可以找其他的活儿干。”
“很好!”瓦尔纳说,“不过我是这么想的,我们学校今年十一月一号才开门,开学之前你完全可以在牛津镇的大学里待着,到了十一月你再来学校教书。开学后你可以把大学里要读的书带到这儿来读,这样不耽误你自己的功课。如果这段时间大学需要你打比赛,你可以随时回大学打比赛,顺便给大学看看这些日子你有没有落下功课。打完比赛后你再回到学校来,在外面耽误的这一两天也耽误不了孩子们的学习。我还可以给你提供一匹脚力好的马,从这里骑到牛津镇也就四十英里的路程,来回八个小时足够了!你爹和我说大学考试的时间在每年的一月,到那时你可以关上这里的学校,回大学参加考试,等到所有科目考完了再回来。到了三月,这儿的学校就可以关门了,那时你不管去大学学习还是做其他事情,决定权都在你,时间你自由支配,只要你愿意,在大学一直待到十月也没问题,十月以后再回我们这里来教书。如果你那么想上大学,四十英里的路程应该不算事儿,对吗?”
年轻人站在吊床旁边,一动不动,似乎和刚才相比没有什么异样,但眼睛睁大了。瓦尔纳还是躺在吊床上,不动声色地打量着面前的年轻人:身上的白衬衫一看就是穿了好多年的衣服,因为洗的次数太多已经薄得像蚊帐似的,窄巴巴的外套和裤子看着明显不是一套。虽然这个年轻人身上的衣服看着不合身,还是旧的,但洗得干干净净,瓦尔纳判断这身衣服应该是对方唯一一身比较正式的穿着,而他之所以给自己买这么一身穿是因为他懂得(或者是别人告诉他的)一个人不可能穿着工装裤去大学里念书的道理。年轻人并没有表现出回过神后欣喜万分的表情,也没有表现出谄媚讨好的模样,只是说:“好吧,我十一月一号来这里教书。”话音未落已经转过身去,似乎等不及要走。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