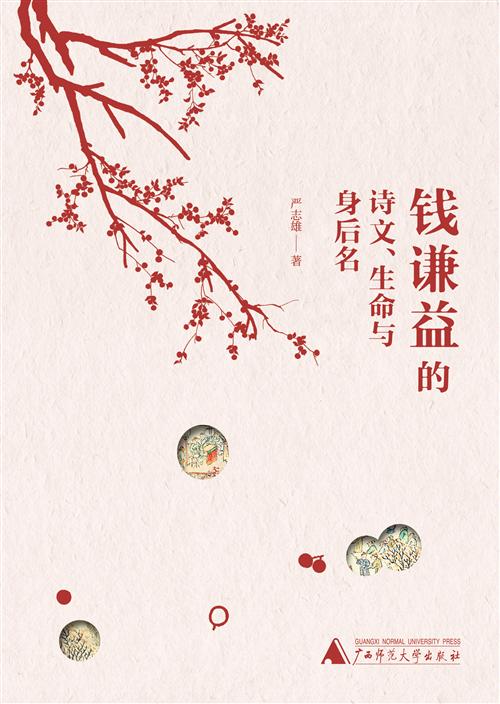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4-08-01
定 价:98.00
作 者:严志雄 著
责 编:赵英利
图书分类: 中国古诗词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文学/中国古诗词
开本: 32
字数: 310 (千字)
页数: 4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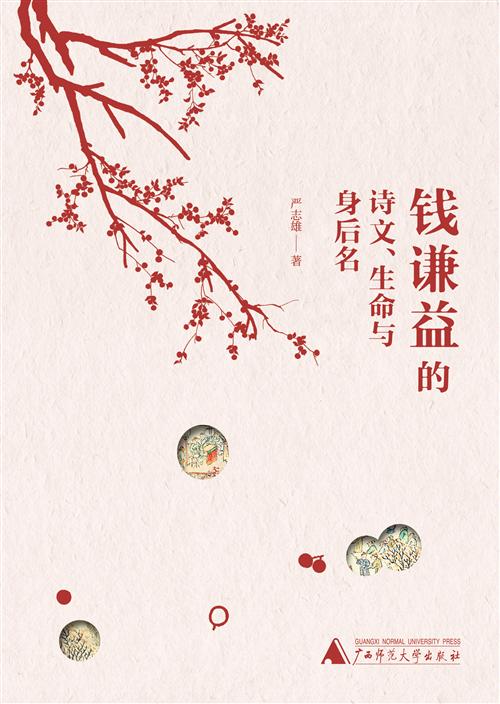
一本讲述十七世纪江南风雅巨擘钱谦益的精彩之作,围绕其诗文、人际交往、功过评说展开,通过解码他诗文中的典故、象征、隐喻,为读者还原了一个立体的钱谦益形象。
本书从钱谦益的诗文入手,讨论了钱谦益对竟陵派的攻排,与柳如是的《东山酬和集》,与王士禛、钱曾等后学的交往,以及逝世100年后乾隆仍禁毁其诗文等诸多议题。同时关注到了钱谦益诗文在海外的流传与影响,以及其诗文在清末民初的“复出”。作者综合运用文本细读、文史考证、人际关系分析等多种方法,其中蕴含了作者长期以来对钱谦益研究、明清诗文研究的深度思考。
严志雄(Lawrence Yim),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教授、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员、台湾清华大学合聘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诗文、文学文化、岭南文学等。专著有 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钱谦益〈病榻消寒杂咏〉论释》、《秋柳的世界——王士禛与清初诗坛侧议》、《牧斋初论集——诗文、生命、身后名》等;编有《千山诗集》、《落木菴诗集辑笺》、《瞿式耜未刊书牍》等。
(简要介绍:严志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教授、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明清诗文、文学文化、岭南文学等。)
导 论
第一章 钱谦益攻排竟陵钟、谭新议
第二章 情欲的诗学——钱谦益、柳如是《东山酬和集》窥探
第三章 哭泣的书——从钱谦益绛云楼到钱曾述古堂
第四章 清初钱谦益、王士禛“代兴”说再议
第五章 春秋有变例 定哀多微辞——试论钱谦益之论次丽末东
国史及诗
第六章 典午阳秋、休听暇豫——朝鲜文士南九万所述钱谦益诗
考论
第七章 钱谦益遗著于清代的出版及“典律化”历程
第八章 权力意志:清高宗乾隆帝讥斥钱谦益诗文再议
第九章 近代上海《申报》中钱谦益的身影
征引书目
通过文本想象作者
从符号、语言、主体的角度哲学性地思考作者、文本的本质意义,可以走到很远、很极端,譬如在福柯(Michel Foucault)那里。
很多年以前,我读福柯的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中译《知识考古学》)至其终章,看到福柯设计“作者”(the author)现身,与他争辩得面红耳赤,煞是有趣。作者亟亟捍卫自己的存在感、主体性、心灵、创造性,福柯则既残酷又温柔地以“话语”(discourse)的真相晓之以大义(其实是再一次宣布“作者的死亡”)。那几段文字太引人入胜了,乃至于从此就烙印在我脑海里。
……
其实,福柯给我最大的启发在于要给予文辞、语言系统足够的重视、思考、分析,以及要尽最大的可能探悉意义的所在、生成过程,包括显露的和被遮掩着的、可以理解的和不能理解的、能言说的以及无法言说的。要往语言内部曲曲折折地走一遭又一遭,也要借着文辞的意义“逆”其所连接的、外部的种种“话语”,见树又见林。拆散七宝楼台,又在那残金碎玉中呼唤起一应亭台楼阁,或空空荡荡。
也许福柯是对的,对于后之读者而言,文本中的“主体”“人的形象”无非是“言说的主体性效应”,而所谓“作者”,只是一个“功能”。但我仍然把这个“效应”“功能”称为“牧斋”,不觉得勉强。于我而言,“牧斋”带有足够的差别性、区分性,有着明显的个性特征、语言风格。在一些情况下,我可能会分不清谁是陈子龙,谁是杜甫,但我不会混淆牧斋、吴伟业、龚鼎孳,甚或与牧斋文字有着师承关系的冯舒、冯班、钱曾。就这一意义而言,“牧斋”具有明晰的身份与形象,甚或主体性。
文字中浮现的牧斋是文辞作用、成就的结果。经由写作主体的匠心独运、经营布置,以及文字系统内各要素的联系协调,这个“自我”(self)在文本记忆(textual memory)中的内涵相对统一,也相对封闭。在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y)中,“牧斋”的含义、形象却是多元的,也不无断裂、矛盾之处。要充分了解此中异同,有必要用别的以牧斋为书写对象的文本作为参照。这就到了牧斋研究最困难、最具挑战性的层面了。任何话语系统都带有自身的逻辑、知识、有效性,以及权力机制,而最强势的,莫过于政治话语、历史话语、道德话语。我们假如不步步为营,理智克制,一不小心就会走进泛政治主义、泛历史主义、泛道德主义那些尴尬、苍白的死胡同。明末清初的历史、政治、文化、文学、社会异常复杂诡谲、丰富多端,我们要全面丰富我们的知识,潜研细究,深思熟虑,才好发言,否则我们就不能真正开显牧斋文字的意义,没有跟牧斋对话,也没有真正了解那个时代。
过去一个世纪,牧斋研究在各方面累积了不少基础知识,现在或许是时候,朝更具反思性、开拓性,更深刻细致的方向发展了。这些年来研究牧斋,我深深体会到牧斋传世文字的珍贵价值,它是极高的文学成就,也是知识的宝矿。这已是学者的共识,就不必多说了。我比较困惑的,是如何从他的文字联系到他这个人。我在上面叨唠了一番关于主体、作者、话语的理论,读者大概会感到纳闷:这是一本研究牧斋的书啊,怎么就扯到那些莫名其妙的西方理论上去了呢?其实我是想走到一个极端(也是异端),换一个哲学的角度,去思考、去展示:谈论“人”,是可以多么的困难,多么的曲折,多么的是非莫辨,也多么的引人入胜。如果我们服膺于福柯的理论,甚至只能谈话语、文字符号的记忆,就不能说牧斋怎样怎样(因为牧斋先生根本就不在那里,别无的放矢了)。固然,福柯的理论没能让我完全心悦诚服,但无论如何,我的确也认为,我们的研究,应尽量顺应着文字、文辞、文本的脉络展开,那样才有可能进入牧斋的语言系统,才能揣摩这个主体的心思、感情。牧斋的内心世界非常丰富、复杂,他所身处的历史世界充满着美好与疯狂。我告诫自己,研究牧斋以及这个历史时段,要带着诚恳、开放的心态,多读书,多思考,不妄言。牧斋的文字非常迷人、蛊惑人,他的学问以博大见称,但也纯杂互见,我们要尽量尝试进入当时的知识、思想、情感世界,回到当初的历史现场,不盲从权威、成说,不妄作批判,努力焕发文本的记忆及生命力,再提炼出自己的见解。
最近偶然重读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看到一段话:“诗人在安排情节并用语言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应尽可能把剧中情景摆在眼前。用这种方法,就会生动地看见每件事情,好像他自己亲历了那些事件,他就能够找到适当的处理方法,不太可能漏掉情节矛盾的地方。”书写主体若然服从这要求,如此结撰,我们不妨也这样往里面走一遭,静心玩索剧中的种种情景,体会、思考其中的世界,然后才说点儿什么。
节选自严志雄《钱谦益的诗文、生命与身后名》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08月
作为十七世纪江南风雅巨擘,钱谦益为身后四百年的文学文化史留下漫长的投影。在笺释《投笔集》《病榻消寒杂咏》之后,严志雄教授转而关注牧斋投向他者的眼光及纠缠于其本人生前身后的诸般凝视:来自诗界后学的仰慕,来自风月红尘的窥探,来自征服者的鄙薄与戕伐,以及来自现代市民与职业史家的想象。牧斋诗文素称难解,而有关牧斋诗文“阐释之阐释”尤难。因为正如本书多次提到的:文艺圈是一个自律性的场域,文人用诗性的语言与世界迂回地交往,只有精准地解码那些典故、象征、隐喻所构设的文本表象,才有可能抵达文人心态史与生命史的实相。而在牧斋的文字迷宫中,有太多的“歧途”和因各种偏见“走失”的读者。作者与牧斋经年为友,由他来为我们指点迷津,应是再合适不过。
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所长 陈广宏
钱谦益为十七世纪江南风雅巨擘,其诗文曾因政治原因遭到禁毁,其人亦被清高宗乾隆列入《贰臣传》,职是之故,其人、诗、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私下流传,近乎是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晚清民国以降文禁稍松,钱谦益诗文通过刻印开始广为流传,然而诗文虽渐流传,解人却少,这与钱谦益博通文史、旁涉梵道,为文作诗又词雅意深、今典古典并用等不无关系,学问渊博如陈寅恪,曩昔作《柳如是别传》时尚且感叹“岂意匪独钱谦益之高文雅什,多不得其解”,可见理解钱谦益绝非一件容易事。
文本永远是我们进入“作者”最主要的凭借,其产生既有赖于“作者”的创造,也深受“作者”所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我们能从什么角度认识钱谦益呢?肤泛的道德批评并不能让我们增进一丝一毫有益的了解,最为稳妥、且最具备可操作性的应当是严志雄教授的《钱谦益的诗文、生命雨身后名》,既从文本细读入手,深入探寻诗文中“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同时注重还原文本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看见”钱谦益生前身后的故事。
情欲的诗学
明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仲冬,柳如是(1618—1664)访钱谦益(牧斋,1582—1664)于江苏常熟虞山半野堂。半年之后,钱、柳结褵于茸城舟中。柳随钱返常熟,钱为筑绛云楼于半野堂后,柳乃称柳夫人。嫁入钱门,柳氏结束将近十年的漂泊生涯。
前此,柳如是漂泊无定,迁转在吴越之间,直至虞山钱谦益之访,始寻得一生之归宿。其时,柳如是乃远近闻名的一代才妓,“从良”前在一艘画舫上不断移徙,目的,是寻觅一个可托付终身的男人。看来,柳如是较诸当时别的女性(如名媛闺秀),似乎拥有较多的自由,可以选择往来的方向、托身的对象。究其实,这自由与特权,却是丧失了正常社会身份地位始能获得的——柳如是是一妓女,寄身、活动于正常社会、道德、伦理价值体系的缝隙中。而且这一艘画舫,是无法自给自足的,每隔一段日子,它必须靠岸——靠近、进入男性主宰的世界——始能获得赖以存活的资源与补给。这船,不事生产,它与世界交易的,是欲望(desire),这欲望就是柳如是。这艘画舫,几乎可以视作柳如是的隐喻(metaphor)。而它在水中漂移时,是约翰·伯格(John Berger)所谓男性观看中的“景观”(a sight)吗?若然,它的身份构成,来自它己身的“观察者”(surveyor),而这“观察者”,又是一个“被观察者”(surveyed)。伯格说:“女性自身的观察者是男性,而被观察者为女性。因此,她把自己变作对象——而且是一个极特殊的视觉对象:景观。”在这样的理论导引下,我们会看到,西方裸体画中,裸女惯常以温顺或诱惑的目光睇视着画框外的观者(画像可能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买家)。这个看法,或可为我们提供思考柳如是现象的一个起点,但柳如是牵动的欲望纠结、权力运作,实则远远超过这种稍嫌简略的“观看之道”。
柳如是可以裸露身体,向观者投以温顺或诱惑的秋波,但这屈从的行为同时也为她攫取得操弄男性欲望的权力。柳如是是一个有情无情似真似假的颠覆。她偶尔“着男子服”,无视传统礼教对女性“性别”服饰的规范要求(而且还习武,有侠义之气)。除了姿容绝世,柳氏“词翰倾一时”,擅长诗词书画,富学识,精音律,通禅理。她与当时江南各地著名文不妨说,在当时构成一个文士身份的种种条件,柳几乎都具备。后来钱谦益有时称柳为“柳儒士”(柳如是的谐音),戏谑而外,不无道理,柳氏拥有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确实不亚于(甚或多于)男性文士。就某一意义而言,当时众多才人学士之所以倾慕于柳氏,是因为在柳氏身上看出某种自己,是自我认同(selfidentification)的结果;而柳氏所拥有的,甚或多于自己,于是他们出于对己身“匮乏”的焦虑,更渴望着柳如是。柳如是是一个“景观”,又大于、逸出于一个“景观”。欲望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是无穷尽的,难以餍足,方死方生,连圣人都只能以“节”“寡”规训,知道不能“绝”。
我们回到庚辰十一月,柳如是拜谒钱谦益那一天的现场吧。据钱氏门人顾苓(1609—1682后)的记载:
庚辰冬,(柳)扁舟访宗伯。幅巾弓鞋,着男子服。口便给,神情洒落,有林下风。宗伯大喜,谓天下风流佳丽,独王修微、杨宛叔与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许霞城、茅止生专国士名姝之目。
在这描述中,柳如是乘的是“扁舟”,小船,意味着柳如是离开了她的画舫、她掌控的资产、仆从、熟悉的环境,果毅地、神情潇洒地趋赴半野堂。(历史学家却可能会败兴地告诉我们,城里的水道,一艘画舫无法通过。此待考。)柳如是向钱谦益献上一首诗,目的,是奉承、诱惑他。此后半年,《东山酬和集》刊刻行世,集内收入钱、柳及钱之友人、门人唱和之诗文。《东山酬和集》是钱、柳的爱情结晶,也是一本欲望之书,镌刻着钱、柳环绕着爱欲的相互建构(intersubjective constitution),也见证着诗歌的语言、书写行为在这段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中所扮演的意味深长的角色。
节选自严志雄《钱谦益的诗文、生命与身后名》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08月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