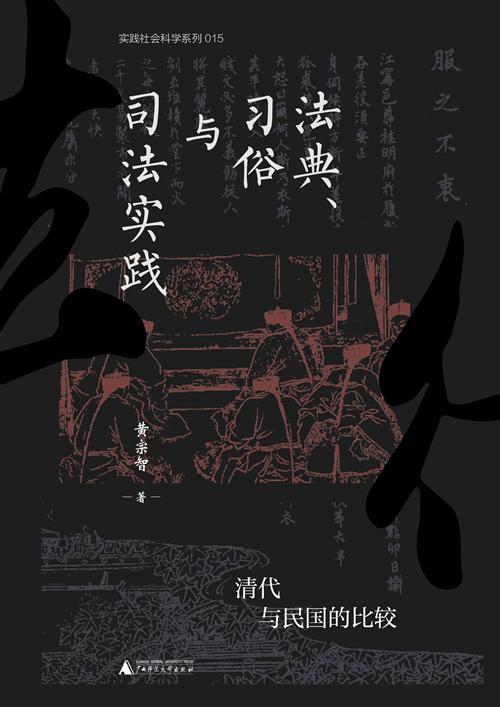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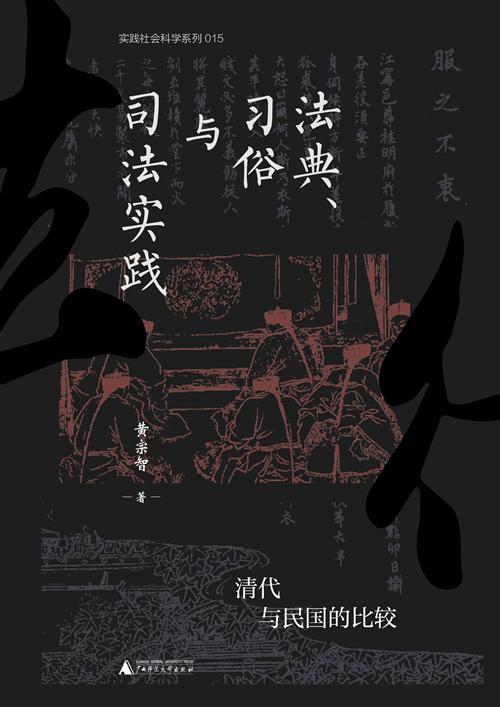
本书为黄宗智教授法律社会史代表作。全书基于大量文献资料,对清代与民国时期中国法律的修订过程做了细致梳理;又从巴县、宝坻、淡水-新竹等地诉讼档案出发,对其进行深挖,比较和还原了清代与民国民法处理户、婚、田土等民事纠纷的不同之处。作者从清代与民国的法律变化观察近代中国转型,全方位展现了清代与民国民事法律之种种异同,以及与社会的复杂纠缠。全书学术视野广阔,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吸收大量中外学者如马克斯·韦伯、瞿同祖、滋贺秀三等的权威成果并尝试与之对话。作者从“表达”与“实践”的角度切入法律社会史研究,深化了我们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解。
黄宗智,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1966年始任教于UCLA历史系,1991年晋升“超级教授”,2004年荣休。主要著作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获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等。
第一章 导论
议题与分析角度
过去的研究
对研究结果的几点说明
上篇 从清代法律到国民党法律
第二章 清末民初的民法:修订过的《大清律例》
清末法律改革
民国对经过修订的《大清律例》的援用
清代法典中的民事条例
清代法典的更改
第三章 清末民初司法制度的改革
晚清司法行政改革
贯彻新的法律体制
第四章 1929—1930年的国民党民法典
国民党法典的起草
从禁与罚到“权利”
资本主义对小农经济
男女平等
社会公正与矛盾倾向
习俗对成文法
下篇 清代与国民党民事法律制度的比较
第五章 典
清代的法典和习俗
清代的习俗与法庭行为
民国时期的典惯习
持续的问题
第六章 田面权
习俗中的佃权与所有权的起源
双层所有权的常规与语汇
成文法
适应与对抗
司法实践
第七章 债
生存借贷与资本主义信用
司法实践中的延续与新发展
法律和惯习间的拉锯战
第八章 赡养
民间惯习
习俗与法律
第九章 清代法律下妇女在婚姻奸情中的抉择
司法分类与相关的法律
清代的构造
司法实践与社会惯习中的变异概念
妇女作为受害者
消极自主的负担
第十章 国民党法律下妇女在婚姻、离婚和通奸中的选择
国民党法律下妇女的自主
实践中的妇女自主
第十一章 结论
清代法律和民间习俗的逻辑
清代的司法实践
向现代法律过渡
现代化的地方实践
附录
引用书刊目录
索引
表目录
编者按:《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是黄宗智教授继《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之后的第二本法律社会史代表作。最近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明显的本土化和历史化转向。在由《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合开展的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结果中,黄宗智教授“倡导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社会科学”位列其中。以下是黄宗智教授《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一书的“导论”部分。
导论
本书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从20世纪初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民事法律制度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与不变?提出此问题当然也是问什么是“中国”或“传统”,什么是“西方”或“现代性”,以及这些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另外,本书对“民事法律制度”或“民事法制”使用的是广义的理解。首先,在成文法律或法典之外,还包括司法实践。其次,是注意法律与民间习俗之间可能存在的背离,以及法庭如何在两者之间斡旋。最后,本书在法律制度之外,还注意当事人所做的抉择,目的在于弄清法律制度的变化在人们生活中的实际意义。
继上一本以清代为重点的著作之后,在本书中我原打算以1900年至20世纪30年代的过渡期为重点,侧重于清朝最后十年的法律改革及其向国民党民法与刑法典的转变。因而本书的出发点,是对清代旧法律修订过程的叙述、过渡期内施行的制度变革及新法典前后相继制定的多部草案。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要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不能仅考察过渡期本身。民事法律制度的变化要在对清末改革之前及国民党掌权之后的比较中才显得清晰。本研究因而逐渐演化为对清代与国民党民事法律制度的比较分析,主要集中在1860—1900年间与1930—1949年间的比较,超出过渡期本身。
这样一来,第一部分中有关过渡期的三章应当作全书的背景部分来读。过渡期内令人惊讶的是民法的延续,新的民国政府没有采用晚清政府以1900年《德国民法典》为范本草拟的新法典,而是继续使用清末修订过的旧法典。结果一部自称为刑法典的《大清刑律》中的民事部分,被出人意料地当作民国民法典使用了将近二十年。
与此同时,过渡期也显示了许多主要的制度变革,包括至1933年全国约半数县建立了西式的或“现代的”法院系统(至1926年国民党统治前夕全国约四分之一的县如此)。该法院系统内民法与刑法、县长与法官被明确分开(而不像以前的县令兼行政、司法于一身)。在1900年后的过渡时期里,制度上与行政上的变革实际上早于成文法的变化。
1929—1930年颁布的国民党民法典几乎完全模仿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但它与以往法典有根本的概念分歧:清法典视父系家庭为基本社会单元,国民党民法典以男女个人为中心。前者的基本经济逻辑是围绕家庭农场组织的、以生存为目的的小农经济,后者的经济逻辑是围绕合同签订者组织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基本的概念差异对本研究中深入探讨的所有议题都有影响。
议题与分析角度
本书无意进行清代与国民党民国法律之间所有差异的全面比较,而只注重那些与社会生活有最大关联的部分。我选择议题主要以档案案例记录中的诉讼频率为基准。这些议题内容分别归属于国民党民法典(总则之外)的四大编:“物权”编下的典卖土地与田面权,“债”编下的不履行债务责任,“亲属”编下的结婚、离异与通奸中妇女的“抉择”,以及“继承”编下的赡养父母。
对每一个案例我首先考虑清代法律与民国法律的不同逻辑。两者面对不同的社会秩序:一个是小农(虽然已部分商业化了的)社会秩序,另一个是资产阶级社会秩序。我比较两者的意图在于把一方作为另一方的参照面,以便揭示出两者的一些基本特性。
做这样的比较,重要的是要避免西方式的或欧洲中心论的先入之见。我们要自觉地批评那种现代西方对非西方的“他者”的优越性假定。从清代法律到模仿西方的国民党法律的转变,并非像某些大陆学者坚持的那样是由落后的封建法律向资本主义法律的简单转变,也不是由非理性向理性、由实体主义/工具主义者“卡迪法”向马克斯·韦伯所谓现代法的转变,或由假定的中国没有民法到开明采用现代西方民法的转变。从一开始我们就要摒弃此类直线发展的、欧洲中心论的看法。
然而我们也不应走向坚持“中华帝国也有”的另一个极端,不应给我们自己提出任务去证明清代法律也具有合同与市场关系的资本主义因素,或清代法律也具备韦伯式的理性,或中国也有西方民法的传统。对这些问题更详尽的讨论,参见黄宗智,1996,第一章。这种论点根本上与上述论点同样唯西方独尊,与正宗的现代化理论并无不同,因为它假定现代西方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标准。
我们需要问的是一方如何使另一方显得更清楚,而不是假定(无论多么含蓄)此方或彼方的优越性,或试图坚持它们完全等同。我们的目的应该在于阐明两者的内在逻辑与囿于文化的不同特性。在好的比较中,任何一方都应成为使相反方更清楚的参照。
不过我们同时也不能止步于仅仅把两者简单对立。国民党法律不是其德国范本的副本,它是以晚清草案为蓝本、经连续两次修订的产物。这些修订在某些重要方面使其更切合中国的既存习俗与现实,在其他方面则引入了更进一步的根本性改变。
考虑到这点,国民党法典史很像广义的中国近现代史。它一方面以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为基础,我们中的许多人的确是以中国与西方开始全面接触为准线来划分中国近现代史的。但这种接触的结果并不仅仅是任何由此及彼的简单变化。另一方面,本土文化在近现代史中不仅是传统与现代间的一种对照与抗争,也是两者间的一种协调与适应。
国民党的立法者们提倡既从旧的、也从新的法律中进行选择,他们甚至提议合并二者以创造一个不同的东西。他们努力的最终目标在于形成一个将以个人为重点的法律融入以社会为重点的法律的综合体,他们草拟的新法典意欲成为、也需理解成包含两种文化的混合体。
此混合体特别包含了成文法意图与惯习之间的双向影响。国民党民法典应被视为一部多层次的文本,不仅包括借鉴自德国范本的概念构成,也包括选择性地保留了习俗与清代旧法律的某些方面。其中大部分仅被吸收为实用条例,不带意识形态色彩,但少部分在概念上依然一仍其旧,有些甚至与新法典的主干概念框架背道而驰。
对两部法典的比较因而牵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概念构成上清代法典体现出的传统中国与新法典表现出的现代西方间的对照,另一方面是让法律适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渐进过程。要理解从清代到国民党时期成文民法的间断和延续,概念构成的对照与适应过程两者不可或缺。
除了成文法的概念构成,本书还考察法律的社会背景及其实际运作。这也是我在“民事法律体系”一词中所表达的意义——以区别于范围较窄的“民事法律”或“法律”(我指的是成文法)。我有意将“民事法律体系”解释成既包括成文法、民间习俗,也包括司法实践。经过对多部法典的分析之后,我的下一步考虑是把它们放在民间习俗的背景中。
在这里可以指出,有关习俗是或应该是所有法律的来源的假定,亦即英美传统的普通法的内含原则,不该硬套于中国。清代及民国法律有时维持、默许,但有时也明确地反对习俗。不考虑国家立法而将习俗与“习惯法”等同是不对的。陈张富美与马若孟(Ramon Myere)以假定清代为西方古典的自由主义放任国家作为其出发点。他们进而认为清代经济增长的根源在于由习惯法支持的组织基础。在他们看来,“国家很少积极地管理习惯法”,尽管它“经常明确地承认各种私立合同”(1976:3)。这样一种假定前提导致他们忽视了国家对习俗与民间做法的压制,例如土地的一田两主制及婚姻中的妇女买卖(见chen and Myers,1978:17—27)。
同时我们要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假定习俗与国家成文法之间只存在对立。梁治平在其1996年的清代“习惯法”研究中同样没有适当考虑成文法。像马若孟与陈张富美一样,他至少含蓄地把太多的自治与权力赋予清代习俗。他的基本信念似乎是这样一个政治信念:要在习惯法中发现(英美式?)多元化政治的空间,反对专制主义国家权力。虽然我基本同意梁的政治观点,但我认为他在两种法律传统间强行画这样的等号是不对的。清代法典不时维持或迎合习俗,而民国民法典通过连续两次的修订也达到了如此效果。分析成文法与习俗之间的关系,需要考虑到特定的法律条文与特定的时间。
有清一代,法律与习俗在继承和债务方面基本一致,在典卖土地和妇女买卖方面则表现为法律逐渐适应社会现实。但在田面权、妇女抉择和养老的某些方面,法律与习俗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矛盾也许是我们研究中最有意义的部分。
民国时期,由于在中国社会实际之上强加了一部高度洋化的法典,可以预料法律与习俗之间的差距拉得更大了。我们因而可以看到本书中研究的所有议题都存在法律条文与民间习俗的明显背离。在典卖与债务领域,立法者最终让模仿德国的法典与习俗更趋一致。而在其他领域如田面权、妇女抉择及继承问题上,法律条文与社会实际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
把法律放在习俗背景下考察,有几重目的。凡是双方一致的地方,留意二者有助于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这可能是不那么明显的逻辑。法律文本特别有助于弄清楚民间做法中未予明言的假定与基本原则,而民间做法则可能使法典中不那么显而易见的东西表露出来。清代的债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凡是法典与习俗不一致的地方,各方在概念化与行为方面都可能使对方显得更清楚。如田面权习俗即带有清代、民国法律都不允许的一种产权逻辑。习俗与法典间的这一直接对抗有助于揭示两者截然不同的产权概念。
另外,同时留意法律与习俗双方有助于确定研究司法实践的背景。我这里用“司法实践”一词,指的首先是法庭的具体行为,其次是法典中纯实用性的规定(相对于意识形态思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典与习俗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双方是基本一致,还是不断冲突或完全背离。
凡法典与习俗一致的地方,法庭行为可能主要是依法行事。在这种情况下,案件档案记录告诉我们的是哪类争端如何及为什么最易引起诉讼。它们表明法典在实际生活中的真正含义。
凡法典与习俗存在不断冲突或完全对立的地方,法庭判案可能会演绎出多种不同的类型。法典本身可能默认习俗的存在,有时这会有悖其主干概念框架,就像国民党民法中的债务一样。或者坚持不迁就习俗,就像清代、民国法典处理田面权那样。至于各级法庭,它们可能依照法典来压制习俗,正如在处理田面权时清代在部分程度上、民国在很大程度上取缔习俗那样;或者也会顺应社会实际,就像国民党法院对待农村儿子赡养父母的习俗;或者调和法典与习俗,就像国民党法院对待女儿继承权。
换句话说,司法实践既不同于成文法,也不同于民间习俗。虽然它与成文法及民间习俗均有重叠之处,我们还是应该把它们分开来看。就像习俗与法典之间的关系那样,我们的研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些议题即法律实践和成文法典的背离之处。法庭记录因而不仅告诉我们法典与习俗间的冲突,也告诉我们法庭如何在二者之间斡旋;它们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了解一些在法律条文上不承认而实际存在的社会习惯和法庭实践的主要信息来源。
总而言之,本书从这三个层面来考虑其主要议题:成文法、民间习俗及司法实践。每一层面揭示其在民事法律制度中与其他层面不同的某一方面。
对清代与民国时期的确切比较不能仅以成文法为基础,因为那样会夸大实际的变化。清代与国民党法律不同的指导意识形态与社会取向的确重要,但它们的不同也可能掩盖了习俗的基本延续及法典的实用条例与法庭的实际行为对习俗所做的重要让步。正是对以上三个层面间相互作用的考察,告诉我们自清代至民国间民事法律制度的变化与连续。
为了了解这些变化与连续的具体内容,我们必须摒弃传统对现代、中国对西方的二元对立结构。变化与连续的过程涉及两者间多侧面的相互作用,既有妥协/适应,也有反对/对抗,每一方都同时牵涉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的多个层面。
过去的研究
我们所涉及的内容中被研究得最多的部分是清代国家的法律体系。美国在此领域已积累了几代学者的学术成果:从卜德与莫里斯(Bodde and Morris,1967)和包恒(Buxbaum,1971)的早期开拓性工作,到包括安守廉(Alford,1984)、布罗克曼(Brockman,1980)和科纳(Conner,1979)在内的第二代学者的著作,到最近依靠档案的研究成果——包括艾力(Allee,1994a)、白凯(Bemhardt,1999)、麦考利(Maculey,1999)、白德瑞(Reed,2000)和苏成捷(Sommer,2000),以及我自己(黄宗智,1996,1998)。但是,没有一位(除了白凯)从与民国的明确比较角度来理解清代,也没有谁侧重于研究本书中研究的具体议题,我在1996年对清代民事法律制度的研究对这些议题也只是一带而过。
在梅尔(Meijer,1950)和约瑟夫·程(Joseph Cheng,1976)的著作中有大量篇幅涉及晚清的法律改革,它们至今仍是对模仿西方的新民法典草案的权威性研究。该草案在1929—1930年后成为中国的法律。但就清末民初而论,我的重点将放在对清代旧法典的修订上,因为此旧法典的民事部分乃民国头二十年执行的民法。
对民国初期及国民党时期的研究都不多,对该时期进行整体研究的(主要英文著作)仍只有范·德·沃克(Van Der Valk)1939年的《概论》。后来的学者相对忽视这一时期,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认为民国不过是从清代到新中国之间的演变中的一个中断期而已(而新中国则受到与清代几乎同等的重视)。
然而本书将阐明,民国时期的情况对我们理解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体系至关重要。后者的法律不仅受到古代中华帝国和现代社会主义理念的影响,也继续受到西方法律的影响,特别是1978年改革以来更加如此。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立法活动的开展,中国再次在许多方面恢复了晚清法律改革者和国民党立法者草创的工作:确立一个既与西方主导的现代立法趋势相一致(及与由改革引起的新的社会现实相一致),又保持中国传统习俗的法律体系。我们也许可以说今日中国法律的出发点更接近国民党法律而不是清代法律。
尽管本书的分析角度与以往的作者不同,我还是从过去的学术成果中获益匪浅,这在全书的引文与讨论中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对已往研究成果的引用显得似乎没有像其他议题那样详尽,那是因为对民国时期的研究委实太少,将民国与清代进行比较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下面再简单谈谈本研究所使用的资料。对清代与民国司法实践的比较,我主要依赖875宗地方案件的档案记录。清代案件来自四川巴县、直隶宝坻及台湾淡水-新竹三地,时间从清中叶到20世纪前十年。民国案件来自河北顺义(今北京市)、四川宜宾、浙江乐清及江苏吴江四县,时间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但顺义县也有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案例。所有使用的案件均依县、时期及有关议题在附表A1、A2中显示。我还利用了最高法院及北京地方法院的案件来补充研究民国时期的部分情况。
就民间习俗而言,案件档案记录本身当然是重要的资料来源,它们很好地展示了法典与民众习惯之间、法典与法庭行为之间的张力。另外,我再次利用了卓越的日本满铁调查资料。对本书研究的主要议题来说,满铁资料提供了至今仍是最好、最详尽的人类学实地调查证据。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司法部对民间习惯的调查(《民商事调查报告录》,以下作《民商事》,1930)也有助于我们更完全地了解情况。在我看来,虽然那些调查在展现民间习俗在不同地区的差异上非常有用,但它们并没有满铁资料的那种细节丰富与实地调查的翔实感。后者是基于村级的人类学调查,而前者则基于县级司法官员所填的问卷(由省上级法院发下)编成。这些资料在实证信息上的弱点,从梁治平的研究中(1996年)清楚表现出来,该研究几乎完全建立在此单一资料的基础之上。
至于1900—1930年的过渡期,现存不仅有清代及国民党法典,而且有改革者修订的清代法典和他们对各类律例的修改所做的说明,以及表现出新旧之间适应与冲突的新法典的三部草案。另外还有最高法院最高法院1906年初创时以“大理院”名之,到1927年改名为“最高法院”。1929年之前最高法院有权听取上诉及诠释法律,1929年后该诠释功能由新设立的司法院接管。1912—1928年、司法院1929—1946年应下级法院的请示对法典中的条款所做的诠释与说明(郭卫编,1912—1927年;1927—1928年;1929—1946年)。此时期内最高法院的案例判决也有助于澄清法律中模棱两可的地方(傅秉常、周定宇,1964年,第二历史档案馆)。
这些资料组成了本书的实证基础。我尝试着利用它们对整个民事法律制度做鸟瞰式的宏观研究,同时也对某些选定议题进行微观分析
对研究结果的几点说明
在回到本书的重点之前,让我简要地讨论一下广为学界考虑的两个次要问题。由于本书一半以上的内容涉及国民党的法治统治,我们免不了要对国民党的统治做某种程度上的评价。多数美国读者将会从以易劳逸(Eastman,1974,1984)为代表的主流派观点来看待此问题。易与同学派的其他学者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上。他们展示出:面对与共产党的斗争,以蒋介石为首的核心领导集团变得越来越狭隘地专注于保住其自身的权力,最终导致出现一些致命弱点,这些弱点解释了其政权崩溃的原因。易劳逸主要研究军事与政治政策及行为。而帕克斯·科布尔(Parks Coble,1986)的重点则在揭示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的财政政策如何同样变得日益专横和自私。
本研究并不挑战这些观点,但仍有与之不同的看法。我的焦点是法律,这也许可以(与其他领域,像教育、运输、通讯,甚至工业发展一起)称之为“二线领域”。因为在蒋介石集团与共产党的角逐中,这些“二线领域”并不如一线政治斗争那样迫切、紧急,它们为不同的理念与行为提供了更多的空间。虽然对政治斗争没有直接的决定作用,但从长期“基础结构”变化的角度看,这些二线领域的重要性仍十分明显。由于国民党的法治成绩与其军事-政治-财经领域的成绩相比较为突出,从某种程度上说,本研究的确提倡对那种仅仅建立在中心政治斗争基础上的观点进行重新思考。
作为对民事法律制度的研究,本书也必然考虑法律如何处理性别关系。在此方面,最近的学术研究很好地展示了妇女在帝国晚期,虽然是在家长制的社会秩序之下,对其自身生活具有的各种自主空间(特别参见科\[Ko\],1994;曼\[Mann\],1997;白凯,1999;苏成捷,2000)。本书的第九章、第十章把重点放在较少被探讨的清代与国民党法律如何看待妇女的意志及其所做的抉择问题上,试图为上述学术问题的研究做少许贡献。我认为清代法律视妇女既非似国民党法典下独立的积极的自主体,也非缺乏意志或选择的纯粹被动体。虽然清代法律视妇女的意志从属于男人,但它赋予妇女在被侵犯过程中和从与反抗的抉择——亦即我所说的“消极抉择”。
本研究进一步追问,在清代法律和民国法律下,妇女在现实生活中所做的选择如何与法律的设想一致或背离。对某些读者来说,令人惊奇的可能是清代法律对待妇女的做法实际上在有些方面起到了保护和强化她们自身的作用(但同时也向她们强加了一些无理期望)。与此相反,国民党法律坚持妇女乃完全独立的、积极的自主体,实际上却造成了取消清代法律对她们的一些保护的结果。
虽然这些问题令人感兴趣,但本书的主要内容仍是广泛比较清代与国民党民事法律制度之间的异同。正如可以想象的那样,对二者的比较形成了某些明显的或众所周知的对照,这正如父系社会秩序与个人社会秩序之间的对照一样。但它也引出了其他也许并非明显的对照:生存伦理与投资伦理之间,土地的永恒产权与土地乃有价物品之间,有拘束的产权与单一的、独立的产权之间等。此外,这一比较也显示了法典与习俗之间的一些根本的对立。本研究认为,总体而言清代法律与民间习俗比国民党法律与民间习俗具有更强的一致性。因此,清代法庭在司法实践中无须做到像国民党法院那种程度地斡旋于两者之间。
最后简单谈谈我在前面提到的一些主要理论问题。作为对自清代至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研究,本书不可避免地要界定“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的概念并处理它们在20世纪的相互作用问题。这样一来,也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时下由后现代主义者和文化研究对旧的现代化范式的批评所引起的方法论与理论上的争论。
理论家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和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曾经特别强调过现代化范式怎样把西方自身的后启蒙现代性当作全世界的准则,他们也批评了现代化模式及其对立面的旧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双方都隐含着唯物主义倾向。另外,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试图运用其“实践逻辑”的概念去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结构主义与唯意志论之间的分歧。本研究从这些理论家那里汲取了不少东西,但也会从他们的贡献与不足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
因为主题的多层面性及书中采用了逐题的组织方法,本导论不打算提供惯常的对主要问题与中心论点的统一陈述。习惯了此类导论的读者也许可以先看结论,其中有对本书主要论点的总结和所采用理论观点的说明,但其他读者可能更乐于就此投入正文,从头看起,让主要论点与经验证据一道逐步展开。
——摘自黄宗智著《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
英文版序
本书原计划是一套以时代为序(清代、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卷本法律史著作中的第二卷,现在变得讲清代和讲民国的内容一样多,原因在导论中有说明。国民党法律被当作陪衬用来澄清清代小农社会和经济中那些明言的和未经明言的逻辑,反过来清代法律也同样如此。我希望这种来回的参照与对比会有助于让两个时段都显得更清晰,而不至于模糊了变化的过程。另外与试图形成一致的叙述或概述不同,本书将重点放在一系列依高诉讼频率选择的议题上。我希望全书能在深度上弥补其在一致性上的不足。
与我以前的三本书不同,本书没有一个单一的、一以贯之的简明主题。部分原因是本书采用了逐个议题探讨的方法,部分原因则是考虑到同时比较清代与民国时期并考察每个时期的成文法、民间习俗与司法实践的复杂性。我希望这一缺陷能由多重主题的丰富内容所弥补。
在本书中我对理论著述的处理也与我以往的著作略有不同。我觉得有必要提及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几个问题,它们最近在学术界极为流行。我在本书中与理论家们的对话既是方法论的,也是实质性的。
我从1988年开始全力投入法制史研究,现在回顾起来仿佛只是昨天的事,但这一小小的领域却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时我复制并以发现的激动心情阅读的案件档案记录,现在已比较容易得到,因为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已把所有的宝坻档案制成缩微胶片,而四川省档案馆也把部分巴县档案制成了缩微胶片。尽管民国时期的案件档案记录仍然不甚容易得到,但广泛利用它们肯定已为期不远。此外,加上本书,“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丛书已经出了六本。从路斯基金会赞助的论文集开始(以四次国际会议中的第一次会议为基础),现在累积的专著已足以让我开设一门新的有关中国法律史的本科生课程。
对我本人来说,自1988年以来这一时段内最强烈的感受,莫过于我自己的两个学生苏成捷(Matthew Sommer)与白德瑞(Bradly Reed)现已成长为成熟、有作为的学者,他们分别在上述丛书中出了一本重要著作,并正着手写第二本。在修改本书稿、听取各方建议时,我很高兴、也很自豪地把他们当作我能想到的最有见地、最好的评论者。而且在本书即将付梓时,我与白凯共同指导的郭贞娣(Margaret Kuo)和胡宗绮(Jennifer Neighbors)正启程前往中国进行博士论文的研究,她们将会是“另一代”有作为的年轻法律史学者。还有陈美凤(Lisa Tran),也很快将开始写博士论文。
除了苏成捷与白德瑞,周锡瑞(Josph Esherick)与戴瑙玛(Norma Diamond)对本书的最后几稿提供了有益的帮助。特别要指出的是,白凯又一次阅读、评论了每一稿,是她鼓励我保留书中与妇女有关的部分。它们有助于我形成对清代和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完整图像。
继以往三本书之后,本书让我第四次领教了Barbara Mnookin严格校对的“折磨”,她坚持用尽可能最少的文字表达最清楚的文意。对作者而言,在当今出版日益仓促、马虎的环境下,这是少有的优待。我要再次感谢她。
最后谈谈对国民党法律史的研究。这几乎是一个完全被忽略了的题目,主要是因为大家下意识地认为此一时期不过是清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一段反常的“中断期”。我希望本书将能够清楚表明这一时期是如何重要和如何显示关键性的主题——当与其他时期对比研究时尤其如此。除了对所选议题比较集中的分析,本书也许可以与白凯的《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一道被视作弄清国民党法律史大致轮廓的部分探索。更多的工作尚有待正在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去完成。
中文版序
本书是我继《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之后的第二卷法律史著作,使用的资料仍主要是诉讼案件档案。但此书集中讨论五个存在较多诉讼纠纷的法律领域,对清代关于民事的法律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同时通过比较,对涉及这些方面的民国民法也做了初步的分析。国内不少读者对我上一卷法律史著作关于清代法制的论点持有保留意见,我希望他们会被两本书结合起来的论证和论据说服,至少会承认清代和民国时期确实有许多普通老百姓使用法律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并且确实有许多县令、法官是依法行事的。可是,我仍然担心不少读者对现在和过去的法律制度成见殊深,不易动摇他们最终可能还是要通过直接阅读清代和民国诉讼案件档案之后才会改变的成见。为此,我希望有学者会在近期热衷于从事编纂介绍诉讼案件档案作品的工作。
在当今中国努力倡导依法治国的情境下,了解清代和民国的法制可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代中国法律所继承的主要是三大传统:一是清代的旧法制;二是模仿西方的民国法制;三是老解放区在否定前两者之后形成的法制,这也是受乡村习俗及其公正制度影响较深的传统。今日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必得取源于这三大传统。本书的重点正在于清代及民国法律与乡村习俗的相互作用,以及其间相悖和相符的各个方面。
本书特别强调法律实践及“实践的逻辑”。我相信,要融会三大法律传统,不能只探讨法理,因为那样必定产生无穷争执,难定取舍。我们应借鉴法律实践之中的效果及包含在其中的逻辑。这个道理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践是相同的。从诉讼案件出发来理解历史上的法律实践,并从中突出和提炼其包含的逻辑及法理是此书的中心议题。本书由我的博士生张家炎为我翻译,谨致衷心的感谢。因本书是译本,要准确表达英文原作颇为不易。更由于英文原作文字比较精练,翻译难度更大。此译本虽经我本人一再校阅,恐怕还是不能完全表达原作的含义,也未能达到原作的文字水平,请读者见谅。
黄宗智先生的《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是一部非常精彩的法律史著作。这本书有几点非常吸引人:一、今天中国法律的很大一部分直接继承自清代与民国的法典,其中经历了哪些损益因革,有哪些得失教训,本书都有详细论述;二、从近代无论是被迫卷入还是主动进入“西潮”以来,中国的方方面面变革都与西方(包括日本)有关,本书详细介绍了清代以来西方法律在中国的“移植”过程,其中诸多“抽象继承”和“创造性转化”的方面,对我们当下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分歧很有帮助;三、启发和帮助我们反思“进步”(如我们很多人下意识就会认为民国民法会比清代民法进步)等已经潜移默化接受的价值,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论述。举例说来:黄宗智先生力图证明,不同于传统的封建、落后等暗黑叙事,清代法律在许多方面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比如对待寡妇、童养媳,在清代法律下妇女或许可通过贞洁理想等得到少数保护,但在民国民法下,新法律根本不承认她们在清代法律下还能要求的这些“权利”。
编者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周黎安教授曾这样评价黄教授的法律史研究:“拜读黄宗智关于法律史的著述对我而言是一种震撼性的阅读体验。”《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是超级教授”黄宗智法律社会史代表作。该书从清代与民国的法律变化看近代中国转型。既是一部法律史著作,又是一部社会史、文化史著作。以下摘选的是此书第三章“清末民初司法制度的改革”的部分内容。
法律职业的兴起
虽然清政府在其最后几年通过与日本(特别是法政大学)合作创办法政学校,在法官与律师培训系统化方面迈出了几大步,但它的几部法典却都没有对他们的资历和审核做出明白规定。有关日本在晚清法律教育中所起的作用,请见雷诺兹(Reynolds),1993:53—57。要到1912年民国肇基之后才有首部律师条例颁布(阿利森·康纳\[Alison Conner\],1994:210;文见《法令辑览》,1917,6:156—174)。
1913年,1426人注册为律师。其中大多数(1118人)是中国新式法律院校的毕业生;余下的曾在日本、美国或英国受训(7人;康纳,1994:220)。到1933年,全国律师协会总共有7651名注册会员,可能是当时现代律师数量较客观的指标。康纳(Conner,1994:229)提供的数字是1934年有6969名注册律师,此数字实际上是1932年的(《申报年鉴》1936:D141)。我们暂时估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从业律师的总数当在10000左右。
这一数目是多是少也要看你从什么角度考虑。10000个律师相对来说是个小数目。正如康纳指出的那样,它等于是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每45000人中才有一个律师;而在1935年的日本,每9700人中就有一个律师(比较改革之后1990年的中国,每年有10000多名法律院校学生毕业,这确实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中国法律年鉴》,1990:1013\])。大多数律师都集中分布在大城市,仅北京、上海、天津就占总数的1/4以上。而沿海省份律师比例比内陆省份高得多。内陆省份律师极为稀少,甚至相对较大的县城也是如此(《申报年鉴》,1935:D139—140)。如四川长宁县,新方志的编纂者们发现他们只找到一件民国时期带有律师的名字的案卷(《长宁县志》,1993:576)。与此相似,开县直到1942年才有律师(当时开设了三个律师事务所),而且直到1943年县法院才出现首个由律师辩护的案件(《开县志》,1990:366)。在中国农村的小城镇和村庄里根本就没有律师。
但是,从被清代国家贬为“讼师”“讼棍”的法律“顾问”到在社会和国家看来都是值得尊敬的律师,实乃巨大的变化,有着深远的意义。律师毕竟属于与法官相同的法律行业,不少人是先当律师而后晋升为法官。清代改革者明确设想法官的社会地位和职务足以与县长媲美。正如我们所见,1908年的《法院编制法》规定过渡时期的法官需要具备与县令相等的资格——举人功名或七品以上官职。
在民国县政府官员的等级中,地方法官地位仅次于县长而位列财务、建设及教育诸局局长之上。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顺义县即如此(《顺义县志》,卷5:1—29)。它反映出与清代一脉相承的官方价值系统,在这一价值系统内,地方政府司法工作与其他工作的重要性程度通过县令不同类型幕僚的薪水体现出来。在各类幕僚中刑名幕友通常领薪最高——在淡水-新竹地区1888年每年1000元(银元),相比之下钱谷幕友800元,主要吏书120—300元,而衙役仅29元(黄宗智,1998:128,181)。
循此,检察官也有很高的地位。我们已经看到,检察官的资历可以作为充当法官的资格。像法官一样,他们毕业于新的法政学堂;他们是法官的同学,与法官具有同等的地位。
据此可推定,律师具有同样的地位,至少原则上如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仍处于对过去“讼师”和“讼棍”等的联想的阴影下,而且在地方上可能不会受到如法官和检察官那样的尊敬。当然,那些在国外受教育、在条约口岸城市代表外国或中国企业的律师,完全属于另外一类。不过,他们与司法官员具有相同的教育背景与依正式章程可能获得司法官职的事实,多半提高了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
法官、检察官的官职,以及私家律师的职业,为民国初期的法律专科人员提供了爬上“成功之梯”的有效途径。根据1933年的数字,113个地方法院(每院6名高等司法人员)及147个分院和县法院(每院3名高等司法人员),在当时的地方法院系统中总共有1100名经过职业训练的法官和检察官。这一数目当然远低于国民党所希望达到的在1933年之前要有8000名在业法官和4000名在业检察官的目标。但是,考虑到在19世纪清代全国县及县以上级正规官员也只有27000名,总数12000名地方司法官员的计划是一个具有相当雄心的目标(Chang,1955:第116页及随后几页)。
正如我们可以预想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法律专科是在地方上晋身精英阶层的主要途径之一。1933年的《顺义县志》给我们举出了特别清晰的例证。对清代,纂修者依照地方志正统的做法把科举及第者列为县里地方上的知名人物,排列顺序如下:首先是进士(8人)和举人(13人),两者均有资格入仕;其次是可以获准进修、随后亦可当官的贡生(135人)和武举;最后是购得功名的监生。在民国时期(1912—1932),他们按同样的思路列出地方上受过教育的精英,按顺序排列依次为男性大学毕业生(51人)和男性中学毕业生,然后是女子大学毕业生(只有1人)和女子中学毕业生(《顺义县志》,1933,卷8:22a—51a)。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第一类,这51名男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与进士、举人、监生相等的人士。表3.1把他们按教育背景分类,可以很容易看出,法政学校毕业生数目最多:22人,或占总数的43%。其他类中相当大的部分(25%)是军官和警官学校毕业生,这两者也是民国时期晋身精英阶层的重要途径。
在17位职业明确的法律毕业生中,8位是见习律师(包括两位前法官),2位是法官,1位是检察官(他曾是法官)。另外,他们当中还有1位县长、1位局长和2名学区委员,这表明通过学习法律专科可以获任其他官职。
当然,顺义县可能不完全具有代表性,因为其毗邻京、津,有好几所新的法政学堂坐落于两市。不过,这里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民国时期新的地方精英形成过程中法律专科之重要性的生动例证。虽然科举考试于1905年正式废除,但教育应是进入官场的主要途径及考试乃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继续左右着官方与民众的思维。1908年以后,就读法政学堂变成最近似于老式的科举备考。从这些学校获得的学位可使学位持有者合格受任在地位上与县令媲美的官职,这点正似旧式的举人和贡生。考虑到周锡瑞和兰金(Esherick and Rankin,1990)的著作,这一点值得多说两句。那本书研究这一时期的地方精英,但几乎没有提到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索引中只有一项与律师有关,没有一条涉及法官和检察官)。
其他一些晋身精英阶层的途径,不具有同样的可靠性和正当性。军警学校提供了相当数量的但可能较少受尊敬的做官机会。尽管科技或师范学院的学位也能带来一定的社会地位,但那样的大学教育并不保证有官可做。在民国所有通向成功的途径中,法律专科是少有的具备旧式成功之路核心特点——获得学位而通向官职的方法之一。从这一角度分析,顺义县高等教育精英们的概况就变得更好理解了,就像新法官和律师系统相对迅速发展一样。
总而言之,晚清和国民党统治在法律系统的制度和程序改革上向着同样的方向运动。但在民国早期,制度改革与援用旧法典的结合表明实践中的法院系统与理论上的成文法之间出现分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法院的实际所作所为与成文法描述它们怎样运作之间也出现分离。法院系统虽然明确区分民事与刑事案件,但成文法仍保留视民事为“细事”的旧概念。然而,尽管援用的是旧的概念框架,但民事法律体系内的法官和律师有完全的合法性,与刑事系统内的法官和律师等同。最后,司法权力也渐渐与行政权力分离,即使它依赖的民事法律是一部由君主集权颁布的禁令组成的法律。
总之,在1900—1930年的过渡期内法律机构制度的变化远远超过成文法的变化。这些变化也许比其他任何变化更好地为采用新的、完全不同的民法典铺平了道路。到该法典颁布的时候,全国相当部分地区已经建立起了全新的法院系统与法律行业。
——摘自黄宗智著《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
编者按:历史一再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已经习以为常的事物,得来非常不易。譬如“男女平等”的观念,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似乎是天经地义、古来如此。然史实并不是这样。黄宗智教授新作《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深入考察清代、民国时期中国修订法律的活动,为我们展示了“男女平等”被接受的曲折过程。以下节选的,是该书的这部分内容。
男女平等
对20世纪早期的中国法律改革者们来说,男女平等可能是德国民法典所有主要组织原则中最难采纳的一条。对此略微的暗示在1906年就引起了张之洞的反对,正是他和其他官员的抵制迫使晚清改革者更谨慎地处理民法草案的“亲属”和“继承”两编,约请了中国法学家起草而非雇用外国(日本)专家参与。1911年他们首先提交头三编的草案,推迟呈递后两编。
总体来看,1911年草案的五编事实上包含新旧观念之间极深的矛盾。俞廉三在其10月26日的前附奏折中解释道,他和法典草案的其他作者遵循了两个原则:一方面采用最好最新的西方司法理论和原则,另一方面针对婚姻、亲属和继承则是“以维持数千年民彝于不敝”为原则(《大清民律草案》,1911:3a—b)。这也是他们在法典的第一部分采用了权利话语,而在第二部分则放弃了那些原则的原因。
在父系继承的“民彝”原则下,妇女基本上没有独立的财产和继承权利。家庭财产必须沿父系世系由父亲传给儿子(《大清律例》,例88-1)如果某男子无嗣,该对夫妻就要从男方侄子中选一位作为继子,这个制度套用白凯的用词就是“强制性侄儿继承”(白凯,1999)。1911年的民法典草案对这些要求或多或少都未予触动(第1390、1466条)。1925—1926年的草案也是如此(第1309、1310条)。1911年草案规定:在兄弟没有儿子的情况下,姐妹的儿子或妻子兄弟的儿子或女婿可成为合法的继承人(第1390条)。1925—1926年草案把舅舅的孙子也列了进去(第1310条)。
直到国民党法典才把个人权利的观点完全贯彻到其逻辑之中。立法者完全摒弃了父系继承和家庭与社会中的旧等级结构。在法律眼里,男女之间、长幼之间没有任何差别。正如中央政治会议在其“立法原则”中解释的那样,在父系制度下,要区分父系亲戚(宗亲)、母系亲戚(外亲)以及妻子的亲戚(内亲),只有父系内的人才有继承权。相反,新概念只区分血亲和姻亲。女儿于是和儿子拥有同等的继承权,妻子和丈夫拥有分别独立的财产权(潘维和,1982:109;亦见范·德·沃克,1939:51—58)。
根据中央政治会议的观点,父系宗祧继承乃周代封建贵族制度的残余,是一个与时代不合的东西。随着世袭贵族的终结,家庭而非父系宗族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单元。祭祖一般由一家一户而非一族一族进行。这样,宗祧继承中留下来的东西就只有无嗣夫妇挑选一个男子作为其家庭继承人(嗣子)这一习俗。依照现在对家庭的重新定义和男女平等的要求,该习俗不可能再维持。法律不再承认宗祧继承原则的任何内容(潘维和,1982:117—119:胡汉民,1978:872—885)。
新法典赋予女性“直系血亲”(“直系卑亲属”)与男性直系血亲在继承上同样的第一优先权(第1138条)。财产继承于是被从宗祧继承中分离出来,完全摒弃男性“嗣子”的概念。如果一对夫妇没有儿子,女儿可以继承财产;如果没有女儿,则父母可以继承;如果父母已过世,则兄弟姐妹可以继承;如果也没有兄弟姐妹,则祖父母可以继承。
另外,相较于法典赋予丈夫和妻子双方对结婚财产的继承权,孀妇会得到与其子女同等的份额;如果她和她的丈夫没有后代,她将得到二分之一的财产,另二分之一归其亡夫的父母亲或兄弟姐妹;如果他没有父母亲和兄弟姐妹,她将继承财产的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归他的祖父母;如果上述人都不存在,则她可以独继财产(第1144条)。在旧法典下,孀妇对财产的“权利”只是其作为继承人的妻子、母亲身份的派生物,她享有代表其丈夫或其子而获得的监护财产权,但没有她个人本身的继承权利。
坚持个人权利和男女平等还导致另一背离旧法的重大后果。1911年草案和1925—1926年草案都保留了清代婚姻须经父母许可的旧规定(第1338、1105条)。不管对于男子还是女子,结婚都从来没有被期望成为可以自由选择的事情。30岁以下要离婚者,无论男女都必须征得其父母的同意(第1359、1148条)。新法典与旧法律和前两部草案完全相背。新法典第972条规定:“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而第1052条列出了允许夫妻中任何一方提出离婚的九种情形:重婚、通奸、虐待、虐待对方直系血亲、试图杀害对方、有不治恶疾、有严重不治的精神病、三年生死不明及被处三年以上徒刑。有另外一种情况只适用于妻子。该条之四允许离婚:如果“妻对于夫之直系尊亲属为虐待,或受夫之直系尊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者”。这里我们不妨推测因为妻子按惯例是与其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的,以致编修法典者根本没有考虑相反的情况。该条款扩大了前几部草案中准许离婚的标准,它改变了只允许丈夫一方以通奸为理由诉请离婚的规定,终止了对妇女的这种不平等待遇(第1362、1151条)。
最后,所有这些加起来等于是对妇女的抉择和自主性进行了根本的概念重订。国民党法典把妇女想象为独立自由的自主体。她们像男人一样继承财产,在结婚和离婚上享有与男人同样的权利。在法律眼中,妇女像男子一样能完全控制其生活。
随着男女平等原则的采用,在中国采用现代西方民法的进程中,国民党法典越过了最后一个难关。1911年和1925—1926年的草案在其头三编中几乎完全模仿《德国民法典》,但后两编并非如此;国民党法典却完全采用了后两编。随着这一改变的发生,现代西方民法已全盘移植到20世纪的中国。
——摘自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
编者按:《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结果指出:“黄宗智的研究是近年来社会科学界寻求构建本土性学科理论体系的代表性尝试。同时也显示出,从中国经验提炼中国概念,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道路,以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共识和自觉。”以下摘选的是黄宗智教授新作《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的部分内容,黄教授对清代、民国时期土地“双层所有权”的常规与语汇做了精彩解析。
双层所有权的常规与语汇
一旦双层土地所有权建立后,田面权的买卖不久就会随之而来。原因之一在于这是一种简单而普遍的买卖财产方式,没有涉及国家。因为田面权所有者没有纳税义务且根本就不在国家税册上,他们可以通过非官方的“白契”进行换手,而不是按规定到衙门注册并为正式的“红契”付3%税(帕尔莫,1987:24—26)。
在某些地方,这一交易导致不在地主的城市资本进入农村投资土地,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江苏开弦弓村,以及1899年时划给英国当局的香港新界那样(费孝通,1939;帕尔莫,1987:40ff)。如费所言,开弦弓的田底能像城里的“股票和债券”一样出售,而不用考虑田面(Fei,1939:186;亦见黄宗智,1992:110)。
上述关于永佃和田面权的叙述表明它们如何形成一个没有明确界限的连续体。永佃可以演化为双层土地所有权,也可以与双层土地所有权混合或共存。两者间的界限常常模糊不清,该事实可以从20世纪初法部调查中的共时证据得到很好的证明。
调查表明,该连续体的一端是明晰的田面所有权。例如,在福建古田县,研究者注意到:
田面主每年收租若干石,多由根主直接送纳。但无论如何,只能向根主追租,不得自由择佃。而田根之主除自己承耕外,批与他人承耕而坐收根租者亦有之。《民商事》,1930:507。根据当地用法,“田面”和“田根”的含义刚好与在多数地区的相反。这里纳税的田根主是“田面主”,而交租的田面主是“田根主”。
此田面所有者(“根主”)像任何土地所有者一样拥有对土地的同样权利:他耕种其地的权利不允许受到挑战;如果他欠田底主(此地叫“田面主”)地租,他可能被迫通过出售他的田面或其他财产来偿付,但不可能像佃农一样从土地上被撵走,他可以把地租给别人而无须与田底主商量(关于松江县类似的惯习,见《民商事》,1930:342)。
另一端是含糊的永佃权。由下面来自同一地区的描述证明:
又有本无田根之人,承批他人根面俱全之田,耕种岁久亦得发生根主权,不许田主自由退耕者。此名白承耕,以无田根契据也(《民商事》,1930:507)。
订“白承耕”者在享有永佃权而并不可能被地主随意赶走的意义上类似于田面主,但与田面主相比,他的权利并未言明。他没有田面权的契约,因此他无法以田面主出售土地的方式售出其地,他也不能把地转租给别人。
在无契约的事实上的永佃权与有契约的完全的田面所有权两极之间,是一个没有明确边界的连续体。例如,在天津,永佃权(开垦海涂)让“佃户可使子孙永远佃种,或任意将田面部分(即永佃权)变卖抵押。即积欠田租,业主提起诉讼,只能至追租之程度为止,不得请求退田”(《民商事》,1930:317)。这里很难辨清永佃权与田面所有权之间的区别。总之,田面耕种者同时既是所有人又是佃户。他享有全部的田面所有权,可以自由出售、抵押或出租。同时,他又是佃户,有向田底主交租的义务,以及遭受天灾时减租的权利。正如一名向法部提供材料的松江司法人员所云,尽管“田面向系种户所有”,但他必须付田底的租,租金“照本地善堂征租之成色而参酌之,如遇水旱虫荒酌量减轻以昭平允”。《民商事》,1930:342。如白凯所说明的,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一个制度化了的惯习在这一地区出现,当地的地主(凭此惯习)与地方政府合作,在收成的基础上每年调整地租(白凯,1992:137—140,172—177)。山西南康县的受访者讲了另外一种情况,他说:“管皮者(即佃户)于该田有永佃权,故对于管骨者(即田主)每年应纳之租额均有一定,无论水旱荒歉概不减让。”(《民商事》,1930:456)但对于全国而言,那更像是例外而不是常规。
民国时期的中文词“永佃”在清代并未使用,但有几种通用的表达方式与之近似,包括“永远耕佃”“永远耕种”“永远耕作”“永远承耕”及“永远为业”(杨国桢,1988:92—99)。“田面”是对表土(权)最平常的称法,在20世纪之前很久就已普遍使用。它一般与“田底”(表示底土)成对,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另一个与它配对的用法是“田根”,如在福建和台湾地区,有时用法与常规用法刚好相反,把“田面”等同于纳税、不耕种的所有权,将“田根”等同于交地租、耕种的所有权。其他代替“田面”的术语在江西和浙江有“田皮”,与之相对的是“田骨”;在长江三角洲的常熟有“灰肥田”(《民商事》,1930:327)。
两层不同土地的所有者最常见的是被称为“田面主”和“田底主”,就像在长江三角洲的绝大多数地方一样。但在福建,他们是“田根主”或“大苗主”和“小苗主”(《民商事》,1930:507,550,559);在嘉兴,他们是“田骨主”或“大业主”和“小业主”(《民商事》,1930:440—441,450)。
田面主付给田底主的通常就称“租”,而租地的行为则称“佃”。但这方面也有变体。在松江,田底主把土地租给田面主叫“外顶”,与之相对的是“招顶”,即既拥有田面又拥有田底者把地租给佃户并换取“顶收”。在福建,租出叫“批”或“批与”,租种叫“承批”(《民商事》,1930:507,544)。如果田面主和田底主都租出,以致两层土地都要收租,在福建区别两者的通常做法是称其中一种为“大租”(由“大主”收),而另一种为“小租”(由“小主”收)。有关闽台“大租”“小租”的更多情况,见杨国桢(1988:268—360),亦见艾力(1994a:52—57)。
双层土地所有制的这些惯习和术语由最常用的措辞“一田两主”概括(杨国桢,1988:99—113)。该概念原则上应该不会给我们带来麻烦,从字面理解,其表示一单块土地有两层。但实际上,“一田两主”表达了一个极端抽象和难以理解的概念。不会有人试着在地上把一层与另一层分开,就像不会有人试着规定表土从哪里终止、底土从哪里开始一样。更不会有人去分开哪是这一层出产、哪里是另一层出产。这是很好理解的。对种地的农民来说,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人人都知道土地的两部分产出同一。
也就是说,人人都知道两层的有形的想象只是隐喻,而非实际。对种地的农民来说,土地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无机的“东西”。你不可能把田面与田底分开,就像不能把活人的皮与骨头分开一样。隐喻的用法所传达的,是与土地相关联的抽象的所有权(两主)及单元整体的不可分性(一田)。
“一田两主”的概念特别适合长时间演化而来的复杂的民间惯习。尽管它承认有机整体的物质不可分性,但它通过具体的形象来传达两主共存,每个主人都有不同的权利,这些权利可永远持有且易于分开转手、继承。这就是为什么“田面权”比别的术语如英文的“用益权”(usufruct)更符合实际,在“用益权”中权利通常在人死时终止。
该双层所有权的习惯概念,也允许在单一业主身上同时呈现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租赁的二元逻辑。这样如下的概念就没有问题了:一位拥有某财产一切常见所有权的人可能同时也有对该财产交租的义务。所有权由田面的想象隐喻地表现,交租的义务由田底的想象隐喻地表现。循此,田面主可能会像所有者一样租出其地,同时又像佃户一样在天灾时对田底享有减租的权利,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双层所有权的思想把这些表面矛盾的想法和惯习调和进一个单一的概念中。它是清代立法者和民国立法者都拒绝的一个矛盾概念。
——摘自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