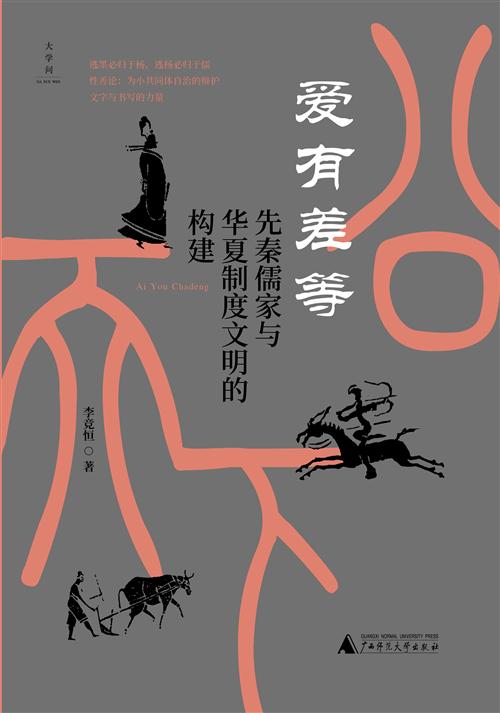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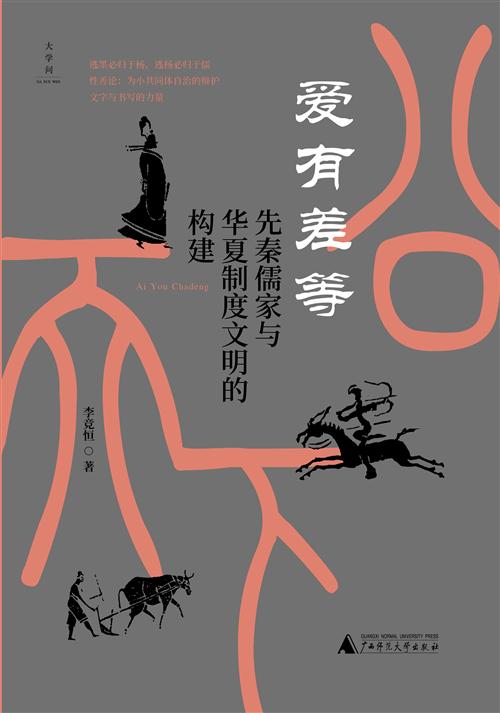
围绕华夏制度文明,回溯儒学的源头,深挖先秦儒家思想精髓。全书分为“政论”“经济”“文化”三大部分,从孔孟原典出发,融合多学科知识,归纳并阐述先秦儒家对国家治理的各项制度主张,全面剖析了原始儒学在政权组织形式、刑罚、税收、资源分配以及社会福利等多维度的制度构建。作者认为孟子的爱有差等是文明社会的基石,不仅深入挖掘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还特别强调家庭、家族和社区在文明社会建设中至关重要的地位,揭示原始儒学在铸就现代文明制度方面的深远影响和滋养现代文明精神的重要意义。
李竞恒,字久道,1984年生,四川江油人。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与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著有《论语新劄:自由孔学的历史世界》《早期中国的龙凤文化》《岂有此理?中国文化新读》《干戈之影:商代的战争观念、武装者与武器装备》等书。
政论篇
爱有差等与文明的构建 003
孔门是模拟周代封建关系组建的小共同体 015
存亡继绝:保持众多平行延续的世家 030
缔结婚姻:从小共同体习惯法到近代国家登记048
三年之丧礼与小共同体 054
孟子与混合政体的“打地鼠”游戏 060
性善论:为小共同体自治的辩护 068
古儒认为忠君并不很重要:兼论《忠经》辨析 078
独立于君权的专业性 085
儒学是鼓励平民模仿做贵族的学问 094
天命和民意 110
禅让和汤武放伐其实是一回事 114
经济篇
“哀哉鳏寡”:首先拯救最无助的原子个体 123
父亲角色、婚姻、家庭和市场经济是文明的基石 130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140
孟子、森林使用权与习惯法 150
孟子谈社会分工与市场 156
孟子与自由贸易 163
恒产恒心:克服时间偏好 171
文化篇
朋友:从血缘、姻亲到跨血缘 183
劝酒:从贵族礼仪、自治社区的酒会到服从性测 190
家庭、乡土熟人层面应保留方言 199
传统文化:吃素还是吃肉? 206
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 216
原始儒家的阳刚之气 222
率兽食人和始作俑者 229
先秦战车:外来的技术 237
秦朝尊重女性?你想多了 244
文字和书写的力量 250
后记 259
序
读书是一件好玩的事,除了“专业”之外,还有广袤而有趣的天地。对于我的学生,我尊重并鼓励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去自由发展适合自己的阅读生命,若能做到博洽淹贯、汇通中西的视野,自然更好。李竞恒跟随我读博时,我就发现他对中国思想史具有浓厚兴趣,当时他出版过一本《论语新劄》,汇通了古文字、考古资料、人类学,甚至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一些内容。学术方法上,显得有些“不守章法”,但能尝试贯通中今中外和跨学科的视野,却往往能从一些“三不管地带”中,发现新的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则自有其意义所在。
中国思想史中的“原始儒学”等问题,可谓十分重要,从汉代以来的学者开始,其学术努力的方向往往是回溯先秦时代“原始儒学”的源头,这种溯求“原儒”思想的探寻,一直深刻影响到晚清、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潮。李竞恒这本“软学术”随笔式的小书,体量不大,但关注的问题意识,仍然是延续了追溯何谓“原始儒学”的这一兴趣方向,并通过很多现代知识,尤其是囊括了经济学、法学、考古学、人类学等现代“西学”不同学科视野的交叉维度,呈现为一种独特的写作风格。我阅读了书稿后有三点印象,第一是知识结构开阔,虽然要探讨“原始儒学”为中心的话题,但是能从多个学科切入,如谈论传统文化是吃肉还是吃素,能从人类学、考古学的旧石器时代饮食结构,再联系到殷周贵族作为“肉食者”与军事贵族的体魄等。又如谈先秦时期山林水泽的资源使用权,能够从“习惯法”的角度,结合英格兰中世纪颁布的《森林宪章》等进行比较。第二是思路比较广阔,用现在网络术语说,叫有“脑洞”。无论是谈“逃杨归于儒”,还是“爱有等差”、“性善论”等话题,都不是按照一般“传统文化研究”角度,而是都能从大、小共同体之辨,从人类学的“邓巴数”到智人大脑还不适应只有五千年历史的陌生人协作复杂社会等角度谈出新意来,至少就阅读感受来说,还是很好玩、很有意思和一些启发的。第三是其志趣,立足于本国历史文化情感,但对于西学并不排斥,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或近现代的材料,信手拈来,态度中正平和,不偏不倚,兼容并蓄,是可取的。
思想史的研究并非我的专长,对于李竞恒书中的一些观点,我也并不完全赞同。在日常交流中,我就和他谈到,对他比较认同的某些芝加哥学派学者,其实也存在着各种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特别是有“致君尧舜上”的想象。而在孟、荀之争的思想史问题上,我也是宁站在荀子一边。当然,学术和思想是开放的,师生之间也不需要在每一个观点上都达成一致。他的这本小书,还是非常有趣,语言也浅白易懂,不故作高深。相信热爱阅读的读者,无论是否赞成其观点,但应该会对这本书的内容产生兴趣。
周振鹤
2023年5月18日
——选自李竞恒《爱有差等:先秦儒家与华夏制度文明的构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
李竞恒这本“软学术”随笔式的小书,思路比较广阔,用现在网络术语说,叫有“脑洞”。许多话题都不是按照一般“传统文化研究”角度,而是能从大、小共同体之辨,从人类学的“邓巴数”等角度谈出新意来。至少就阅读感受来说,是很好玩的,语言也浅白易懂,相信热爱阅读的读者,无论是否赞成其观点,都应该会对这本书的内容产生兴趣。
——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周振鹤
竞恒此书,以原始儒学的问题意识,汇通苏格兰启蒙的脉络与方法,将中、西方优秀正典结合起來。使用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写作,去揭示原始儒学精神对于滋养现代文明的时代意义。
——上海开放大学教授?鲍鹏山
在我所认识的80后学者中,若论闻见之广、学养之厚、才华之俊、思力之敏,李竞恒恐怕要算十分特出的一位。其学出入古今中西,博而能约,专而不滞,新而有守,辩而可亲。此书通过对“爱有差等”的“小共同体”社会文化传统的文明性的阐释,充分释放了原始儒学的真精神,拓展了现代文明的新视野,既有正本清源、抽丝剥茧的辨析,又不乏新人耳目、曲径通幽的巧思,相信此书定会给读者带来“脑洞大开”和“欲罢不能”的阅读体验。
——同济大学教授?刘强
李竞恒兄笔下的中国传统,不是故纸堆里的陈旧知识,而是内在于中国人血脉、历久弥新的思想资源,是时至今天仍然可供我们安身立命的精神养分。现在李兄的文章结集出版,我在羡慕之余,更想推荐给更多朋友阅读。
——宋史研究者、《风雅宋》作者?吴钩
这是一本在阅读过程中令人一会儿抓耳挠腮,一会儿又拍案叫绝的有趣小书。抓耳挠腮是因为深深地被它的内容吸引,被来自两千年前至今不衰的争鸣与论辩激发得百感交集;拍案叫绝是因为书中有许多脑洞大开的观点,加上幽默诙谐的论述,可以启发许多新知。
这是一场激发想象力的知识之旅。初翻目录,可能会惊讶于孟子与打地鼠游戏之间的奇妙联系,或是禅让与汤武放伐的惊人相似,甚至是传统文化对食肉的推崇。别急,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类比,正是本书魅力所在。这本书从孔孟原典出发,融合了古今中外各种知识与理论,兼容并包,只为肃清“原始儒学”的本来面貌。
在这个创意与规范并行的时代,我们渴望阅读那些能够激发思维、拓展视野的佳作,却又往往对创新之作持保留态度。这本书将向你证明,好书是敢于突破常规、引领思考的。它不仅能够激发你的理解力和联想力,更会以文化史论的深度,锻炼思辨性。本书的核心议题“爱有差等”,乍看之下似乎颠覆传统,实则深藏玄机。很多人将墨家的“爱无差等”误解为儒家理论,忽视了《孟子》此句中紧跟的“施由亲始”——从最关心、最亲近的人开始实践,激发恻隐之心。到底理想的爱的序列是什么样的?就请大家跟着本书,去一览先秦文明的缤纷色彩吧。
爱有差等与文明的构建
到底是“爱无差等”更文明和高级,还是“爱有差等”才是真正的文明基石,这是自古以来争论的核心问题。一些宗教、学派鼓励“大爱无疆”,认为无差别地爱每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不限于狭隘的小共同体如家人、朋友等范围,这才是高贵的圣徒。这种大爱,认知低级的人不懂。狄更斯小说《荒凉山庄》里的杰利比太太,“她的眼睛看不到比非洲更近的东西。杰利比太太整天写信支援尼罗河上的一个部落,任凭她在伦敦的家庭因此毁灭”([美]罗伯特·D.卡普兰:《无政府时代的来临》,骆伟阳 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7页)。一些“进步”的现代人,其价值排序也主张自己的家人或国族共同体,并不应该优先于遥远的非洲,即应该爱无差等。
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传统古老小共同体被打破和瓦解,国家之间人员流动性增加,陌生人越来越频繁的互动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爱无差等”的思想,为打破家庭、家族、村社、朋友圈的边界叫好。《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墨家信徒夷子,就主张“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即从价值维度上来说,爱父母和爱陌生人应该相同,只是从技术实践角度,可以先从爱父母做起而已。显然,夷子这番爱无差等的论述,是在偷换概念,尤其是在零和选择的极端状态下,一定是会逼出价值排序的。就像曹丕问群臣:“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邴原悖然回答“父也!”(《三国志·魏书·邴原传》注引《邴原别传》),在零和选择的极端状态下,如果在父亲和君主之间只能救一个,那么邴原的儒家价值就将父亲的排序放到了君主之上,体现的正是爱有差等的原则。
孟子说:“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意思是,夷子真正以为人们爱他的侄儿和爱他邻居家的婴儿一样的吗?夷子只不过抓住了一点:婴儿在地上爬行,快要跌到井里去了,这自然不是婴儿的罪过。[这时候,无论是谁的孩子,无论谁看见了,都会去救的,夷子以为这就是爱无差等,其实,这是人的恻隐之心。]况且天生万物,只有一个本源,夷子却以为有两个本源,道理就在这里(杨逢彬:《孟子新注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6页)。孟子的意思很清晰,墨家信徒夷子所谓爱无差等,看到陌生人的婴儿快要掉到井里去了,赶快去救援,这只是人们的恻隐之心,并不意味着对陌生婴儿的爱就等同于自家孩子的爱。
儒家对文明构建的理解,既反对只是原子个体的自私,更反对无差别的大爱无疆。爱的价值排序,应该是由近及远的层层外推,从小共同体推向中级共同体,再推向大共同体,在推导和流溢的过程中,层层变淡,但却是最现实的方案。顾炎武读《诗经》,读到“言私其豵,献豜于公”,先保有自己私家的猎物,再将其它拿给领主,他感慨这才是正确的,所谓“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日知录》卷三)。顾炎武的阅读和思考纵深,是重回原始儒学,他特别注意到,爱有差等才是人性的“情之所不能免”,以家庭为基础的“私”,才是构建文明的基石。在这个基础上,西周的君王尊重大家的“私”,最后“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只有在尊重差等和保护“私”的基础上,层层推进,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反之,如果以“公”的大义名分去践踏“私”,最后得到的一定不是真正的“公”,而是大伪。
我们智人的大脑,在长达二十万年的历史中,熟悉的是家庭、氏族这类小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在这种小规模的共同体内,讲大爱是没问题的。但进入体量达到多少万人一起合作的大共同体时间,也就是跨入文明社会的这五千年。我们的头脑,其实和旧石器时代晚期差异并不大,能长期保持熟人和有效社交的关系圈,其实就在最大“邓巴数”(Dunbar's number)这个范围内,一般不超过一百五十人。能具有超越管理这个数量级以上大脑能力的人,历史上是很少的。如梁、陈时期的大军阀王琳,能够做到“军府佐吏千数,皆识其姓名”(《南史·王琳传》);北齐的唐邕,据说也可以“于御前简阅,虽三五千人,邕多不执文薄,暗唱官位、姓名,未常谬误”(《北齐书·唐邕传》);唐朝的李敬玄,“性强记,虽官万员,遇诸道,未尝忘姓氏”(《新唐书·李敬玄传》),能记住上万人的姓氏;唐代的唐宣宗也特别能记住大量陌生人的名字和信息,所谓“宫中厮役给洒扫者,皆能识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无差误者。天下奏狱吏卒姓名,一览皆记之”(《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五》宣宗大中九年)。或者像古罗马的凯撒,据说能记下自己的手下每个士兵的面孔和名字。王琳、唐邕、李敬玄、唐宣宗、凯撒之类属于极少数特例,因此才被史书记录。而最常见有效社交和维持情感的共同体边界,从史前到文明时代,一般都不超过一百多人的最大邓巴数。文明时代,其实是依靠跨越血缘、跨村社的官僚组织、商业手段,实现了大量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但这种合作不是通过“爱”,而是通过更冷寂的行政、商业、契约之类的技术手段来实现的。当然,随着长期的合作,小共同体之间古老的爱,也慢慢流溢到大共同体的陌生人社会之间,救援孺子入井等各类恻隐之心开始大量涌现。随之而来的,是各类大共同体和陌生人之间讲究大爱的思想、宗教开始出现,一旦处理不好价值排序问题,就会产生“整天写信支援尼罗河上的一个部落,任凭她在伦敦的家庭因此毁灭”这类画面。
有句阿拉伯谚语说,我和兄弟针对堂兄弟,和堂兄弟针对陌生人,其实就道出了“爱有差等”的一个圈层结构。《孝经·圣治》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也是讲最基本的差等之爱,如果连对自己的双亲都不敬爱,却去敬爱其他的陌生人,这就是悖逆德性与传统习惯法的。体现在丧服习惯法上,儒家根据爱有差等的亲疏远近,制定了各类丧服,儿子为父亲服最重的“斩衰”,父亲也为嫡长子服最重的斩衰,为母亲服“齐衰”三年(父亲在则杖期一年),为自己的祖父母、兄弟、嫡长孙都是服齐衰不杖期一年,为堂兄弟服七个月或九个月的“大功”,同族远房堂兄弟则服三个月的“缌麻”。这种依次递减的差序格局,体现的正是“差等”和圈层远近的分寸感。古儒讲究血亲复仇,《礼记·檀弓上》记载:“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孔子的意思是,对杀害父母的仇人,绝不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哪怕追杀到天涯海角,也要报仇;而对于兄弟的仇,如果他逃到外国,就可以暂时不找他报仇;对于堂兄弟的仇,如果需要武装械斗,则可以拿着武器站在队伍的后面参加,尽一些义务。显然,这种一层层向外延展的责任不断降低,正是爱有差等的体现。在史前时代,人们爱的范围限于本家庭和氏族最大邓巴数群体内,而文明时代拓展了这个范围,让爱和恻隐可以流向更广袤的群体。儒家当然鼓励这种爱向更遥远的流溢,但前提是不能破坏差等的结构,搞成本末倒置。
其实即使是构建家族共同体,如果不讲究差等之爱,也是存在很多隐患的。南北朝到唐宋时期,民间社会出现了一些动辄超过八代、十代甚至十几代人不分家的大家族,在家族内实行财产共有,吃大锅饭,“一钱尺帛无敢私”,叫累世同居的“义门”。当然,从重建社会自治小共同体的角度,防止原子化、散沙化弊端的角度,这种中古时期出现的十几代人不分家而共财的中间组织,当然具有积极意义。但其弊端往往是从另一个角度,如果不能落实爱有差等,给大家族内的核心小家庭以空间,很多甚至会出现兄弟反目之类悲剧。杜正胜引用《四库珍本别辑》中的《袁氏世范》中就认为兄弟“义居”这种多代不分家,如果出现一人早亡,“诸父与子侄其爱稍疏”,就会出现长辈瞒幼辈,幼辈又悖慢长辈,“顾见义居而交争者,其相疾有甚于路人”,最后从大爱变成大仇,就是因为没有差等和边界感。唐高宗时的张公艺,九代义居共财不分家,唯以上百个“忍”字来传家,看得皇帝都落泪了。这些“百忍”的内容,一定包含了大量家长里短和鸡零狗碎,不讲差等与边界感,走得近反而导致走得远。正因为这种规模超出邓巴数,还实行共财义居模式,是违背了爱有差等这种智人本性的。其实这种不讲差等的“义居”大爱模式,虽然也还是一种小共同体,有一些现实的操作空间,但因为无差等,也是违背原始儒学精神的。在宋元以后,这种模式被更体现差等的新型宗族模式取代,所谓“避免累世同居的弊端,又能发挥宗族通财的精神,于是产生新的宗族形态”( 杜正胜:《传统家族试论》,自 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家族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83页)。这种新的模式,更接近原始儒学的差等结构,即各小家庭分开玩,不搞同居同财同吃。但又通过义庄、义田之类产业,类似家族基金,保持一定限度的互助合作形式,既保持小共同体的凝聚力又维持合理的分寸感。
在这一点上,儒家爱有差等的价值观,与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颇有相似之处。休谟在《人性论》中说:“人类的慷慨是很有限的,很少超出他们的朋友和家庭以外,最多也超不出本国以外。在这样熟悉了人性以后,我们就不以任何不可能的事情期望于他,而是把我们的限于一个人的活动的狭窄范围以内,以便判断他的道德品质”。高全喜教授认为:“休谟所说的同情很类似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差等之爱,它是一个由己推人的逐渐扩展的量化过程,也就是说,同情以人的自私或自爱(self-love)为出发点,然后由己推人,从个人推到家庭再到朋友,乃至到整个社会”(高全喜:《休谟的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5页)。休谟的人性论,和法国大革命提出那种“博爱”的豪情壮语相比,确实显得冷寂而不够“激情燃烧”,但却是符合真实人性和现实操作的。反之,法国大革命那种没有现实根基的“博爱”激情,以公共性的名义破除各种“私”,最终得到的却是残酷杀戮。休谟的人性论与古儒相近,可以对应一个近代市民的工商业社会,也落脚到私有财产权的意义。
如果考虑到“爱有差等”的操作性,很多带些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方式,只要限定在一个极小的共同体边界内,其实是可以实行的。有人说,我和家人之间实行共产,和朋友之间实行社会主义,和陌生人之间通过资本主义进行合作,其实就说到了要点。即使是按照奥地利学派所说高度自由放任的市场模式下,人们在家庭内部,家人之间其实还是以共同分享财产为主的。在一个邓巴数之内的小共同体社群,如美国阿米绪社群、以色列基布兹公社之类,也都可以在现代社会存在,前提是各小共同体之间以陌生人社会方式进行合作。进入了文明时代以后的社会,陌生人之间可以通过跨血缘的官僚组织、商业贸易、契约等方式进行合作,近代以来通过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进行合作,陌生人之间讲究私有财产权、严格的契约,看起来不像小共同体内那种温情脉脉,但却是最有效、最现实的庞大陌生人社会合作手段,整个大社会也通过这种合作方式增进了总体财富,做大蛋糕,因而人人获益。反之,如果将小共同体的模式强行推广到庞大的陌生人社会,通过“改造人性”、“狠斗私字”来实现“大同”,最终只能得到相反的结果。康有为讲“大同”,首先要从破除家庭开始,因为家庭这种血缘共同体就是“爱有差等”的基石。很多要追求“爱无差等”的运动,也都是从破除或反对家庭开始,引发出灾难。学者就注意到,“姓氏作为家庭和家族最重要的标识,要想打破亲疏之别,废除姓氏便是其中之义。废姓与废家的讨论和举动也并非个例,颇能反映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态。其实,较早康有为设想,废除姓氏之后,人的命名应该以所生之人本院所在之位置、院室名称命名,即某度、某院、某室、某日”(赵妍杰:《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50页)。晚清、民国以来的激进主义思潮,正是着眼于要打破爱有差等与亲疏之别,要从破灭家庭入手,将人们变为类似数字编号的平等原子个体。
爱有差等,才是文明社会的基石,家庭制度和私有财产权,就是爱有差等的产物。讲究爱有差等,不是说要冷酷的自私,拒绝对陌生人有恻隐之心。恰恰相反,正因为爱有差等保护了人们最关心、最重视的人,以及相应权利,以及一层层有序的边界感,才能培养出仓廪足而知礼仪的君子,才能将在小共同体内养成的美好品德,一层层向外拓展、流溢给陌生人,共同构成文明社会的温度。反之,号召爱无差等的运动,以破除“私”去实现“公”,最终却往往产生装扮成大爱无疆的“大伪”、“大奸”之人。从孟子开始,就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所代表原始儒学的文明构建思路,正是首先尊重人性“老吾老”、“幼吾幼”的古老自然本能——即对自家老人的爱,对自家小孩的爱,通过这种对自己小共同体之爱的真实情感之体认,再外推给更远和更陌生人的人群,将这些温度流溢给别人家的老人、别人家的孩子。只有将源自小共同体的真实之爱层层外推出去,以构建一个更大共同体的方式,自然能形成天下的良性治理,即孟子所说“天下可运于掌”。王夫之对孟子的这种将差等之爱外推给的方法,十分欣赏,认为“有其心,必加诸物,而以老吾老、幼吾幼,则吾老、吾幼即受其安怀;及人之老,及人之幼,而人老、人幼亦莫不实受其安怀也。扩大而无所穷,充实而无所虚,以保妻、子,以保四海,一而已矣,则惟其有恩之必推者同也”(《读四书大全说·孟子·梁惠王上》)。王夫之把孟子所提出,将最初源自小共同体的爱,以有差等的方式向更广袤的社会领域推进,最终让整个社会收益,得以保障天下四海的良风美俗与治理。
对于将小共同体的差等之爱,一层层外推给国家和天下这样的陌生人社会和大共同体,朱熹有也一个论述非常有道理:“且如爱其亲,爱兄弟,爱亲戚,爱乡里,爱宗族,推而大之,以至于天下国家,只是这一个爱流出来;而爱之中便有许多差等”(《朱子语类》卷九十八《张子之书一》),就是将小共同体中养成的爱心,一层层外推给宗族、家乡,再外推给国家、天下之人。在外推的过程中,会形成各种差等,但通过层层真实的流溢,这些爱的推及所处,却都是真实可靠的。如果这个顺序被搞错,那些产生的所谓“大爱”,很可能就是大伪,或者成为“大私”的欺骗手段。
或许有人会问,那假如这些小共同体之爱,只是被限于小共同体内部,而拒绝外推给天下之人呢?那不是成了有利于小圈子贪腐或犯罪之类的了,就像广东以前的“制毒村”那样,村里人作为小共同体一起互助发财,确实是真实的爱(按:对 于“制毒村”这种错误现象必须要加以严厉批判。在此选取其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极端反面案例,就是因为其道德水平类似于远古部落时代。从现代角度来说,村中之人的发财是“互利”,但从古代语境来说,互助互利确实和“爱有差等”意义上的“爱”是同体两面的。这类极端案例恰恰表明了,在现代社会中如果只 有那种如同原始时代土围子一般的小共同体本位的话,那么根本 不可能产生文明,而且会是反文明的)。但是将毒品卖给村外的陌生人,这就成了只爱小共同体,却祸害陌生人。显然,像制毒村这样的存在,只是一种最原始状态下,智人古老小共同体之爱的本能,其实是缺乏教化和士绅共同体的结果。传统社会的小共同体中,普通村民或百姓其实没有参与大共同体建构的能力,很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活在村子里,甚至没去过最近的县城。对于这种,小共同体就是整个世界,爱村就是爱世界。但是村内的士绅,因为是读书人,通道理,天下的读书人以文化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士绅或士君子共同体,就像阎步克所说,至迟在汉代,士林的活动就是跨越县、郡,甚至是全国性的,如郭泰死后,二千里内上万名士人前来悼念;陈寔去世后,海内三万士人来吊丧。在这个时代,已经形成了“天下士大夫”、“海内士人”这样一个文化纽带的大共同体(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04—105页)。这个跨越了自然村落、县域、郡域,将全天下受过教化、教育者的心智都抟成一个能够相互认信、相互爱戴,远远超越了小小“土围子”的狭隘之本能,而能将爱的边界拓展到“天下”之大的延伸。但这一“天下”的范围,又不同于现代全球化语境中的“全世界”,因为“天下”的共同体范围依赖于文化共同体。
甚至日本、朝鲜、越南的士绅,作为传统“天下”这一文化共同体内的成员,也可以通过汉字笔谈和诗书礼乐文化的认同,而作为一个共同体互动和认同。在朝鲜燕行文献、日本漂流日记等材料中,这些例子非常多,即日本人说“四海兄弟,文语情通”(王勇等:《〈朝鲜漂流日记〉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1页)。也就是说,有士绅、士君子的时代,士绅可以教化和引领自己的小共同体,再以士绅、士君子为纽带,将天下人之爱凝聚起来,形成大共同体之爱。士君子阶层本身能突破狭隘和更原始的村落、土围子范围内的小共同体之爱,通过“天下”的共同体构造,形成更大之爱的构建范围。而在小的层面,士君子也有教化的职责,让只知有村的愚夫愚妇,能产生更高的德性认知,将小共同体之爱外推给外部世界,最低限度必须是士君子的责任,并将其教化给身边的成员。哪怕是《弟子规》这种比较鄙陋的蒙学教材,也会宣讲“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这种更高的道理,即通过教化将爱外推给更普遍性的“人”。
孔子讲“仁者爱人”,孟子讲“不忍人之心”,都是要将小共同体内涵养出的仁爱之心,一层层外推给天下之人。对此,朱熹也有重要的论述:“能尽父子之仁,推而至于宗族,亦无有不尽;又推而至于乡党,亦无不尽;又推而至于一国,至于天下,亦无有不尽。若只于父子上尽其仁,不能推之于宗族,便是不能尽其仁。能推之于宗族,而不能推之于乡党,亦是不能尽其仁。能推之于乡党,而不能推之于一国天下,亦是不能尽其仁。能推于己,而不能推于彼,能尽于甲,而不能尽于乙,亦是不能尽”(《朱子语类》卷六十四《中庸三》)。朱熹讲得很清楚,如果不能将对家人的爱外推给家乡的外人,那就根本谈不上是仁。如果把爱外推给了家乡的陌生人,但却不能再进一步外推给全国的人、全天下的人,那仍然也不能算仁。像广东制毒村那样,就是典型朱熹所说“能推于己,而不能推于彼,能尽于甲,而不能尽于乙”,不能将爱外推给国人、天下人,就是缺乏仁义教化的精神病态。要避免制毒村这种情况,不是要取消小共同体之爱,而是要建立教化和士绅,将小共同体之爱外推给国人、天下人,以实现真正“仁”的状态。那些想通过取消小共同体之爱,去实现“大公”的思路,最终不但会消灭真实的小共同体,最后也不会得到“大公”。最后能得到的,只能是原子化个体和各种伪装成“大公”的大伪而已。
——选自李竞恒《爱有差等:先秦儒家与华夏制度文明的构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