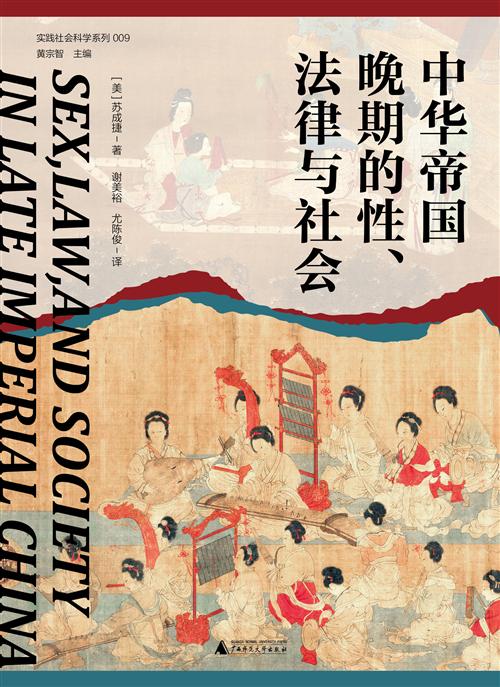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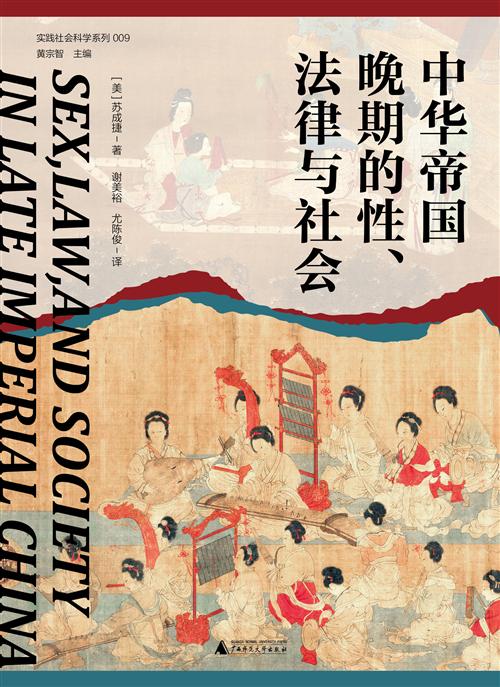
本书是一部法律史领域研究性犯罪问题的经典之作。书中运用了唐代以来的大量法律史文献,聚焦清代社会中寡妇、娼优、雇工、乞丐等底层人物,用比较史的眼光对性行为管制、寡妇守贞、“光棍例”、“卖娼”等问题进行分析,还原真实案例,展现了微观视角下的平民婚姻,以及女性短缺、妇女歧视等现象。
作者将性别史、法律史和社会史等不同研究进路熔为一炉,将性犯罪与法律问题进行宏观考察,探讨了清代对性行为和性观念的规制与引导。书中案例生动鲜活,人物形象立体丰满,语言流畅,展示了一个复杂且富于动态变化的中华帝国晚期社会。
苏成捷(Matthew H. Sommer),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博士,现为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擅长利用司法档案研究清代中国的性、社会性别关系和法律。出版有Sex,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和Polyandry and Wife-selling in Qing Dynasty China两部学术专著,并在Late Imperial China、Modern China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谢美裕,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历任斯坦福大学人文学概论讲师与俄亥俄州立大学马里恩校区历史系助理教授。
尤陈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8年度)。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有专著《聚讼纷纭》《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从诉讼档案出发》等多部编著,以及译著《爪牙》。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论题
第二节 资料
第二章 一种关于性秩序的愿景
第一节 “奸”的概念界定及其涵盖范围
第二节 父亲和丈夫所享有的特权
第三节 主人与其女性奴仆发生的性关系
第四节 义绝:夫妻间道德纽带的断绝
第五节 “凡女必归于男为妇”
第三章 强奸罪相关法律的演变:女性贞节与外来男子的威胁
第一节 对强奸罪受害者的资格审查
第二节 是否被男性性器官侵入下体至为关键
第三节 强奸与和奸的对比
第四节 关于危险男子的刻板印象
第五节 清代中央司法官员的实际做法
第六节 结语
第四章 关于被鸡奸男性的问题:清代针对鸡奸的立法及对男性之社会性别角色的加固
第一节 论题
第二节 立法史
第三节 异性性犯罪的标准被适用于鸡奸罪行
第四节 那些易受性侵的男性和危险的男性在司法中的刻板印象
第五节 大众观念中的等级体系和污名化标签
第六节 阶层分化与男性之“性”
第七节 男性性器官侵入对方体内之行为的含义
第五章 贞节崇拜中的寡妇:清代法律和妇女生活中的性与财产之关联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官方对贞节的评判标准
第三节 寡妇作为一种有性欲的生物个体
第四节 强迫再嫁、自杀和贞节的标准
第五节 没有资财的寡妇
第六节 拥有财产的寡妇及其姻亲
第七节 争斗的诸种情形
第八节 结论
第六章 作为身份地位展演的性行为:雍正朝之前对卖娼的法律规制
第一节 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第二节 立法层面对不同身份群体的区分
第三节 推行身份等级原则:明代和清初的实践
第四节 适用于娼妓的宽松刑责标准
第五节 法律拟制与社会现实
第七章 良民所应遵循的诸标准在适用范围上的扩张:雍正朝的改革与卖娼入罪化
第一节 学界以往对雍正元年“开豁贱籍”的解读
第二节 “广风化”
第三节 雍正元年之后在法律上如何处置卖娼
第四节 雍正朝以降一些经中央司法机构审理的案件
第五节 小结
第八章 结论
第一节 法律的阳具中心主义
第二节 从身份地位到社会性别的变化,以及对小农家庭的新关注
第三节 含义发生变化的“良”
第四节 生存逻辑与性事失序
附录A:针对性侵犯的基本立法
附录B:清代针对鸡奸的相关立法
附录C:针对强迫守志寡妇再嫁的处刑
附录D:吕坤的“禁谕乐户”举措
参考文献
译后记
简体字版中译本序
我非常欢欣地看到,自己这本最初于200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专著,如今终于有了简体字版中译本。在本书英文原版付梓后迄今的这二十多年间,有许多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性(sex)、社会性别(gender)和法律的学术研究新成果陆续问世。但是,我并不打算试着对本书的内容做那种无止境的更新,而是决定让其保持英文原版问世时的原貌。我希望中国的读者会发现这本书依然有其学术价值。
我对本书简体字版中译本的译文准确性充满信心。不过,倘若读者对我在书中表达的意思或意图有任何疑惑,则可参看本书的英文原版(我对英文原书中的表述独立承担文责)。
我想对所有为本书的中文翻译提供过帮助的人致以诚挚的谢意。我攻读博士学位时的指导教授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先生,多次鼓励我将本书的英文原著译为中文出版,并最终促成这一想法如今变为现实。若没有他的帮助,本书的这个中译本将不会存在。本书实际的翻译工作,首先要归功于我曾指导的学生谢美裕(Meiyu Hiseh),不过杨柳也对最初的那一版译稿付出了心力,尤陈俊教授则对照英文原书,在之前那版中译稿的基础上,逐字逐句地进行了最终的校译、修改和润色。我自己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为几位译者提供英文原书中引用的那些中文史料原文。本书的翻译工作,得到了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中国研究中心(该中心由黄宗智教授倡议成立,后来他出任创所主任)、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s)的经费支持。我也要对让本书简体字版中译本得以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隆进编辑表示感谢。
本书的英文原版是献给我的双亲唐纳·M. 萨默(Donna M. Sommer)和约翰·L. 萨默(John L. Sommer)。我想在此再次感谢他们为我所付出的一切。同时,也要感谢拙荆张梨惠(Ih-hae Chang)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我想把本书的简体字版中译本献给我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黄宗智教授。当初正是黄宗智教授向我介绍了清代司法档案,指导我进行研究和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自研究生阶段算起的这数十年里面,他一直是我所熟悉的孜孜不倦的导师。对于他为了促进我的职业生涯发展和丰富我的生活所做的一切,我铭感五内。
苏成捷(Matthew H. Sommer)
2022年10月6日
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
节选自[美]苏成捷《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书。作者将清代那些对“性”加以规制的法律的变化,与清代司法档案呈现的奸情结合起来探讨,探幽索隐,对于传统中国的性、法制、社会提出了一系列新看法,更新了我们对身份等级社会的认知。本书作者的研究,摆脱了将中国与西方二元对立两极化的立场,不把个人自由的扩张作为观察中国晚近历史的唯一参照标准,而是从广阔的历史变迁视角,理解清代对“性”所做的规制,同时将清代对“性”的规制置于宽阔的社会情境中加以审视,探讨其与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心态及实践之间的关联。
——常建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本书作者论证了清代“犯奸”法律及其背后“宽阔的社会脉络”已在18世纪出现了本质性转变,既借以批评瞿同祖有关晩清以前中国法律身份等级规范从无任何重大变化的论述,也对经君健主张当时中国市场经济促成个人自由的发展趋势提出修正,强调应将此种本质性转变视为18世纪清朝因应人口压力带来社会失序危机的一种法律与社会互动,也从而呼应了黄宗智超越西方社会理论范式以找寻中国自身历史变化路径的重要主张。直至今日,这些精彩论证仍然非常具有启发性,确实是一部值得如此认真中译的好书。
——邱澎生(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本书结合传统史学与性别史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了清代的各类奸情案件,以雍正年间“开豁贱籍”为切入点,探讨了“良”在法律与观念上的含义变化所引发的从身份地位向社会性别的转变,以及扩张适用于所有人的性道德和刑事责任标准的确立过程,从而较为完美地诠释了“性别作为一个有用的方法”对于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
——阿风(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书以明清时代“性”秩序的相关立法及法律实践为中心,探讨了中国帝制时代晚期对性行为和性观念的规制与引导,从社会控制理念和治理方式的视角,解释性秩序传统的变迁规律。全书的论述洞烛隐微,结论发人深省,是中国社会史和法律史研究领域的一本重要著作。
——王志强(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时至今日,苏成捷此书已经完全称得上是法律史与性别史两大领域里的经典著作,影响过数代学人。在本世纪初,本书以新颖的视角与材料迅速吸引了学界的关注。而即便在今日,其分析深度与思维活力,依然足以为青年学者们树立良好的典范。中译本的出版,再次激发它的学术生命力,实为造福学界之事。
——张泰苏(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
该书绝非一本猎奇“性”的轻浮作品,而是一份厚重、严肃且令人深思的学术研究。作者结合传统史学与性别史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了清代的各类奸情案件,成功揭示了中华帝国晚期在相关法律方面发生的那些影响深远的深刻变化。
“光棍例”
生活在家庭制度之外的底层男性被统称为“光棍”,他们总人数众多,并在当时日益壮大。他们被妖魔化为性侵犯者,被视为对正经人家中的守贞妻女及年少子弟构成了威胁,于是国家出台了大量新的法律规定,对他们加以震慑。本书展示了当时国家为应对社会结构和人口状况方面正在发生的诸多令人不安的变化所做出的努力。为了适应正在变得更具流动性的社会结构,国家抛弃了法律上某些不合时宜的旧有身份类别,强制落实严格的社会性别角色,以支持小农家庭对抗由单身无赖汉们构成的底层男性阶层。
明清寡妇之“性”与财产
相较于对其他类型的女性,明清两代的法律均在财产和自主性方面赋予了寡妇以最大限度的权利。但寡妇能获得这些权利的前提是她须保持贞节,而再婚或与人通奸均会破坏这种状态(因此,再婚和与人通奸只是同一主题的不同表现方式而已)。性与财产之间的这种相互关联性,为大量的民、刑事司法审判提供了素材,而这些审判活动正是清廷用来落实其推行的那些道德准则的最直接手段。现存的案件记录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新的窗户,让我们得以一窥清廷是如何致力于推广女性贞节观的,以及此种努力又会对清代普通百姓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丈夫对其妻子所拥有的包括使用暴力的权力在内的合法权威,并非绝对,也不能恣意妄为。丈夫对其妻子行使其权威,必须符合儒家所预设的那种家庭秩序的利益。妻子的顺从以及在性方面服从其丈夫的义务,也取决于这项根本原则。
——编者按
义绝:夫妻间道德纽带的断绝
前已述及,丈夫对其妻子所拥有的包括使用暴力的权力在内的合法权威,并非绝对,也不能恣意妄为。丈夫对其妻子行使其权威,必须符合儒家所预设的那种家庭秩序的利益。妻子的顺从以及在性方面服从其丈夫的义务,也取决于这项根本原则。如下两种被中国帝制晚期的律典纳入“奸”罪的情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丈夫能够享有对其妻子的“性独占”的先决条件。这种性独占只能由丈夫本人享有,而不可与他人分享。
一、获得丈夫同意的非法的性交行为
倘若丈夫允许自己的妻子与其他男子发生性关系,则法律上将如何处置?本书中关于卖娼的那两章将详细讨论此问题,不过在这里可以先对我的主要观点做一概述。直到18世纪,法律上仍然容许卖娼,不过仅限于那些世袭贱民身份的女性,特别是乐户。清初的案件记录和其他史料表明,这些女子均有丈夫,并由其夫为她们招揽嫖客。针对奸罪的相关法律,并不适用于这些被认为不配由法律来加以约束的女子,良民男性享用此类女子的性服务,也不构成犯罪。
与此构成对比的是,若与良民女性发生任何形式的婚外性交行为,则会被作为奸罪论处。此外,若良民丈夫为自己妻妾的卖娼招揽嫖客,则无论是否征得其妻妾的同意或强迫她们如此行事,均被视为彻底背叛了他们之间的婚姻道德基础。易言之,这种行为将被纳入“不以义/礼交”的类别。早在12世纪的南宋时期,当时的一道法令便规定,犯有上述罪行的良民夫妇须强制离异。直至清朝结束,强制离异始终是对此种犯罪的惩罚之一。在元代,良民身份的丈夫若“纵妻为娼”,则会被视作一般的通奸加以惩处:丈夫、妻子和嫖客均将被依照已婚妇女“和奸”的法律规定处以相同的刑罚,即杖八十七,并强制这对夫妻离异,女方须被遣返娘家改嫁他人。明清时期的律典对这种犯罪的处刑规定与元代相同,只不过将杖刑数增加至九十下。那种支付报酬以从某位女子那里获得性服务的行为,并没有被处以任何额外的刑罚;被惩罚的乃是那种与不特定对象发生性关系的淫行,而非这种用金钱购买性服务的行为。
要知道,强制离异是一种严重的惩罚,至少对丈夫来说如此。在中国社会里面,结婚以往(可能现在仍然如此)被认为是真正成年的标志。而在贫苦农民当中,婚姻对男子而言是一种重要的身份地位象征,其象征意义随着妻子来源短缺这种状况的加剧而递增(因此,在不少卖妻案件中,是妻子更希望被卖掉,而非丈夫迫切地想卖掉其妻子。受到此类法律影响的群体,是那些已濒临绝望而不得不考虑卖掉自己妻子的男子。一旦离婚,他们当中还有多少人能重新获得那些可供再婚的必需资源?
当时的法律是基于何种理由禁止这种性关系,进而强制存在这种情形的夫妇离异?元代的司法官员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可被视作代表了他们的后世同行们就此所持的基本立场。元代大德七年(1303),一位资深的官员称“夫纵妻奸”乃是“良为贱”,即良民身份之人在行事上却犹如贱民身份的娼妓那般。同年,刑部研议后认为:“人伦之始,夫妇为重,纵妻为娼,大伤风化……亲夫受钱,令妻与人通奸,已是义绝。”刑部将这种行为称为“义绝”(夫妻之间的道德义务纽带断绝),而这是自唐代至清代的历代律典中所规定的强制离异的法定条件。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传统中国的法律专家们将其分为“天合”关系(例如父子关系)与“人合”关系(例如婚姻和收养关系)。这两种关系皆被认为以“义”为其本质。“义”是一种将不同的义务赋予人际关系双方的道德纽带。而根据前述伏胜对性犯罪所下的那个经典定义,“义”当然也是使性交行为得以正当化的条件。人们可能在一种“天合”关系中违反了道德义务(例如不孝的行为),但在法律上,这种道德纽带无法改变,故而无法被割断(“绝”)。因此,就像清代的一些案件记录所表明的,如果良民身份的父亲为其女儿卖娼招揽嫖客,那么他将被惩处,不过其女最终仍将归他监护。然而在“人合”关系中,道德纽带可被割断。因此,若丈夫纵容或强迫妻子犯奸,则这对夫妇就应当被强制离异。
元明清三代的法律均使用“纵”这一术语来称呼丈夫纵容其妻犯奸的行为,这暗示夫妻双方均被视为主动行事的共犯。“纵”的字面含义是“放纵”或“放任”,它也可被用来表示“纵容”。按照儒家所设计的蓝图,丈夫的职责是训教其妻,给她提供道德指引,并为她的行事划定界限。于是,上述律文所用措辞反映出来的图景便是,若丈夫纵容其妻在性关系方面滥交,则他便是失责。正是由于这种失责,该名丈夫丧失了继续拥有其妻子的权利。
倘若丈夫并非“纵”,而是强迫其妻与其他男子发生性关系,则上述原则仍然适用,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对妻子的惩罚会有所不同。按照元代法律的规定,被“勒”为娼的妻子是否应受惩处,需“临事量情科断”。明律(清代沿用了其中相关的规定)对这种犯罪的处置是,被“抑勒为奸”的妻子不受任何处罚,仅是被遣返娘家,其丈夫应被杖一百,而与她发生性关系的另外那名男子则须被杖八十。在这里,由于丈夫的允许和强迫才是决定性因素,故而主要责任在于丈夫,而不是像在纵容妻子犯奸的案件中那样三方均承担相同的罪责。不过即便如此,此处对这两名男子的惩罚,仍远轻于对强奸同等身份地位女性之罪犯的法定处刑(绞监候)。事实上,元明清三代针对丈夫强迫其妻与其他男子犯奸的律文规定,均刻意避免使用“强”这一专门用以界定强奸罪名的字眼。这种“抑勒为奸”之罪名与强奸罪名的区别在于,该女子的丈夫允许另一名男子对她行奸。正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沈之奇在对相关律文的注释中所指出的,“凡抑勒妻妾……与人通奸,若妇女不从,奸夫因而强奸者,似难即坐以强奸之罪”。这种罪行有着违背女性意愿而发生非法的性关系的表象,但被强奸女子之夫的授意,使得此种罪行大异于“强奸之罪”,其严重程度也被认为远较后者为低。
二、被视为奸罪的卖妻行为
另一种导致夫妻义绝的罪行是“卖休”,即丈夫将其妻子嫁卖给另一名男子。管见所及,最早言及“卖休”之罪名的是元代的法律。元代的法律显然是将这种罪行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不过有些模棱两可。元代的法律在“户婚”门中规定:“诸夫妇不相睦,卖休买休者禁之,违者罪之。”这条法令并未明确指明惩处的具体方式,不过它接着补充规定称:“和离者,不坐。”此类犯罪的第二种形式,见于元代的法律的“奸匪”门之规定:“诸和奸,同谋以财买休,却娶为妻者,各杖九十七,奸妇归其夫。”
上述第一条法令仅禁止与其妻子相处不睦的丈夫将她卖给另一名男子,而并未提及“奸”。第二条法令则明确对因通奸而引起的卖妻行为加以禁止,即禁止男子将与他私通的奸妇从其本夫之处买来。在第二条法令中,法律上的重心在于通奸而非卖妻行为本身,故而只有通奸的双方受到惩处,其中女方则应被交还给之前将她卖掉的本夫。
然而,元代大德五年(1301)的一条法令规定,若丈夫将其妻子“卖休”给另一名男子,则属于“已是义绝”,该名妻子应“离异归宗”。促成这条法令出台的那起案件,看起来在卖妻行为之前并没有发生任何通奸的情形。除了规定没收卖妻所得的钱财,这条法令未规定其他任何刑罚。该法令虽然并未指明所针对的究竟是“义绝”的哪一种情形,不过看起来是认为前述两种情形当中的任何一种均将导致夫妻之间义绝,因此强制要求该女子须离开其本夫和买休的男子。
如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元明两代的法律在对卖妻行为的司法处置上有着很强的延续性。明律中有下述规定:
若用财买休卖休,和娶人妻者,本夫本妇及买休人各杖一百。妇人离异归宗,财礼入官。若买休人与妇人用计逼勒本夫休弃,其夫别无卖休之情者,不坐。买休人及妇人,各杖六十,徒一年。妇人余罪收赎,给付本夫,从其嫁卖。妾减一等。媒合人各减犯人罪一等。
这条法律看起来包含了前述元代大德五年法令中的那种逻辑,将本夫、买休的男子和妇人三方均同等处刑,并强制女方离开其本夫和买休的男子。该律文的后半部分则明确规定了何种情况下本夫无罪,即如果他是其妻与买休者之共谋的受害者。
这条律文乃是出现在明律的“刑律·犯奸”门当中。事实上,它是一条用以禁止丈夫纵容或抑勒其妻与人通奸的单独条款。与元代的法律不同,明律的“户律·婚姻”门当中并无使用“买休卖休”这一术语的规定。明律将该条款置于“刑律·犯奸”门之中,这显示了其试图将那种由妻子和买休的男子事先通奸所引发的卖妻行为纳入涵盖的范围。该律文后半部分的措辞便是在强调此点。然而,“奸”字完全没有出现在此律文的文字表述之中。到了16世纪,上述这种模棱两可(这也许是沿袭了元代法律中的那种模棱两可)的情况,在明代的司法官员中引发了一场关于此类罪行的确切性质究竟为何,以及其与“奸”这一更大的罪行类别之间是何关系的争论。其中尤其存在争议的是,那种事前并不涉及通奸情形的卖妻行为是否应当被问罪。
有一派司法官员主张应当对此律文采取广义解释,即主张禁止擅自卖妻的一切行为,而无须考虑其原初的动机。例如雷梦麟便如此认为:
律本奸条,不言奸夫而言买休人,不言奸妇而言本妇,则其买休卖休固不全因于奸者,但非嫁娶之正,凡苟合皆为奸也,故载于奸律。
也就是说,从本夫处买来一名女子为妻的行为,并不能构成正当的婚姻,因此,借由这种交易而发生的性结合,应被视为通奸。买休的男子在买来这名女子之前是否曾与她通奸,这并不是司法上要考虑的重点。从道德角度来看,无论是否存在上述所说的事先通奸情形,均应按照相同的方式治罪。这种对“买休卖休”律文的扩大解释,看上去相当契合那个将此类性犯罪概括为“不以义/礼交”的经典定义。而且,按照当时的一般观念,这种解释也很合乎情理。据小川阳一所言,在明代的白话小说中,“奸通”一词仅用于指称“非法的婚姻”(顾名思义,那种缺乏正当婚姻仪式的男女结合)。
不过另一派司法官员则主张应当对此律文采取狭义解释。例如明代隆庆二年(1568),大理寺少卿在上奏当中对适用此律文时普遍存在的混淆加以抱怨:
至若夫妇不合者,律应离异;妇人犯奸者,律从嫁卖;则后夫凭媒用财娶以为妻者,原非奸情,律所不禁。今则概引买休卖休和娶之律矣。
简言之,大理寺少卿认为,当时的法律允许在特定情形下可以离婚、再婚和卖妻,但这些正当的行为却常被与“买休卖休”相混淆;只有那种由事先便已发生的通奸行为直接推动的卖妻行为,才应当受到惩处。
皇帝对上述抱怨的响应,乃是下旨认可应当对该律文采取狭义解释。然而争议仍未平息。次年,都察院重申应当对此律文采取狭义解释,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案:
看得买休卖休一律……今查本条……原文委无奸字,故议论不同,合无今后图财嫁卖者,问以不应,量追财入官。其贫病嫁卖,及后夫用财买娶, 别无买休卖休奸情者,俱不坐罪。
也就是说,都察院认为,纯粹基于钱财考虑的卖妻行为是另一回事,即便要对这种行为加以惩罚,也应从轻处置。只有当买妻者事前与女方有通奸情形时,才应对卖妻行为加以惩处。
这份奏折给出的上述方案,后来得到皇帝的允准。
尽管朝廷就此做出了上述明确声明,但倡导应当对上述律文采取广义解释者,在明代仍不乏其人。而正是这种针对该律文的广义解释,后来在清代成为主流。
清代律典的最初版本保留了明代的“买休卖休”律,但在该律文行间添入如下小注文字:“其因奸不陈告,而嫁卖与奸夫者,本夫杖一百,奸夫奸妇各尽本法。”这种将上引小注文字添入该律文之中的做法,无疑表明事前存在通奸只是适用此律文的诸多情形之一。如此一来,所有擅自卖妻的行为,均应被按照“买休卖休”律论处,因为此类行为被认为从本质上讲皆构成通奸。康熙五十四年(1715)时,律学家沈之奇就其中的关联做出如下解释:
盖卖休者自弃其妻,既失夫妇之伦;买休者谋娶人妻,亦失婚姻之正。有类于奸,故不入婚姻律而载于此。
清代18世纪经中央司法机构审理的案件之记录表明,“买休卖休”律被从严适用于各种卖妻行为,其中包括那些与事先通奸无涉的卖妻行为。实际上,贫穷显然是这种卖妻交易背后的主要动因。然而,至少一直到嘉庆朝晚期,刑部都始终极其严格地将卖妻行为视作“奸”的具体形式之一。
节选自[美]苏成捷《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

|

|

|
| 会员家 | 书天堂 | 天猫旗舰店 |
 |  |
| 微信公众号 | 官方微博 |
版权所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GROUP) | 纪委举/报投诉邮箱 :cbsjw@bbtpress.com 纪委举报电话:0773-2288699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署) | 网出证 (桂) 字第008号 | 备案号:桂ICP备12003475号 | 新出网证(桂)字002号 | 公安机关备案号:45030202000033号